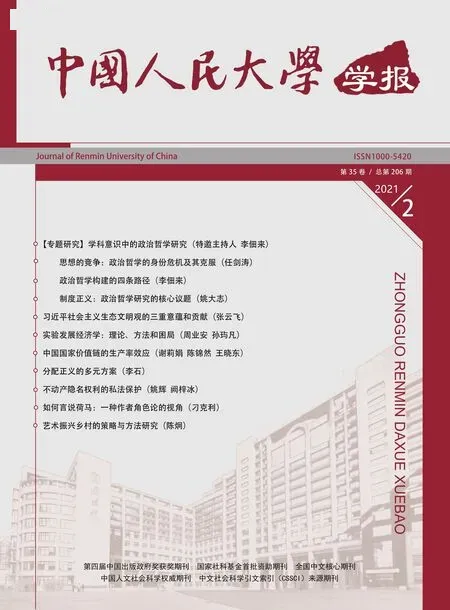强化团结规则是否有利于促进群体内部合作?
——来自人工实地实验的证据
一、引言
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领域,如何有效促进合作一直都是研究的重点。现有研究发现包括交流机制①Isaac,R.M.,and J.M.Walker.“Communication and Free-riding Behavior:The 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Economic Inquiry,1988,26 (4):585-608.、惩罚机制②Fehr,E.,and S.Gächter.“Cooperation and Punishment in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4):980-994;汪崇金、史丹:《利他惩罚威胁足以维系社会合作吗——一项公共品实验研究》,载《财贸经济》,2016 (3)。、领导机制③Güth,W.,Levati,M.V.,Sutter,M.,and E.van der Heijden.“Leading by Example with and without Exclusion Power in Voluntary Contribution Experiment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7,91 (5):1023-1042;周业安、黄国宾、何浩然、刘曼微:《领导者真能起到榜样作用吗? ——一项基于公共品博弈实验的研究》,载 《管理世界》,2014 (10);周业安、黄国宾、何浩然、刘曼微:《集体领导者与个人领导者——一项公共品博弈实验研究》,载 《财贸经济》,2015 (5)。、税收和补贴机制④Falkinger,J.,Fehr,E.,Gächter,S.,and R.Winter-Ebmer.“A Simple Mechanism for the Efficient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Experimental Evide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 (1):247-264.、组成员选择机制⑤Gunnthorsdottir,A.,Vragov,R.,Seifert,S.,and K.McCabe.“Near-efficient Equilibria in Contribution-based Competitive Grouping”.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0,94 (11-12):987-994.在内的诸多机制均能够提升合作水平。近年来,随着阿克洛夫 (G.A.Akerlof)和克兰顿 (R.E.Kranton)将身份变量引入经济学模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在研究合作问题时开始关注群体因素的作用。①Akerlof,G.A.,and R.E.Kranton.“Economics and Ident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115 (3):715-753.根据其模型的含义,个体的效用不仅受到自身决策和他人决策的影响,还取决于个体对身份所属群体产生的社会认同。更进一步,个体对身份的认同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成员自身的行为以及他人的行为;二是成员的群体类别,这会影响到其自身的权力和地位等;三是社会规范对成员的约束,当个体行为决策偏离身份所属群体对应的群体规则时,会使自身效用产生损失。因此,如果将合作问题推广到社会层面,社会分群和群体规则均会通过社会认同影响群体合作。
每个群体均存在一系列群体规则,其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维系群体的稳定性,因此可以将团结规则视作群体规则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规则。从社会认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本文将探讨团结规则强化是否能够有效提升群体内部合作,以此作为促进合作机制相关研究的补充。以规则为主题的现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主要探讨规则的形成过程,试图通过不同的制度设计促使群体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群体规则。②Peysakhovich A.,and D.G.Rand.“Habits of Virtue:Creating Norms of Cooperation and Defection in the Laboratory”.Management Science,2016,62 (3):631-647;Han,X.,Cao,S.,Shen,Z.,Zhang,B.,Wang,W.,Cressman,R.,and H.E.Stanley.“Emergence of Communities and Diversity in Social Network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7,114 (11):2887-2891;Krupka,E.L.,Leider,S.,and M.Jiang.“A Meeting of the Minds:Informal Agreements and Social Norms”.Management Science,2017,64 (6):1708-1729.例如,韩 (X.Han)等基于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证据表明,相比于随机互动形成的社会网络,通过理性提议者和回应者的互动而实现内部一致意见的网络更具有稳定性和多样性。而且社区的多样性和群体规则正是在上述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另一类研究主要考虑既定规则如何改变个体的行为决策,这类研究大多围绕奖惩机制展开。③宋紫峰、周业安:《收入不平等、惩罚和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载 《世界经济》,2011 (10);连洪泉、周业安、左聪颖、陈叶烽、宋紫峰:《惩罚机制真能解决搭便车难题吗? ——基于动态公共品实验的证据》,载 《管理世界》,2013(4);Zhang,B.,Li,C.,Silva,H.D.,Bednarik,P.,and K.Sigmund.“The Evolution of Sanctioning Institutions: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the Social Contract”.Experimental Economics,2014,17 (2):285-303;Weng,Q.,and F.Carlsson.“Cooperation in Teams:The Role of Identity,Punishment,and Endowment Distribution”.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5,126:25-38;范良聪、刘璐、张新超:《社会身份与第三方的偏倚:一个实验研究》,载 《管理世界》,2016 (4)。例如,连洪泉等研究了外生惩罚、事前内生惩罚和事后内生惩罚三种不用的惩罚机制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惩罚违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合作行为,但是上述不同惩罚机制的效果存在差异。翁(Q.Weng)和卡尔森(F.Carlsson)在公共品博弈中研究了禀赋异质性对身份认同与合作行为的影响,并考虑了惩罚机制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当不存在惩罚机制时,无论被试处于禀赋同质组还是禀赋异质组,认同感越强的被试捐赠额都越高,即更愿意合作。而在引入惩罚机制后,惩罚对合作的影响取决于个体对内群身份的认同程度以及惩罚措施是否有效。范良聪等借助劳动场景中的第三方惩罚博弈检验了规范实施效果中的社会规范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规范是否能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动者在规范实施中对社会规范内容的认同程度。上述这类研究虽然结合了身份认同与规则认同,但是不同的规则具有外生性,这意味着实验中供被试选择的规则可能并非源自群体内部达成的共识。
本文是在第二类研究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贡献:
第一,本文从社会认同的视角重新看待群体规则,主要研究的团结规则内生于群体本身,是任何群体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从理论上讲,通过强化团结规则可以提升个体对身份所属群体的社会认同,进而增加个体与内群成员的合作水平。此外,本文将身份拥有时间纳入研究范畴,以进一步识别干预机制的效果。
第二,为了分离出团结规则效应,本文将借鉴社会心理学中的激发工具 (priming instrument)达到目的。①激发工具的作用为,通过短时间内提供情境线索或暗示,使个体拥有的身份效应凸显,因此个体行为会更符合该身份所属群体的相关规则。激发工具的形式可以为调查问卷、文字、图片等,具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直白的激发工具 (blatant priming instrument)和含蓄的激发工具 (subtle priming instrument),前者所包含的情景线索或暗示直截了当,而后者往往经过精心设计。为避免被试产生需求效应,本文在实验中采用含蓄的激发工具以达到研究目的。该方法主要用于分离个体本身固有的社会身份,从而探讨不同社会身份导致的行为决策差异。不同于以往,本文并非对身份进行激发,而是对身份所属群体的团结规则进行激发。为了进一步验证团结规则强化机制对群体内部合作的作用,本文考察了身份重叠时不同身份群体内部合作水平如何改变。
第三,在实验方法和被试选取问题上,本文将利用人工实地实验 (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的研究方法,以真实社会组织中的个体为被试展开实验。这一方法能弥补实验室实验研究的不足,因为在实验室实验中短时间的实验干预难以真正形成群体规则,由此所得结论的准确性存在质疑。此外,本文在人工实地实验中对标准公共品博弈进行改装,利用真实捐赠活动模拟公共品博弈过程,以此量化合作行为。这使得实验过程贴近实际,避免被试产生的需求效应干扰实验结果。
本文的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模型及假设;第四部分为实验设计及实施;第五部分为实验结果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
自阿克洛夫和克兰顿首次将身份变量引入新古典效用模型以来,大量研究开始围绕身份对经济决策的影响展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实验室实验中研究人为构造的组身份对行为决策的影响②Eckel,C.C.,and P.J.Grossman.“Managing Diversity by Creating Team Identity”.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2005,58 (3):371-392;Chen,Y.,and S.X.Li.“Group Identity and Social Preferenc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99 (1):431-457;Chen,R.,and Y.Chen.“The Potential of Social Identity for Equilibrium Selec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1,101 (6):2562-2589.;二是对个体固有的身份进行研究,如种族身份、性别身份、种姓身份、宗教身份、罪犯身份、邻里身份、户籍身份等。
现实中每个个体均有多重社会身份,每个社会身份都对应于该身份所属分类所具有的一般特征、规则、社会预期等。③Deaux,K.“Social Identification”.In Higgins,E.,and A.Kruglanski(eds.).Social Psychology: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6,pp.777-798.如何才能分离出不同的社会身份,从而研究一个特定身份对经济决策的影响呢? 近年来,为达到研究目的实验经济学家借鉴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即激发工具。阿弗里迪(F.Afridi)等研究了激励条件下,户籍身份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④Afridi,F.,Li,S.X.,and Y.Ren.“Social Identity and Inequality:The Impact of China's Hukou System”.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5,123:17-29.实验以小学生为被试,采取问卷方法作为激发工具,通过让学生填写与户籍身份相关的题目使户籍身份效应显现,并通过公开确认户籍身份来强化这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户籍身份被强化后农村学生在认知能力测试中的表现不如城市户籍学生,而竞争机制的引入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村学生的劣势。霍夫 (K.Hoff)和潘迪(P.Pandey)也进行过类似研究,同样使用激发工具研究印度种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问题。⑤Hoff,K.,and P.Pandey.“Discrimination,Social Identity,and Durable Inequalit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 (2):206-211;Hoff,K.,and P.Pandey.“Making up People—The Effect of Identity on Performance in a Modernizing Societ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4,106 (1):118-131.又如本杰明(D.J.Benjamin)等在实验室实验中研究了宗教身份对经济行为的影响。通过让被试重构句子激发被试的宗教身份,而后测度了被试在公共品博弈和独裁者博弈中的捐赠水平、风险厌恶水平、时间风险偏好、既定工资下的努力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激发工具确实有效,其中新教徒身份被激发后会提升公共品供给额度,而天主教徒则反之。①Benjamin,D.J.,Choi,J.J.,and G.Fisher.“Religious Identity and Economic Behavior”.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6,98 (4):617-637.
上述各类研究的共同之处是,当个体固有社会身份被激发后,个体对固有身份所属群体的社会认同发生变化,进而使经济决策产生差异。事实上,导致这种差异的本质原因是社会认同作用下个体改变了对群体规则的偏好。任何一个社会身份必然与身份所属的群体相对应,而每个群体同样存在对应的群体规则。所以当个体固有的社会身份被激发后,其对身份所属群体规则的认同程度也会相应提升,从而使自身决策与群体规则预期相一致。更进一步,社会认同影响下个体行为决策产生差异的原因很可能取决于个体自身的群体规则偏好。现有的研究主要检验社会认同在个体经济决策中所产生的差异,而在解释这种差异时通常将其归结于身份对应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和制度规定等。无论上述哪种因素,均可以归类于群体规则范畴,也就是说,社会认同实际上是以作用于个体群体规则偏好的方式改变个体行为决策。例如,阿弗里迪等将农村户籍学生认知能力较差的原因归结为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②Afridi,F.,Li,S.X.,and Y.Ren.“Social Identity and Inequality:The Impact of China's Hukou System”.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5,123:17-29.,也就是说,农村人口普遍存在的低文化水平等负面标签是导致农村学生认知能力更差的原因。其实这种刻板印象可视为固化的群体规则,即在普遍观念上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低于城市人口。所以,阿弗里迪等激发学生被试的户籍身份,可以使农村户籍学生强化对上述群体规则的偏好,进而导致农村户籍学生在认知能力测试中的表现更差。再如,科恩(A.Cohn)等在实验中研究了罪犯身份和诚信的联系,发现激发罪犯身份会导致更多的不诚信行为发生。③Cohn,A.,Maréchal,M.A.,and T.Noll.“Bad Boys:How Criminal Identity Salience Affects Rule Viol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5,82 (4):1289-1308.这说明如果将罪犯群体本身具有的欺骗行为视作群体规则,则被试对罪犯身份的认同程度会随着身份激发而提升,进而其行为也更加贴近罪犯群体对应的规则,最终使自身诚信水平降低。伯特兰德(M.Bertrand)等用美国家庭调查的经验数据检验了不同性别对应的群体规则所能产生的影响。④Bertrand,M.,Kamenica,E.,and J.Pan.“Gender Identity and Relative Income within Household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5,130 (2):571-614.研究发现,女性群体中“妻子的收入不应超过丈夫”这一群体规则可以解释女性劳动参与率、家庭收入分配以及离婚率等现象。这种解释成立的原因在于女性认同上述群体规则,因而其自身行为决策会与该群体规则相一致。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社会认同能够改变个体的群体规则偏好,当个体对身份所属群体的社会认同提升后,其自身行为也会符合群体规则的预期。
综上可见,本文利用激发工具强化团结规则,通过社会认同路径提升群体内部合作水平的构想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另外,无论哪个国家,均推崇互帮互助、奉献社会、团结友爱的美德。因此,被试在公共品博弈中的自愿供给行为同样可以视作许多社会中的规则⑤Ostrom,E.“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0,12 (4):137-158.,这意味着团结规则强化后,个体对身份所属群体认同感的提升可以通过公共品博弈中捐赠水平的增加体现出来。
三、理论模型及假设
本文的理论模型是在阿克洛夫和克兰顿、本杰明等的基础上扩展而来①Akerlof,G.A.,and R.E.Kranton.“Economics and Ident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115 (3):715753;Benjamin,D.J.,Choi,J.J.,and J.A.Strickland.“Social Identity and Preferenc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 (4):1913-1928.(下文简称BCS 模型)。具体地,令x为个体所做的经济决策,例如个体对公共品的捐赠数额、在社会救助中的捐赠水平、个体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等。C为个体所处的一个社会分类,也可理解为个体拥有的社会分类所对应的身份,例如学生。s为个体对社会分类C的认同程度,假设s=s(p1,p2,……,pn),其中pi为个体身份对应的第i个群体规则。此外,个体在不考虑身份因素时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决策行为对应x0,个体在完全遵从社会分类C对应的规则时经济决策行为对应于xC。因此,任何偏离自身偏好和群体规则的行为均会导致效用损失,个体在考虑身份因素时所做出的决策必然会最小化其自身的效用损失。通过对个体决策偏离x0和xC导致的效用损失进行加权平均,可得个体选择行为的效用最大化条件为:

其中,w(s)为个体对所属社会分类C中的规则赋予的权重,有0≤w(s)≤1。当个体对身份所属群体完全不认同时(即s=0),有w(0)=0;此外,随着个体对群体认同程度的提升,个体对规则赋予的权重会增加,即w'(s)>0。因此,当s增加时,个体偏离群体规则的行为会导致效用损失的增加。求解(1)式的一阶条件,可得最优解为:

由(2)式可见,个体的最优决策为不考虑身份因素约束时的选择与完全遵从群体规则时选择的加权平均。在BCS模型中,激发工具会起到短暂强化身份的作用,即s'=s+ε,ε>0。本文中的模型侧重考虑群体规则强化时个体对身份认同的改变,因而在激发工具强化群体规则时,有。此外,考虑到个体身份的自尊 (self-esteem)因素,当强化群体规则时个体会对身份所属群体产生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因而有∂s/∂pi>0或∂s/∂pi<0。例如,李(Li)等在研究中考虑了个体的地位差异,认为对身份的激发会导致高地位群体提升对身份的认同,低地位群体降低对身份的认同。②Li,S.X.,De Oliveira,Angela C.M.,and C.Eckel.“Common Identity and 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2017,142:32-46.鉴于本文涉及的团结规则有利于巩固群体内部关系,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团结规则强化有利于提升个体对群体身份的认同,进而促进群体内部合作。
为了进一步考虑身份拥有时间不同的个体在进行群体规则强化时的行为决策差异,在上述模型中以t0为划分时间长短的标准,根据个体在群体中的时间t大于或小于t0,可将同一群体中的成员分为两部分。设H={Junior,Senior},因而有:,其中εH,i>0。
综上所述,利用激发工具对群体规则进行强化时产生的效果可以表示为:

本文通过现实中的捐赠活动模拟公共品博弈模型,因而在个体行为符合群体规则时,xC≥x0成立,这意味着在遵循群体规则的情况下,个体对公共品捐赠的水平高于不考虑身份因素限定条件时的捐赠额。此外,本文认为身份拥有时间不同的个体在同一激发工具的作用下,对群体认同程度的改变并不相同,因此有∂s/∂pJunior,i≠∂s/∂pSenior,i。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拥有身份时间长短不同的个体,团结规则强化产生的实验效应不同。
四、实验设计及实施
(一)样本选择
本文的实验于2017年10月在广州市展开,共有82名被试参与此次实验。所有被试均为某船运公司正式员工,在公司的统一组织下进行为期3个月的培训,培训目的是帮助员工通过各类职业资格考试。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本文获得了与被试相关的基本信息,如年龄、工作年限等。本文选取上述人员作为被试的原因有以下四点:第一,所有被试均为同一家公司的正式员工,具有统一的群体身份、相近的社会生活背景。因此,在根据员工基本属性信息随机分组后,实验组和控制组被试可视作近似相同的群体,这有利于提高实验结论的可靠性。第二,所有被试均已在该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因此共有的社会身份具有稳定性。在同一家公司内,较长的工作年限意味着更稳定的身份认同,因此本文实验效应的影响路径可归结于实验组被试所共有的群体身份认同,而排除其他可能的干扰因素。第三,所有被试的职业均为船员。众所周知,为了保证航海安全,船员间需要相互配合完成任务。这意味着,团结规则在被试群体中深入人心,是群体内部成员所形成的基本共识。第四,参与实验的被试不仅有相同的公司员工身份,还具有相同的学员身份。鉴于此,本文可以进行被试内实验设计,在个体具有多重身份的情况下检验实验效应是否依然存在。
(二)实验设计及实施
本文的实验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要求被试在10分钟之内阅读一段话,然后简要写出阅读感想,回答超过50字即可获得10元现金奖励。第二阶段为两个改装的公共品博弈,要求被试做出捐赠决策。在第一个捐赠活动中,每名被试可以自由支配10元人民币,需要决定保留额以及对公司工会捐赠额。被试的捐赠额经由实验员双倍支付给公司工会,而公司工会承诺将得到的人民币收益用于购置集体物品,每个人均会获益。第二个捐赠活动与第一个类似,唯一的差别是捐赠的对象改为学校。上述捐赠活动采用实名模式,被试的捐赠额可以与其姓名进行对应,但只有实验员知道捐赠信息,被试之间并不知情。本文采用实名捐赠的目的在于使改装的公共品博弈模型更加贴近实际,避免需求效应干扰被试决策。现有关于实名捐赠主题的研究中,部分研究表明实名捐赠模式本身会提升个体的捐赠水平,其既可能源于对名声、社会认可等社会激励 (social incentives)的考虑①Andreoni,J.,and R.Petrie.“Public Goods Experiments without Confidentiality:A Glimpse into Fund-raising”.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88 (7-8):1605-1623;Soetevent,A.R.“Anonymity in Giving in a Natural Context:An Economic Field Experiment in Thirty Church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 (11-12):2301-2323.,也可能源于实验员与被试间非匿名性的影响。②List,J.A.,Berrens,A.P.,Bohara,A.K.,and J.Kerkvliet.“Examining the Role of Social Isolation on Stated Preferenc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 (3):741-752;Alpizar,F.,Carlsson,F.,and O.Johansson-Stenman.“Does Context Matter More for Hypothetical than for Actual Contributions?Evidence from a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Experimental Economics,2008,11 (3):299-314.本文中实验组和控制组被试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实名捐赠,且被试间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捐赠额,因而本文的实验结果可以排除上述社会激励的影响。对于实验员与被试间非匿名性的问题,现有研究表明,在实验组与控制组采用相同实验流程时,这种非匿名性并不会改变被试的社会偏好,因而也不会改变被试的捐赠决策。①Barmettler,F.,Fehr,E.,and C.Zehnder.“Big Experimenter Is Watching You! Anonym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e Laboratory”.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2012,75 (1):17-34.第三阶段为调查问卷,内容涵盖员工的日常工作、学习及集体生活等方面。
本文的实验设计由一个控制组和一个实验组构成,两组在实验内容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阶段,其余各阶段均相同。在第一阶段中,控制组被试阅读的内容与创新相关,并要求回答问题:“请通过自己观察和思考,谈谈创新的重要性”。实验组被试阅读的内容是与团结相关的小故事,同样需要回答问题:“作为公司的一员,请通过自己观察和思考,谈谈员工之间相互团结对于公司的重要性”。第一阶段中,通过现金激励的方法可以促使被试深入思考创新问题和团结问题。而对于实验组被试来说,第一阶段起到了激发工具的作用,通过强化团结规则唤醒被试的共有员工身份,提高被试对共有员工身份的认同感。
为避免被试间相互交流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本次实验安排所有被试在同一地点同时进行。被试的所有决策均在问卷上完成,并通过随机发放实验组和控制组问卷完成被试间的随机分组。随机分组的结果(参见表1)表明两组被试在各主要属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两组被试近似相等。由于实验中包含两个捐赠活动,为避免顺序效应(order effect)的影响,本文对问卷中两个捐赠活动的顺序进行了调整。实验各阶段均由实验员引导完成,整场实验持续时间约为30分钟。

表1 实验组和控制组随机分组结果及组间差异检验

续前表
五、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实验中各组被试捐赠额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控制组被试对公司和学校的捐赠额相当于初始禀赋的45.48%和39.29%,这与以往研究所得结果相近①Andreoni,J.“Warm-Glow versus Cold-Prickle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Framing on Cooperation in Experiment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 (1):1-21;Gächter,S.,Herrmann,B.,and C.Thöni.“Trust,Voluntary Cooperation,a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urvey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2004,55 (4):505-531;陈叶烽:《亲社会性行为及其社会偏好的分解》,载 《经济研究》,2009 (12)。,表明本文实验设计及具体操作具有合理性。从表2中可以获取两点重要信息:一是无论控制组被试还是实验组被试,其对公司的捐赠额均高于学校;二是团结规则强化机制下,实验组被试对公司和学校的捐赠额均高于控制组被试。从图1中可以直观地看出上述差异。

表2 控制组、实验组被试对公司和学校捐赠额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图1 控制组、实验组被试对公司和学校的捐赠额 (单位:元)
为了检验被试对公司和学校捐赠额的差异以及强化团结规则所产生的实验效应是否真实存在,本文首先进行样本层面的统计分析。表2中Wilcoxon秩和检验的结果表明,控制组被试对公司的捐赠额并非显著高于学校(p=0.217);相比之下,实验组中两种捐赠额之间的差异在1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p=0.063)。上述结果说明,对共有员工身份对应的团结规则进行强化后,被试对共有身份对应群体的认同度产生变化,即由控制组中对公司和学校认同度的无差异转变为实验组中对公司的认同度显著高于学校。从另一方面看,这个结论说明本文利用激发工具强化群体规则的实验设计达到了预期效果。
为了进一步检验实验效应是否真实存在,本文将进行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对比分析。表3中的结果表明,相比于控制组,实验组被试对公司 (p=0.023)和学校 (p=0.036)的捐赠额在5%的水平上均有显著增加。这说明团结规则强化确实能够提升个体对群体身份的认同,使群体内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而在身份具有重叠性的情况下,团结规则强化产生的实验效应具有一般性,即不仅会提高个体对群体规则对应群体身份(公司)的认同度,还会提高个体对重叠身份对应群体(学校)的认同,使被试对两者的捐赠额均有提升。

表3 实验效应的统计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团结规则强化机制对拥有身份时间长短不同的个体所能产生的效果差异性,本文根据工作年限对被试进行划分,工作年限低于均值的被试视作新员工,工作年限高于均值的被试视作老员工。两类群体的捐赠额及统计检验结果如表4、表5所示。可以发现,无论对公司还是学校,团结规则强化机制对新员工捐赠额的提升显著有效(p=0.002;p=0.007),而对老员工效果并不显著(p=0.799;p=0.741)。此外,控制组中老员工对公司和学校的捐赠额均高于新员工(5.727>3.25;4.455>3.35),而且本文经过Wilcoxon秩和检验后发现,控制组被试中老员工对公司的捐赠额显著高于新员工(p=0.027),但老员工对学校捐赠额与新员工则并不存在显著差异(p=0.356),这从另一层面证明了被试的身份拥有时间越长,其对本群体认同程度越高,进而越愿意与群体成员进行合作。

表4 对公司捐赠过程中新员工、老员工实验效应的统计检验

表5 对学校捐赠过程中新员工、老员工实验效应的统计检验
下面,本文将利用计量模型进行个体层面的分析。首先,为研究团结规则强化机制下个体的内群合作行为如何变化,本文利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实验组变量是虚拟变量,当其值为1时,表明被试来自实验组;岗位变量为数值型变量,取值为1至4,分别对应不同的岗位;其余变量含义及数据结构与上文相同。对比回归结果可以得到稳健的结论,即:相比于控制组,团结规则强化机制下实验组被试对公司和学校的捐赠额在5%的水平上有显著提升,且实验组被试对公司捐赠额的增加值高于对学校捐赠额的增加值 (0.794>0.749;0.979>0.882)。表6中回归分析所得结论与表3相同,表明团结规则强化机制确实能提升个体的身份认同,使个体表现出更高的内群合作水平,因而假设1成立。此外,由表6中列 (2)可知,被试对公司的捐赠额还受到其在本公司工作年限的影响。整体上看,被试拥有公司员工身份的年限每增加1年,对公司的捐赠额就会增加0.203元人民币,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个体拥有群体身份的时间因素会改变个体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进而影响群体成员间的合作水平。

表6 实验效应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上述时间效应是否真实存在,本文构建新的回归模型,基于T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回归模型中老员工变量为虚拟变量,当其值为1时代表工作年限长的老员工,反之则为新员工;其余变量含义及数据结构均与前文相同。模型中各项估计值的含义如下:实验组变量的估计值度量团结规则强化机制对新员工捐赠额的实验效应;老员工变量的估计值度量控制组中老员工与新员工捐赠额的差异;交叉项(老员工×实验组)的估计值用于衡量实验效应在新员工和老员工之间的差异,即实验效应的双重差分值;实验组变量的估计值与交叉项的估计值相加之和度量老员工捐赠额的实验效应。
首先观察被试对公司捐赠额的回归结果,如列(1)和列(2)所示:实验组变量的估计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团结规则强化机制能够提升新员工被试对公司的捐赠额;交叉项的估计值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团结规则强化机制的效果在两类员工间确实存在差异,即新员工的实验效应高于老员工;实验组变量与交叉项的联合检验并不显著,说明实验组中老员工的捐赠额并没有显著提升。再来观察被试对学校捐赠额的回归结果,如列(3)和列(4)所示:团结规则强化机制对新员工效果明显,即实验组中的新员工会显著提升对学校的捐赠额;而老员工的实验效应,以及两类员工实验效应的差异均不显著。
由表7中的回归分析可知,团结规则强化机制的有效性对新员工和老员工存在差异。在对公司捐赠过程中,团结规则强化机制对新员工效果显著,对老员工的效果并不显著,二者之间的差异显著存在;在对学校捐赠过程中,上述规律同样存在,只是实验效应在新员工和老员工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新员工和老员工的差别在于工作年限的长短,表6和表7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团结规则强化对拥有身份时间短的个体更有效,这意味着拥有身份时间短的个体在受到干预时对群体身份认同度的提升程度更大,这一结论与表4、表5中所得分析结果相一致,因此假设2成立。

表7 团结规则强化机制下身份拥有时间的回归分析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人工实地实验中,通过对标准公共品博弈进行改装,以被试对公司和学校的捐赠额量化群体合作,并基于被试内和被试间的实验设计研究了团结规则强化机制下群体内合作如何变化。本文在实验设计中既兼顾了实验展开的现实条件,又对实验过程进行了必要的控制,因此所得研究结论准确有效。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团结规则强化机制能够有效提高个体对自身所处群体的认同,使个体表现出更高的内群合作水平。此外,本文还发现团结规则强化机制对身份拥有时间不同的个体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即新员工在接受了团结规则强化后捐赠额提升得更高且显著,而老员工在接受团结规则强化后内群合作水平不存在显著变化。最后,本文通过被试内的实验设计证明了当存在身份重叠时上述结论依然存在,说明本文结论具有一般性。
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在真实生活中,可以通过学校、媒体等途径发挥团结规则强化机制的教育作用,以此提升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在公共品自愿供给、社会救助等活动中,利用上述措施可以有效提高个体间合作水平,有助于达到政策目标。二是在对个体进行旨在提升群体认同度的教育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措施。由于个体拥有群体身份的时间不同,规则强化对其作用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现实中,针对“新”“老”个体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使政策具有针对性,更好地实现政策初衷。再推广之,一直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同样可以视作强化群体规则,目的是提升学生对集体的认同度。学生自入学起在各阶段均接受各式各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仅限于书本中的理论知识还是另有其他? 或者说,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普通人的社会认同塑造作用到底有多大? 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借鉴本文的研究方法则可以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总的来说,本文为群体规则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得到的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公共政策,提升社会救助水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