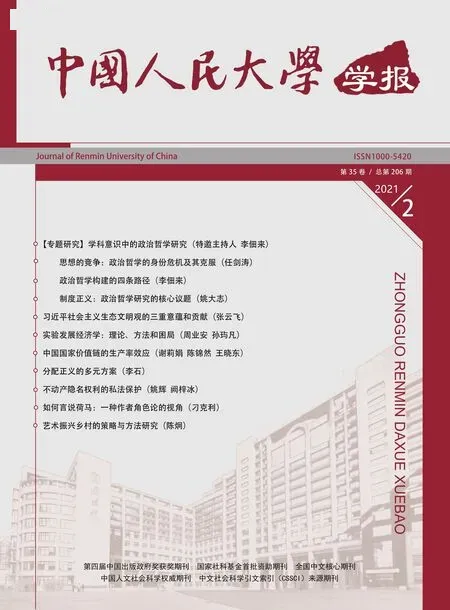场域决定思想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的知识社会学逻辑(1978—2000)*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独特的变迁史,背后有着怎样的动因和逻辑? 这个问题既是理解中国政治和文化转型的关键,也是探索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的一个突破口。一方面,当代中国与欧美先发现代化国家和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不同,市场化和全球化并未带来自由主义主导的政治思想,而知识界引进的新思想有时能改变社会,有时却得不到其他阶层的回应。这种思想变迁的保守性和不同步性,都亟待我们解释。另一方面,学界关于现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思潮的论著虽多,但其研究范式仍与传统西方政治思想史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类似,基本属于人物和文本梳理。这样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有哪些思想”“在怎样变化”,却无法回答思想“为什么这样变”。正是出于这两方面原因,笔者试图走进思想的背后,对1978—2000年这一段时间的政治思想变迁给出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解释。
一、“何时变”“是什么”与“为什么”: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变迁之谜
回顾海内外学界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可以识别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处于一个规范主义的阶段。其关键词是“何时变”,因为“中国如何现代化”“中国人何时接受民主思想”这样的规范诉求是这一阶段研究的重心。虽说国内学界“左右论战”存在内部分歧,其实只是自由主义学者主张学习欧美主流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路线,而新左翼理论试图将其升格为更激进的大众参与和经济平等诉求。①相关总结参见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就海外学界而言,此时正值罗尔斯(J.Rawls)等人复兴自由主义和政治哲学后的热潮,同时发生的南欧、拉美和苏联东欧的“第三波”民主化又在践行自由主义的成熟宪制框架。因此,当研究者把目光投向同样在转型的中国政治思想,其焦点自然也是中国什么时候完成“自由民主化”。②影响较大的论著如Ronald Glassman.China in Transition.Connecticut:Praeger,1991;Andrew J.Nathan.China's Trans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更不必说在学术界之外,几乎每年都会有一批畅销书来争辩中国政治是否将迎来大转变。然而,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并未像预期的那样发生西方式转变。
以2003年左右“中国崩溃论”遭质疑、“威权主义韧性”之争③Andrew J.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Journal of Democracy,2003,14(1).引发关注为标志,整个中国研究界开始转向。于是21世纪初的研究进入一个实证主义的阶段,试图回答“是什么”。海外学者开始提倡“进入”中国,探寻中国的知识分子、干部和民众的思想究竟如何。几个重要的调查项目催生了一波针对民主、权利和东亚思想传统的新论著,发现:干部的学历升高,但思想上仍然以经济和稳定为先;民众中的民本主义者、缺乏政治知识者要多于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虽然熟悉各派现代性思想,却缺乏政治影响——这三个阶层的研究构成了一幅保守而稳定的思想画面。④对这些研究的梳理参见黄晨:《近年美国学界中国民主研究评析》,载 《国外社会科学》,2016 (1)。而在国内学界,一方面思潮研究兴起,学者开始总结中国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政治思想⑤如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高瑞泉、杨扬等:《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王炳权:《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关于知识分子的访谈和论著汇编则更多。;另一方面,解读“中国模式”的作品多以大政府和民本主义传统来解释中国政治思想的独特性与稳定性,也与海外中国研究的结论遥相呼应。
无论学者们对中国的思想现状在价值上如何评论,今天都可以说,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是什么”的问题已逐渐明晰,接下来的挑战则是回答“为什么”。尤其是:为什么在革命年代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想和20世纪80、9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都逐渐保守化,甚至转向民本主义等传统立场? 对于这一关键问题,海内外学界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中国民众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倾向于信任现政府⑥Elizabeth J.Perry.“Chinese Conceptions of‘Right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08,6(1);Tianjian Shi.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有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动引导的结果⑦Wenfang Tang.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闾小波:《从守成到能动》,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 (1)。;还有的研究揭示了外部知识对思想的影响,例如看到外国动乱的人更容易支持保守和稳定⑧Haifeng Huang.“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Domestic Evaluations in a Changing Society:The Case of Chin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5,109(3).。
这些方兴未艾的、探究外部因素与政治思想关系的实证研究各有贡献,也开始超越了20世纪下半叶“经济发展—民主思想”的旧理论。但是,很多热门著作并未深入思想生产和变迁的内部,甚至存在严重的误读。一个例子就是沈大伟 (D.Shambaugh)的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⑨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有不少他认为来自“共产党”的“分析”,其实出自中国的学术期刊和专著;他引用的“分析家”,也有不少是专业学者,这些人未必代表或者赞同官方的观点。研究者如果不知道其分析的这段思想到底代表谁、从哪里来,即使数据再庞大、细节再丰富,也可能成为误读。
因此,笔者提倡一种不同的研究方向:进入思想的社会实践过程。因为无论实证研究发现了多少影响思想的因素,研究者都需要进入思想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本身,才能完整地揭示思想变迁的逻辑,此即由来已久却未在中国学界引起足够重视的知识社会学 (sociology of knowledge)方法。
二、“窄”与“宽”:知识社会学及其本土应用
当孔子师徒完成《论语》,或者洛克的《政府论》被引入中国,整个国家的政治思想就会因此而改变吗? 这就是知识社会学处理的问题。传统思想史研究所不能解释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们大多是对孔子、洛克的人物研究或者《论语》《政府论》内部的命题研究。梁启超曾批评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因为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①梁启超:《新史学》,载 《新民丛报》,1902,第1号。此话当然过于夸张,但确实点出了传统人物导向研究的问题,因为它们对某几位精英、某几本著作、某几句名言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这种思想史叙述可以称之为“窄的思想史”。思想史之所以偏爱窄叙述,究其根源,是研究者的关切在规范层面上,要发掘“谁的思想更有价值”,而不是要回答“谁的思想影响了历史”。
20世纪初,曼海姆(K.Mannheim)开创了第一代知识社会学。他综合了马克思等人的成果并提出,任何思想均由历史—社会情境塑造,思想不能与思想者的行动和阶级 (class)分开。②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但第一代方法过于强调阶级决定论,对知识形成和传播的微观机制不甚了了。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福柯(M.Foucault)和布迪厄(P.Bourdieu)为代表的第二代知识社会学渐成主流。③国内外学界对此已有归纳,参见E.Doyle McCarthy.Knowledge as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6,pp.1-20;赵超、赵万里:《知识社会学中的范式转换及其动力机制研究》,载 《人文杂志》,2015 (6)。一方面,福柯强调国家权力的影响,正如他在《规训与惩罚》中的名言:“权力—知识造成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可能性”④福柯:《规训与惩罚》,35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另一方面,他们更关注具体场景对思想知识的塑造。如今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正在从知识的传播扩展到知识的生产,将知识分子看作更多样化的群体,更关注微观的场域(field)和小圈子(circle),并开始结合性别和地理研究。⑤Peter Burke.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pp.8-9.
如果说两代知识社会学已大幅推进了欧美的思想和历史研究,那么今日更亟待开拓也更重要的一个领域,则是用知识社会学来观察中国政治思想,最终解释“为什么”。最初的尝试来自郝志东,他基于曼海姆和葛兰西(A.Gramsci)的经典框架,将知识分子划分成掌权的革命知识分子、为各阶层代言的有机知识分子、充当反对派的批判知识分子以及远离政治的专业研究人员等四个亚群体。⑥Zhidong Hao.Intellectuals at A Crossroads.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p.7-44.后来的研究则继承第二代知识社会学,以生产思想的场域和圈子为划分标准。例如齐慕实(T.Cheek)将20世纪知识分子的场域分为从晚清到民国的印刷资本主义、从蒋介石时期到新中国的宣传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新媒体博弈的混合状态等三个阶段⑦Timothy Cheek.The Intellectu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Introduction.;饶兆斌 (N.C.Bing)则将场域分为国有、官方支持、社会和异见等四种。⑧Chow Bing Ngeow.“Conceptualizing Intellectual-State Relations in China”.Issues&Studies,2007,43(2).
虽然这些先行者已展示了解释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的巨大潜力,但目前的研究不仅规模极为有限,离真正以知识社会学来理解中国乃至发展中国理论更为遥远。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两类研究虽然让读者知道了中国有哪些生产知识的群体和场域,但无法回答这些群体和场域是如何产生的,更没有意识到权力对这些场域的决定性影响。社会和异见场域是本来就存在的? 还是随着经济发展自动形成的或是政府权力塑造的? 如果是塑造出来的,权力治理场域的逻辑又是怎样的? 怎样的治理逻辑才是有效的? 不回答清楚这些问题,就无法完整描绘从政治权力转型到场域形成、再到思想变迁的完整因果链条。
但凡想要传播或让人接受某种思想,可用的手段只有三种:强制的(coercive)、利益的(remunerative)和规范的(normative)。这在社会、政治学家中已成共识。①Amitai Etzioni.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Minnesota:The Free Press,1975,pp.5-6;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14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Dennis H.Wrong.Power.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5,p.21。他们都使用了类似的三分法。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场域之所以产生、政治思想之所以发生变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治理手段从过去的官僚制强制和意识形态规范,转向了以利益激励为主。
第二,即便是那些流行的群体和场域概念,大部分仍然是照搬自葛兰西或者布迪厄。很多概念和类型只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未必适合描述中国。例如中国未必存在多元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国家掌控的场域并不是一直保守的,新媒体等社会场域也不一定是反国家或者亲西方的。②例如广泛存在的所谓“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党”)等自媒体,对它们的研究参见Rongbin Han.“Defending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Online”.The China Quarterly,2015,p.224。如果照搬欧美理论,把新媒体都当成新思想甚至对抗性思想的载体,显然就会低估部分人思想的保守性。
笔者认为,中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了更贴合现实的术语群:就场域而论,知识界可以分为“理论界”(official theoretical field)“公共知识界”(public intellectual field)和“专业学术界”(professional field)等;就作者群体而论,知识分子也相应地分为“理论家”(official theorist)“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和“专业学者”(professional)。权力对不同场域中的治理逻辑不同,这些场域生产、传播政治思想的结果也就不同。
第三,国内学界虽然知晓知识社会学,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像海外中国研究一样将其投入实证研究。眼下的政治思想史和当代史研究仍然以人物和文本解读为主,面对知识社会学以及相关的政治文化、新文化史成果,往往谨守门户、极少引用,甚至以知识社会学为题的论文,也大多只是对马克思、曼海姆和福柯等的人物研究。这也说明了推进真正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接下来,笔者将运用这些本土语境中的场域和群体概念,分析为什么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会出现保守的、不同步的变迁。在1978年以后的权力转型中,依次诞生了三种基本的场域,这些场域又决定着政治思想的生产和变迁,最终形成了我们在21世纪看到的场景。
三、第一种场域:“理论界”与思想的一致性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最大的区别,在于改革前是一种国家统领全局的全能主义社会。全能主义在政治思想上的特征就是一致性,知识分子的思想几乎都围绕着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而展开。思想一致性的社会基础,正如齐慕实所论,就是当时只有一个“定向的公共空间”③Timothy Cheek.The Intellectu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10.。这个空间亦即场域就是人们熟悉的理论界。与其他场域相比,理论界的核心特点就是知识与政治权力高度嵌合,因为理论家们都在行政—官僚系统内有级别和任务。官僚制的权威既是理论界形成的原因,也是其生产、传播思想的主要逻辑。
与既有研究相比,我们试图做两项拓展:第一,理论界场域的独大,影响的不仅是生产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其他社会群体获取思想知识同样有着决定性影响。第二,这一思想状态并不会随着政治领导人的更换而立刻瓦解,而是不断延续。
学界谈到中国的思想解放,或者以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分界线,或者关注1979年初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①后一种意见如Erza Vogel.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257-261。这两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在中央部署下展开的,仍然是理论界内部的行动。略览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参与者——胡耀邦领导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胡乔木与邓力群领导的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三报一刊”②当时指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 《红旗》杂志 (1988年改版为 《求是》杂志)。和行政级别不低的笔杆子们——就能发现,他们仍然属于理论界,或者称之为政府改革的“智囊团”(intellectual network)。③Merle Goldman.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这种身份一方面有助于他们直接影响各级政府的改革决策,另一方面也将他们限制在传统的话语中,而不太可能像后来的党外知识分子生产、传播国外的新知识。④连文艺界人士也如此,中国歌剧舞剧院一位著名导演看到同期党外知识分子的访谈后表示:“我们这些人是比较正统的……我们和他们完全不一样。”参见王雅琪:《歌剧重演,我们必须重新排练》,载苏峰编著:《1978大记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改革初期,理论界提出了丰富的改革建议,居功甚伟。但是,思想的多元化程度不高,主要是因为理论家对改革的探讨往往处于同一种话语体系中。综观整个知识界,大学和民间知识分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也没有独立于理论界的思想,因为单一的场域决定了他们在知识资源和机构平台两个方面都没有太大变化。
对从事研究或者求知的人而言,除了一致性的官方读物,最丰富的资源就是所谓“灰皮书”“黄皮书”了。这些书诞生于中苏分裂的20世纪60年代初,是将有关“修正主义”材料翻译介绍给国内供批判用的。到1980年左右,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论著开始成规模地引入。政治书籍翻译出版也随之提上日程,出版、理论界的几位新领导组织选出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著作,然后请示中央。胡耀邦虽然表示支持,不过又说“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让他们继续精简。据人民出版社方面的回忆,四年内他们才出版了100种书,基本都是葛兰西、麦德韦杰夫(R.Medvedev)等左翼学者的代表作。而这些著作在发行时也仅限于大城市,不发县级及以下新华书店。⑤张惠卿:《“灰皮书”的由来与发展》,载 《炎黄春秋》,2013 (4)。因此,彼时的普通学者还很难接触到新知识。
与知识资源出版相比,机构平台的重建相对顺利一些。改革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核心,《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法学研究》等各学科权威刊物纷纷创刊或复刊,而政治学、社会学等曾遭废止的所谓“资本主义学科”也得以重建。到1980年,正式期刊数已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数十种攀升到2191种。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等编:《中国出版年鉴》(1981),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政治思想的生产,算是重新拥有了一个从生存机构、期刊到大学讲堂的完整平台。不过,这个平台仍然受理论界领导管辖,什么样的观念能在上面生产、传播,与每个时期的改革方向密不可分。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这种状态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甚至在此后理论界也是最具话语权优势的场域。因此,在诸种回顾思想史的“80年代”的论著中,王学典认为当时是理论界处于领导地位⑦王学典:《“80 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载 《开放时代》,2009 (6)。,这是最接近实际的结论。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年中,理论界思想的主题虽然从革命变成了改革和思想解放,但改革的知识资源是高度集中的,风向是高度一致的。
四、第二种场域:“公共知识界”与新思想的传播
公共知识界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第二种场域,它更接近于其他第三波国家中“国家—社会”分化的状态,也构成了知识分子生产主流意识形态以外新思想的基础。严格地说,这一场域直至1983—1984年才诞生。我们除了分析场域的生成,还关注场域中的知识分子如何影响其他群体的政治思想。
在理论界的领导下,非官方①在单位制下,所有人都有一个单位和编制。这里的“非官方”强调的是其思想与理论界有区别,而这样的人多半也没有行政职务。知识分子想要发表论著或译著,就必须依靠正式的组织关系或非正式的人际关系。而改革开放以后传统强制手段的软化,给了他们活动的空间。在组织上“挂靠”于一个理论界单位,可以让新团队在单位制下取得半合法地位;在人际关系上请支持改革的领导或者理论界前辈挂名,也会让知识分子在资源获取上大为便利,并避开政治风险。于是在全能主义的变革时期,20世纪早期曾经活跃过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界得以重生。
几乎所有论者都会提及当时活跃的几个小知识群体。②类似的群体还有上海的 《新启蒙》杂志、武汉的 《青年论坛》杂志和贵阳的 《传统与变革》丛书等。这些群体成员虽然年轻,但都深谙挂靠之道。《走向未来》丛书以译介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前沿成果为主,编委会多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年轻学者,他们挂靠到新建的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名下,解决了出版社不敢接的问题,并得到了保护。③Fong-ching Chen,and Guantao Jin.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08-123,p.141.致力于重估传统文化的中国文化书院则由北京大学一群中国哲学学者发起,他们找到一个理论团体——马列主义教学研究会——才得以解决。④汤一介:《自我学术研究的回顾与瞻望》,载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马国川编:《我与八十年代》,33-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成员多出身于中国社科院外国哲学所,他们在代际上最年轻,也与西方思想最接近,算是几个群体中唯一没有稳定挂靠单位的。⑤查建英编:《八十年代》,2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就知识分子的思想交流方式而言,除了组织化的机构和群体,还有许多零散化的会议和沙龙等“小圈子”。后来经济学界津津乐道的莫干山会议就是一例,几位年轻人发起的学术会议,从省部级领导到在校研究生都获得了发言资格。⑥柳红:《八十年代》,427-44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莫干山会议首次将知识分子的建议直接提交国务院,不仅参会的张维迎、周其仁、华生等青年学者在知识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部分参会干部也在此后步入政府高层,影响改革决策。此外,围绕知识分子也会形成私下的小圈子,例如读者结伴登门拜访作者。法学家梁治平回忆道:“那时人与人的关系,还有人际之间的沟通方式和现在很不一样。”⑦马国川编:《我与八十年代》,25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这正是新思想对封闭已久的社会的吸引力。
有学者将1984年到1987年称为民间思想文化复活的“黄金三年”。⑧Fong-ching Chen,and Guantao Jin.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08-123,p.141.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一致性的知识界分化成了两个亚场域:理论界和公共知识界。前者是政府和知识界之间的桥梁,后者是知识界影响社会的渠道,也因此能够生产独立于政府意识形态的新思想。
这种分化如表1 (见下页)所示:

表1 1983年以后的两种亚场域
公共知识界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似乎比对知识界本身还要大。因为大众除了读书和思考政治,更关注物质生活和流行文化。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有这么一句话:“听歌要听邓丽君,嫁人要嫁海陆空。”①“海”即有海外关系的人,陆 (“落”)即落实平反政策、返还财产的人,“空”即有空房子的人。这两者分别象征着大家对流行文化和物质条件的渴望,而它们多半从资本主义的欧美、港台而来。在当时的人看来,一个人同西方的接近程度往往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步出现。
在这样的认知方式下,便不难理解那些正式或非正式的知识圈子为何如此火爆了。代表着20世纪80年代思想传播热潮的有两份文本:从台湾引进的柏杨作品《丑陋的中国人》,两家出版社在一年内就分别印行了210万本和90万本②这个印数还是出版社“为了稳妥起见”加以控制的结果,实际征订量更多。参见蒲荔子、周豫:《〈丑陋的中国人〉大陆出版内幕》,载 《南方日报》,2008-05-08;弘征:《在大陆首家出版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琐忆》,载 《芙蓉》,2010 (4)。;还有此后大陆公共知识分子自己制作的 《河殇》,借中央电视台这个大平台,更是在城市范围内家喻户晓。③中央电视台还收到了上千封观众来信,参见晓蓉:《〈河殇〉主要撰稿人之一苏晓康谈 〈河殇〉之争》,载 《西藏艺术研究》,1989 (1)。今天看来,这两份文本都过于美化西方,贬低中国文化——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严肃的学术作品。但历史地看,这种火爆象征着公共知识界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大众知识获取的多元化。用出版数据来衡量社会知识的多元化程度(见图1),以每年出版的图书为例,1989年平均每种书发行7.8万册,1977年平均每种书发行25.7万册。①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中国出版年鉴》(1980),619-6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也就是说,很难再有一种读物及其思想能垄断整个场域,即便是前述两份文本也只能影响一部分人。公共知识界的总体读者规模虽然大于理论界,但读者的政治思想已经走向了多元化。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除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笼统的现代化思想乃至各个小思想流派都开始兴起,并塑造着社会运动。

图1 1977—1989年图书、报纸和期刊的多元化程度④计算自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等编:《中国出版年鉴》(1980—1986),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986;《中国出版年鉴》(1987—1991),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7—1991;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 (现代部分)》(第3卷下),216-218、226-227、523-525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公共知识界与理论界的一度抗衡,也成为西方政治学界认为中国将加入第三波转型的主要依据。而2000年以后网络的快速发展再次丰富了公共知识界的传播渠道,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读者群比书报期刊更大。于是,世纪之交又有一波学者开始预测网络如何推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转型。那么,为什么很多社会群体还是一样保守或者不关心政治呢? 因为中国迎来了第三种场域。
五、第三种场域:“专业学术界”与政治思想的边缘化
20世纪90年代和80 年代的改革侧重有很大不同,这也导致了知识界场域的变化。1989—1992年的治理整顿,清理了一些不符合政府改革路线的学术和出版机构,公共知识界的规模有所下降。不过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迅速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线。1993年全国已有1812万科研人员和954万大、中、小学教师②分别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5),807、805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专业建设也步入正轨。
如同经典民主化理论描述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和社会扩张的确带来了更多的学术平台,出版了比十年前更多的知识读物。知识界讨论改革路线的“左右论战”也正是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将80年代模糊的现代化诉求深化为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学理辨析。因此,很多学者在观察当时的知识界和思潮后,以为他们将再次影响政治改革乃至推动“自由民主化”③如Yijiang Ding.Chinese Democracy after Tiananmen.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1,pp.31-32。作者列举了20世纪90年代迅速增加的政治学、法学学者名单,以为论据。。我们要做的不同解释仍然侧重于两个方面:新场域的生成,以及这一场域对知识分子和社会群体思想的影响。
解释的关键,在于1992年以后知识分子的新一轮分化,公共知识界的规模缩减了,其活跃区域也有所变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思想,主要在以下三种平台上发表:一是港台的期刊和传媒,多由外迁的大陆学者或者境外华裔创办,例如率先讨论“保守与激进”的《二十一世纪》和引入了“市民社会”概念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二是获得相关领导支持的研究会和期刊,例如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④初任领导有萧克、谷牧和张爱萍,参见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简介》,载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网站,http://www.cssm.org.cn/files/hedingben.html。主办的《战略与管理》就成为“左右论战”的阵地之一;三是非政治性的文学文化期刊,像三联书店主办的《读书》和海南省作协主管的 《天涯》,面对市场化的冲击它们希望推陈出新,杂志内容从“小文学”变成了“大文学”⑤韩少功语,参见 《韩少功与 〈天涯〉》,载中新网海南,http://www.hi.chinanews.com/hnnew/2016-03-31/4_62142.html。,随着 《天涯》1997年刊登汪晖的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左右论战”便在这些文学刊物上展开了。不过总的来看,这些平台及其作者群都只是知识界的一小部分。
那么,20世纪90年代与日俱增的知识分子是以什么人为主的呢? 他们正是在专业学术界中活动的职业化“专家”“学者”。他们的知识生产既不是出自官僚制的权威,也不完全跟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而是围绕学科自身的内容,或者把它当作谋生的手段。在多达数千万的知识分子队伍中,以公共事务为业的无疑是少数。知识界进一步分化为三个亚场域,这种最复杂也最适合商业社会的知识社会学结构也持续到了今天,见表2:

表2 1992年以后的三种亚场域
对以学术为谋生职业的专家来说,知识生产是“院校—专业—项目”这套系统赋予的绩效任务,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也是面向现实需要的。1992年以后的市场化改革推行到知识界,其实就是变强制和规范手段为利益激励。正如批判理论家所指出的,这种经济社会中的知识生产“不再以知识本身为目的”①利奥塔:《后现代状况》,36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而是在某种供求关系的支配下,完成申请、预订、生产乃至包装推销等环节。这种知识产出的“数量”,开始成为科研机构评价人员绩效的最高标准。此时政府和社会的知识“订单”一边倒地偏向经济性、实用性的学科,作为政府需求风向标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就是最佳的证据。在1994—2000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中,经济类学科 (25%以上)的数量一直远多于政治类(10%以内),而在政治类学科中,独立的政治科学(3%上下)与马列、党建比起来又只是小头。②计算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http://fz.people.com.cn/skygb/sk/index.php。
当然,并不是说非政治学学者就没有政治思想,毕竟学者们都有利益和矛盾的诉求,他们都需要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多推广成果的渠道。但在新的现实条件下,他们最理性的表达策略是接近资源提供者,而不是借助新思想来进行抗争。各大学和科研院所先后推行量化考核体系,专业学者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公共领域的政治行动不仅耗费心力,还可能妨碍个人获取资源。因此,无论就政治思想还是政治行动而言,专业学术界在社会上越来越边缘化。
那么,在迅速扩张的消费社会中,大众接受的政治知识又有何变化呢?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各地新华书店和《中国图书评论》等刊物开始制作畅销书排行榜,这为分析提供了更准确的参照。有意思的是,“畅销书”这个概念的流行本身就是商业化的象征,因为在发行方和评论者看来,是否在市场中受欢迎才是一本书是否“成功”的评判标准,甚至领导人著作也要放到这个榜中。1993年,上海市新华书店系统公布了全年的销售排行,虽然刊载南方谈话的 《邓小平文选》一直占据榜首③需要说明的是,中央发布的政治类读物即使没有零散消费者的追捧,也会有政府和国企的批量采购,所以它们至今都稳居各类畅销书榜的前列。,但实用性的工具书在各店的份额已普遍超过五成,有的店里甚至超过了七成。④白雪:《一九九三:上海畅销书一瞥》,载 《中国图书评论》,1994 (3)。而这一年仅仅是确立市场化改革后的第一年。
1999年北京和广州的畅销书榜可以给我们一个更直观的认识,给民众提供政治知识的读物主要是“社科类”“文学类”“青年读物类”。如表3所示(见下页):

表3 1999年末北京和广州新华书店各类畅销书一览①整理自 《1999年11月至1999年12月新华书店畅销书情况一览表》,载 《中国图书评论》,2000 (1)。
民众的“社科”需求基本由经济法规读物组成;“文学”的主角从批判性的“伤痕”和文化上的“寻根”转向了题材更广泛、更私人化的小说;曾以科学启蒙著作为荣的“青年读物”则被实用工具书所替代,在世纪之交又进一步缩减成了应试教辅书的天下。学校教育文本的转变同样让人记忆犹新,例如数学课上教乘方的应用题,几年前还以“地主向你收租”为例,如今已经变成了“你在银行存款”。这些领域的知识都传达着同样的信息:对公民而言,以金钱为核心的实用性是最优先的价值。正是新的知识基础,造就了学界所谓“不关心政治”(the apolitical)的中产阶级。②Andrew Nathan.“The Puzzle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Journal of Democracy,2016,27(2).
从这个视角来审视“左右论战”以及此后的“中国模式”,新左翼和新儒家的一个流行结论——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在商业社会中占据了“统治性地位”③这种说法很常见,例如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载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1 (42)。十年后的部分“中国模式”论者也持此看法。就值得商榷了。实际上,自由主义只在公共知识界内部占据主流,左翼和儒家思想常以一种反抗者的身份出现。但如果算上理论界和专业学术界,哪个流派占据支配地位就不好说了。将视野拓展到整个社会,可以说各个流派的政治思想都居于边缘。因为在左右翼的争论热火朝天时,政府和民众对此并不像之前那么关心,也没有任何一本政治思想著作进入畅销书榜。诚如傅士卓 (J.Fewsmith)所言,从此以后知识精英与政治活动已经没有直接关联了。④Joseph Fewsmith.China since Tiananme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52.
六、结语:一个解释,一种范式
分析完三种不同场域的逻辑及其对思想的作用,我们就能够从内部性的视角解释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变迁:全能主义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强制与规范相结合的治理逻辑塑造了理论界场域,而理论界占据中心又使得此时全社会的思想基本保持一致;80年代中后期强制和规范的软化导致了公共知识界与理论界的分化,新思想也开始生产并影响社会大众;90年代后以利益激励为主的治理转型孕育了专业学术界,它吸引了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以左右翼政治思想的研究虽然更深入了,其影响力却被限制在少数群体中。
社会大众、政府干部与知识界的政治思想,因场域逻辑的不同而不同,这就是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的不同步性。20世纪末左右翼政治思想在其他场域走向边缘,民众对经济实用知识的追求压倒了对政治参与的关心,表现为政治思想的保守性。思想变迁的直接动因是场域变迁,而非经济增长、传统文化等外部因素。
在当代中国以外,知识社会学的场域分析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式。因为无论想解释哪个国家、哪个时段的政治思想变迁,都有必要放眼于“文本”之外,考察哪些社会场域塑造了文本、文本又如何影响着社会。美国思想界为什么会有时选择汉密尔顿的大政府思想,有时偏好杰弗逊的小政府思想? 在中国古代朝堂上、乡野中运行的儒家思想,与孔孟的原儒思想相比有什么变化? 一言以蔽之,我们看到的“某国政治思想的变迁”,往往是其中重要场域及其生产逻辑的变迁所塑造的。孔子的《论语》或者洛克的《政府论》固然重要,但它们直接改变的只是一群读者的思想,要改变某个国家的思想——或者思想被这个国家所改变——就一定要凭借场域性的变化。这就是笔者呼吁以知识社会学重书“宽的思想史”之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