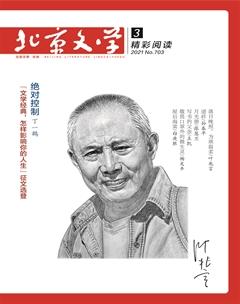17岁那年,我遇见《傅雷家书》
老哲
1982年我17岁,在太原二十六中读了两年高中,参加高考,只考了381分。当年山西省本科录取线是390分,我名落孙山,遭遇人生中的第一个挫折。我在复读班恶补数学一个月,痛苦不堪。父亲托熟人为我补报了一个专科志愿,于是收到了太原师专中文科的录取通知书,心有不甘地进入了一所不是自己预期的学校。
为何不再考一次?作为一个刚刚迷恋上文学的狂热少年,在数学课上忍不住偷读《安娜·卡列尼娜》,梦想当作家的人,实在禁不住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的诱惑。正是在读师专期间,我遇见了影响我一生的《傅雷家书》。
读高中起,我就养成了光顾书店的习惯。那是一个新书好书迭出的时代,一周不逛书店,再去定会有意外的惊喜。80年代初经常去的书店共四家,解放路和五一路的新华书店,古籍书店和外文书店。三联书店1981年8月初版的《傅雷家书》,小32开,傅雷的老友庞薰琹设计的封面,亚光白,一支鹅毛笔,傅雷先生的面部轮廓简笔画,书名是集作者遗墨,四个湖蓝色汉字,内敛娟秀,只有薄薄的268页,定价0.95元。何时在哪一家书店所购,已经不记得,但我写满了一个本子的读书笔记,保存至今。楼适夷在《代序》中,称它为“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真的是恰如其分。我这个艺术学徒,在刚刚开始的阶段,幸运地遇见了一位造诣深厚知识渊博的导师,虽然他已经含恨离世,但他写给自己儿子的私人信件却由于范用先生的卓识与勇气,在刚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成为公共出版物,傅雷先生一夜之间变成了我们这一代渴求知识和热爱艺术的少年们共同的教父。《傅雷家书》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上百万册的发行量(仅三联一家),不知使多少像我这样的艺术学徒受益。
文学、绘画、雕塑和音乐是相通的,思想和艺术是一体的,《世说新语》和《柏拉图对话集》是同样伟大的。在80年代初,谁有这样的眼光,谁能给我们这样的教诲,我们自己的父辈,我们大学里的老师,都不能有像傅雷先生一样的学识和眼界。从《傅雷家书》开始,我阅读了傅译《巨人三传》《艺术哲学》以及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我和朋友们交换盒式磁带,用半头砖那样的录音机对照着傅雷的解说听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和肖邦,并且怀着极大的热情听了一次盛中国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我们搜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的单页名画欣赏,把大卫和维纳斯贴在居室的墙上,将贝多芬的石膏像置于案头,以近乎虔诚的心敬奉艺术,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完全是受了傅雷的教诲。
将近40年过去了,我已经接近了傅雷先生弃世的年龄,虽然没有功成名就,却矢志不渝地走在追求艺术的人生道路上,无怨无悔。
从世俗的意义上,傅雷的一生谈不上成功。幼年丧父天资极高的他,17岁就有短篇小说发表,因为叛逆曾被几所中学开除,20岁自费留法,四年后归国,曾短期任职于上海美专、昆明国立艺专等学校,因与人不能合作而辞职,以翻译法国文学和艺术名著作为一生的事业。新中国建立后,傅雷未进入体制内领工资,和巴金、汝龙等成为少数几个靠版税生活的文学个体户。反右运动中不肯听从上海作协领导的好心暗示对自己“深刻检查”而被划为“右派”。
当今社会,对于青少年励志教育的误区在于,鼓励所有的人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名利和权势,而忽略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似乎只有战狼式的人格,才能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立于不败之地。无论职场官场,年轻人的生存压力巨大,跟40年前的社会氛围差异很大。我常常问自己,今天决心献身艺术和文学的青年,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并且将会面临怎样的艰难和曲折。假如有人问我,该拿什么样的理想人格,拒绝天下无敌的战狼,我要用《傅雷家书》中的原话来回答,那就是“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这是我们固有文化中的精华”。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滴雨斋自述》,全文如下:余十有五而志于文学,凡三十年,昼夜笔耕,未尝稍怠,而竟一无斩获,亦不介怀也。雪泥鸿爪,浮云苍狗,屡变屡幻,历历在案。日未落而作,日将出而息,力口而食,茗泉而饮,名缰利锁,于我何有哉?秉烛彻夜读,心从古人游,自励复自娱,不与时文畴,书日增而盈室,识益卓而见空,万山丛中独行难,一山放过一山拦。集字为句非易事,登高必赋遣余怀。只不过三寸毛颖,换成了一尺键盘。华章未竟岂甘休,壮心雕龙续文脈。昔日长沟游子,忽忽鬓已染霜。瞻望前路,人生苦短,幸有妻女相伴,如花似玉,锦心绣口,不以无闻责我,聊慰平生。庚寅初春,客寓京师十载,由感而兴,啜此数句,略申吾意。
又十年过去了,意思还是这样的。《傅雷家书》中的一句话,是我的座右铭。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