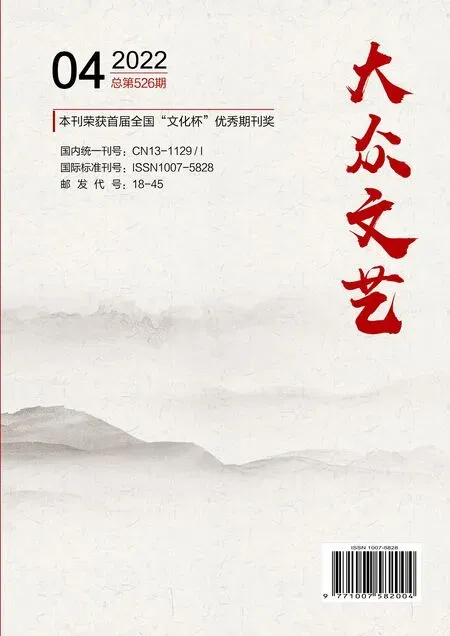拉莉萨·舍皮琴科电影中的表演艺术
汤旭坤
(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北京 100081)
拉莉萨·舍皮琴科(Larisa Shepitko)的电影创作处于苏联社会变革时期,经历了十月革命的洗礼,苏联在整个文学、艺术领域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性与先锋性。然而,面对根深蒂固的东正教唯心主义与自然主义传统,新兴的“社会主义”信条的“极端性”又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畸变。一方面,在“社会主义”以及政府的文化钳制下,舍皮琴科所处的政治社会空间要求演员对于空间、社会、自身进行深度体验,将演员放置在真实的空间中,体验身体的极限;另一方面,东正教的精髓也成为当时创作者所无法规避的事实,导演要求演员在真实体验的基础上展现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神秘的思辨属性。因而,处于“最两极化的民族”之中,这两种模型相互交叉叠加形成了舍皮琴科电影中表演艺术的“两翼”。舍皮琴科将其对于生命、世界、宗教的思考融入影片,在现代与传统的交织中,显示出独特的电影表演艺术模型,即“社会主义”体验派的客观性与宗教形式主义的思辨性,这就要求演员在体验权力空间的基础上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
一、环境体验:空间记忆与表演生态
空间是身体控制的外部表征,空间在无时无刻地“控制”演员的表演方式并将演员的表演同社会政治相连。舍皮琴科的电影中,导演要求演员体验文本与环境生态的身体范围,构筑演员、电影空间与时代社会的关联。如果说演员表演是微观视域的呈现,那么观演空间则是衡量历史、文化的宏观标尺。宏观与微观的呈现即构成电影整体的观演脉络。观众对于影片的感知则是通过宏观的环境空间抵达微观的演员再创造,尤其对于演员的行为举止以及微相的快感体验。这就要求演员在体验环境空间的“客观性”后进行表演艺术的再创造,而这种“客观性”的体验更多的是来自演员切实的身体感知,包括恶劣环境对身体的压制、狭小空间对身体的禁锢以及开放空间对身体的释放。这便形成了舍皮琴科表演艺术的其中“一翼”:空间体验与演员记忆。
舍皮琴科电影中对于极端环境的构筑与其所关注的乌克兰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1932年开始,天灾与人祸直接导致乌克兰饿死了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苏联也在长达两年的饥荒中死伤惨重。这一人间炼狱成为信奉天主教的舍皮琴科所无法排解的创作源头。电影中贫瘠的土地、恶劣的环境以及压制的空间均成为其影片生态环境的特定表达对象,这种对于真实环境空间的建构来源于唯物论的“社会主义”体验。《炽热》中贫瘠的草原、《上升》中被大雪覆盖的场景使得渺小的人物与无限扩大的环境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演员放置在空间构图的一侧,让宏观的空间展现出微观的人物背景。一方面将演员放置在真实的环境中,承受现实空间的最大忍耐极限。在濒临崩溃与绝望的边缘,考量空间背后的演员自我“存在”与剧本逐渐“消解”的真实情绪体验;另一方面,演员在承受极端环境的考察后会进入一种“短暂”的想象,或仅出现了一个极其微小的动作、身形,甚至是背影,但是在后续的表演中,这种微观的体验将会被不断放大,直至面部以及细节的特写。导演对于空间的构筑是有意识的,在形成影片空间层次的基础上,将演员与角色间的距离融合,最终形成演员自身表演环境的空间记忆与情绪积累。
演员的空间记忆不仅是舍皮琴科所刻意营造出的环境生态,更重要的是将空间记忆融入后续的表演状态之中。在不同的环境空间中找寻原初的空间印象,成为舍皮琴科电影中对于演员表演的基础训练方法。开放的空间与幽闭的空间、真实的环境空间与虚构的舞台空间之间存在空间记忆的差别。贝拉·巴拉兹在《可见的人:电影精神》中对于特写镜头(“微相”),进行了探讨。在他看来,演员的面部感知正是电影生命的展现,而对于面部的塑造即是对于生活细节的书写,在天然的细节与日常的表达中完成电影形象的塑造是演员必须经历的训练。将空间环境氛围与演员面部以及细节的特写相联动可以创造出超越影片本身的内涵。舍皮琴科在对演员的塑造方面更加倾向于以面部细节、微表情以及动作的特写的创作,她的电影中动作与微相在某种程度上有超越音乐、对话的绝对优势,配合空间记忆的感官外化,将演员与日常空间进行捏合,形成“开放空间”+私密的人物关系或者“封闭空间”+疏离的人物情感。影片《翱翔的女飞行员》,女主角娜迪达曾经是一名飞行员,退役后娜迪达对于天空无限怀念,而现实却困住了她,让她落入学校琐事、家庭困境、社会压抑的困顿之中。因而,形成了“开放空间”+私密的人物关系,当演员面对开放的环境空间时,在表情微相中往往呈现出喜悦、幸福的状态。然而,当她回到家庭封闭的空间中,封闭的空间给演员造成了心理空间的压迫感。娜迪达边削土豆,边自言自语,这时的她之所以是幸福的,取决于演员上一场表演中开放空间的记忆惯性。这种短暂的记忆会伴随演员的空间沉浸体验逐渐消退,家庭空间逐渐取代田野空间,压抑、失落之感侵入演员,形成“封闭空间”+疏离的人物情感。客厅空间与田野空间相比,显然前者更为狭小,演员之间本能的“亲近感”没有因为空间而变得更加紧密,相反在局促的空间中,演员之间的关系(包括外在的亲缘关系以及内在的心理距离)更为疏离。演员对于空间的体验来自舍皮琴科所营造的真实空间,透过真实空间对身体的训练形成初步的空间印象,这种印象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印象是暂时的、潜意识的,会随着空间的变化而逐渐模糊,这就需要导演多次对空间与人物关系进行强化,在不断更改与身体体验后,演员形成了对于空间情感的最终记忆。这便成了舍皮琴科表演艺术中完整的“社会主义”体验派表演记忆的核心。
二、内心体验:宗教寓言与自我感知
探究在东正教影响下的表演形式,一方面形成了舍皮琴科表演艺术中另外“一翼”:宗教感知与心灵救赎;一方面在感知情绪的过程中,演员通过体验东正教的神秘感与自我规劝属性建构个体表演风格。苏联拥有贯通亚洲与欧洲大陆广袤的土地,多样的地貌环境与冰冷而漫长的冬季困住了苏联人的活动范围。因而,苏联人形成了天然的孤独感与非理性的执念。与东正教不重视理性思辨、强调内在的心灵体验相契合,苏联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注重内心的感知与灵性的修炼,电影中无法规避的展现出东正教的救赎观念与内心准则:其一,广泛的彰显出东正教的受难与宽容、忍耐与虔诚的宗教内涵。无论是实验电影《电器之家》中在干涸的伏尔加河河畔祷告的老人,还是《上升》中在战争环境下受难的个体,演员在建构形象时无一例外达成了信仰的真实;其二,东正教对人类的关怀与普世价值成为舍皮琴科电影表达的参照系。舍皮琴科要求演员神态的“宗教”表达,即与宗教绘画、祷告实景相模仿的思辨式体验模型,他将演员放置在意志与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使得演员在面对极端的道德与个体困境中走向灵魂的自我完善。《上升》中,索特尼科夫却拥有比“耶稣受难”更为复杂的心灵纠葛。索特尼科夫与雷巴科夫在一次为滞留在沼泽的游击队员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遭遇德军袭击,索特尼科夫腿部中弹,而后两人不幸被俘虏,收留过他们的无辜的人们也被迫卷入了死亡的深渊。整部影片无疑是带有强烈的宗教寓言性质的,索特尼科夫即是无辜的受难者,又成了让他者无辜枉死的施害者。演员在诠释索特尼科夫时,舍皮琴科采取了摄影机“凝视”的状态,在演员枯槁的、45度仰望上帝的面容上,将救赎、牺牲的东正教寓言完美的诠释。这种隐喻与形式感不仅体现在索特尼科夫的面部微相上,还有被无辜绞死的老村长、妈妈以及犹太女孩。面对死亡,老村长眉头紧锁望向远方,演员显然对于人物死后的精神延宕进行了宗教式体悟,形成了坚定的殉国立场与忧虑的基督式拯救;同时,单亲妈妈的角色承受着双重的心灵困境:在死亡的边缘演员想的不仅是作为个体的恐惧,更多的是对于孩子的不舍以及对德军控诉;即使德军发现女孩的身高无法满足成人的绞刑绳索,随手拿了一个皮箱垫在女孩脚边,演员仍然很自然的站到了箱子上,这一细节有效地将女孩的状态与耶稣拯救的形式感相互文,在受难与拯救面前没有年龄、性别的区分;索特尼科夫的牺牲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演员的“牺牲”。在表演中,演员同人物共存亡,这既是剧中假定人物的最终宿命,更是演员在“救赎”与“牺牲”的灵魂体验后所呈现的表演诉求。俄国谚语很少区分罪行(crime)和罪(sin),他们几乎不用犯罪这个词,他们简单地称它为罪。而罪犯就是罪人,或者是不幸的人。演员在体验、表现“罪恶”或“不幸”时,往往从自身的行为准则出发,将内心的苦难与角色的苦难相结合。东正教认为没有经历受难的心灵是罪恶的,因而在舍皮琴科的电影中,演员通过导演对恶劣环境、黑暗现实的营造,将文本中的情感体悟连同宗教感知,透过带有仪式感的表演方式进行二度创作,并认为这便是演员对于人物体悟苦难、走向救赎的唯一通路。无论是《上升》中的宗教体验式表演,或是《电器之家》中宗教信仰的自我置换,演员在建构影片核心观念时,将东正教的仪式感与人物的行为准则相结合,完成导演架构的整体电影系统的同时生成了表演艺术的宗教体验模式。
舍皮琴科电影从空间环境体验入手,将电影中演员的模拟表演与身份体验作为研究基础,对宗教形式感与马克思唯物主义两者对立统一的探索,将演员放置于身体与精神的极限,在受难与拯救的双重精神状态下达成对于人类、社会的终极思考,最终形成舍皮琴科独特的“社会主义”体验派表演艺术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