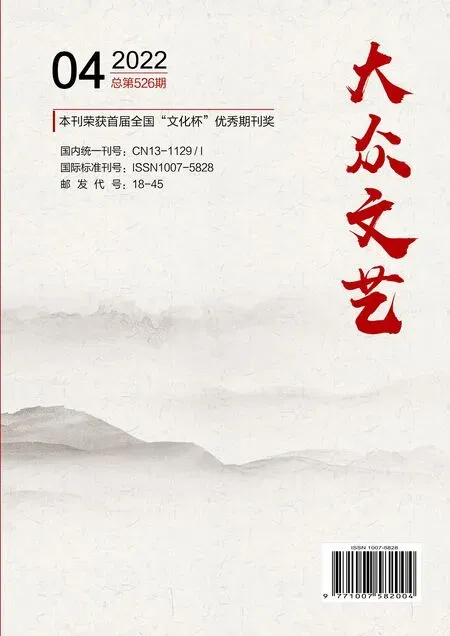参与式文化视角下的明星人设再生产过程探讨
李林静
(武汉理工大学,湖北武汉 430070)
一、导言
1.问题的提出
2018年节目《偶像练习生》的热播开启了我国造星新时代,各类选秀节目层出不穷,粉丝社群也因此不断扩展。截至2020年12月,新浪微博超级话题#蔡徐坤#拥有1181万粉丝,#易烊千玺#952万粉丝,#王一博#534万粉丝,粉丝群体地位与主体性伴随着人数扩张得以彰显,由松散的趣缘群体发展为强话语权团体,具备较强的组织力、传播力与造势力,拥有明星人设塑造的部分决策权。
粉丝作为具有创造性与能动性的主体,以明星原本对外形象及其作品、商务活动、社交关系等为素材原本,对明星的符号形象进行主观上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既可能是明星原本某些人设标签的强化,也可能是对明星人设的扩展。被粉丝群体加工后的明星人设以粉丝内容产出为载体,经由社交媒体高效而广泛的传播,在圈内掀起热度浪潮的同时,部分内容的“出圈”也改变着广大路人群体对明星的看法。
然而,这种再生产活动有时无法与明星利益方的发展方向相契合,粉丝再生产的明星人设与实际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矛盾,当明星外在表现与自身认知存在差异时,“违和”便成了大量路人与非核心粉丝的第一感知,明星人设崩塌的风险提高,同样不利于其未来发展。
粉丝群体的变化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在粉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粉丝群体作为“产消者”的地位与影响力越发突显。那么,粉丝以何为动力,又如何参与到明星人设的再生产过程中?这种再生产又会给明星利益方乃至于网络环境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笔者试引入詹金斯参与式文化的相关概念,对粉丝群体的明星人设再生产过程进行探讨。
2.文献综述
“人设”原指文艺作品中作者在人物家庭、外貌、性格、穿着、造型等方面的设定。随着和娱乐产业的发展,“人设”开始与造星联系在一起,演绎出虚构作品之外的明星人设。
我国学界关于明星人设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产生于造星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在翟天临、靳东等明星“人设崩塌”事件后,出现过一次集中讨论的浪潮。然而,此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星人设建构的伦理边界与人设崩塌后的社会影响上,价值观上均呈现对明星强行营销“假人设”行为的批判,并未对明星人设的建构过程进行详尽梳理与探讨。
标签设定鲜明的养成系明星的兴起带动了明星人设与粉丝相互作用研究的兴起,粉丝在明星人设建构中的能动性价值越发被学界认知。刘诣、汤国英在《生产、维持和崩塌:明星人设的三重逻辑》中指出明星人设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在进行角色实践前需要实现人设与粉丝满足、大众认可、自身能力足够承担三方平衡,并对人设崩塌后的社会风险进行了探讨,确定了明星人设地树立需要考虑粉丝群体喜好与粉丝预期相吻合的前提。於振鹏《符号消费与社会共谋:体育明星人设的生成、维持与崩塌》以体育明星为切入点对消费时代明星符号商品价值最大化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样表示泛娱乐化传播中社会角色期许与自我呈现趋同促成了明星人设的生产过程。刘怡《论网感化语境下青少年受众对影视明星人设的期待结构》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以青少年群体为主的受众群是明星人设塑造中的能动构成,明星为迎合受众期待对人设进行调整,进一步明确了粉丝群体对明星人设建构的影响力。
综合来看,在明星人设与粉丝群体相互关系的研究中,粉丝与明星利益方共同构建明星人设已成为共识,然而当下研究存在与粉丝经济现状相悖的两大问题:
其一,从人设建构与传播的时间跨度来看,明星人设会在不同的时间阶段进行扩展,如黄子韬成名后,以在微博中称《Fate》系列作品女主角之一的远坂凛为“老婆”为契机树立起“二次元”“型月厨”人设。然而,当前研究中的明星人设却异常死板,只在生产过程中为满足多方期许进行调整,忽视了明星人设进入社会实践后,传播过程中的一系列变化。其二,从粉丝群体身份上来看,粉丝也仅仅作为文化符号的消费者与助推者,却忽视了粉丝主动参与文化生产的过程,也与粉丝群体“产消者”身份的新变化不相符合。
综上所述,当下粉丝在明星人设制造及其传播中的作用应当被重新审视,其自主文化生产的能力亦应当被重新评固。在此,本文拟引用“参与式文化”的概念,从多个粉丝团中负责内容生产的用户人群入手,分析粉丝群体对明星人设再生产的实现方式和实践路径,并对这一文化再生产行为的边界进行探讨,以期为当下粉丝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多参考。
二、传播技术进步与参与式文化的发展
“参与式文化”由美国传播学家亨利·詹金斯提出,是迷社群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属性,是指以web2.0网络为平台,以全体网民为主题,以积极主动地创作媒介文本、传播媒介内容、加强网络交流为主要形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自由、开放、共享、交互的新型媒介文化样式。在詹金斯的描述中,粉丝群体一改传统社会认知中狂热偶像追随者和盲目信息接收者的形象,成了主动创作媒介文本、传播媒介内容的富有开放性的组织社群,他们围绕着自身热爱的流行文本,积极从事再生产活动。
诚然,参与式文化概念诞生距今已近30年,其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参考价值,传播技术的进步从创作和传播两方面为粉丝群体从事参与式文化提供动力。
1.新媒介环境和媒介技术拉低粉丝群体表达与创作的门槛
网络是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赋予了个人说话的“权利”,允许个人进行意见表达。同时,信息实现了实时的交互与共享,媒介话语权已不再完全由大众传媒把握,用户意见表达的门槛大大降低。同时,新媒体也为用户的参与提供了先进的工具,文化产品生产与制作流程和技术壁垒逐渐小节,粉丝群体可以运用各种软件进行内容创作,其文化参与能力达成了一次飞跃。
2.无尺度网络的扩展刺激文本大范围传播
传播路径的网状化是网络传播的一大特点,在网络中,信息不是沿着一条线性路径传播的,而是在进行着网状扩散,每一条信息在数字平台都可以借助网络从一个点扩散到一个面。用户创造文本可以通过网状传播路径实现大范围扩张,在粉丝群体中,以明星本人作为主线的信息很容易引发关注,参与创作的粉丝也更易于获得粉丝群体的集体认同,也为参与式的文化生产拓宽了路径。
三、人设的再生产的动机
“人设”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物化的形象”。在偶像工业时代,偶像最重要的作品事实上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以他本人为原型创造出来的、某种可被放置于亲密关系想象之中的形象。这一形象在官方经纪公司与粉丝的共同作用下得以确立,原始的人设文本由经纪公司提供,而粉丝群体则一方面通过圈内意见表达,另一方面以各类应援形式表达对这一人设形象的意见喜好,部分参与偶像人设建构的行为决策。再生产则是一种基于已成功生产建构出的偶像人设的二度重构,代入粉丝群体为主视角看,这种重构行为基于自我与社群两方面认同而产生。
1.作为认知主体的粉丝:自我价值的实现
弗洛伊德“投射”理论认为,投射是从别人身上发现自己的情感、想法或愿望的心理保护机制,粉丝群体往往希望在偶像身上寻找理想自我。迷群文化起源于对理想自我这一主观情感构成体的想象。某种意义上,偶像人设正是追随者心中的情感投射。
粉丝对理想自我的主观认知同样会作用于明星人设这一文化符号上。粉丝们往往会采用“情感现实主义”的立场,投射个人经历解读明星人设,并结合个人立场实现自身期望具象化,形成区别于明星原人设的形象。而代入自我讲述偶像的故事,或见证偶像获得成就,都会给自身带来强大的满足感与归属感,从而实现“自我认同”。
2.作为参与主体的粉丝:群体认同的争取
获得群体认同是粉丝群体参与人设再生产的另一动因。网络技术的进步使得粉丝的参与式创作更具交互特色。参与式文化认为,粉丝社群中的会员们建立起了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并通过身份认同、信息表达、信息传播等手段和方式共同创作出来的。因而,乐于创造文化与分享创作成果的个体更有可能与社群中的其他粉丝构建联系,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认同。
以新浪微博明星超话为例,当一个粉丝在超话中发帖时,会获得其他粉丝的及时反馈,通过转发、评论,更可以看到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从而实现社会关系的建构和地位的获取。因此,在粉丝社群中,产出型的粉丝往往拥有极高的声望地位,在社群中被敬称为“老师”“太太”,虽然他们往往不会直接参与粉丝社群的管理和决策,其意见表达在整个社群内都显得举足轻重。
四、参与式文化与人设再生产行为:创造与传播
1.创造:文本盗猎与艺术加工
盗猎文化与参与式文化一脉相承,指受众将作品中感兴趣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直接“掠夺”走,作为自我阐释和二次创作的原材料。明星人设的再生产便是一种基于盗猎的创造,盗猎的主要对象为明星的原人设,粉丝也会有选择地掠夺包括明星的社会关系、商务活动、作品等一系列暴露于社交媒体上可供收集和传播的话语。
当媒体所提供的内容不足以令粉丝获得精神满足,或某些内容可起粉丝群体的联想时,富有主观能动性的粉丝群体便拥有了文本盗猎的动力,明星人设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加工改造,成为承载着粉丝群体期待与精神追求的造物。这种盗猎,既可能是对明星方所发布信息的直接主观解读,也可能是某种艺术化的创作。
主观解读经纪公司发布明星相关信息的盗猎行为往往只作用于单一信息,粉丝群体带着浓烈的情绪与表达欲望,以用户参与的形式对信息的意义进行牵引扩充,由此联想到明星本人,从而实现对其人设的强化或丰富。如1月27日,超话#王一博#下,达人@YIBO加油站|王一博发表了【2020,愿你更好】超话贴,对王一博出道以来呈现的各种细节进行了复盘与解读,作者以“酷惯了的人,突然流露出许久未曾流露却原本人人都知的温柔时,真的好想让人流泪”一句作结,在王一博“酷盖”人设之外,为其添加了天生温柔外冷内热的人设标签。为明星补足其对外形象的不足,使“人设”这一媒介人格更加立体细腻,更适宜用于创造亲密关系的想象,达到固粉目的。
利用文本盗猎呈现人设再生产的最显著创作形式便是同人作品,即利用原人物角色进行二次创作,在新的情节、社会关系乃至于世界观下扩充人物形象,以满足个人想象与期待,创作中也使得明星人设得到的再度的扩展。社交媒体创作环境相对自由,此种创作得到大量追捧,甚至部分明星也会主动参与到这次“再生产”的狂欢中,给予创作者肯定的同时也激起了观看者的热情。
在综艺《说唱新世代》选手衍生同人视频《【禹翅】夏之禹×鱼翅|夏头人和他的芭比娃娃》中,创作者盗猎说唱歌手夏之禹和鱼翅的形象,并将众多文本元素进行重新加工排列,对两人的亲密关系进行阐释。至于其对明星人设再生产的影响,以夏之禹为例,从视频的弹幕和评论区中可以发现,“你好爱他”“文化绿洲的惺惺相惜”“他张开那么久的手臂就等他过来一个拥抱”等基于视频作品情节的解读性话语屡见不鲜,使得夏之禹“自在表达的chillboy”形象更加立体,有态度的夏之禹终于在另一个“文化绿洲”前翻了车,自在也同时有了牵绊,成了这个“怪人”难得而唯一的浪漫。
2.传播:内部欢腾与印象覆盖
当某一再生产内容得到粉丝社群的认同时,共享与传播便被提上了日程。参与式文化视角下的粉丝群体是整个网络中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十分乐于创造与共享,并在每一次转发中添加个人的意见表达。产出型核心粉丝作为人设再创造的主体,其创作的图文视频等文化作品可以十分轻易地使人实现情感代入并产生认同,实现以理解为前提的圈内传播。这种粉丝群体“内部的狂欢”,使得经盗猎改动后的明星人设有了相当的认知度,甚至在某些情境下覆盖掉明星原人设在粉丝群体心中长久存在。
五、人设再生产的影响
现代网络网状化传播的特性和透明化的信息呈现使得对于明星人设的再生产活动不可能永远是粉丝小圈子内部的作业与集体欢腾,当某一作品热度过高,“出圈”便提上了日程。作品与新人设将被明星经纪公司,甚至于粉丝圈层之外的广大网络用户所认知,产生种种连锁反应。
1.明星人设的调整
粉推经济时代粉丝群体已经拥有了明星相关事物的部分决策权。粉丝不仅能够参与明星人设的生产,在“人设”这一有成长性的文化符号进入传媒领域传播的过程中,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发展方向。当明星经纪公司在粉丝自主的人设再生产过程中意识到粉丝群体的喜好时,将对其人设形象进行些许调整,渐渐使得明星所表现出的媒介形象与粉丝的期望相拟合。当下大部分参与过选秀综艺打投活动,有过相当经济和情感付出的养成系偶像的粉丝,往往期待在投入后获取回报的“双向奔赴”式的相互关系,无怪乎大部分明星经纪公司都在通过多种方式塑造并强化着明星的“宠粉”人设。
2.明星影响力的扩大
文化作品,尤其是自主创作同人作品的传播门槛相较于粉圈内部的话语文本将大大降低。文学性语言取代隐晦难懂的圈内用语,原创乃至于架空的情节大大减少了因对明星不了解造成的区隔感。作品的火爆在一定程度上可带动明星暴露于大众视野,扩大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实现在粉丝市场越发细分,粉丝圈层越发多元的当下一次难得的“出圈”。
3.人设崩塌的隐患
然而,再生产的明星人设也存在着一定隐患,当某一再生产人设传播速度过快使得经纪公司无法及时调整策略,或与原人设差异过大,很容易在两种媒介形象之前产生割裂与违和感。本已沉浸于自主加工后的明星人设给自身带来满足与愉悦的粉丝突然被事实惊醒,再看到与自身想象不甚符合的原始人设时,也容易产生失落不满等情绪。部分激进化的粉丝甚至会以明星失去本心为由脱粉回踩,尽管责任并不全在明星利益方,明星却要为一个并不在计划方案内的二创人设负责,这一结果也不可不谓荒诞。
六、总结与反思
综上所述,当下粉丝群体作为参与式文化的主体已经拥有相当的自主性,粉丝群体可以通过盗猎文本的形式实现明星人设的再生产,并在圈层内部高速传播。虽然以参与式文化实现明星人设的二次创作可以为明星人设带来更多调整参考,在其破圈的同时也带来了人设“被动崩塌”的隐患。
诚然创作自由属于当下社会所提倡的媒介表达形式,作为明星人设生产的参与者与决策者,粉丝也有对“人设”这一话语进行建构与修改的权力。然而,为了保证明星的长久发展和圈层的内部稳定,粉丝群体的人设再生产活动也应该抱持某一与明星方达成共识的边界与限制,粉丝应当拥有对明星人设进行再生产创作的权力,而当其与明星原本人设或明星发展方向发生矛盾时,最终的解释权力应当由媒介官方所有,由此尽量减少因为人设差异而造成的矛盾与割裂感,实现明星人设参与社会实践长久有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