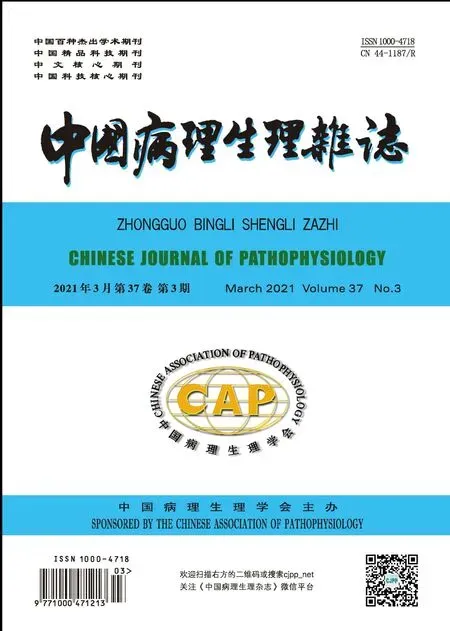巨噬细胞在不同组织再生中的研究进展*
王伦平, 陈 蕊, 严金川, 刘培晶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江苏镇江212001)
组织再生是指身体剩余的健康细胞增殖并替代受损丢失部分的过程[1]。实现组织再生对维持机体的正常结构和功能至关重要。不同组织的再生能力因物种、组织部位和生长发育的阶段的不同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譬如,非哺乳脊椎动物心脏损伤后具有高度再生能力,而成年哺乳动物心脏受损后再生能力有限[2]。再生能力受限的组织在损伤后多表现为纤维化瘢痕修复,但纤维化进展可导致组织的结构和功能障碍,进而继发多种临床疾病。干细胞移植是当前最重要的再生疗法,但是具有干细胞存活率低、分化不成熟等缺陷,移植后易致心律失常、肿瘤发生等风险增加。实现组织再生是医学领域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3]。巨噬细胞广泛分布在全身组织中,是诱发机体炎症免疫反应的一种关键细胞,主要包括胚胎卵黄囊来源的巨噬细胞(embryonic yolk sac-derived macrophages,YSDM)和骨髓源性单核细胞分化而成的巨噬细胞(macrophages derived from bone marrow-derived monocytes,BMDM)两种[4-5]。生理条件下,人体组织中长期驻留的巨噬细胞主要来源于卵黄囊、胎肝和造血干细胞;组织损伤后,炎性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前体)在趋化因子和黏附分子引导下可从循环中募集至损伤部位并分化为巨噬细胞。巨噬细胞主要包括经典的M1 促炎型巨噬细胞和M2 抗炎型巨噬细胞(M2a、M2b、M2c 及M2d 四种亚型)。此外,巨噬细胞还可以分化为Mhem、M4、MOX及根据细胞表面标志物表达差异而定义的其他多种亚群。巨噬细胞具有高度可塑性,在不同刺激下可以分化为特定的表型[6-7]。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对巨噬细胞通过诱发免疫反应促进组织损伤的表型、形态和机制的观察和描述上。随着再生医学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的逐步发展,近期研究发现,巨噬细胞在促进心脏、肝脏、肾脏、肌肉、神经等不同组织再生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同病理微环境下巨噬细胞通过分泌再生相关细胞因子、极化为不同表型甚至转分化为其他细胞类型调控组织再生。不同损伤模型中巨噬细胞耗竭会引起相应组织器官再生受阻。为此,探索再生过程中的巨噬细胞的表型及作用机制有助于为组织再生障碍所致疾病开发新的治疗策略。
1 巨噬细胞与心脏再生
众所周知,成年哺乳动物的心脏再生能力有限,其心脏损伤后多表现为纤维化重塑,但是非哺乳脊椎动物和部分新生哺乳动物心脏损伤后具有明显的再生能力。已观察到新生小鼠、斑马鱼和蝾螈的受损心脏可以完全再生[8]。探索心脏再生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细胞和机制有助于为开发人类心脏再生能力提供理论基础。研究发现,巨噬细胞在心脏再生中发挥关键作用,它可以通过触发炎症免疫反应、促进血管新生、直接或间接调控细胞外基质蛋白合成等多种途径促进心脏再生[9-11]。
炎症反应已被诸多研究证实有助于心脏再生。巨噬细胞是参与心肌梗死后炎症反应的一种主要细胞类型,其可以通过触发炎症反应调控心脏再生。受损心脏中巨噬细胞主要包括心脏胚胎源性驻留巨噬细胞和外周单核细胞分化而来的巨噬细胞。研究表明,新生小鼠在心脏受损后通过选择性扩增心脏中的MHC-IIlowCCR2-驻留巨噬细胞产生微小的炎症反应,诱导血管生成和心肌细胞增殖,促进心脏再生;而成年小鼠受损心脏主要招募MHC-IIhighCCR2+巨噬细胞,触发持久的炎症反应,导致心脏纤维化[12]。进一步研究发现,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MCP-3、趋化因子(C-X-C 基序)配体1[chemokine(C-X-C motif)ligand 1,CXCL1]、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等趋化因子和炎症相关因子在MHCIIlowCCR2-驻留巨噬细胞中表达极低,而在MHC-IIhighCCR2+巨噬细胞中高表达。靶向微调巨噬细胞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可能有助于受损心脏再生。此外,利用选择性CC 趋化因子受体2(CC chemokine receptor 2,CCR2)抑制剂阻止成年小鼠受损心脏募集单核来源的CCR2+巨噬细胞,同时保留CCR2-驻留巨噬细胞,结果显示心脏受损区域的炎症减轻,冠状动脉微血管生成密度增加[10]。这提示CCR2 抑制剂有望用于临床心肌梗死的靶向治疗。有趣的是,另一项研究发现心脏过表达CCL2(CCR2 的配体)诱导CCR2+单核巨噬细胞大量浸润可以促进心脏血管生成,改善心肌梗死后左心室扩张和功能障碍[13],提示CCR2+巨噬细胞可能在心脏损伤修复中发挥双重作用,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明确。
巨噬细胞还可以通过调控心脏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的生成促进心脏再生。ECM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结构框架,同时参与生化信号和电信号传递[14]。此外,研究发现斑马鱼和蝾螈心室遭受冷冻损伤后形成特殊的ECM 胶原网络,该网络允许活化增殖的心肌细胞迁移并参与受损心肌壁的修复,从而促进心脏再生[15]。Godwin 等[9]证实巨噬细胞可以通过活化成纤维细胞、调控ECM 而促进蝾螈心脏再生。当巨噬细胞耗竭后,受损心脏中的成纤维细胞数量显著减少,且ECM 的合成、重塑及交联等特征发生明显改变,受损区域形成高度交联的纤维化瘢痕,引起心脏再生受阻。最新研究发现巨噬细胞还可以通过转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样细胞自主沉积胶原,促进斑马鱼受损心脏再生[11]。另外,对小鼠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心脏受损后的巨噬细胞进行RNA-Seq 基因转录分析发现,新生小鼠和成年小鼠心肌损伤后,巨噬细胞调控ECM 相关基因的表达,以实现再生修复过渡到纤维化修复。以上研究结果证实巨噬细胞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调控ECM促进心脏再生[11]。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缺血/再灌注损伤引起心肌细胞死亡中,早期ECM 的快速沉积有助于防止心脏破裂,但ECM 过度沉积则会引起心脏纤维化和心力衰竭。进一步明确巨噬细胞调控ECM 促进心脏再生或心脏纤维化的差异有助于为心脏再生治疗提供新的治疗思路。
2 巨噬细胞与肝脏再生
肝脏在遭受部分切除或毒素损伤后具有高度的再生能力[16]。肝脏再生过程中残余部分实质细胞和非实质细胞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发生增殖并替代丢失组织,从而实现肝脏再生[17]。库普弗细胞和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约占肝脏细胞总量的20%,在肝脏再生中发挥重要作用[18-19]。
库普弗细胞是肝脏的驻留巨噬细胞,位于肝细胞周围肝窦腔中,可以通过旁分泌重要的生长调节介质诱导肝细胞增殖,在肝脏再生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研究表明,库普弗细胞在肝脏部分切除术后72 h 达到增殖高峰[16],它通过上调影响细胞周期的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及增殖性细胞因子TNF-α 和IL-6 的表达促进肝实质再生。接受肝脏部分切除的小鼠在耗竭库普弗细胞后,肝组织中NF-κB 的活性丧失,同时血清中TNF-α 和IL-6 浓度下降,增殖标志物PCNA 和细胞周期特异性蛋白cyclin B1 表达下调,导致细胞增殖延缓,肝脏再生受阻[4,20]。单核来源的巨噬细胞是肝再生过程中的另一 个 关 键 角 色。Graubardt 等[21]的 研 究 表 明,由Ly6Chigh单核细胞分化而来的Ly6Clow巨噬细胞在扑热息痛所致药物性肝损伤中通过减少产生活性氧的中性粒细胞浸润,加速炎症消退,促进肝脏再生;在Ly6Clow巨噬细胞缺失的情况下,中性粒细胞大量聚集,产生活性氧,触发严重的炎症反应,从而导致肝损伤;同时,该研究发现选择性消融Ly6Chigh单核细胞和Ly6Clow巨噬细胞后肝脏再生受损。
此外,一项针对药物性急性肝损伤的最新研究发现,使用CCL5 抑制剂或CCL5 中和抗体诱导巨噬细胞从M1 表型向M2 表型极化可以促进肝实质再生,从而显著减轻扑热息痛引起的急性肝损伤[22]。这表明CCL5抑制剂和CCL5中和抗体有望用于药物性肝损伤的临床治疗。同时,进一步明确肝脏损伤后促进巨噬细胞向M2 表型极化的相关机制可能为急性肝损伤的治疗提供新的策略。另一项关于慢性肝损伤的研究发现,肝细胞死亡后巨噬细胞可以吞噬坏死细胞碎片使Wnt3a 表达上调,并进一步激活肝祖细胞(hepatic progenitor cells,HPC)中经典的Wnt 信号,诱导HPC 向肝细胞分化,促进慢性肝损伤的肝脏实质再生[23]。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巨噬细胞可以通过Wnt3a 信号途径上调Numb 表达,从而抑制Notch 信号,使HPC 向胆管细胞分化受阻。由此可见,巨噬细胞所涉及的不同信号通路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正确调控肝脏再生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不同类型巨噬细胞在肝脏损伤后再生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巨噬细胞向M2 表型极化或选择性诱导Wnt3a 表达为肝损伤治疗提供了新的治疗策略。另外,目前关于巨噬细胞促进肝脏再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核细胞源性巨噬细胞或库普弗细胞,但是巨噬细胞具有高度异质性,是否存在其他细胞转分化为巨噬细胞并促进肝脏再生尚无文献报道。
3 巨噬细胞与肾脏再生
肾脏细胞在遭受缺血/再灌注损伤或毒性损伤后仍具有一定的恢复能力,这依赖于肾小管上皮细胞根据损伤性质和部位再生[24]。巨噬细胞是浸润受损肾脏的一种主要细胞类型[24],在肾脏再生中发挥重要作用。明确巨噬细胞调控肾脏再生的相关机制,有助于为治疗急慢性肾损伤提供新的治疗手段。
巨噬细胞可以通过触发Wnt 信号驱动肾脏再生。肾脏损伤后,巨噬细胞中Wnt 的配体Wnt7b 显著上调,通过激活Wnt 通路使肾小管上皮细胞克服G2细胞周期阻滞,引导细胞进展、基底膜修复和肾小管再生,促进肾脏修复再生。而巨噬细胞消融后,肾上皮细胞中经典的Wnt 信号通路反应明显减低,肾脏修复和再生能力下降。研究发现,当巨噬细胞中Wnt7b缺失后,肾小管上皮细胞的正常再生受阻,血浆肌酐值无法恢复正常,肾脏修复能力减弱,而在注射Wnt 通路激动剂Dkk2 后肾脏修复能力显著增强[25]。目前Wnt7b+巨噬细胞调控肾脏再生的具体机制及其是否参与调控其他组织器官再生尚待进一步研究。靶向上调巨噬细胞中Wnt7b 可能为促进人类组织器官损伤修复提供新的治疗模式。
巨噬细胞还可以通过分泌脂质运载蛋白2(lipocalin-2,Lcn-2)促进小鼠肾脏损伤后肾小管上皮细胞再生[24]。肾小管损伤后,凋亡细胞分泌的鞘氨醇-1-磷酸(sphingosine-1-phosphate,S1P)促进巨噬细胞产生并分泌大量Lcn-2,后者可结合并转运铁至上皮细胞中,促进肾脏上皮细胞增殖,诱导肾小管再生[26];通过小鼠尾静脉注射过表达Lcn-2的巨噬细胞可以促进肾小管上皮细胞增殖,而该过程能被Lcn-2中和抗体所阻断[27]。此外,Rota等[28]发现,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通过归巢到肾脏介导巨噬细胞向M2抗炎表型极化,进而促进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的肾脏再生。这些研究表明,促进巨噬细胞向M2表型极化或调控巨噬细胞Lcn-2的表达可能有助于阻止或延缓急性肾损伤。
总之,巨噬细胞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在肾脏再生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关于巨噬细胞调控肾脏再生的文献报道较少,进一步研究巨噬细胞诱导肾脏再生的相关机制可能对急慢性肾损伤及其相关并发症的治疗有所启迪。
4 巨噬细胞与周围神经再生
周围神经系统(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PNS)在遭受损伤后,其轴突再生和再髓鞘化能力受限[29-30]。因此,目前临床上多采用缝合重建技术促进受损周围神经修复,然而由于缝合线无法完全密闭神经导致重要物质漏出,且对操作者技术要求极高,最终受损部位形成纤维化瘢痕,难以恢复正常功能,因而临床预后差[31]。探索周围神经再生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机制有助于为神经损伤开发新的再生疗法。周围神经横切损伤后,远端神经轴突与胞体分离,远端轴突通过沃勒变性发生快速退化,随后髓鞘卵状体崩解产生大量髓鞘碎片,神经元胞体中再生相关基因表达上调以促进近端轴突再生,最后再髓鞘化以完成神经再生;该过程中沃勒变性延迟、髓鞘坏死碎片清除缓慢或不足会抑制轴突再生[32-33]。巨噬细胞可以通过清除髓鞘碎片、分泌生长因子、诱导血管新生等促进轴突再生和再髓鞘化,在周围神经再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明确巨噬细胞促进周围神经再生的相关机制可以为靶向巨噬细胞治疗受损神经提供新的治疗方略。
周围神经损伤后,巨噬细胞大量募集至损伤区域,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周围神经再生。Forese等[29]发现前列腺素D2 合成酶(L-prostaglandin D2 synthase,L-PGDS)可以通过非细胞自主机制使巨噬细胞获取合适的吞噬能力以清除髓鞘碎片,利于轴突再生和髓鞘再形成。同时巨噬细胞还可通过调节施万细胞的吞噬能力而清除碎片,促进轴突再生。最近,有研究表明巨噬细胞可以通过诱导新生血管产生而促进周围神经再生。受损周围神经再生过程中两神经残端实现重新连接必需具备一种神经桥组织,随后由施万细胞集体迁移,引导再生轴突过桥,从而促进PNS 再生。巨噬细胞响应缺氧环境而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A,VEGF-A),通过诱导桥区产生一种特殊的极化新生血管而缓解缺氧,施万细胞则在该血管的引导下集体定向迁移并介导再生轴突过桥。扰乱巨噬细胞诱导的新生血管组织,会导致细胞定向错误而整体迁移周围组织中,再生轴突过桥失败,阻碍正常的神经修复[34]。此外,巨噬细胞通过向M2表型极化促进Ⅵ型胶原蛋白分泌而调控周围神经再生,Ⅵ型胶原蛋白进一步正反馈诱导巨噬细胞极化,从而促进神经再生。进一步在动物模型研究中发现,与对照组小鼠相比,Col6a1-/-小鼠Ⅵ型胶原的组装和分泌受阻,导致M2极化受阻,周围神经损伤后再生延迟。而移植野生型骨髓细胞后周围神经再生活力恢复[35]。另有研究发现,氧化半乳糖凝集素1 可以促进巨噬细胞分泌促轴突生长因子和促施万细胞迁移因子,促进轴突再生和施万细胞迁移[36]。
综上所述,巨噬细胞在周围神经再生中发挥多种功能。目前巨噬细胞促进周围神经再生的具体机制尚不完全明确,相关研究仍有待开展。促进巨噬细胞募集并适时向M2极化偏斜、增强巨噬细胞吞噬能力、正确诱导极化血管化可能为治疗外周神经受损相关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思路。
5 巨噬细胞与骨骼肌再生
骨骼肌受损后具有显著的再生能力[37],其再生能力主要依赖于卫星细胞(satellite cells)的增殖和分化。激活的卫星细胞一部分转化为成肌细胞,后者通过迁移、彼此接触和融合形成肌管,新形成的肌管生长并化为成熟的肌纤维,实现骨骼肌再生。巨噬细胞是参与骨骼肌损伤后触发炎症免疫反应的一种关键细胞,可以通过活化卫星细胞、促进血管新生等多种途径促进骨骼肌再生[38]。
众多研究表明,M2型抗炎巨噬细胞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促进骨骼肌再生。Jiang等[38]发现,大麻素2型受体(cannabinoid receptor subtype 2,CB2R)介导巨噬细胞向M2表型极化有利于小鼠骨骼肌再生;敲除CB2R后,M2 型极化受阻,肌源性调节因子MyoD 和myogenin 表达下调,卫星细胞活化减少,这将导致新生的中央核肌管的数量显著降低,并且再生肌纤维体积显著缩小,导致坏死性肌纤维和炎性细胞浸润显著增加。Zhang 等[39]的研究显示,内皮细胞在缺血期间通过糖酵解产物启动乳酸盐穿梭,使巨噬细胞向M2 型极化并分泌大量VEGF,强化血管生成正反馈回路,提高血管生成密度,促进肌肉血运重建,诱导骨骼肌的肌源性祖细胞(myogenic progenitor cells)增殖和分化,从而促使肌肉再生。McArthur等[40]的研究表明,骨骼肌损伤后巨噬细胞通过上调膜联蛋白A1(annexin A1)表达激活FPR2/ALX 受体和下游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信号,促进巨噬细胞向M2 型极化偏斜,抑制炎症反应,促进肌肉再生。Iavarone 等[41]发现,骨骼肌损伤后CD206(M2标志物)阳性巨噬细胞中Cripto表达上调并部分抑制内皮细胞向间充质细胞转化(endo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ndMT)促进血管重塑,提升肌肉再生潜力。髓系细胞的Cripto基因消融后,CD206+细胞数目减少,EndMT明显增加,进而干扰血管重塑,肌肉再生能力显著下降。此外,研究发现间充质干细胞和细胞外基质也可通过调控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而促进肌肉再生[42]。
以上研究结果为M2型巨噬细胞促进骨骼肌再生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适时调控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可能为肌肉再生治疗带来更高的临床收益。此外,有部分研究表明,骨骼肌损伤后巨噬细胞可以通过上调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PPARγ)[43]、机械生长因子(mechano growth factor,MGF)[44]、ADAMST1(a disintegrin-like and metalloproteinase with thrombospondin type 1 motif)[45]、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1,IGF-11)[46]等的表达促进骨骼肌再生,但具体作用途径尚为完全阐明。
6 结语与展望
巨噬细胞是由经典的M1型和M2型为主的多个亚群组成的免疫细胞,在人体组织中广泛分布,通过表型转换能有效适应微环境的变化。巨噬细胞激活后可分泌多种趋化因子、炎症介质及生长因子,通过调控ECM 合成、促进血管重塑及血管新生、调节邻近细胞增殖分化而参与心脏、肝脏、肾脏、肌肉、神经等组织的再生。目前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巨噬细胞具有促进组织损伤和再生的双重作用,其具体作用取决于参与反应的细胞类型及环境因素。受损组织中M1 型巨噬细胞可分泌大量的促炎因子参与炎症反应,其持续反应可加重组织损伤;巨噬细胞由M1型向M2型极化往往有助于控制炎症反应,增强细胞的吞噬能力,促使血管新生和重塑,促进各种组织再生。其他类型巨噬细胞在不同组织再生中发挥的作用是否一致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组织再生是一个由多细胞、多因素共同参与的复杂动态调控过程。巨噬细胞在炎症免疫反应及组织再生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巨噬细胞具有高度异质性、可塑性和功能多样性。不同起源的巨噬细胞可以根据病理生理微环境的不同调整自身表型、形态和功能,参与组织损伤和促进受损组织再生。巨噬细胞在损伤组织中的动态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表型,但目前缺乏特异性的分子标志物对各表型的巨噬细胞加以准确分类。谱系示踪、细胞过继转移研究及RNA-Seq 转录分析等新技术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再生相关巨噬细胞的具体表型及其涉及的相关作用机制,以揭示组织器官再生的本质规律,为人类开辟新的再生疗法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