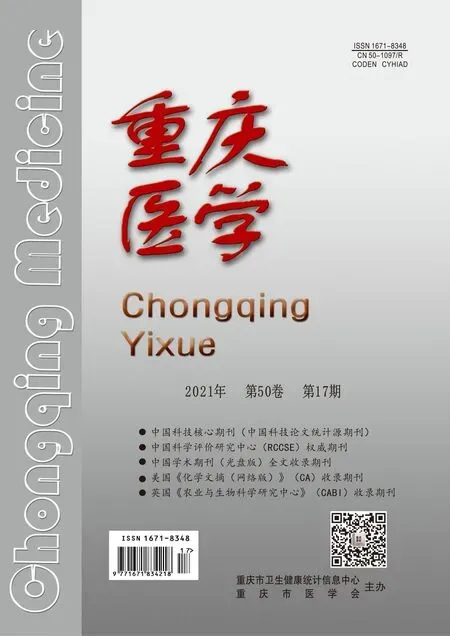儿童气质的研究进展
孙艺凡 综述,刘俊宏 审校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日间外科病房/儿童发育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儿童发育重大疾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重庆 400014)
随着医学模式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渐被社会-生物-心理医学模式取代,人们逐渐意识到从心理学的角度观察疾病的原因和变化的重要性[1]。气质是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表现在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力特征方面(如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指向性等)。近年来在相关医学领域,对儿童气质的重要性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现综述如下。
1 气质理论
1.1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气质理论
古希腊哲学家EMPEDOCLES(公元前495-435年)提出“四根说”(空气、火、水、土),认为人的心理特征不同是由于身体“四根”的配合比例不同。古希腊著名医生HIPPOCRATES在此基础上提出“四液说”,将气质分为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抑郁质。罗马医生GALEN最先提出用拉丁语“Temperameteum”一词来表示气质。
1.2 我国古代气质理论
《黄帝内经》中提出5种气质类型: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孔子的气质说把人分为“狂”“狷”“中行”3类;宋明理学家张载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任性二重说,提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认为气质之性是因人而异的。
1.3 西方早期气质理论
19世纪初,前苏联生物学家巴甫洛夫(1849-1936年)首次提出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的概念(兴奋型、活泼型、安静型、抑制型),高级神经活动的反射学说被认为是气质类型的生理基础。
1.4 现代儿童气质理论
现代儿童气质的研究在1956年由美国心理学家THOMAS和CHESS等发起,他们在Allport研究情绪的基础上采用交谈和问询法,数年间定期随访研究对象的母亲,基于大量资料总结出了一套理论。他们从9个维度对儿童进行追踪研究,包括:活动水平、节律性、趋避性、适应性、反应强度、反应阈、情绪本质、持久性和注意分散度。根据这9个维度,将气质分为3种类型:容易型、困难型、迟缓型,并指出个体气质不仅受到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还受内在的生物因素的影响[2]。
在此基础上,CLONINGER提出4种气质类型:探求新奇性(novelty seeking)、回避伤害性(harm avoidance)、奖赏依赖性 (reward dependence) 和坚持有恒性 (persistence),其研究指出气质类型分别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多巴胺、5-羟色胺及去甲肾上腺素有关。因此,神经递质基因成为气质遗传学研究中的首要候选基因,这为研究气质的生物学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3]。
此外,PLOMIN还通过双生子研究发现,个体的情绪性、活动性和社交性是在婴儿期就出现的气质特征,这些气质特征是持续稳定的并可以遗传至后代。遗传因素对成人气质特征的影响很小,而儿童期的气质特征主要受遗传因素的影响[4]。
2 气质的影响因素
2.1 遗传、性别因素
多项双生子研究发现,儿童期气质差异主要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气质维度的遗传度一般为30%~50%,同卵双生子的同病率大于异卵双生子[5]。国内一项关于学龄期双生子的气质研究发现,女童活动水平、节律性等部分气质维度的遗传度明显高于男童[6]。
2.1.1多巴胺系统
多巴胺D4受体基因的第三外显子区含有一段48 bp的可重复序列[7]。以色列的一项针对12个月龄婴儿的研究发现,有多巴胺D4受体长重复片段基因的婴儿会表现出更多的负面情绪和多动行为。但LAKATOS等对高加索人群12月龄婴儿的研究显示多巴胺D4受体基因多态性与儿童气质无关。EBSTEIN等在犹太人群中进行的研究发现多巴胺D4受体基因的可重复序列多态性与外向性及探求新奇性类型相关。但在高加索、瑞典和韩国人群中进行的几项研究提示,多巴胺D4受体基因的可重复序列多态性与外向性及探求新奇性类型无关。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研究方法、研究人群、年龄、性别及气质人格量表的使用不同有关。另有研究发现多巴胺D2和D3受体基因多态性与探求新奇性类型相关[8]。
2.1.25-羟色胺系统
5-羟色胺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其转运体启动子区有一段44 bp的可重复序列(5-HTT gene linked polymorphism region,5-HTTLPR),内含子区存在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多态性(VNTR)。研究发现,5-HTTLPR与易怒、焦虑、恐惧、避免伤害等有关,而内含子区基因多态性与气质无关[9]。GILLIHAN等在高加索人群中进行的研究示5-HTTLPR与人格5因素量表中的外向性明显相关。而GUSTAVSSON等在高加索人群中的研究结果则显示5-HTTLPR基因多态性与神经质无关。这一研究结果的差异或许是由于研究中使用的人格量表不同所致,尚需进一步研究[8]。
2.1.3泛素特异性蛋白酶46(ubiquitin-specific protease 46,USP46)基因
泛素-蛋白酶体途径(ubiquitin proteasome pathway,UPP)是细胞内一个重要的蛋白质降解调控系统,通过对底物蛋白的泛素化和蛋白酶体降解参与调控细胞周期、基因转录等过程,由多种泛素结合酶和去泛素化酶调控[10-11]。研究表明,人类USP46基因具有去泛素化酶活性,小鼠USP46基因突变(第92号赖氨酸缺失)导致酶活性的改变是突变小鼠(MT小鼠)在悬尾实验和强迫游泳实验中不动时间缩短的主要原因[12]。泛素化是影响突触发育和功能的关键步骤,USP46基因参与调控大脑兴奋性突触的传递,与大脑的功能密切相关[13]。一项在557名韩国健康人群中进行的研究发现,通过对USP46基因中rs346005、rs2244291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基因分型,结果显示USP46基因多态性可能与气质特征有关[14]。以上结果为进一步研究气质相关的生理学基础提供了新的方向。
2.2 母亲情绪及孕期睡眠情况
母亲的情绪在儿童的情绪与行为发展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母亲表达负面情绪多则孩子更易出现焦虑等情绪[15]。母亲抑郁的婴儿往往有较低的活动水平,坚持度和生活规律性更差,对外部的环境和陌生人表现退缩,环境改变后不能适应或适应缓慢,消极情绪的婴儿使母亲更加抑郁[16]。一项在日本进行的研究记录了103 099例孕妇的睡眠情况,结果显示母亲在孕期睡眠不足6 h,婴儿往往会出现强烈的哭泣(RR=1.15,95%CI=1.09~1.20),这表明母亲孕期的睡眠问题与婴儿气质有关[17]。
2.3 儿童出生情况
儿童出生时的状况对学龄前儿童情绪反应、对新鲜刺激的适应性有一定的影响。早产儿与足月儿气质类型存在差异,早产儿中困难型、中间型、迟缓型所占比例较高[18]。研究表明早产儿存在大脑部分区域发育不成熟或有损伤,部分早产儿出生时有呼吸窘迫综合征等并发症,早产儿由于受到更多侵入性操作导致更多的疼痛暴露使其应激激素调节产生变化等,这些因素与其易产生更多消极情绪及更不容易调节情绪等气质特征相关,增加了未来出现行为问题的风险[19]。早产、低体重儿具有节律性差,适应性、注意力低的特征。黄美琳等[20]对269例足月单胎新生儿进行了1年随访,结果显示自然分娩的婴儿中,困难型所占比例明显低于剖宫产分娩的婴儿(P<0.05),且在有出生窒息史和胎盘早剥的婴儿中,气质类型以困难型居多。除此之外,出生时感染、缺氧、黄疸、硬肿、酸中毒都和气质类型有关[21]。
2.4 家庭因素
父母亲性格特点、家庭结构、家庭收入和父母的教养方式等因素对儿童气质均有影响。一项父母产后抑郁与婴儿气质的相关性研究显示:父母均有抑郁和仅母亲有抑郁均是婴儿抚育困难型气质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3.92(95%CI:1.38~11.12)和3.99(95%CI:2.11~7.54)[22]。父母的教养方式影响儿童的气质。研究显示,积极的教养方式,儿童气质愈偏向易养型、中间偏易养型;而儿童的消极情绪也能够调节父母的教养方式[23]。易养型儿童父母对孩子的关心理解程度较启动缓慢型和难养型高;三代同堂的家庭中难养型儿童比例较大。还有研究发现,邻里或家庭社会地位较低的儿童往往具有较低的社交能力、较高的反应性和较低的持续性,且这些联系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而家庭收入与儿童的情绪性、注意分散度、节律性等无明显相关[24-25]。
3 气质的评价方法
气质的评价方法很多,如访谈法、问卷法、观察法和实验室方法(如生理学测量、脑电技术等),目前主要采取问卷法。在众多的测评方法中,CAREY和MCDEVITT等依据 THOMAS和CHESS等的“儿童气质理论”发展出的一系列问卷是临床中最常用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包括《幼婴气质问卷》《婴儿气质问卷》《1~3岁幼儿气质问卷》《3~7岁儿童气质问卷》《8~12岁儿童气质问卷》,共5套。
气质与儿童疾病之间有一定影响,不同的气质特征与疾病发生之间存在关联性,如活动水平高、节律性差,患儿更倾向于发生生长迟缓、肠痉挛、睡眠障碍等。气质也会影响儿童对疾病诊疗过程的反应,在临床工作中,由于容易型儿童的反应阈高、反应强度低,病情较难被发现且易被低估;而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反应阈低、反应强度大,较多表现出消极、不愉快的情绪反应,易于早期发现疾病[26]。
4 小 结
多种气质理论都指出儿童气质是成年人格特质的组成部分,个体气质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稳定性。但儿童的气质受母亲情绪、出生情况、家庭因素等各方面影响,这表明儿童气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的。在儿童的养育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气质特点,从家庭环境等方面进行积极干预是可行的。近年来人们对气质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较多成果,今后有必要将气质与疾病的预防、诊断及治疗相结合,以达到疾病预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