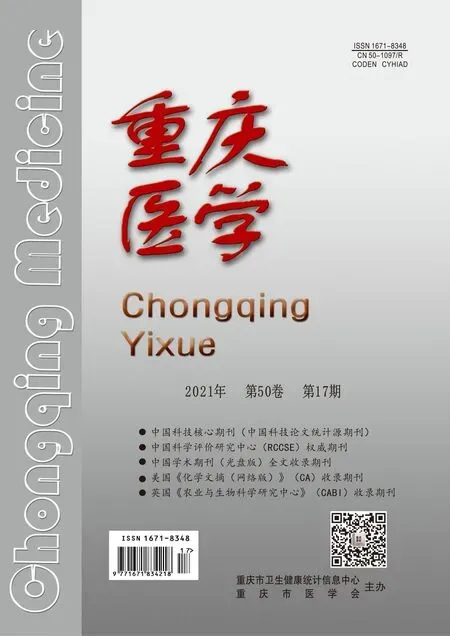胰腺导管腺癌微环境的研究进展
胡元杰 综述,苏 琨,吴 涛 审校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昆明 650000)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消化系统实体肿瘤,预后极差,据我国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其5年生存率仅为7.2%[1]。2018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根据全球癌症流行病学数据库统计胰腺癌是全球癌症死亡的第七大原因,约459 000例新发病例和432 000例死亡病例,胰腺癌整体发病率在所有肿瘤中发病率不高,但病死率却位居前列,且与许多其他癌症不同,胰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在逐年增加[2]。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占胰腺癌的绝大多数,且在所有消化系统实体肿瘤中预后最差[3]。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手术+辅助治疗。然而,大多数PDAC患者起病隐匿,确诊时已处于晚期,导致无法行手术治疗。尽管PDAC的治疗近些年有许多改进,包括提高生存率的联合化疗,如辅助治疗中的吉西他滨联合卡培他滨,以及晚期疾病中使用氟尿嘧啶、亚叶酸钙、伊立替康和奥沙利铂(FOLFIRINOX)和吉西他滨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等,但胰腺癌患者的远期生存仍不甚理想[4]。肿瘤微环境在PDAC发生、发展及治疗中起着关键作用,其特征是主要由大量免疫细胞、癌相关成纤维细胞、神经元、受压血管和大量细胞外基质成分如胶原蛋白、纤维连接蛋白和透明质酸组成[5]。PDAC微环境中的胰腺星状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髓源性抑制细胞等在肿瘤进展和肿瘤免疫方面有着重要作用[6]。长期以来都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集中在PDAC预防、诊断和治疗上,本文旨在综述PDAC微环境研究的最新进展,以期了解目前国内外PDAC微环境研究的现状,为PDAC治疗和微环境研究提供依据和思路。
1 PDAC肿瘤生物学
PDAC的发生、发展已经被证明是由Kras癌基因的激活突变,导致腺泡导管化生,随后随着胰腺上皮内瘤变等级的增加和多个抑癌基因的突变(包括p16/CDKN2A、TP53、SMAD4),最终发展为PDAC[7]。从腺泡细胞到PDAC的过程中伴随着丰富的间质纤维化增生是复杂的微环境基础。肿瘤微环境的构成大致可分为细胞成分和非细胞成分。细胞成分包括癌相关成纤维细胞、肌成纤维细胞、胰腺星状细胞、血管细胞和免疫细胞等。非细胞成分包括胶原蛋白、纤维结合蛋白和多种可溶性因子(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细胞外基质中的生长因子)等[5]。肿瘤微环境中的这些成分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同一种成分在PDAC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
2 基 质
2.1 胰腺星状细胞
正常人胰腺中的胰腺星状细胞具有维持结缔组织结构的功能,通常处于静止状态,占实质细胞的4%~7%。胰腺星状细胞中含有维生素A的细胞质脂滴,在静止状态下,胰腺星状细胞将维生素A储存在细胞质脂滴中,并产生较低量的细胞外基质。但在胰腺损伤,如慢性胰腺炎和(或)PDAC发生、发展时,胰腺星状细胞的细胞质脂质储存功能出现异常,增加细胞外基质的产生,获得肌成纤维细胞样表型,并表达成纤维细胞激活标记物——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这些活化的胰腺星状细胞分泌过量的细胞外基质成分,呈现出典型纤维化病理学表现[8],基质成分甚至可能占到肿瘤体积的90%。
胰腺星状细胞在PDAC中与多种成分有着复杂而重要的作用。活化的胰腺星状细胞有助于分泌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IL)-1、IL-6、IL-8和IL-10]和生长因子[如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CTGF和C-X-C基序趋化因子12(CXCL12)],促进血管生成和癌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进而导致转移[9-10]。研究表明,PDAC细胞诱导胰腺星状细胞自噬分泌丙氨酸,以维持PDAC细胞在缺乏营养的胰腺癌环境中的生长和代谢需要,并证明干预丙氨酸的转运可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和生长[11]。最近,HESSMANN等[12]证明胰腺星状细胞通过诱导PDAC癌细胞捕获吉西他滨到细胞质中,进而限制了吉西他滨对癌细胞的作用和促进PDAC耐药。这些研究支持胰腺星状细胞促进PDAC癌细胞的生长和侵袭。此外胰腺星状细胞还与肿瘤微环境中多种免疫成分串扰。例如,动物实验证明胰腺星状细胞增加调节性T细胞、M2型巨噬细胞和髓样来源的抑制性细胞等抑制性免疫细胞的数量,降低荷瘤小鼠脾脏和肿瘤组织中CD4+T、CD8+T细胞和M1型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的数量,阻止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反应[13]。胰腺星状细胞在PDAC的生长、代谢、侵袭、转移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对其进一步研究有可能提供PDAC诊治新方向。
2.2 免疫细胞
大量的纤维化和广泛的免疫细胞浸润都是PDAC肿瘤微环境的特征。研究证明,这些免疫细胞不仅与炎症有关,且与PDAC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VUJASINOVIC等[14]对前瞻性收集的慢性胰腺炎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进一步证明慢性胰腺炎患者PDAC发病率的增加这一说法。即使是在PDAC的早期阶段(胰腺上皮内瘤变和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瘤),免疫细胞的浸润也提示处于免疫抑制状态,随病情发展由早期病变的CD4+T、CD8+T细胞浸润为主,演变为PDAC的调节性T细胞为主导的免疫抑制状态[15]。
2.2.1肿瘤相关巨噬细胞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许多肿瘤中被发现,具有免疫抑制作用,并且由于其促进肿瘤生长、侵袭、转移和血管生成的能力,通常与预后不良相关。根据巨噬细胞的功能对其进行分类,分为M1型和M2型(常用CD163、CD204和CD206识别)[16]。M1型主要分布在PDAC微环境的非肿瘤炎症区,而M2型主要分布在肿瘤炎症区,是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主要部分且与预后不良相关,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作用可能与其数量和空间定位密切相关[17]。一项动物试验证明,炎性单核细胞和组织内巨噬细胞都是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来源,意外的是胰腺组织内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胚胎发育过程驻留在胰腺组织内的巨噬细胞,其在肿瘤进展过程中通过原位增殖进行扩张。单核细胞来源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抗原呈递中发挥着更有效的作用,而胚胎来源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显示出更高的促纤维化因子表达,表明它们在细胞外基质的产生和重塑中的特殊作用;且还证明人PDAC组织中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亚群类似于小鼠胚胎来源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18]。目前有一些针对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潜在治疗靶点,例如动物实验证明抗CD47处理可以增加荷瘤小鼠肿瘤内M1巨噬细胞,减少M2巨噬细胞,重塑荷瘤小鼠的瘤内巨噬细胞。此外,抗CD47处理还增加了肿瘤内CD8+T细胞的数量,并使T细胞簇向着更活化的簇重塑[19]。
2.2.2髓源性抑制细胞
髓源性抑制细胞是由未成熟髓系细胞组成的混合物,包括两种类型的细胞:粒细胞型和单核细胞型。然而,由于目前缺乏明确的表面标记物,识别困难。肿瘤细胞产生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吸引未成熟的髓系细胞聚集,并使其向髓源性抑制细胞分化。然后,髓源性抑制细胞抑制CD4+T和CD8+T细胞,削弱CD8+T细胞免疫监视功能,促进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调节性T细胞扩张[20]。HASNIS等[21]使用原位胰腺癌模型研究发现,与每周单独吉西他滨相比,每周吉西他滨治疗联合吉西他滨节律化疗(MC,即每天小剂量给药)一定程度上能抑制髓源性抑制细胞浸润、肿瘤转移和复发。值得注意的是,与MC吉西他滨方案相比,每周单独使用吉西他滨治疗观察到更多肿瘤血管生成和肿瘤动员的髓源性抑制细胞,这与促动素2(PK2,参与髓源性抑制细胞动员和分化的因子)的表达增加有关[21],或许靶向PK2的方法可用于预防化疗诱导的PDAC的髓源性抑制细胞动员,改善患者的预后。类似的靶点还有α-烯醇化酶(ENO1)、CXCR2、尿激酶型纤溶酶原及其受体[20]。
2.2.3肿瘤浸润性T细胞
PDAC的微环境基质中T细胞的主要成分是CD3+T、CD4+T和CD8+T细胞。CD4+Th细胞分化为两个亚群Th1和Th2。Th1细胞分泌IL-2和γ-干扰素,负责介导细胞免疫。Th2也被称为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它分泌IL-4、IL-5、IL-9、IL-10和IL-13,参与体液免疫反应。Th1细胞参与细胞免疫杀伤肿瘤细胞,研究证明,Th1和(或)CD8+T细胞水平较高的患者生存时间明显延长[22]。然而,在PDAC微环境中主要的CD4+T细胞是Th2细胞,以往的大多数研究表明Th2细胞在PDAC中发挥主要的免疫抑制作用,与患者的预后不良相关,但最近有动物实验表明Th2细胞的减少加速了PDAC的发生、发展[23]。
CD8+T细胞,是负责抗肿瘤免疫的主要效应细胞,在PDAC患者的抗肿瘤免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PDAC微环境中的CD8+T细胞水平与患者的预后呈正相关[22]。PDAC患者的预后还与CD8+T细胞的空间定位有关,肿瘤中心和肿瘤边缘之间的CD8+T细胞存在明显差异,肿瘤中心的CD8+T细胞浸润非常少,研究发现肿瘤中心的CD8+T细胞浸润多的患者生存期相对延长[24],说明阻碍CD8+T细胞发挥抗肿瘤免疫作用的不仅与数量有关,还与其空间分布有关。目前,单剂量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难以对PDAC发挥作用,最近的一项体外实验证明使用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阻断剂联合C-X-C趋化因子4型受体(CXCR4)阻断剂后,在活体显微镜下观察到PDAC肿瘤微环境中的CD8+T细胞从肿瘤边缘的基质迁移到肿瘤细胞旁,加速肿瘤细胞凋亡[25]。虽然目前这种联合阻断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这个研究证明了肿瘤边缘浸润的CD8+T细胞仍然具有潜在的抗肿瘤活性,可以通过联合免疫疗法重新激活,这一发现为PDAC联合免疫治疗的合理选择提供了新的依据。
Th2细胞与CD8+T细胞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困扰着研究学者。JANG等[26]通过动物实验和体外实验证明Th2细胞可以通过结合CD11c+树突状细胞使其处于免疫抑制的状态,进而抑制CD8+T细胞活化和抗肿瘤细胞毒性作用,导致(不论早期或晚期)PDAC病情进展和肿瘤生长。他们在动物实验中证明,使用人类白喉毒素(DT)耗尽PDAC微环境中的Th2细胞后,肿瘤浸润CD4+T和CD8+T细胞激活和扩增明显增多,疾病进展明显延迟,肿瘤体积的明显减少和生存期的延长。
2.3 细胞外基质
细胞外基质是一个由结构蛋白、衔接蛋白、蛋白聚糖和酶组成的致密网络,存在于所有组织中,为组织稳态提供支持。在PDAC微环境中,细胞外基质的沉积明显增加,主要是Ⅰ、Ⅲ、Ⅳ型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肿瘤基质的生物活性成分,不仅仅具有结构支架的作用,而且对癌细胞增殖、存活和转移有直接影响。LAKLAI等[27]研究表明,高表达透明质酸和Ⅰ型胶原蛋白的患者的总体存活率比不表达的患者差,然而,当以这种方式研究全部胶原蛋白时,未观察到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
3 小 结
目前,PDAC仍然是一种难治疗的消化系统实体肿瘤,预后极差。肿瘤微环境的研究在不断加深,学者们也逐步认识到了其中许多复杂的成分和相互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许多非常有潜力的诊断、检测、治疗和预后评估的新方法,有的甚至已经取得一定的临床效果。但目前PDAC患者的远期生存仍不理想,还需要对PDAC的肿瘤微环境继续深入研究,探寻更多、更有效的诊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