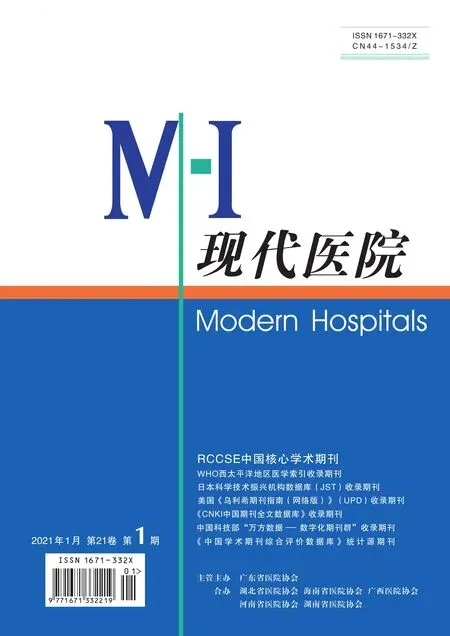新冠肺炎集中隔离社区居民及医护人员心理影响调查分析
黄翠仪 陈俊泳 冯惠颜 陈文荣 唐 智 陈尚丽 山艳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coronaviruspneumonia,NCP),简称“新冠肺炎”,是指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该病作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管理。目前研究已知新型冠状病毒人群普遍易感,主要传播途径为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气溶胶和消化道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1-2]。隔离是控制传染病传播的有效方式之一,但可能会对隔离者造成心理影响。为应对和加强疫情防控,多地采取了对疑似病例及密切接触者采取集中隔离的措施,本研究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的高峰期进行的,目的是了解在新冠肺炎防疫中采取集中隔离社区居民及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和方法
1.1.1 对象 2020年02月08日—02月14日对因新冠肺炎隔离的社区居民及参与工作的医护人员以及周边未隔离的社区居民及未直接参与隔离工作的医护人员进行调查。其中男79 人、女105 人,年龄17~88岁,平均年龄(48.53±14.54) 岁;社区居民108人,医护人员66人,共174人。
1.1.2 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3],分别对因新冠肺炎隔离的社区居民(68人)及参与工作的医护人员(36人)以及周边未隔离的社区居民(40人)及未直接参与隔离工作的医护人员(30人)进行调查。量表调查时间选择在隔离期间进行,隔离地点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调查采取网上问卷的调查方式,由参与隔离工作的医护人员经被调查者同意后,将问卷一对一发送至被隔离人员手机进行调查,要求被试者当场完成问卷调查。对于无法自行填写问卷的患者,可由患者进行口述,并由工作人员代为操作。本研究共发放网络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为174份,有效回收率为 87.0%。
1.3 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SCL-90测评结果
隔离社区居民在躯体、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等因子的得分明显高于参与隔离医护、非隔离社区居民和非隔离医护(P<0.05);参与隔离医护在抑郁、焦虑和恐怖的因子得分明显高于非隔离社区居民和非隔离医护(P<0.05)(表1)。

表1 新冠肺炎集中隔离社区居民及医护人员SCL-90评分比较
2.2 SDS、SAS测评结果
隔离社区居民SDS量表分值与隔离医务人员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但明显高于非隔离社区居民和非隔离医护(P<0.05),隔离社区居民SAS量表分值与隔离医务人员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隔离医务人员SAS量表分值亦明显高于非隔离社区居民和非隔离医护(P<0.05)(表2)。

表1 新冠肺炎集中隔离社区居民及医护人员SDS和SAS评分比较
3 讨论
自2019年12月武汉市发现多例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相关肺炎以来,疫情来势凶猛,确诊及疑似患者数量上升趋势明显,国家已启动一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响应,防控形势严峻。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有较多医护人员感染病例[4-6],这不仅会引起医务人员的紧张不安,也严重影响着医疗救治工作的正常运行,为应对和加强疫情防控,多地采取了对疑似病例及密切接触者采取集中隔离的措施。国内外研究显示重大灾难后精神障碍的发生率为10%~20%,常见的症状包括:分离性反应,创伤后应激反应(闯入、回避、警觉性增高等)、抑郁反应、焦虑反应、躯体化反应等[7]。隔离可通过切断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以控制 COVID-19的暴发[8],为应对和加强疫情防控,多地采取了对疑似病例及密切接触者采取集中隔离的措施,但会使患者产生孤立感和病耻感,从而产生消极心理影响[9]。通过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隔离社区居民在躯体、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等因子的得分明显高于参与隔离医护、非隔离社区居民和非隔离医护(P<0.05)。参与隔离医护在抑郁、焦虑和恐怖的因子得分明显高于非隔离社区居民和非隔离医护(P<0.05),提示隔离措施不仅对社区居民造成了消极心理影响,同时对参与隔离工作的医护人员都不同程度出现了抑郁、焦虑、和恐怖等负面情绪,隔离社区居民SDS量表分值与隔离医务人员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但明显高于非隔离社区居民和非隔离医护(P<0.05),隔离社区居民SAS量表分值与隔离医务人员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隔离医务人员SAS量表分值亦明显高于非隔离社区居民和非隔离医护(P<0.05),提示患者显得更焦虑。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①对疫情的恐慌,社区居民大多医学常识缺乏,网络以及社会上的传言夸大了该病的严重程度,使一些集中隔离人员担心疾病治疗和预后,对隔离的居民和医护人员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②社会联络体系的缺失,严格的集中隔离措施会使被隔离人员感到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产生强烈的恐惧感,担心、忧虑、不安全感随之产生;③封闭式管理导致生活单调乏味:为避免交叉感染,人员被单独单间隔离,不得串门接触,环境压抑、活动范围受限、人际交流减少,情绪无处宣泄与释放,容易出现失眠、多梦、易怒、敌对等负性情绪[10-11]。对于在抗“新冠肺炎”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来说,除了本身的技术工作要求高、责任重,隔离区域导致的自由度小、缺乏沟通,医务人员紧缺导致劳动时间过长、睡眠不足,尤其是后勤物资的保障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这些因素构成了“新冠肺炎”应激,医务工作者面临躯体、精神和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刺激,使医务工作者心理负荷加重,情绪压抑和身心疲惫[12]。在2003年SARS疫情中,有学者[13]对社区隔离点人员开展健康教育及心理干预,采用健康教育知信行调查表及SCL-90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现场调查,结果显示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对改善社区SARS隔离人员的知信行与心理状况有一定效果。为了更好的防控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们不仅要主动做好传染病疫情的防控工作,同时也要要努力营造积极的支持环境,加强对隔离对象的心理疏导及一线医务人员的身心关爱,减少因控制疫情暴发采取的集中隔离措施,而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相关问题[14-17]。
综上所述,在应对新冠肺炎突发疫情时,集中隔离措施不仅对社区居民造成了消极心理影响,同时对参与隔离工作的医护人员都不同程度出现了抑郁、焦虑、和恐怖等负面情绪,对集中隔离人群更应加强心理疏导,减少集中隔离措施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