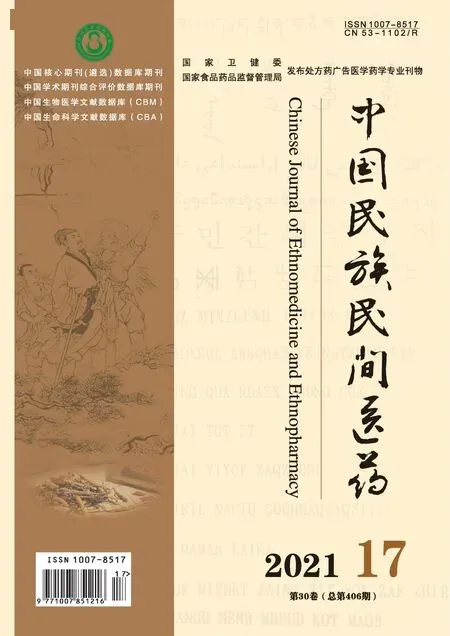由傅山辨治月经病探析其对《黄帝内经》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孙瑞英 崔轶凡 王志平
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 太原 030619
傅山,字青主,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以及医学家,山西太原阳曲人。中医提倡重经典、重临床,《傅青主女科》是后人根据傅青主所撰写文稿辑录而成,此书作为中医经典,对妇科相关病患的辨证论治独具特色。《女科》所论囊括经、带、胎、产、杂病,尤其重视月经的调理。傅氏在《女科》里提到“妇科调经尤难,盖经调则无病,不调则百病丛生”[1]。本文就调经篇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探讨,管窥其对《黄帝内经》[2]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脉络。
1 经水出诸肾
1.1 “经水出诸肾”思想的产生 《黄帝内经》首次提出“经水”,并在《素问·离合真邪论》中提到:“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这里的“经水”乃指河流,象征着人身体的经脉[3]。傅山认为古昔圣贤之所以命名为经水,是因为水出于肾,即肾主水,为水脏,由癸干所化[1]。“夫癸者,天之水,干名也。”[4]故“癸干”乃天癸也。肾水的本体是天癸,癸者,水也,肾在五行中属水,故而傅山认为“经水”之名更能够将月经与肾、天癸之间的密切联系阐释清楚。此外,还提出了“经水”是由肾中至阴之精作为物质基础所化生而来,并非仅仅是血性物质,之所以将其误认为血性物质,是因为其在至阳之气的温煦下,经色呈现为赤红色,故似血。由此可以看出傅山从对经水本源有着深刻的理解,并提出了“经水出诸肾”的理论,确定了补肾调肾是调经的第一要法[5]。
1.2 “经水出诸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经水出诸肾”的思想强调了肾在经水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肾的生理功能有着密切联系,肾可藏精,精可化血,故精血同源。其不仅是傅山对前人学术思想的继承,更是在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融汇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加以发挥,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学思想体系。傅山调经思想主要源于《内经》,《内经》云:“肾脉微涩为不月。”“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揭示了肾、天癸及冲任与月经产生的紧密联系。此肾气、天癸、冲任与月经是妇女所特有的生理现象,诚乃傅氏女科调经治病的主要学术思想内容,现代亦有许多学者论述傅山的调经思想与《内经》的经水学说是一脉相承的[4-5]。并在《内经》基础上,傅山对肾在月经失调中的机理作了更全面的分析,提出了“肾水火太旺”“肾中火旺而阴水亏”“肾之或通或闭”“肾气之涸”“肾气无所生,肾水无所化”等是经水先期或先后无定期或行经后少腹疼痛或年未老经水断的主要病因。其“经水出诸肾”学说对现代学者治疗月经病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刘奉五教授曾提出“调治月经似是治血而非治血,而是治天癸和调整脏腑功能”[6]。蔡小荪教授[7]在调经时同样重视天癸的生理功能,将调肾放在重要位置,提出了“调经治血须滋水益肾”的观点。
2 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主要探索木火土金水五行的概念、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生克乘侮规律。《黄帝内经》以五行生克解释脏腑生理功能的相互联系,相乘相侮阐释脏腑之间失衡后的相互病理影响,并提出“亢则害、承乃制”的重要机理。傅山曰:“妇科一门,最属难治……难于辨证也。”运用五脏六腑的生克制化胜复乘侮规律来阐明妇科疾病的发展变化,是《傅青主女科》辨证的重要核心内容。纵观调经篇可以看出傅山非常善于运用五行学说来认识妇人的生理、病理并将其作为月经病的辨证理论依据。
“经水先后无定期”篇论述:“肝为肾之子,肝郁则肾亦郁矣……或曰肝气郁而肾气不应……子病而母必有顾复之情……即肾气之或去或留,相因而致,又何疑焉。”[1]指出其病机主要为“子病及母”,终至肝肾皆郁而导致经水先后不能按期而来,或肝气过旺,而截肾阴,导致肾虚摄纳失职而致经水不调。此篇主要论述了肾水与肝木之间的相生关系。傅山明确提出治宜解郁疏肝,肝郁开,则肾郁可解。此为母病治子之义也。
“行经后少腹疼痛”篇:“盖肾水一虚则水不能生木,而肝木必克脾土,木土相争,则气必逆,故尔作疼。”[1]详细论述了肾、肝、脾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肾属水,肝属木,肾为肝之母,肝为肾之子。肾水不足,母病及子,而致水不涵木,即肾脏不能濡养肝脏,导致肝亢盛,则肝木必克脾土,最终导致木旺乘土,气机逆乱,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发为疼痛。傅山认为其治法主要以舒肝为主,加补肾之药,肾水充沛则肝亦得滋养,即滋水涵木,肝舒则气机畅,肝脾和,痛自止,此为母子同治。
“年未老经水断”篇则论述脏腑关系较为复杂,涉及肝、肾、脾、心[1]。本篇以肾为中心,论及五脏之间的相互制化关系,《内经》曰:“亢则害,承乃制。”在本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傅山认为素体脾虚,脾虚则不能制约肾水,从而导致肾水旺而制约心火,使心阳不足,不能温煦肾水,肾水不化,而精满才能化为经水,即精充则血充,反之则血少,终致经水断。或平素肾虚,肾水不足,则不能制约心火,导致心火旺盛,制约肺脏,肺属金,肾属水,金为水之母,母病及之,则肾气无所生。肺脏受损,使肝失去制衡,肝火旺而克伐脾土,使肾气无以成。傅山提出治法宜疏心、肝、脾之郁,主要补其肾水,佐以补其心肝脾气,则精满而经水自调。
3 气血学说
《素问·八正神明论》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素问·调经论》所云:“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妇人由于其自身的生理特点,常累耗于血,以血为本,血伤则气亦陨,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故傅氏治疗妇科疾病,非常重视脾胃气血的生理功能。以“调经篇”为例分析傅山对气血学说的运用。
傅山在“月经过多”篇认为其病机是由于血虚导致的,血病则气亦不健,最终导致气虚不能摄血而发为病。“经前泄水”篇认为是由于脾虚不能摄血,又脾主运化水湿,脾虚而致脾失健运,终致湿邪不化下注血海发为经前泄水。强调其治法应注重调理气血,而气能生血,气旺则湿除,湿除则经水调也。“经水忽来忽断时痛时止”,指出其病因乃是月经来潮之时风寒内袭使肝气失于调达所致,常人治疗多以疏风散寒为主,傅山则用加味四物汤补肝中之血为主,使血行而风灭,达到调经目的。
4 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傅山在调经篇中的又一重要思想,是人们认识宇宙万物最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宇宙万物变化的总规律。《内经》认为:“生之本,本于阴阳”,故“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才能保障是生命活动始终处于井然有序的谐调状态。傅山提出:“阴不欲无阳,阳不欲无阴”的观点,认为一切事物都以阴与阳的形式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的两个方面存在着。阴阳学说始终贯穿在傅山临证诊治过程中,现以“调经篇”为例,具体分析傅山治疗月经病重在调整脏腑气血之阴阳失衡状态。
月经先期篇,傅山根据月经量的多少将其分为肾中火旺血热(量多)和肾中水亏血热(量少),即实热和虚热之分[1]。治疗方面则根据其病机不同,实热应清热调经,方用清经散。方中药物全是清热之味,但同时又有滋阴的作用,火清热下火的同时而不损伤阴水。纵观全方,可以看出其药物主要治疗机制乃是滋阴清热,凉血养阴,使热去而阴不伤,血安而经自调。而对虚热,傅山强调重点补其水,认为心属火,肾属水,心火与肾水相互协调,维持生理功能的相对平衡,故当肾水充足可上济心火,使心火消退,为心火既济。方用两地汤,生地、地骨皮能够清骨中之虚热,肾主骨生髓,故骨中之热源于肾经之热,因此清骨髓之热,则肾气之热自消,且不损胃气,此治之妙也。且全方皆是滋阴补水之品,水盛而火自消。黄绳武在《傅青主女科评注》[8]中言“此方之意乃是壮水以制阳光,育阴潜阳,补阴配阳,从而达到‘水胜而火自平,阴生而经自调之目的’。”
“经前大便下血”篇,傅山认为心肾不交导致大肠之血妄行乃是其病因病机[1]。在生理状态下,心火和肾水互相协调,心居上,肾在下,一升一降,彼此相通,共同保持动态平衡。病理状态下,多由肾阴亏虚,阴精不能上承,导致心火偏亢,心属阳,肾属阴,心肾不交,两者失去协调关系,则阴阳失去平衡,疾病遂生。故治宜大补其心与肾,使心肾相交,阴阳平衡,使大肠之血继续听命于心肾二经之摄,自不妄行,而经自顺。方用顺经两安汤,全方益气养阴,滋补心肝肾之津液以壮水之主而火自退,升麻升举阳气,黑芥穗引血归经,一升一降,气机升降顺畅,旨在调和阴阳。
“行经后少腹疼痛”篇,傅山认为其病因病机是由于平素体虚,肝肾亏虚,或因房劳多产损伤,以致精血暗耗,阴损及阳,阴阳皆损,冲任失养,经事净后血海更虚,“不荣则痛”,则发为腹痛[1]。方用调肝汤,方中当归、阿胶滋养阴血,白芍可缓急柔肝以止痛;山萸肉益精气养肝肾;巴戟天温补肾阳。肝肾同调,阴阳双补,冲任得养,不止痛而痛自止。体现了阴阳学说中阴阳互根互用的关系。
调经篇的用药规律也体现了阴阳学说思想。傅山用药,常动静结合,补气健脾同时不忘调气活血,进补益药时必用梳理气机之药,使动静、疏滞合宜,从而达到阴阳平衡。
5 经络学说
经络学说源于《黄帝内经》,这个思想贯穿全书,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形体官窍、沟通上下内外、传导信息的通路系统,由经脉和络脉组成的。冲、任、督、带属于奇经,与妇女生理病理的联系最为紧密,它除了对十二经脉的气血运行起着蓄溢、调节外,在天癸的作用下,各司其职,对维护月经行止、聚精成孕、提胞系胎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水将来脐下先疼痛”篇中指出其病因病机是由于寒湿外邪侵袭冲任二脉,气机不畅,邪浊内乱所生[1]。治疗应温散寒邪,化湿利浊,调理冲任。方用温脐化湿汤,方中白术为君利腰脐之气;巴戟、白果通任脉;用扁豆、山药、莲子肉以固冲脉。全方重在祛寒湿,寒湿去则任脉通、冲脉固,经水调也。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傅山调经篇学术思想的总结,发现其与《黄帝内经》渊源颇深。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气血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还对《黄帝内经》的相关学术进行了发展,在病因病机、方药治疗上体现了自己的独到之处。傅山调经理论不仅是他个人医学理论的实践和创新,更是对中医妇科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