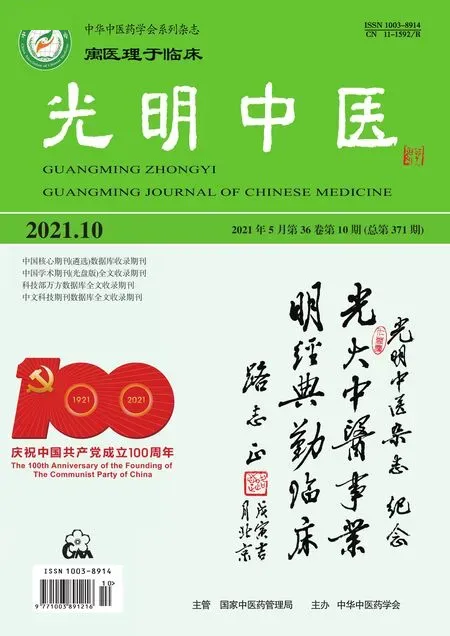益气活血解郁法双心同治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理论探讨
郭 放
心力衰竭是各种病因所致心脏疾病的终末阶段,由于心衰具有病程长、病情易反复等特点,容易合并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类疾病。研究显示,现阶段心力衰竭患者抑郁发病率约为40%。且焦虑抑郁发病率与心功能级别呈正相关[1]。美国心力衰竭患者随着纽约心功能分级增加,焦虑障碍及抑郁障碍的发病率成倍逐级增加[2]。在没有禁忌证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心血管患者都需要积极进行心脏康复,以使其恢复最佳的体力、精神及社会活动[3]。其中心理处方尤为重要,中医药是心力衰竭患者心理处方的补充[4]。中医药可通过多途径、多层次、多靶点作用于疾病的各个环节,对于调护患者心理状态,改善临床症状,辅助患者心脏康复都有良好的效果。
1 双心同治慢性心力衰竭中医理论基础
1.1 中医对双心疾病的认识中医是一门整体医学,虽然没有双心疾病的病名,但对于心系疾病与精神情志异常之间的关系早有论述。《黄帝内经》云:“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 恐伤肾”“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思则气结”“恐则气下”“惊则气乱”。《灵枢·本神》中提及:“故智者之养生也,必和喜怒而安居处……”,《灵枢·师传》云:“殊不知人情恶死而乐生, 凡致死之事,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七情五志密切相关,重视情志异常及情绪疏导是中医学的特点之一。《素问·调经论》提出“心藏神。”《类经·疾病类》云:“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数千年前中医就提出了“心主血脉”“心主神明”的理论,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各自的生理功能以及神志活动都离不开气血的充养。心藏神,各脏腑功能及精神活动的正常需要心的调控。情志的异常是各种心系疾病的主要病因,同时因为心系疾病病程较长,伴随症状较多,迁延难愈合,随着疾病的发展情志异常亦是多发的伴随症状,从而进一步加重原发病的治疗难度。《黄帝内经》云:“怫郁不舒,心系不宁”。二者为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5]。中医对双心疾病的论述与认识与现代医学双心医学的理念不谋而合。
1.2 心与双心疾病心与双心疾病情志异常的关系,与中医学心的脏腑功能特点一致,主要表现为心主血脉与心藏神之间的关系。心系疾病的发生发展主要与血脉运行障碍和情志活动异常相关。心主血脉、藏神,若心之气血阴阳调和,血脉运行通畅,则各脏腑气血充盈,同时心血充足,心神得养,则情志调畅。若心之气血阴阳不足,不但会引心悸气短、胸闷、心胸隐痛等心系症状,同时也会影响其他脏腑功能并导致神的异常,如心气虚则易出现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语声低微、精神萎靡不振、情绪低落等;心血虚则易出现易惊失眠、健忘等;心阴虚则易出现五心烦热、失眠多梦等;心阳虚则在情志异常基础上甚至会出现昏迷。若情志出现异常,神明躁动,则也可损伤心之气血阴阳而发为心系疾病。《医学入门》[6]云:“悸痛,内因七情……重则两目赤黄,手足青至节, 即真心痛,不治”。
1.3 肝与双心疾病中医认为情志异常是心身疾病的主要病因,而气机疏泄异常是心身疾病的主要病机。肝主疏泄,调情志,故与双心疾病息息相关。元代王安道《医经溯洄集·五郁论》:“凡病之起也,多由乎郁,郁者,滞而不痛之义”。双心疾病患者往往因久病气机失调,肝气郁滞所致。肝、心为母子之脏,其气相通,肝气不足则易引起心气受损,从而使血脉运行无力,周身失养,神无所依,从而出现心悸、气短、乏力、焦虑等症。肝郁日久,易化肝火,母病及子,引动心火,火扰心神,患者除出现胸闷、胸痛、心悸、气促等心系疾病的症状外,还可见心肝火旺的症状如头晕头痛、烦躁、易怒、惊恐、狂躁、失眠等;如气机郁滞日久可致血瘀,则脉络不通,血行不畅,心失所养,不通则痛,而出心悸、胸闷、胸痛等症;患病日久,肝火灼烧阴液,致肝阴不足,肝肾同源,必致肾阴不足,且肾与肝亦是母子关系,水竭无以滋木,使肝火更旺,同时肾阴不足不能上奉于心,水火不济,则心阳亢盛,扰动心神而致心烦、易怒、失眠等症状。
1.4 心与肝在气血运行与调节情志之间的关系在双心疾病中,心处于核心地位,心肝之间紧密联系。《类经》云:“五志惟心所使也”。心行血,肝藏血。心主神志,肝主疏泄,能够调畅气机,调节情志。心与肝的关系,即体现在气血生化与运行之间的关系,又体现在主宰神明与调节情志之间的关系。气血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心之气血充沛,肝有所藏,则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则全身气机疏通畅达,气血平和,情志安稳。若心之气血不足,累及肝脏,肝无所藏,肝失所养继而造成疏泄失职,则易情志失和,出现焦虑、抑郁、惊悸、失眠、多梦等情志症状。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主要由心主宰,且与肝的疏泄功能密切相关。情志活动依赖于气机的调畅。若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则气机调畅,情志正常。若肝的疏泄功能异常,必然会影响肝的调节情志功能,继而出现烦闷、抑郁、焦虑、惊恐等表现。
2 运用益气活血解郁法“双心同治”治疗慢性心力衰竭
慢性心力衰竭属中医学心系疾病中的“喘证” “心水” “水肿” 等范畴。现代专家共识认为本病属本虚标实,本虚以气虚、阴虚、阳虚为主,标实以血瘀、水饮为主[7]。心衰病患者素体心气不足,推动无力,血行不畅,留于脉中,形成瘀血。气虚精液输布失常,日久肾阳亏虚,化气行水不利,造成水饮内停。双心疾病最常见的是心血管疾病合并焦虑症或抑郁症等,中医归为“郁证”“脏躁”“百合病”等范畴,也与气血密切相关。《景岳全书》:“其在于人,则凡气血一有不调而致病者,皆得谓之郁证”。《医方论》:“凡郁病必先气病”。脏躁者,脏阴不足也。精血内亏,五脏失于濡养,五志之火内动,上扰心神,以致脏躁。从病机角度,情志异常疾病以气机疏泄异常引起的气机郁滞为主要特点,随着疾病发展,可出现血瘀、痰浊、化火等,疾病初期多属于实证,患病日久则易由实转虚,出现脏腑阴阳气血的亏虚,可见虚实夹杂,影响五脏的生理功能。从病因角度,内伤七情为心衰病的主要病因之一,情志异常也是心衰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这与两病共有的发病机理,气血变化特点等息息相关。
从证候病机角度,心气亏虚是心力衰竭的根本原因,瘀血内阻是心力衰竭的重要病理环节[8]。伴有情志异常的心衰患者的发病与心、肝密切相关,而情志异常疾病的主要证候表现为气机郁滞。肝主疏泄,与气机密切相关,一旦气郁体内,肝气不顺,则肝火上升,易化火伤津,扰乱心神[9]。同时,若肝失调达,肝郁气滞;气滞日久,血行不畅,瘀血阻脉,则也会形成血瘀,痹阻血脉。《医林改错》云:“血管无气,必停留为瘀”。故在治疗上易梳理肝部,使气机舒畅,心神得安,血脉得通。综合以上拟益气活血解郁法双心同治慢性心力衰竭,方选通补心宝方合柴胡疏肝散加减。通补心宝方为津门名中医马连珍老先生的经验方[10],其组成为:红参、黄芪、丹参、桃仁、川芎、赤芍、葶苈子、桑白皮等。并根据病情变化予以加减,血瘀较重者,可加三棱、莪术等;久病入络者,可加僵蚕、地龙、全蝎等;患病日久气血不足症状突出者,则可加归脾汤以加强补气养血功效;阴血不足者,加生脉饮或天王补心丹以滋阴补血、养心安神;阳气亏虚者,可佐以参附强心汤加减,以温补心肾阳气。心肾不交者,可予交泰丸、黄连阿胶汤等,以滋阴降火、清心安神。若心神失养较重者,则加用柏子仁、酸枣仁、夜交藤、合欢皮等。若心神不宁,心悸明显者,则可加用龙齿、珍珠母、寒水石等重镇安神之品。肝火旺盛者,可以丹栀逍遥散合小陷胸汤或黄连温胆汤以清泻肝火。痰浊较重者,可加胆南星、天竺黄、竹沥等。水饮内停较甚者,佐以车前子、车前草、大腹皮等。
3 验案举隅
患者,女,66岁。2016年12日初诊。主诉:胸闷喘促间作2年余,加重伴双下肢水肿3 d。既往慢性心力衰竭病史2年,冠心病病史10年余,高血压病史20余年。患者2年前劳累后出现胸闷喘促间作,无明显胸痛,偶发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于外院诊断慢性心力衰竭,予抗血小板聚集、扩冠、减轻心肌耗氧、降脂、利尿、降压等西药规范治疗,患者症状时有反复。3 d前活动后自觉胸闷喘促较前加重,伴双下肢水肿,故于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就诊。现症:神情,精神可,情绪紧张,神情焦虑,胸闷喘促间作,无胸痛,时心悸,气短乏力,胁肋胀满,善太息,纳差,夜寐欠安,多梦, 尿少,口唇轻度发绀,舌暗,苔薄白,脉沉细。西医诊断:慢性心力衰竭。中医诊断:心衰病,证属气虚血瘀肝郁,水饮内停。治以益气活血解郁、利水安神为法,初诊以通补心宝方合柴胡疏肝散加减,佐以利水安神之药:车前子15 g,大腹皮10 g,龙齿15 g,珍珠母15 g。水煎服,7剂,早晚分服,日1剂。同时安抚患者,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缓解患者的恐惧焦虑情绪,并详细交代相关疾病的注意事项。二诊患者服药后胸闷喘促明显减轻,水肿改善,胸胁胀满及心悸缓解,自觉周身轻松,纳可,寐欠安,小便增,大便可。舌质暗,苔薄白,脉沉,原方加酸枣仁15 g,夜交藤15 g。服用1个月后,患者病情稳定,胸闷喘促明显改善,活动耐量增加,神情平和,胸胁胀满及心悸明显减轻,双下肢不肿,纳可,夜寐改善,二便可。舌质暗,苔薄白,脉沉较前有力。
按:患者女性,高龄,既往高血压、冠心病多年,患病日久,运动耐力降低,生活质量差,对疾病认识不足,终日焦虑惊恐,纳眠不佳,方中以通补心宝方合柴胡疏肝散为主,方中红参、黄芪补气培元,丹参、桃仁、川芎、赤芍活血化瘀,桑白皮、葶苈子泻肺平喘,利水消肿。柴胡疏肝解郁,香附、陈皮理气行滞,芍药、甘草养血柔肝。并佐以车前子、大腹皮、龙齿、珍珠母、酸枣仁等以增强利水安神之效。全方攻补兼施,益气活血解郁的治法贯穿全程,同时对患者予心理疏导,故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4 双心医学与中医结合模式的探讨及展望
双心医学实现了传统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但是目前对于双心疾病的研究与治疗仍以西药为主。其中抗抑郁药物的使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患者疾病的进展,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心血管疾病患者常患病时间长,并发症多,需要长期规范的服用西药治疗及联合用药,在应用抗焦虑抑郁药时需要考虑到各药物之间的不良反应及禁忌证。同时大部分患者往往更加重视自身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常否认或忽视自己存在心理精神疾病,临床上很多双心疾病的患者不认同抗焦虑抑郁类药物的作用,对其不良作用恐惧,致使其依从性很差,使疾病更加迁延难愈。中医治疗双心疾病有其独到之处,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未病先防的理论体系,以阴阳、脏腑、经络的辨证思维方式,多层次、多维度的治疗方法,如中医的耳针穴位按摩,中医特色的运动模式:太极拳、八段锦等,中医五音疗法,更加符合“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理念,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医注重七情五志、以人为本的理念,可以帮助患者安抚情绪,提高依从性,建立更深更牢固的医患关系。目前在双心医学的中医治疗已取得一定进展,中医学可以伴随患者治疗的始末,从预防、诊断、治疗到康复,但各个阶段的治疗还是以各医家的经验体会为主,尚没有针对性的辨证分型,缺乏整体的医疗体系规范及临床疗效评价手段,笔者相信,双心医学与中医相结合的新模式,必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5 结语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焦虑抑郁障碍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同时焦虑抑郁会显著增加心力衰竭患者的病死率[11]。中医药是心脏康复的新助力,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中药可伴随常规心血管的西药长期服用,且安全性较好,经济负担小。笔者认为心衰病合并情志异常的主要病机与心肝二脏密切相关,主要为气虚血瘀,肝气郁滞,心神失养。治疗当以益气活血解郁为主,并根据患者脏腑阴阳虚实的情况和兼症的表现,施以不同的方药,疗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