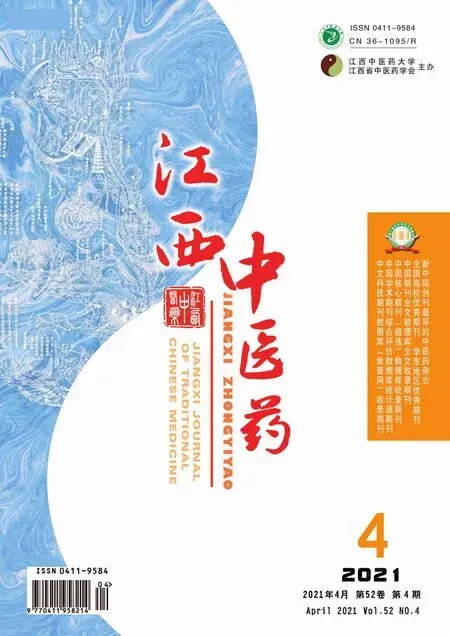咳嗽临床诊治验案二则
★吴骄(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成都 610041)
咳嗽或咳嗽兼痰喘是临床常见病症,致病因素众多,尽管咳嗽不离乎肺,但与其他脏腑均有密切关系,《黄帝内经》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笔者认为临证之时,应详细诊察病因,同时又要辨别病机,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上立法、处方、用药,则可做到有的放矢,效如桴鼓。下举二则验案以共同道。
1 病案举隅
1.1 验案一 患者某某,男性,77岁,咳嗽、咳痰4个月于2019年9月9日就诊。患者4个月前因感冒而出现发热、咳嗽,感冒痊愈后仍有咳嗽、咯痰。曾服顺尔宁、复方鲜竹沥、沐舒坦等药,但咳嗽症状不减,且影响睡眠,故来就诊。刻下:咳嗽、咳痰,痰少而黏,咽痒,咽部不舒,二便可,睡眠欠佳,舌质红、苔薄黄,脉弦细数。辨证为:痰热郁滞,肺气失宣;诊断:咳嗽。拟以宣肺降气,止咳化痰,清肺泻火为法。方药:炙麻黄6 g、炒苏子10 g、金银花15 g、黑元参15 g、全瓜蒌20 g、鱼腥草10 g、金荞麦20 g、牛蒡子10 g、生黄芪15 g、山萸肉10 g、炙桑皮15 g、苦杏仁10 g、炙紫苑10 g、陈皮10 g、蝉衣10 g、桔梗10 g、生甘草10 g,7剂。水煎服,日1剂。
9月16日二诊:咳嗽症状明显减轻,咳痰减少,咽痒好转,口干,舌质红、苔薄黄,脉弦细。继以宣降肺气,止咳化痰,清理肺热,益气补肾为法。方药:炙麻黄6 g、炒苏子10 g、金银花15 g、生黄芪15 g、山萸肉10 g、黑元参15 g、全瓜蒌30 g、鱼腥草10 g、金荞麦25 g、牛蒡子10 g、炙桑皮15 g、苦杏仁10 g、炙紫苑10 g、川贝母10 g、熟地20 g、陈皮15 g、蝉衣10 g、桔梗10 g、生甘草10 g,7剂。水煎服,日1剂。患者服药后咳嗽已止,诸症基本消失。
按语:《素问·宣明五气论篇》曰:“五气所病……肺为咳。”《医学源经·咳嗽篇》曰:“肺为脏腑之华盖,呼之则虚,吸之则满,只受得本脏之气,受不得外来之客气,客气干则呛而喘矣,亦只受得脏气之清气,受不得脏气之病气,病气干之则亦呛而咳矣。”肺位置最高,为娇脏,不耐寒热,无论外来之客气,抑或内在它脏之影响,均易致肺的宣发、肃降失职而引起咳嗽。临证时,要谨守肺之病机,顺应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处方以宣肺止咳化痰为要。北宋医家庞安时曰:“人身无倒上之痰,天下无逆流之水,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随之顺矣。”[4]故方中用陈皮、全瓜蒌理气健脾、清热化痰、宽中散结,以顺肺气宣发肃降之性而调之,使肺更好地发挥主治节的作用。现代研究证明,清热化痰药本身具有影响慢性气道炎症、氧化应激、气道黏液高分泌等诸多机制。
患者77岁,年事已高,且咳嗽4个月,久咳则必致肺虚,因此须补益肺气,而虚则补其母,脾为肺之母,在补益肺气的同时,辅以健脾。研究表明,补益脾肺之气,可提高气道受体的磷酸化水平,抑制氧化应激反应。肺肾母子相关,肺主呼气,肾主纳气,一呼一吸,相得益彰,因此同时也须兼顾益肾,而益气滋肾能发挥抗氧化应激作用,与肺功能潮气量、呼气峰流速和50 %潮气量等指标成正相关。
患者咳嗽日久,郁而化热,辅以清热解毒之药,对本病治疗大有裨益。方中金银花,清热解毒,透散表邪,现代研究其具有抗菌活性的作用;鱼腥草,味辛、性寒,能宣肺散结,清热解毒,为治痰热壅肺之要药,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作用较强;金荞麦,清热解毒,祛痰止咳,能增强抗菌作用。诸药协同,切中病机,临床疗效自然确切。
1.2 验案二 患者陈某,男,65岁,因疲乏,间断咳嗽、喘憋1年余于2018年10月8日就诊。患者2018年9月因疲乏,间断咳嗽、喘憋于我院就诊。行胸腔超声示:右侧大量胸腔积液;行右侧胸腔闭式引流术,共引流约500 mL血性胸腔积液,胸水病理未找到肿瘤细胞;行支气管镜检查示:右肺下叶开口处可见新生物,病理回报提示鳞状细胞癌;胸部CT示右下叶不规则团块影致右下叶支气管阻塞、右侧胸水、纵膈(气管隆突下)及右肺门淋巴结增大;腹部超声及全身骨显像、心脏超声、头颅增强MR未见转移,初步诊断为右肺鳞癌(cT4M31a)。医院建议放、化疗法治疗,患者拒绝,遂就诊于中医。刻诊:疲乏无力,手足凉,间断咳嗽,痰少、黄白相间,饮食尚可,右协胀疼,大便正常,舌质淡红、苔薄白,脉沉细数。诊为咳嗽。拟补肺益肾,止咳化痰,解毒散结为法。方药:黄芪30 g、山药20 g、熟地30 g、山萸肉12 g、紫苑15 g、全瓜蒌30 g、葶苈子15 g、大枣10 g、茯苓30 g、猪苓30 g、陈皮10 g、泽泻20 g、鸡血藤20 g、菟丝子10 g、当归15 g、蛇舌草30 g、天门冬15 g、生薏仁30 g、蛇莓15 g、山慈菇6 g、甘草10 g。7剂,水煎,日1剂,分2次服。患者外地休息,持续服药,症状基本平稳。
2019年4月2日二诊:血色素130 g/L,白细胞7.5*109个/L,中性粒细胞78.9%,血小板342万/L,疲乏明显,腹胀,右协胀疼,气喘,下肢浮肿,手足凉,饮食尚可,晚餐12个水饺,舌质暗红、苔黄腻,脉沉细无力。拟补肺益肾,温通阳气,止咳化痰,利水消肿,解毒散结为法。方药:党参30 g、五味子15 g、车前子30 g、炒白术20 g、白芍20 g、砂仁6 g、山药40 g、女贞子10 g、大枣20 g、生黄芪105 g、熟地40 g、山萸肉10 g、枸杞子40 g、猪苓70 g、青皮20 g、当归20 g、半枝莲15 g、山甲珠20 g、焦三仙30 g、全蝎15 g、白花蛇舌草15 g、细辛3 g、黑附片28 g、葶苈子30 g、红景天40 g、炙甘草20 g、柯子肉10 g、薏苡仁80 g、元胡30 g、泽泻20 g、炒香附18 g。7剂,水煎服,日1剂,分2次服。
2019年5月24日三诊:患者疲乏无力,困倦,双下肢水肿明显,便秘,右协胀疼,舌质暗淡、苔黄厚腻,脉沉细无力。拟补肺益肾,温通阳气,止咳化痰,利水消肿,健脾和胃,解毒散结为法。方药:冬瓜皮30 g、乌枣50 g、赤小豆30 g、党参50 g、五味子15 g、车前子40 g、赤芍20 g、砂仁6 g、炒香附18 g、山药40 g、生黄芪105 g、熟地40 g、山萸肉15 g、枸杞子40 g、猪苓90 g、青皮30 g、当归20 g、半枝莲15 g、白英15 g、山甲珠20 g、焦三仙30 g、全蝎15 g、酒大黄23 g、细辛10 g、桂枝30 g、黑附片35 g、葶苈子30 g、红景天50 g、炙甘草20 g、柯子肉25 g、薏苡仁100 g、元胡30 g、桔梗10 g、金钱草60 g、泽泻20 g,7剂。水煎,日1剂,分数次频服。
2019年7月30日四诊:血色素109 g/L,白细胞8.8*109个/L,中性粒细胞74%,血小板320万/L,生化系列、肝功能、肾功能正常,白蛋白稍低。拟补肺益肾,温通阳气,止咳化痰,利水消肿,健脾和胃为法。方用:冬瓜皮60 g、乌枣50 g、赤小豆60 g、党参120 g、五味子15 g、车前子50 g、炒白术30 g、赤芍30 g、砂仁6 g 、山药50 g、 阿胶珠20 g、生黄芪105 g、熟地50 g、山萸肉20 g、枸杞子70 g、猪苓120 g、青皮30 g、当归20 g、半枝莲20 g、山甲珠30 g、焦三仙30 g、全蝎15 g、炙龟板40 g、酒大黄28 g、细辛10 g、桂枝30 g、黑附片40 g、葶苈子40 g、红景天70 g、炙甘草20 g、柯子肉25 g、薏苡仁120 g、元胡30 g、桔梗20 g、金钱草60 g、泽泻20 g、炙鳖甲30 g,7剂。水煎,日1剂,分数次频服。
按语:中医无“肺癌”之病名,多归于“岩”或“鼓胀”“积聚”之类。《灵枢·百病始生篇》曰:“卒然外中于寒,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气不通,经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滞涩,著而不去,而积皆成。”指出外感六淫兼之内伤七情,内外交感,肺气郁滞日久而发本病。《本草求真》曰:“壮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成病。”《活人机要》曰:“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指出本病与患者素体虚弱相关。《医宗必读·积聚》曰:“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攻补,末者,病魔久之,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 《医学源流论》云:“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能伤命,隐然一敌国,病方进,则不治其太过,固守元气,所以劳其师。”指出病久日深,正气渐耗伤,病情进一步加重。因此在治疗方面,初立补气温阳、解毒散结、攻补兼施,后则以扶正祛邪、益气健脾、温阳补肾、利水消肿为法。
本患者病情日久,虚实互夹,病机复杂,治疗应补虚而不忘泻实。患者疲乏、咳嗽无力,需脾肺并补。生黄芪甘温入脾肺经,具有生发之性, 用于气虚衰弱,体倦乏力,懒言食少等症, 实验证明生黄芪具有显著的强心、改善全身血液循环和营养状况的作用[1];党参,味甘、性平,不燥不腻,善于补脾养胃,健运中气,养血生津,凡是脾胃气虚,体倦食少,肺气不足,气短懒言用之最为适宜,实验证明党参具有强壮补血作用,对神经系统有兴奋作用,能增强机体抵抗力,并能增加红细胞和血红蛋白[1];红景天,味甘涩、性寒,有补气清肺,益智养心的功效,主治气虚体弱、气短乏力、病后畏寒之症,《本草纲目》记载:“红景天本经上品,补诸不足,祛邪恶气,为补益药中之罕见。”《现代实用本草》言其有中枢抑制、抗疲劳、强心、抗过氧化作用。
癌毒日久,既伤阳又耗阴,临床以气阴两虚者居多。《景岳全书·新方八略论引》曰:“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所以本病治疗过程中以益气养阴为主,佐以温阳补血,故本案以黄芪、党参、红景天配当归、阿胶、枸杞子,附子配熟地、山萸肉等,以达补气养阴、温阳补血之目的。
患者喘憋,手足有凉感,舌淡、苔薄白,脉沉细,提示阳虚见证,须温阳利水。方中黑附片辛、大热,通行十二经,具有回阳救逆、助阳行水之功能,用于肾阳衰微,身面浮肿,腰以下肿甚,既能追复散失之亡阳,又能资助不足之元阳,与补益药同用,可治一切内伤不足,阳气衰微之症。《古今名医方论》云:“脾家得附子则火能升土,而水有所归矣,肾中得附子则坎阳鼓动,而水有所摄矣,更得芍药之酸,以收肝而敛阴气,阴平阳秘矣”[2];茯苓甘平,性质平和,补而不峻,利而不猛,既能扶正又可祛邪,可健脾补中,运化水湿;猪苓甘、平,入肾、膀胱经,是临床常用的利水渗湿之品,研究证明猪苓对抗肿瘤化学药物所致的免疫系统的抑制有明显保护作用,且猪苓多糖有抗癌作用[3]。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固护脾胃是补益人体正气、抵御外邪的治本之法。焦三仙,健脾开胃、消食,助脾胃健运,既可化生气血以补益后天,又可固护中州以利于药物吸收,同时可减少清热解毒药对胃的不良影响;砂仁甘温,入脾、胃、肾经,具有温脾止泻、行气止痛、温胃止呕之作用,且即可袪滞又可温胃护胃,还可用来防止大量温补药和寒凉药致气滞碍胃,戕伤脾胃;半枝莲,苦凉,清热解毒,利水消肿;金钱草,清热解毒,利湿退黄;大黄清肠通便,肺与大肠相表里,府气一通,则肺气宣发肃降皆畅, 且大黄逐瘀通经,可治症瘕积聚,瘀血肿瘤,泻火解毒,使肺热毒火顿清,大黄伍黄芪,二者甘苦并进,寒温并用,升降相因,攻补兼施,充分体现了扶正与祛邪兼顾的思想[4]。
本案治疗中,党参120 g、生黄芪105 g、红景天70 g,补气药用量大,且多味合用,具有协同作用。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云:“史观江河湖海,未有不载于土上,行于土中者。故水得之充气而足为蛟龙之所潜藏,可知肾之蛰藏必借土封之力。”[5]大剂量用黄芪,使脾得健而升清于上、运湿于中,以致水精四布,清升浊降自无湿邪内聚,精微外泻之虞。从本患者用药后的反映来看,黄芪用110 g时,会感到腹胀满不舒,而105 g则无此不良作用,可见黄芪用量须因人而异。患者皮肤有凉感,按之不温,提示阳气受损,需辅以温阳。温阳药黑附片40 g,需久煎,且至少煎煮1 h。若服药时有口唇麻木感,则提示煎煮时间不够,应延长煎煮时间。应该注意的是,补气药和温阳药是一个逐渐加量的过程,以使患者能耐受且改善症状为目的,却不可盲目加量滥补。
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同时又是吸收药物治疗之基,因此临证以时时顾护胃气为本。《素问·平人气象论篇》曰:“平人之长气稟于胃,胃者平人之长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指出胃气为人体之本,胃气的有无与疾病的治疗、转归、和预后密切相关。健脾养胃、益胃生津以清养胃气,并注意慎用苦寒有毒药物、少用走窜虫类药物、缓用力猛攻伐之品,以免伤及胃气;助胃是指恢复脾胃生理功能活动的动力,脾喜燥恶湿、主运化,胃喜润恶燥、以通为用、以降为顺,所以用青皮、焦三仙,理气畅中,消食导滞,疏导中焦以助胃气和降顺达[4]。
临床上,此类肺癌患者一般存活期多为半年,而本患者在中医辨证论治下,已存活近一年,且病情平稳。
2 结语
咳嗽、痰喘是临床常见病,多以外感或内伤,或内外因相感致肺的宣、降功能失常而引发本病症。理论上,尽管咳不离乎肺,但又不止于肺,正如《素问·咳论篇》曰:“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因此,临证时既要明辨咳嗽的致病因素,又要注意患者自身体质状况,以及病情久暂所致的邪、正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注重肺宣发肃降、主治节失常的病机变化,又要考虑肺与其他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辨治之时,既要祛邪,又要扶助正气;既要宣肺降气,又要调理相关脏腑。只有做到四诊合参,整体审察,灵活用药,才能收到治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