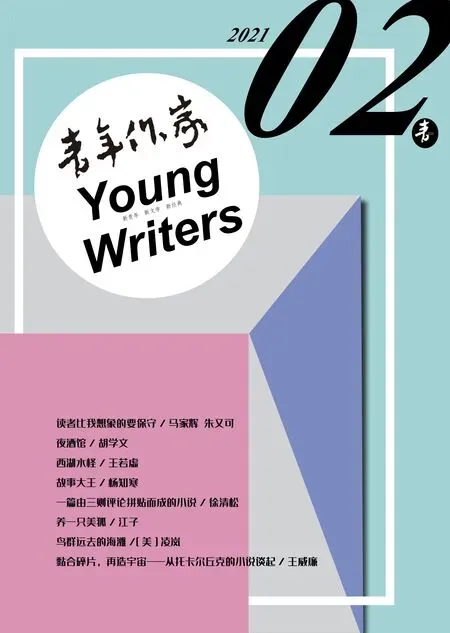鱼王塘传说
于则于
一
鱼王塘在陈庄西北,不大,四周长满桑树。塘水墨绿,幽深不见底。传说直通东海龙宫,有鱼王把守。塘边孤零零两间红砖瓦屋,是陈宇营的家,老太婆死后,剩他一个人又住了快十年。他是兽医,以前庄上家家都喂牛,一年到头少不了请他。现在英雄无用武之地,每天在庄上和鱼王塘之间来回走,走几趟天就黑了。
这天他到陈宇德家门口,被陈宇德叫住,让到院子里坐。原来陈宇德喂了头羊,大肚子,快生了,让他看看。生就生呗,你叫我看啥。嘴里虽这么说,人还是在凳子上坐了下来。陈宇德递过去一直支烟,给他点上。我也不知道是咋了,总觉得心里惶惶的。陈宇德也坐下来,一起看着面前的母羊。这羊也是作死,从昨天晚上就叫唤,硬生不下来。你赶它站起来,这么卧着可不行,陈宇营说。陈宇德走过去,嚯嚯地赶。母羊不情愿地站起来,走几步,凄厉地叫。十分疲惫似的。陈宇营说,这羊,肚子里至少得有四五个小羊羔,怪不得生不下来。再等等。陈宇德便又回去坐着,把手里的烟放到唇间,狠吸一口。
母羊换个地方又卧下去。
陈宇德问陈宇营,你刚才从鱼王塘过来,看没看见一阵人?陈宇营看见了,问陈宇德他们是干啥的。你没看见他们车上拉的机子?要打井呢,天旱成这样,上面拨的钱,要打井浇庄稼。他接着说,早上陈勇从路上过,见人就说这回好了,上面给钱了,叫打十四口井。十四口井?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四个角上,再加上雁河外边,一共打十四口井。陈宇营不说话,陈宇德又说,陈勇比他叔强,听说过段时间还要装太阳能发电,到时候用电就不要钱了。陈宇营住得远,庄上的电线拉不过去,一直都是点煤油灯,用电要不要钱跟他都没关系。
他从鼻子里哼一声,半天才问,太阳能发电装哪儿?陈宇德说,听人说是要把杨树林子砍了。往上说一百年,杨树林子是庄上的坟地,埋了不少先人。后来不埋人了,各家都栽杨树,长得快,好卖钱。杨树砍几回,里面的坟虽都渐渐平了,但装上发电机,成天轰隆隆响,不知道先人还能不能睡得安稳。陈宇营的太爷太奶也埋在那里,他心想真到那一天,要迁坟也不容易,挖出来估计骨头都散了,混在一起,分不清楚谁是谁的。
陈勇说鱼王塘那边不打井了,塘里有水,旱不着旁边的几块地。陈宇德又感叹一句,那几块地才真是好地。但陈宇营接过去说,他懂啥是好地。陈宇德说,好地是我说的。
陈宇营的烟抽完了,烟屁股在手里夹半天,才扔出去。
陈宇德忽然靠过来,压低声音问他,都说鱼王塘里有鱼王,老哥你到底见过没有?天旱成这样,陈勇要真抽塘里的水浇地,还不把水抽光了。到时候真有鱼王恐怕也藏不住。陈宇营看他一眼,不回答,反问他说,你也活了七八十年,你见鱼王塘啥时候干过?那也是那也是,陈宇德说。
母羊站起来,烦躁地走来走去,嘴里一声接一声叫唤。差不多了,陈宇营说。陈宇德从坐的地方站起来,但他不知道要干啥,空站着,手没地方放似的。陈宇营让他去抱一抱麦秸来,他去抱来,铺在地上。母羊把头凑过去吃两口,又掉转身子。他们看见,母羊屁股后面有一个青色的东西出来了,是小羊的蹄子。母羊叫得厉害,前腿跪下去,整个身子都在朝后使劲。小羊的蹄子出来一点,却又没动静了。母羊卧下去,嘴里已经叫不出声。陈宇营走过去把母羊赶起来,跟陈宇德说,看上去是要难产,你去弄盆洋胰子水来。说完开始朝上捋袖子,按住母羊,用一只手去拉出半截的小羊蹄子。
陈宇德把水端来,陈宇营洗了手、洗了胳膊,让陈宇德帮忙按着,手伸进母羊屁股里掏。半天终于把小羊掏了出来,丢在麦秸上。母羊转过头来,在小羊身上舔,没动静,小羊已经憋死了。母羊肚子还鼓着,陈宇营又把手伸进去掏,这回比较顺利,很快又掏出一个来,仍是死的。陈宇德在旁边叹着气,问还有吗?陈宇营说,没了,羊羔子这么大,我还以为有四五个呢。又说,怪不得生不下来。
母羊仍不停地舔着小羊,舔完一个又舔另一个。小羊身上的黏液被舔干净,毛卷成一圈一圈的,直到脸上。脸上,小羊乌青的眼睛紧闭着,十分硕大,跟身体不成比例。腥臭的气味吸引苍蝇聚来,都落在小羊眼睛上。母羊像是在帮小羊赶苍蝇。
陈宇营又洗一遍手,甩干,在凳子上坐下,从兜里掏出烟点上。陈宇德站在那里没动。陈宇营说,现在羊也卖不着钱,不喂就不喂了吧,我看你天天割草放羊也累。陈宇德吐一口气,然后才回去坐下。他没说话。
陈宇营又陪他坐一会儿,站起来走了。到下午,他在杨树林子里拾干树枝,打算捆起来,拿回去当柴烧。一个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跑来,递给他两盒烟,说是陈宇德给的。德老太爷说不能让你白忙活,叫我给你送两盒烟,我跑鱼王塘去没找着你。陈宇营看这孩子眼熟,想问他爸是谁,可低下头把两盒烟在兜里装好,再抬起头,孩子已跑远了。
二
陈宇营不急着做饭,先到屋后面坐着乘凉、吸烟。他面前隔着棵桑树,就是鱼王塘的水面。天长,太阳虽落了山,还有晚霞将白日延续着。霞光倒映,水面上开了布店,红的黄的交织一大片。抬眼间,陈宇营看见飘在塘边上的小船,他一直藏在桑树根底下,怕在水里一直泡,泡烂了,不知道被谁拉了出来。他骂一句,站起来,朝小船走过去。水边凌乱踩着许多脚印,都不大,大脚拇指压出来的坑才跟蚕豆似的,应该是一群孩子。他想起下午送烟给他的那个孩子。心想下次看见得训他几句,要不一定会闹出啥乱子来。
没系缆绳,船竟没飘到塘中间去,还真是运气好。陈宇营双手用力,想把船拖上岸来,一下子没拖上来,船底在水面产生波动,朝外荡漾开去。他的眼睛跟着水波走远,忽然就有些神往。他已经很久没到塘上去了。
于是他又重新用力,把船往水里推,人也坐进去。船底放着一根木棍,那是船桨,他捡起来,在岸上抵一下,船就往塘中间滑去。塘水泛着光,平静如水泥地。他用手里的木棍胡乱拨几下,便停了手,任船飘着。他抬头看天,天上的霞光正慢慢退去;又看四周,四周桑树阴森森的像要扑过来;再看水,水下漆黑一团。他忍不住心里有些发怵。
老太婆刚死那一年,他几乎天天都把船划到塘中间去,坐在那里等天黑。天黑了,月亮浮上来,黑色的影子也都从水底浮上来,把他围在中间。他跟他们说话,能说到半夜。他们有时候回答他,有时候不回答,他就自己说,累了,才把船划回去。他知道他们中有他闺女儿子,有老太婆。大殓后,他趁夜深,人都走光了,把老太婆从棺材里抱出来,用半扇石磨绑好,一起沉到塘底下。第二天封棺,他握着锤子钉棺钉,一边钉一边喊着让老太婆躲,喊得很不用心。等到出殡,抬棺材的人都说他老太婆心善,死了也不拖累人,棺材轻得像纸盒子。棺材板虽是桑木的,却是早做好放了几年,已经干透。棺材里只有一张草席、几件单衣服,棉衣服都没有。棉衣服里的棉花还能掏出来再用,埋地下白可惜了。哪能不轻?陈宇营自己也想到塘底下去,去和他们在一起。但他知道没那么容易,死后身不由己,埋他的人不会替他想的。除非他跳进塘里淹死,身上绑着剩下的半扇石磨,沉到水底淤泥里,漂不上来,他们也捞不到。他都算计好了,只等一个时候。
时候快到了呀——他没忍住说出了声。
如果陈勇真的要抽塘里的水浇庄稼,就算抽不干,水浅了,说不定也会露出塘底的骨头架子,那样他就真的活不成了。骨头肯定还会有的,以前他们挑河工,常能挖出骨头来,有些颜色发黄,老人们说是百年前死的人。可见人烂得快,骨头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烂干净。
陈宇营想塘底还有其他的人也说不定,百年前的人。那样他倒不用太害怕,他们不会轻易就怀疑到他头上来。但除了他自己,他也得替他闺女儿子和老太婆想,死都死了,不能再把他们捞出来,晒在太阳底下。老太婆不怪他,闺女儿子却不一定。淹死的时候没能把他们捞上来埋在土里,他已经是后悔不已,现在要是把他们捞上来了,他怕是真的没脸再当他们爹。
闺女儿子死的时候,陈宇营记得他才不到四十岁,赶集遇见孙王庄的亲家,到年就把闺女嫁过去了,亲家怕出啥岔子,要跟他再商量商量,非让他到家去喝酒。他喝醉了,倒在孙王庄外面的麦秸垛上睡半下午,回到家天都黑透了。闺女儿子没回来,老太婆那时候还不是老太婆,是他年轻力壮的媳妇。她担心,出去找一圈没找着。见他回来,让他也去找。他不当回事,串了几家门问,问不出啥,就回去吃晚饭,桌底下摸出瓶子,又给自己倒了二两酒。准备睡了,闺女儿子还没回来,他才开始觉得不安,嘴上一连串地骂着要把他们的腿打断,看以后还怎么野。他媳妇拿了手电筒挨家问,问到有人说没看见他们闺女,就看见晌午他儿子朝鱼王塘去了。他们跑去看,塘边看见儿子的一双鞋和一件短褂子。鞋是白里黑面的单口鞋,短褂子是粗棉布缝的,盘云纹扣子。用手电筒朝塘上照,塘面黝黑,不惊波澜。不用说,闺女也在塘里面了,儿子是下去捞她的,要不然也不会脱了鞋和短褂子。
那天晚上,陈宇营肚子盛满了酒,脸上热,被夜风一吹,禁不住打寒战。再过一会儿,他媳妇便哭开了,他不耐烦,啪啪扇她两个巴掌。她把哭声咽回去,以为他要怎样,但他许久也没动静,她便又嚎了出来。声音凄厉,前后几个庄都听得见。后来他们在鱼王塘边盖了房子,守着闺女儿子,前后几个庄上的人仍不时听到凄厉的嚎哭声。
陈宇营的闺女儿子似乎是开了个头,之后的几年,鱼王塘里便经常死人。先是赵庄的小开,嫁过来第二天跳进去的,捞几天没捞上来。然后是陈宇清的闺女,三天回门时候路过鱼王塘,不知道怎么就掉进去淹死了。然后就接二连三,死的多是刚嫁娶没多久的年轻女子,多是和陈宇营的闺女一样的年纪。于是便渐渐有了传言,说嚎哭声听上去像人哭,其实是鱼王的长啸。鱼王想吃人,不得,所以长啸当哭。算起来,都是陈宇营的闺女儿子让鱼王开了戒,腥了嘴,所以才索了其他年轻女子的命。一时间,前后庄上传得沸沸扬扬,说啥的都有。
传说一开始也许是有人附会,或大人故意编来吓唬小孩子的,但传久了连陈宇营自己也分不出真假来。好几次夜里听见,他似乎真觉得那凄厉的声音是从塘底发出来的。但伸一伸脚,碰不到老太婆的热身子,他才知道是她又去了塘边。陈宇营便披上衣服起来,拿一件衣服,走到塘边,把衣服给他媳妇披上。他不敢劝她,就蹲在她旁边听她边哭边说。她说的都是后悔的话,说如果不是她没看住,闺女也就不会跳塘死了。她哭够了,说够了,才站起来往回走。第二天问她,她啥都不记得。陈宇营想她也许是故意的,也许是真的梦游。也许她已经不是她了,她被鱼王附了体,不嚎到嗓子流血是停不下来的。后来她果然得了细病,嗓子像被绳扎起来,吃东西咽不下去,活活饿死。
风一阵阵地吹在陈宇营身上。他头耷拉着快睡着了,一个激灵又醒过来。他看见一道比黑夜更黑的影子从水底浮上来,围着小船转。然后又有越来越多的黑影浮上来,像是真的有一群大鱼,真的有鱼王在他们之中。
他看着他们,嘴里喃喃地说,都别急,别急,总会有办法的。
三
陈勇小时候见庄上打井,都是两个人,用一根木棍绑在铁管子上,推磨一样转圈,把铁管子一点点磨到地下去。下到五六米,水冒出来,插一根空心管子进去,井就算打成了。再朝前,听说井是挑出来的,两个人到底下去,朝上挖土,直挖到水眼。现在打井真是简单得多,一个螺旋的钻头,发动机打开就朝下钻,一边钻一边把泥甩上来。机器上定好数字,没一会儿就钻到了三十米,钻头拉上来,地上就有半米宽的一个洞。打井的人车上拉着砖头水泥,在洞边砌几层作栏杆,防人掉下去,井就算打好了。陈勇感叹说现在真是做啥都太方便,打井的人说这算啥,还有更方便的哩。陈勇笑笑,心想更方便的自然得花更多钱。打井的人干完,收拾东西放回车上,陈勇带他们去下一个地方。头一天下来,十四口井就打好了十一口。第二天上午再去雁河外边,陈勇本以为半上午就能结束,不耽误他去镇上,没想打第一口井就遇到麻烦,钻头钻到砂礓,嘎嘣一声断了。打井的人没说什么,似乎是常有的事。但他们没带着别的钻头,要回去换。他们跟陈勇商量,说下午再打,陈勇没办法,只能说好。于是打井的人开着车走了,陈勇自己回庄上。他脚上沾了泥,一边走一边在草上蹭,还是没蹭干净。
走到庄头,几个人坐在那里,看见陈勇,都跟他打招呼,问他吃了没。陈勇看陈宇德也在他们中间,就问他昨天羊生了几个。还生几个呢,生两死胎!陈宇德没好气地说。陈勇哦一声,然后又问他卖了没,现在县里时兴吃小羊羔呢。他说,最好就是刚生下来的,放锅里整个蒸熟,加上葱姜蒜,好家伙,一盘菜卖四百多块。四百多?快赶上一头活羊的价了,还真有人吃?当然有人吃。陈宇营也坐在那里,他见得多,知道蒸羊羔不是啥稀罕的,便不说话。陈勇跟陈宇德他们感叹完,像是突然想起啥来,转过来跟他说话。他辈分低,管他叫营爷,跟他商量,到时候用鱼王塘里的水浇庄稼,跟他借两块木板垫机子,就不从庄上带过去了。
正说这个事呢,陈宇营慢吞吞地说,浇庄稼肯定是好事,不过我就怕鱼王塘里的水不能用。咋?陈勇问他。其他人也都看陈宇营,等他把话说出来,他却又闭上了嘴。陈勇接着说,咋不能用呢,往年天旱,边上几块地浇水不都是从鱼王塘里抽水么,今年庄上用就不能用了?陈宇营说,我不是说不能用,你用就用呗。
见陈勇摸不着头脑,边上一个端着空碗的妇女跟他解释,营叔是怕鱼王塘里有鱼王,今年旱这么厉害,怕塘里的水抽干了,鱼王恼了,要兴风作浪。陈勇咧嘴想笑,其他人没笑,便又忍回去。有鱼王怕啥,水抽干正好捉上来,分给大家吃。他终于还是没忍住笑了,像自己刚才说的是一个笑话。没人应和他,他又说,我是没吃过鱼王,说不定比蒸羊羔好吃。说完又转向陈宇德,问他,德爷你把死羊羔子埋哪了,还不如我去挖出来,提到镇上去给瘸子,让他拾掇拾掇。拿着空碗的妇女抢在陈宇德前面说,天这么热,早该生蛆了。陈勇说,也是。然后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就走了。
等陈勇走远,陈宇营才在嗓子里咳一声,吐一口痰,把手里的烟屁股也扔出去。拿空碗的妇女问他,营叔,你到底见没见过鱼王?陈宇营点一下头,然后说,我还真说不好,白天是没见过,晚上就看见有黑影子,尾巴一甩,半个鱼王塘那么大,水哗啦啦响,不是鱼王是啥?陈宇德在旁边点头,等陈宇营说完,他接着说,我就说那一年去刘集,夜里从鱼王塘走,看见水里黑乎乎一条大鱼,我还说拿网去逮,后来俺娘非不让去。现在想想,可不就是鱼王。又说,不说这个,就问问前后几个庄上的人,三十年前,谁没听见鱼王成夜叫唤?拿空碗的妇女说,那时候都说是风吹得响,不是鱼王。但等一会儿,她又说,要真有鱼王,可不能让陈勇那个憨货抽干塘里的水,那几年不就连着死好几个新媳妇,谁知道会再出啥事。她旁边抱着孩子的是她儿媳妇,一直没说话,这时候插嘴说,我也听人说了,死好几个新媳妇,到底是咋回事?妇女瞪她一眼,指一下陈宇营,然后朝她使了使眼色。陈宇营没动,脸上也没表情。儿媳妇又说,我看也不能抽,这种事,说不准就是真的。人家旱天都是拜龙王,咱要是把龙王的家都拆了,谁知道会出啥事。陈宇德看着她,点点头,然后说,是得想个办法。
他们再说一会儿,天就快晌午了,拿空碗的妇女最先觉得时间不早,手里的碗底都结了一层嘎巴,便先走了。她儿媳妇怀里的孩子要奶奶,也跟着走了。陈宇德问陈宇营,昨天的两盒烟给他没有,陈宇营说给了。他也正好想起来问他那是谁家的孩子。陈宇德说,不就是陈勇的那个侄子么,他哥跟他嫂子在外边,儿子丢家里让陈勇两口子看着上学。陈宇营哦一声,没再说什么。
人不说话了,蝉声就特别响,趴在耳朵根上似的。太阳直照着头顶的树,从树叶间漏出更多的光,陈宇营一只脚全晒在太阳光下,感觉烫了才意识到。他便动动,把脚挪到阴凉里去。
陈宇德站起来,拍拍屁股,说他还得回去给母羊喂豆饼。又问陈宇营,还要不要喂别的给母羊补补。陈宇营想想说,喂豆饼就怕发奶,还是喂青草好。他又说青草也都是药,说不定哪一味就是补药,不过像蓖麻叶有毒,可不能让它吃。陈宇德又说了几句关于蓖麻叶的话,就走了。
陈宇营从兜里摸出烟来,用打火机点上,抽完,也站起来要走。但他坐太久,猛站起来,眼前发黑,差点摔下去。等眼前明亮,身子站稳,再往前走,又发现一条腿也压麻了,瘸几步才走得正常。他个子高,走起路来两个肩膀交替晃着,从后面看,像是不停地摇着头。也许是太阳晒得人发昏,他摇头是为了清醒清醒。
四
下半天,陈宇营在凉席上睡了一觉,醒来全身都是汗。他起来到外面去,外面倒有风。风里夹着几声嬉笑,他以为是自己还在梦中没有醒,转回去倒半盆水,把毛巾打湿擦在脸上,又伸一个长懒腰。却还是听见嬉笑声。他这才起疑,从窗户看出去,鱼王塘的水面上,几个孩子光着屁股,正撑着他的小船戏水玩。一定还是昨天那几个孩子,陈宇营仔细看,果然看见陈勇的侄子也在其中。陈勇吃得白白胖胖的,他侄子却又黑又瘦,胸口的肋骨一根根清晰可见。小肚子瘪瘪的,没有二两肉,下面挂着蚯蚓一样缩着的小鸡鸡。
陈宇营想该出去训他们一顿,让他们把船撑回来,他们这样闹,非得把船弄坏不可,但又有些不忍心。
太阳大,水面反射着太阳光,上下连成一片,光屁股的孩子们在其中,反而是黑色的。像镜子上的黑斑。现在他看清了,一共是四个孩子,三个在船上,还有一个在水里,手扶着船帮。水里的孩子用力晃着船,想把船上的孩子都晃到水里去。船上的孩子则打着他的手,想让他松开。水里的孩子寡不敌众,又突然被用来当船桨的木棍打在胳膊上,吃痛,手从船帮上松开。随即头就沉到水里,不见了影子。船上的孩子都伸头向水里看,想找到他。陈宇营也伸长了脖子。船上的孩子嘴里笑着,没一会儿都不笑了。水里的孩子还是没露出头来。陈宇营心里不安,想马上冲出去,不知道为什么脚底却黏住了,迈不开步。他低下头去看自己的脚,心怦怦地跳得很厉害。
船上的孩子尖声叫起来,突然炸开了锅。陈宇营再看,才知道是水里的孩子钻到船的另一边,跳上船,把他们吓了一跳。陈宇营鼻子里出一口气,脚才能活动。
他走出去,冲水面上的孩子嚷嚷,让他们把船划上来,别再闹了。
孩子们怕他,不敢再闹,七手八脚地用木棍在水里滑,很快到塘边,跳下船,都朝自己的衣服鞋子奔过去。塘水脏,陈宇营看他们身上挂着一道道水纹,让他们别急着穿衣服,先去洗洗。他们怕他动手打人,都抱着衣服散开,听他这样说,不相信似的又聚拢在一起,跟着他朝小屋走。陈宇营进屋舀了一瓢水倒在轧井里,轧几下出了水,让他们自己洗。他则端一个凳子,坐在阴凉处看。
四个孩子一般大,都在庄上的小学念三年级,三年级一共六个人,还有两个是女孩。陈宇营问他们名字,只记住陈勇的侄子叫康康,其他都没记住。他让他们在塘边玩到傍晚,给他们吃他种的香瓜,然后才放他们走。他算好了他们第二天还会再来的,就等着他们,果然没失望。他们仍要划船到塘上去玩水,他故意装作不同意,直到耐不住他们的央求,才同意了。
陈宇营跟他们一起坐在船上,但船太小,载不了所有人。于是他出主意,让四个孩子都脱光衣服到水里去,像昨天那样两只手扶着船帮,跟他划船向前。孩子们起初不太掌握要领,拖得船划不动,但很快就熟练了,不仅能靠两只脚浮在水面上,还能帮着把船向前推。快到塘中间,陈宇营收了桨,让船又滑行一段距离。孩子们两条腿也扑腾得累了,都停下来,互相泼着水。不小心泼到陈宇营身上,他索性把衣服也脱了,露出桑树皮一样的上半身。他又把衣服浸到水里,搓几下,拿起来摊在船帮上。
孩子们再闹起来,晃得船像要翻了,陈宇营两只手撑住船帮才稳下来。他呵斥他们,让他们停下来,听他说古。孩子们不闹了,一边两个,用上半身扒住船,两条腿则在水里小心地踩水,好维持身体浮在水面上不沉下去。水慢慢恢复了平静。
陈宇营说,很久以前,鱼王塘还不叫鱼王塘,叫啥,他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他呢。后来为啥叫鱼王塘了呢?因为鱼王塘里有鱼王,康康插嘴说。陈宇营看他一眼,然后说,康康说得对,有了鱼王,所以才叫鱼王塘。鱼王是东海龙王派来守在这里的,因为这里直通东海龙宫,另一个孩子抢着说。陈宇营说对,你们还知道啥?康康说,东海龙宫里有法宝,龙王怕人去抢法宝。一个孩子说,有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金箍棒在孙悟空耳朵里,不在东海龙宫,笨蛋。被骂笨蛋的孩子打了骂他的那个一下,那个则朝他脸上泼一把水。陈宇营拦住他们,然后说,你们都不知道,其实鱼王是要吃人的。这塘里以前有小鱼,鱼王来以后把小鱼都吃光了,后来没东西吃了,就吃人。庄上的人想求鱼王保佑,就每隔几年送新媳妇给鱼王吃,新媳妇比小鱼禁饿,吃一次管几年。鱼王才不吃人,鱼王是好的,一个孩子说。你咋知道?另一个孩子也问陈宇营。我咋知道?因为我闺女就是被鱼王吃掉的。听完,四个孩子都噤了声,呆呆地看着他。他忽然惊叫起来,快看,水底下那是啥!四个孩子都扭过头去看,一边问哪儿哪儿,一边吓得身子朝船上窜。
船翻了。
掉到水里的那一刻,陈宇营还在想刚才听他讲故事,四个孩子围在船边上,和以前每天晚上那些黑色的影子围着他,听他说话的场景很像。以后这四个孩子也会变成四个黑色的影子,加入他们中间吧。可惜的是,再也不能听他说话。他想陈勇他们肯定会把他们捞上来的,就算捞不上来,把水抽干也能找到他们。但他管不了那么多。或者他们这样死在鱼王塘里,说不定真能吓住陈勇,让他以为是鱼王生气,不敢再抽塘里的水。
不管怎样,总算都没他啥事了,他死了,还拉几个垫背的,对他闺女儿子,还有老太婆都能交待了。带着泥腥气的塘水朝他嘴里灌,他张大嘴让水灌进去,他想灌吧灌吧,灌得越多死得越快。
五
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他们从镇上给他做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见义勇为”四个字。陈勇带人给他送过来,还买了一挂鞭炮,炸得震天响。陈宇营想,他们像是给死人上坟呢。但他还是赔着笑,看着他们走到他床前,围着他或站或坐着。乱哄哄的,陈勇让他们安静下来,说了一通话。总之是感谢陈宇营,多亏他住在鱼王塘边,要不是他,四个孩子可能都得淹死。而他也因为救他们生了病,躺床上半个多月还没好。所以他代表庄上,也代表四个孩子的家长来给他送锦旗。为了表示郑重,陈勇又把锦旗拿在手里,站起来走到陈宇营床前,双手递给他。四个孩子都没来,除了康康爸妈,其他几个孩子的家长却都来了,他们商量说要给陈宇营磕头,陈宇营死活没让他们磕。他说等我死了再磕吧,他们也只能不磕了。
接着他们就说起鱼王塘来,说起鱼王的传说,陈宇营不愿意再多说,但他们一直问,由不住他不说。他就仍搬出先前的那一套话,末了说这几天热,孩子们天天都来玩,我看不会出啥事,也没拦他们,谁知道就出事了,真说不好是咋回事。四个孩子也都咬定他们看见了鱼王,一个黑色的影子,有两层楼那么长。他们的家长这时候说出来,都担忧地看陈勇,让他拿个主意。陈勇倒说起打井的事,十四口井都打好了,上面拨的钱也用完了。鱼王塘这边要再打一口井,除非庄上出钱。
他们走了,陈宇营把锦旗捡起来,扯着上面金色的绳子摊开来看,字是金色的,布血红,让他眼晕。他用手揉几把,胡乱塞在床边。到下午,有人拿了几捆黄纸到鱼王塘来烧,到陈宇营屋里借火。陈宇营问他们烧给谁,他们说是陈勇交待的,烧给鱼王。陈宇营问他们,陈勇还说啥了。但陈勇没说啥了。
到底还是抽了鱼王塘的水浇地,陈宇营躺在床上起不来,让照顾他的侄媳妇出去看,侄媳妇不耐烦,出去看一眼,回来说水多着呢,抽不干。他不放心,夜里偷偷地下床,脚放在地上,人站起来,却立即就摔了下去。两条腿使不上力,像两截木头。他用手又掐又捏又捶了半天,才勉强站起来。床边,挨墙竖着锄头,他拿锄把当拐杖,勉强才能挪动步子。他想真的是时候到了,生一场病,床上躺半月,就到了这个地步。或者不用等陈勇把塘里的水抽干,他就先走了。
他就这么一点点地把自己挪到了鱼王塘边。塘里的水确实还多着呢,月光下泛着波纹,浩浩荡荡似的。他放了心,露出笑容,但没过一会儿而又流下眼泪来。他拾衣襟揩揩眼睛,心想一定是风的缘故。夜里风大,连塘边的桑树都被吹得簌簌响,更别说是他一个病人了。他扶着锄把坐下去,坐不住,几乎是瘫在了地上。
眼泪水又流出来,但他没再擦了,眼泪水顺着他脸上的沟壑布散开来,转眼又被风吹干了。脸上痒,他才拿手抹了一把。老太婆临死的时候,也是躺在床上流眼泪,他不停地替她擦。老太婆说不出话了,眼泪是她最后告诉他的话。再朝前,则是闺女儿子,他哪能没替他们擦过眼泪。他想,闺女儿子,还有老太婆,他们在召唤他呢——
第二天清早,浇地的人先来,从塘的另一边看见这边的红布,跑过来看,见是送给陈宇营的那块锦旗。上面的绳子挂在锄把上,锄勾着岸边的桑树。另一头则挂着陈宇营的脚。陈宇营头朝下泡在水里,早就断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