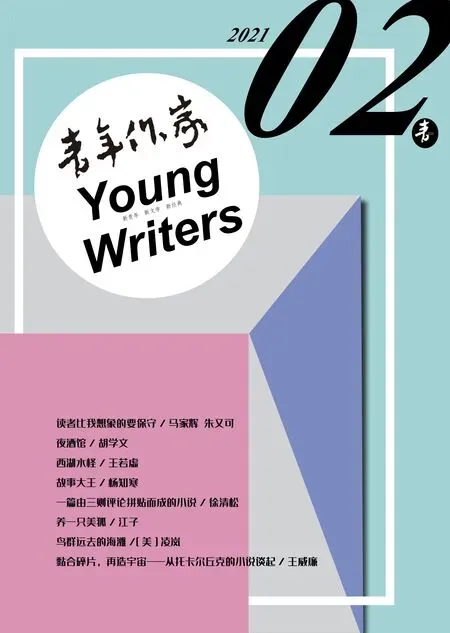口袋子
武 歆
一
李晓莉走进病房,凉气还浮在外衣上,目光也没安稳,病床上的老李便向她扬起枯瘦的胳膊。
不用问,李晓莉也知道老李的意思。她依旧慢慢脱外衣,大事小事跟他作对,较着劲儿,她心里才算痛快。
老李见她慢待的表情,不说话,喉咙里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是一条筋疲力尽的老狗发怒。
李晓莉把外衣夹在胳膊下,懒懒散散弯下腰,伸出两个手指头,捏起掉在椅子下面的口袋子,顺眼一瞅,袋子上面印有药品广告,质地很差,不用对着光线看,都能看见布纹间稀松的缝隙。
她站在病床旁,看着脸色暗黑的老李。父亲老李的目光,像他的脸色,也在逐渐黯淡。
老李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李晓莉末尾。
李晓莉的两个哥哥,一个溺水早亡,一个躲债远走他乡。
李晓莉的母亲去世早。母亲咽气时,小学二年级学生李晓莉刚从烈士陵园扫墓回来,来不及脱下白衬衣、蓝裤子,趴在母亲身上“呜呜”哭起来,眼泪把脚上的白球鞋打湿了,鞋上的白粉流到砖地上,一条弯弯曲曲的线,看着特别柔弱委屈。
老李家五口人,算下来,几十年里都是李晓莉和父亲两个人一起走过来的。在老街坊眼中,好像老李家一直就是两口人。
这些年里,老李腿脚不利索,走路两腿互相打架。眼睛和脑子却是好使。
老李问:“你啥时搬家?”
李晓莉说:“下个月。”
老李命令说:“到我那儿拿口袋子去。”
李晓莉“嗯”了一声。有时候,较过几次劲儿,她又觉得对不住父亲。他还能活多久?
李晓莉下个月搬家,把大房子让给准备结婚的大龄儿子。
晚婚晚育的李晓莉,儿子才三十出头,个子高,亲朋好友喊他“大个子”。
大个子不爱说话,却有个艺术性很强的职业,策展人。最近脑瓜长草,又爱上了音乐集会,成了两个领域双跨的艺术人。经常联络一些艺术组织或是策划团队,组织一些满脸胡子拉碴、裤子破洞的青年,专门在废弃的厂房里组织艺术演出或是艺术展览。
李晓莉与儿子相依为命。她的男人一辈子不着边际。不着边际男人的三个硬性指标,喝酒赌博打老婆孩子,他全都满分。李晓莉这个当娘的,管不了自己的男人,只能加倍心疼儿子。前些年,男人死了,李晓莉可以做主了,自己住小房,也要把大房子让给儿子,伸把手,暖暖心,让儿子忘掉童年惊恐,忘掉少年仇恨,做个心智正常的人。
老李倒是支持女儿,对外孙格外关爱,转过头,喉咙里响了几声之后,还是不忘叮嘱女儿:“多拿点口袋子,搬家没有口袋子哪成?听见了吗?多拿点!”
李晓莉只好辅助高兴的表情,连声应答:“爸,放心吧,我去拿。”
老李还不忘一件事,命令女儿晓莉,让小宝来看我,一个礼拜没来了。
老李嘴上的“小宝”,就是李晓莉的儿子“大个子”。
二
老李住院一个多月了。不,快两月了。
老鳏夫的家,像凄凉的荒原;没人住的老鳏夫家,除了像荒原,还像寂寞的戈壁。
自从父亲住院,李晓莉还没来过,暖气不热,屋里阴冷刺骨。地上悬浮着灰色的尘埃,她提着气走,生怕打扰尘土。这段时间忙乎儿子婚事,怠慢了父亲。见面与父亲较劲儿,可是转过身去,心里又是内疚。
开了卧室门,打开床边的木柜子。
柜子里的口袋子,多大的都有,多小的也有。大的,能把一个成年人装下;小的,只能装一把勺子。这些口袋子,有商家搞活动时免费赠送的,有各种展览会、展销会用来包装材料的,也有运输物品所用的内包装……老李不知从哪儿捡来的,据说还有的袋子,是老李腿脚灵便时,没事逛商场随手买来的。
老李喜欢口袋子,过去身体硬朗时,经常一个人在家里折腾口袋子,偶尔停下来,向窗外眺望,眼神迷离。
李晓莉小时候听母亲讲过父亲家族和口袋子的故事。
民国时期,李晓莉祖父被土匪绑架,向李家索要赎金。李家乡村豪绅,倒是有些银两,可是绑匪狮子大张口,赎金太高,假如满足了,李家老老少少马上就要去讨饭吃了。几番讨价还价,扯来扯去,绑匪没了耐心,不再搭理李家。
几天后,李家院子里“飞进来”一封信,简单几个字,“你们收尸去吧。”那封“收尸”的信,套在一把闪亮的飞刀上,深扎在李家大院子里一棵银杏树上。
小河边有一间废弃的草屋。草屋的远方是一片阴森森的树林。荒野上没有一个人。河边长着半人高的蒿草。草屋周边没有一道车辙,平展展的。李家人一路都在琢磨,周边没有一道车辙,好长时间也没有下雨,人是怎么到了这里的?
李家人胆战心惊地进到草屋里,一个木头柜子,干干净净立在中央,屋内再没有其他东西。众人屏住呼吸,不敢出声。几个汉子用锄头小心翼翼地撬开木柜子,看见一个圆鼓鼓的米袋子。上好的白布,织得很细,就是放进一把刀子,也不会刺破口袋子。口袋子一端被眉毛粗细的麻绳捆扎,特别紧,能够想象出来捆扎麻绳人的模样。不一定膀大腰圆,手掌也不会有多大。但一定是个心细的人,有的是时间,蹲在口袋子前,慢慢捆扎的。
众人不用走脑子,立刻猜测出来,口袋子里装着一个四肢团起来的人。老李那时候还是青皮小子,躲在叔叔身后,闭紧嘴巴。叔叔攥着一把刀子,壮着胆子上前,有力地咳嗽一声,刀刃朝上,用力,再用力,才把麻绳子挑开。木柜左右的李家人,齐刷刷地“啊”了一声。
母亲跟李晓莉说,你爷爷死在盛米的口袋子里。
很多年以后,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有画面出现在李晓莉眼前。祖父身边都是闪闪发亮的大米,祖父嘴巴里、耳朵里也是大米。祖父愤怒地睁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眼睑里也有几粒大米。李家人合力把人从米袋子里拽出来,伴随着僵硬的尸体,大米“哗哗哗”流了一地。地上的尘土,随着米粒肆无忌惮地飞溅起来,久久不肯落下。
李晓莉曾经问过母亲:“绑匪为何把爷爷捆在米袋子里?”母亲说:“笑话老李家贪财呗。”李晓莉又问,“把人放在米袋子里,就是笑话人吗?”母亲叹口气,想要解释,又有些慵懒,摆摆手说:“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长大后的李晓莉,有一次又问母亲:“我爸怎么这么喜欢口袋子?”
母亲说:“你爷爷不是死在口袋子里吗?”
李晓莉还是不解:“那……那我爸恨口袋子才对呀?”
母亲说:“越是恨,越会喜欢。”
李晓莉更糊涂了,还想再问。
母亲还是那句话:“你还是小,以后就会明白了。”
还没等李晓莉继续长大,母亲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教会学校上过学的母亲,咽气时,面色安详,一点没有留恋世间的神情。
想起往事的李晓莉,站在父亲装满各种口袋子的木柜子前,还是不明白父亲为何这样热衷收存口袋子。
三
大凡琢磨不透的事,就总要琢磨。父亲热衷收集口袋子,李晓莉想起来这件事,关于父亲的往事就会波浪翻滚。
李晓莉听老邻居讲过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件事。她问过父亲,求证真伪。父亲“嘿嘿”一笑,点点头。
1949 年1 月,共产党的军队马上就要攻进来了,城市快要解放了。大街上的警车呼啸而过,天天抓人,天天杀人。城市外面挖了一丈多深的壕沟,城外所有民房、树木,或是拆毁或是烧掉。视野开阔,一眼望穿。架上几挺重机枪,多少英雄好汉都无法前行。通往城外的道路,角角落落都布上了地雷。城外几十公里处,是共产党的围城军队。
已经围城一个多月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老李是个裁缝。老李学徒的师傅是宁波人,手艺高超。老李最初学做西装,面对上层人士。后来北方吃紧,有钱人跑去南方了,做西装的人越来越少。老李不再讲究,什么衣服都做。就连过去看不上眼的小棉袄也做了,攥着手工钱,来不及揣进口袋里,忙不迭地跑去买玉米面,不买怎么成,过一会儿,又涨价了。
围城前夕,老李彻底回家,自己单干。摆上一台缝纫机,做些劳苦百姓的衣服。缝缝补补的小活儿也做。兵荒马乱,谁还做好衣服,命要紧呀。肚子里的埋怨,早就让老李不顾及身份了。
围城那段日子,白天还算平稳,到了晚上,大炮响个不停。家家户户都用棉被把窗户挡住,害怕漏光。街上人传说,外面的炮弹长眼睛,哪有光亮,炮弹就奔哪儿。
这天傍晚,老李住的院子,走进来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人。头发很短,露着青色头皮。脚上一双黑色布鞋,鞋面非常干净。中年人自我介绍“免贵姓王”。
老李问:“王先生,啥活儿?”
王先生说:“面口袋子。”
王先生倒是本地口音。只是话多时,偶尔会蹦出来山东尾音。
老李疑惑:“我可是裁缝,面口袋还用裁缝做?”
王先生笑了,说:“杀鸡有时也用牛刀。”
老李看着王先生,静等下文。老李天天跟人打交道,啥人都见过。没见过找裁缝做面口袋的主顾。
王先生说:“我们东家是粮老板。运粮食得用口袋子。李师傅手艺好,远近闻名。”
老李咂吧一下嘴,点点头,算是答应了。
王先生说,早上我把布送来,太阳落山前收活儿。一个口袋子五毛钱,一天我要两百个。老李惊问,这么多呀,怎么做得了?王先生说,做得了、做得了。老李较真儿,说,面口袋子要做结实了,线开了,那就糟了。王先生笑道,我这面口袋子,不用太结实,大针码,粗点,明白吧?
老李眨巴眼睛,没明白。面口袋子怎么是大针码?虽说心里不明白,脸上却是不动声色。
王先生见李裁缝不语,笑起来,主动说:“您还想加价呀?”
老李拿着劲儿,说:“哪有一口价的活儿,有些话不用讲,心知肚明。”
王先生没言语,眼睛看着窗棂。窗棂上的窗纸已经破旧,才过完新年,没多长时间。
王先生忽然自语道:“火烧云呀,明个儿可是好天呀。要变天了,是不是李师傅?”
老李看着王先生意味深长的目光,刚想要说“算了,五毛就五毛”,可王先生开口了,“好,再给你加一毛”。
老李立刻答应下来。
转天一早,王先生带着伙计来了,问老李布匹卸哪儿?老李走出院子,看见一辆手推车停在院门口,推车的小伙子正在擦汗。腊月的天气,小伙子头上冒着热气。小推车上堆着粗白布,一米多高。老李指挥伙计,把布匹搬进屋里。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满满当当。王先生拿出一打钞票,放在缝纫机上,笑着说,李师傅辛苦了,我天黑前来。
王先生一连来了三天,全都满意而归。老李用的大针脚,只要一用力,口袋子就能轻易撕开。王先生看了看大针脚,却是特别赞赏,连声夸赞“好好”。
第四天,出事了。
院子里一共六间房,四户人家。阳面的房子,一拉溜三间,住着一户人家;阴面的房子,也是三间,却住着三户人家,都是老实巴交的人。
阳面房子人家,不简单。姓马,跑合的。书本上管“跑合的”称作“掮客”,给生意人搭桥做生意的中间人。老马能说会道,把死人说活了,随后再把活人说死了,外号“马铁嘴”。只要马铁嘴出马,两边生意肯定能成。马铁嘴在院子里,阴面房子的三户人家都不敢惹他,裁缝老李更是躲得远远的。马铁嘴为显示自己公正,有言在先,“我不欺负老实人,可谁要跟我作对,我让他必死无疑,尸体扔到乱葬岗子去。”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你们要听我话,不听话,没有好下场。
这天早上,王先生带着伙计刚要进院子卸布匹,马铁嘴走出院子,挡在王先生面前。
马铁嘴问:“你是做啥的?”
王先生看着马铁嘴锃亮的大背头,姿态并不示弱,依旧挺直身板,嘴上却是非常客气:“做生意的。”
平日里马铁嘴饭前饭后,嘴里总是叼着一个牙签。高兴时,牙签粘在嘴唇上,一跳一跳的;不高兴时,就会把牙签“呸”地吐到地上。
已经把牙签吐到地上的马铁嘴,喝道:“做生意的?我看你像共产党!像八路!”
院子里的空气,像是顽皮的孩子,被一双强有力的大手按住,一动不动了。
老李揪着心,想要劝,又不敢劝;他知道此刻老婆抱着大儿子正躲在炕上,大概已经吓得浑身发抖了。老李第一天接下这个活儿,老婆就嘀咕,这个王先生来历不明。老李不说话,心里非常清楚,王先生身份确是可疑,哪有面口袋子要求大针脚的?都是要求越结实越好,他怎么要求扎得稀松点儿?
老李犹豫不决,木呆呆地站在那儿。
王先生面对咄咄逼人的马铁嘴,一点儿也不怕,笑道:“你说我是共产党,你说我是八路,没办法,那就是吧。”
马铁嘴想要发火,老李立刻央求马铁嘴,家里揭不开锅了,孩子还没出满月,家里的被大炮吓得没了奶水,这咋活呀?
马铁嘴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对老李说:“街坊邻居的,看你可怜。”随后又对王先生说,“你不能来了,明天要是再来,我就报官。”
王先生嘻嘻笑着,嘴里应着“好好好”,随后跟伙计一起上手,把布匹卸下来。老李也跟着一起搬,快点结束,省得麻烦。
当天晚上,王先生带着伙计把面口袋拉走了。马铁嘴对着王先生后背再次警告,明天不能来了。王先生依旧呵呵笑着,走了。
果然王先生没再来。
王先生不再来的转天晚上,大炮整夜响个不停。信号弹划破夜空,门窗挂着棉被,信号弹的亮光都把棉被给“刺”破了。
连续三天晚上,整夜大炮响。
这天一大早,院子外面响起敲门声。有人喊,老乡呀,开门呀,我们是共产党,解放了,解放了。
全院的男人都出来了,站在院子里。
马铁嘴不让开门,对着门外喊,院子里有女眷,你们去别处吧。
老李想要打开院门,马铁嘴不让开。老李迟疑了一下,终于上前一步,对马铁嘴说,解放了,解放了。
老李勇敢地打开大门,一群戴着狗皮帽子、穿着破烂棉衣、手拿大枪的军人站在门口,他们倒是客气,说,老乡,能进去烧点热水喝吗?
老李赶紧把大兵们让进院子来。马铁嘴耷拉着脑袋。大兵们站在小院里,四下看了看,一起去了阳面的三间屋子,开始烧水喝。
转天一大早,“狗皮帽子”走了。
几天以后,院子里来了一个身背盒子枪的人。进了院,正好碰见要出门的马铁嘴。马铁嘴天天与人打交道,过目不忘,立刻认出,来人竟是王先生,还认出王先生身上挎着的盒子枪是外国造的,子弹打得快、飞得远。马铁嘴的瘦脸,白得像是死人,愣住片刻,赶紧掉头回屋。
王先生喊:“老李,李师傅。”老李出来,看见王先生的装束,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赶紧把王先生让进屋。
老李说:“前几天我就猜出来了。”
王先生笑道:“猜出来我身份,还把价码抬得那么高?老李呀,你都变成奸商了,大针脚的面口袋子,硬要我六毛钱。”
老李赶紧赔不是。
王先生看看坐在炕上围着棉被、头戴棉帽子的老李老婆,还有老李老婆怀里的小孩子,摆手道:“你是劳动人民,共产党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财富都是劳动人民的,多给你几毛,那也是应该的。”
老李红了脸。
王先生告诉老李,他马上要随大部队走了,还鼓励老李说,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也作了贡献,那些面口袋子运出城外,是给部队做军服用的。整匹整匹的白布运不出去呀,做成面口袋可就方便多了,城里地下党又打通关节,哨卡守军睁一眼闭一眼了。
老李感慨,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事。
王先生拍着腰上的盒子枪,问老李,要不要教训马铁嘴?老李赶紧摆手说,你教训完了,你走了,我跟他可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王先生说,解放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不怕他们。老李连连称是。王先生稍坐片刻,忙着走了。
老李送走王先生,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嘴里不住地叨咕:“解放了,解放了。”
四
老李住院前,面对柜子里的口袋子,目光里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李晓莉在旁边给父亲收拾住院的衣服、被褥,心里不耐烦,可也懒得再劝说父亲扔掉那些破口袋子。
老李真是与口袋子纠缠了一辈子。
老李跟女儿李晓莉也讲过,这辈子,好事坏事都离不开口袋子。只要关系到口袋子的事,人生肯定是在岔路口。
李晓莉曾经问过父亲,一堆破口袋子,怎么就会与人生有关联。老李曾经不屑道,幸亏你还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有啥不明白呀?人生路口,不明白呀?”
李晓莉真的不明白,也不想再说什么,就随嘴“哦”了一声。
老李住院后,有一天情绪有些激动,对坐在病床边的李晓莉说:“当年你爹戴着大红花,走上几千人的大讲台。一条写着‘红管家’的红绸子拿在厂长的手里,厂长向台下的人抖了抖,给我戴在肩上。左肩右挎,就是绶带。当年你爹特别威风。”
“因为口袋子?”李晓莉不相信,“口袋子还能给您带来威风?您又不是拿着大刀大枪,有啥威风?”
老李总结道:“因为口袋子,你爹当年真的威风过。”
那天老李情绪好,给女儿晓莉讲起来他的光荣历史。
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裁缝师傅老李离开老本行,去了一家面粉厂当了仓库保管员。面粉厂,离不开口袋子。口袋子又不是铜墙铁壁,总有损坏的时候,裂缝、开线或被锐器戳破了。有的工人大手大脚,口袋子破一点,拿着旧袋子就去仓库领新袋子。
老李不声不响,把旧口袋子缝补好。负责后勤工作的主任来仓库检查,老李让主任看缝补好的旧口袋子。主任也没当回事,眼皮不撩,声音含在嗓子里,轻描淡写道:“好好。”领导没有表扬,老李不觉得委屈,也没感到羞辱,照旧缝缝补补。有时新口袋子没有及时运来,老李缝补好的旧口袋子便派上用场。有的工人埋怨,新社会了就要新,怎么还用旧口袋子?有个叫小蔡的工人更对老李冷嘲热讽,说老李缝补旧口袋子,分明是把新口袋子拿回家了,老李假装好人,监守自盗。
老李心里委屈,也不争辩,依旧每日缝补旧口袋子。好在门卫站出来作证,说老李大好人,一个口袋子都没拿走过,我在门卫室看得清楚。
不久,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开始,老李突然成了大红人,在全厂大会上,厂长亲自表扬老李,还狠狠批评了铺张浪费的工人小蔡,还有那个不负责任的主任。
厂长动情地说,老李裁缝出身,劳动人民,懂得节约;姓蔡的,资本家出身,少爷羔子,所以铺张浪费。
厂长激动得眼含热泪,继续说,我们全厂一针一线都是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财富!老李做得对。
又过了几年。
批斗会、批判会越来越多。
有一天,小蔡和厂里几个出身不好的人被揪上台批斗。厂里的小礼堂,平时也是食堂,开会时就会变成礼堂。
批斗会开着,突然口号声响起来,紧接着冲进来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学生。面粉厂对面是一所中学,学生早就不上课了,有的“串联”去了,有的抄家去了,还有的搞批斗会去了。
冲进面粉厂的学生们高呼口号,把工人师傅请下台,他们代替工人师傅批斗台上的坏家伙。在那场批斗中,小蔡因为反驳学生,不肯低头认罪,还骂了革命学生,情绪高涨的学生们掀起批斗会的高潮。
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学生,不知道从哪里抱来一个大门闩。女学生抱孩子一样,充满友情地“抱”给了一个壮实的男学生。男学生英武地点点头,随后一边喊着“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一边像鲁智深一样挥舞起门闩……
老李目光迷茫地对李晓莉说:“小蔡的尸首,装进面口袋子里,放在手推车上,被学生推走了。”
“死了……”李晓莉问。
老李自顾自地说:“那个面口袋子,旧的,特别小,硬是把比我高一头的小蔡放进去了,身子团缩着,像个包在包袱里的孩子。”
沉吟了一会儿,老李忽然泪流满面,说:“以后我死了,给我找个大口袋子。躺着舒服点。”
“瞎说啥呀!”李晓莉埋怨道。
老李用巴掌抹掉眼泪,嘿嘿一笑,表情倒是散淡,说:“人死了,总要被口袋子装走的,世上所有的口袋子,就是装东西用的。人也是东西。”
老李又说:“我知道自己啥时候死,我不想死在家里,死了人的房子卖不上高价钱,我要住院,我要死在医院里。”
李晓莉感觉鼻子酸酸的。
五
李晓莉刚搬完家,老李的情况就有些不妙。
老李的主治医生找到李晓莉,问她还治不治?李晓莉明知故问,是不是……不成了……?医生说,九十七岁的人,不简单了。动不了手术,肿瘤太大了,扩散了,肺部、肝部都有,骨头里也有。靠杜冷丁扛着,真不是办法。
李晓莉喃喃地低下头。
主治医生是个女子,个子不高,头发漂染过,稍微有点黄。大眼睛,鼻子尖,挺好看的。
“保守吧。”李晓莉说,“我不想让我爸受罪。他明白时也这么告诉过我。”
主治医生点点头。
老李不再输液,李晓莉守在父亲身边,看见嘴唇发干了,就用棉球蘸点水,湿润一下。不敢给他喝大口的水,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喝水,容易呛着。
主治医生悄悄说过,一个礼拜,多也超不过九天。
李晓莉悄悄地“嗯”了一声。
第三天了,老李还是清醒。三天不吃不喝,眼睛睁开了。李晓莉吓得心脏都要蹦出来,虽然坐在病床边,身子却是向后仰,好像担心父亲突然坐起来,她好躲开。老李眼珠左右动了动,嘴巴张开。李晓莉小心地俯下身子,问爸爸想要说什么。
老李声音很低地说:“我对不住……小蔡。”
“小蔡?”李晓莉问,“哪个小蔡?”
老李说:“面粉厂的同事。”
李晓莉怔了怔,想起前些日子父亲跟她说过的早年往事。老李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堆话,李晓莉经过一番梳理才恍然大悟,原来父亲要说的是,当年面粉厂开批斗会,街对面那所学校的学生突然冲进来,“接管”了批斗大会,小蔡因为顶撞学生,被学生用门闩砸中脑袋,死了。原来是老李偷偷跑去学校告诉学生的。老李想让学生教训一下小蔡,以后不要浪费公家东西,工人的话你不听,“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话你还不听?可是没想到……青皮小子们手脚重呀……
老李说完这件事,精神放松了,又闭上眼睛。
这一闭,再也没有张开。
老李去世了。老李消耗了九天才走,达到了人的生命极限。
李晓莉看着父亲的遗体,看着瞬间惨白下来的脸,木木地站着,不知道怎么办。主治医生小声说,人走了……是拉回家里,还是太平间……还是殡仪馆……
李晓莉要给儿子打电话,手机明明拿在手里,却对主治医生讲找不着手机了……哪儿去了。
这时,有两个小伙子站到李晓莉身边,个子不高,面无表情。他俩什么时候来的,李晓莉不知道。
主治医生告诉她,这是医院太平间的人。
人死了,要么赶紧拉走,要么送进太平间,死人不能在病房停留太久。可是李晓莉哪敢拉回家,答应放到太平间。
“怎么走?”李晓莉问。
其中一个黑眼圈的小伙子,把手里一个浅褐色的口袋子举了举。李晓莉不解,目光茫然。主治医生小声告诉她,尸袋子。李晓莉这才机械地点点头。
另一个小伙子不知道从哪里推来一辆车。两个小伙子把尸袋子的拉锁打开,把老李“顺”进口袋子里。
可是袋子小,装不进去。
李晓莉大喊起来:“不装了,太小,太小。”
黑眼圈小伙子说:“这是最大的,最大的了。”
李晓莉无奈地蹲下身子,双手扶住运尸车,呜呜地哭起来。主治医生也蹲下来,用手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说着柔软的安慰的话语。
老李终于“走进”了那个浅褐色的尸袋里。真的有点小,老李的双脚直直地板起来,勉强装进去。
六
老李火化了。
按照当地习俗,他的衣服还有生活用品也要一同烧掉。到了“那边”也还是要用的。“那边”也是离不开吃喝拉撒睡这些琐碎的事。
李晓莉带着儿子,把父亲生前的衣服、鞋子、碗筷还有一柜子的口袋子,都拉到了火葬场旁边一个小广场里。那是专门进行这项仪式的地方。小广场有许多乡村猪圈一样的砖砌围挡。人们躲在围挡里烧。假如从空中俯瞰,像是郊外的烧烤摊。
一路上,大个子一言不发。他的发型有特点,偏离脑瓜顶、稍微向后、再向下的地方扎着一个小抓阄,走起路来,来回摆,仿佛大公鸡的冠子。
望着从家里拉来的堆砌得像小山一样的口袋子,大个子不错眼珠地看着,一肚子的心事。
李晓莉说,一会儿烧,你也帮把手,姥爷最疼你。
大个子答非所问,姥爷是个艺术家。
李晓莉撇了撇嘴巴说,这是姥爷活着时特别叮嘱的,死了,要把他存的这些口袋子给他带上。
大个子眼神有些发怔。
火葬场的那片空地上,游弋着一些手里提着木棍儿的小青年。只要有人烧衣服,他们就会主动过来帮忙。焚烧衣服需要一点技艺,用木棍不断挑拨,这样才能烧得透,火势旺,才能快点送达“那边”。大家心知肚明,帮忙也不是白帮忙,无非就是得点“好处”。
有两个拖着木棍子的小青年,已经站在李晓莉面前,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恭敬地看着她。李晓莉想都没想,拿出两张百元钞票,给了两人。两人连声谢谢,开始工作。
“这也烧……?”一个小青年看着小山一样的各种颜色的口袋子,疑惑地问李晓莉。
“烧!”李晓莉说。
两个小青年不再说话,把口袋子堆成宝塔形状。就在两个小青年准备点火时,却被李晓莉儿子大个子突然拦住了。
李晓莉不懂儿子的动作,问他还有啥事?
大个子说,妈,我把这些口袋子拉回去。
什么?李晓莉虽然压低声音,旁边两个黑衣小伙子还是听见了。
大个子平静地说,妈,你喊什么呀?
你要这些破口袋子……做啥用?李晓莉眼睛睁大,感觉不对劲儿,胡思乱想起来,姥爷最疼这个外孙子,莫非施了什么咒语……
大个子对身边两个小青年说,谢谢两位好兄弟帮忙,口袋子不烧了。
两个小青年后退一步,感觉大个子要掏他们俩的口袋,要把两百块钱拿走。大个子摆手,说,钱不要了,麻烦你们帮忙找几段绳子,把口袋子捆好,一定要捆得紧绷点,后备厢小。
一个小青年扔下棍子,跑着去找绳子。另一个小青年不离左右,继续寻找需要帮忙的人家。
李晓莉不说话了,看着目光忽然变得无比坚定的儿子。平日里,大个子的眼神永远是飘浮的,透着无尽的迷茫,难得有刚劲、坚毅的时候。
找绳子的小青年很快回来了,又把四处找业务的小伙伴喊过来,大个子也主动上前帮把手。三个小伙子把口袋子分类、整理、折叠,很快捆扎好了十几个长方形的背包。长宽高皆是半米左右,捆扎得特别结实,有棱有角的,像是野战军战士的行军背包。
大个子把这些“背包”放在后备厢,满满的,厢盖子压不下去,用细绳子拉拽好;后座上也放满了……还是放不下。
大个子麻烦两个小伙子,把剩下的“行李包”拉到火葬场外面。
李晓莉质问道:“拉到外面,就能带走?”
大个子说:“我再找一辆出租车不就成了?”
几个人来到火葬场外面,出租车已经等候在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出租车司机点头答应了。
拉开副驾驶的车门,看着眼前的口袋子,还有出租车上的口袋子,李晓莉满脸疑惑、满心恼怒,在此质问儿子,这些口袋子放到哪里?绝对不能放家里,这可是从“那边”来的。
大个子说,妈,您就放心,不会放家里。
七
大个子精心策划一场展览会、一场音乐会。道具就是他姥爷留下的那些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口袋子。这场“二合一”的活动,是为一家纸箱公司做产品宣传。纸箱公司看了大个子的文案,非常欣赏,立即掏了一笔不菲的宣传费用。大个子找到一家拥有废弃工厂大院的文化公司,共同进行合作宣传。
别看废弃的工厂大院、厂房破旧不堪,却经常有影视公司在这里拍戏,这座城市的人们,经常在银幕和荧屏上,看见这座熟悉的大院和厂房。
这家工厂曾是中国有名的重型企业,他们生产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奔走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曾经跨洋过海支援过阿尔巴尼亚、伊拉克,如今厂房里的机器没有了,大部分地皮都被房地产公司买走了,只剩下一座破败的庭院、两间破败的厂房,一家文化公司有前瞻眼光,第一时间出手租下来,经过一番包装改造,成为“活着的布景”。
展览开始了,有相关企业代表、少数传统媒体,余下的便是几个行业内的网络大V,剩下与会人员,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自媒体。如今企业宣传,不在乎现场有多少人,而是注意网络影响力。
这是一个星期天。
所有来到现场的人,全都吃惊地张大嘴巴。原来,他们看到了一个用各种颜色口袋子“扎”起来的巨大“子宫”。所有进到“子宫”里的人,意味着已经在参观展览了。厂房光线比较暗,房间上下的四个角落,有几盏发黄的灯光照向“子宫”。
每个嘉宾都要发言,说一说对“口袋子”的认识,说一说生活中与“包装”有关的故事。大个子把大家的发言叫“故事会”。如此新颖的形式,让来宾很是兴奋。
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布展人大个子。
大个子讲了这些包装“子宫”的口袋子的来历,讲了姥爷与口袋子的三段故事,来宾们听得入了迷,举着手机现场直播。暖黄色的“子宫”里一片安静。
大个子讲完了,来宾开始讲。
网络上参与者很多,纷纷留言。轮到最后企业老板“讲故事”时,他宣布要把来宾讲的故事,还有网络上的精彩留言,经过汇总、筛选,做成一本“包装故事”的书出版发行。
展览结束,音乐会马上开始。所谓的音乐会倒是简单,一架钢琴,一男一女两个人,轮流弹奏钢琴,所有演奏的曲子都是世界名曲。来宾们手里举着香槟酒,说着生意上的事情。
大个子忙得很,他没有发现角落里始终站着一位认真倾听的中年妇女,那是他的妈妈李晓莉。
李晓莉看着那些熟悉的口袋子……仿佛它们被一把火点燃,迅猛地燃烧起来。火光冲天,火苗向上蹿,最上端像是摆动的龙头。
李晓莉身子摇晃了一下,眼前闪过一片光,随后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