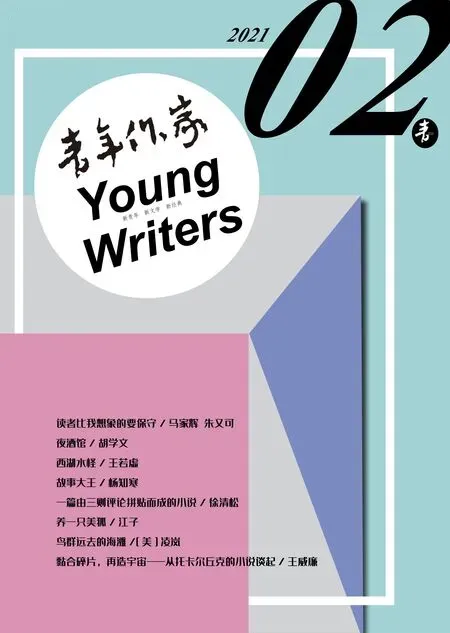失 眠
梁宝星
一
父亲拖着长长的影子站在街头,神情呆滞,脸颊和眼珠下陷,破旧的棉衣露出灰白色的棉丝,毫无预兆地轰然倒下,像落叶贴着地面。
倒下之前,父亲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这辈子都没睡过几次好觉,疲惫与孤寂占据了黎明到来前那段漫长的时光。长期失眠导致他的身体急剧衰竭,记忆力也早早衰退了。
父亲说他最早的记忆是寒冷、寂静与黑暗,他被困在一所幽暗的楼房里,房间的墙壁用沉重的青砖砌成,墙壁与天花板交界处有几个洞眼,最初的光就是通过那些洞照进来的。父亲对眼前的陌生世界感到恐惧,没日没夜地哭泣,那时候他根本不清楚什么是威胁,只是哭喊着划动四肢,试图捉住任何可以依靠的事物。
一个穿长袍、戴眼镜、两撇胡子又细又长的高瘦男人走过来,一只手推摇篮一只手晃铃铛,嘴里哼着低沉的歌谣。高瘦男人刚走开,一个脸色苍白神情怪异的女人推开房门走进来,她跪在父亲面前,对着父亲举起了手中的镰刀……
房子外面是荒野,金灿灿的芦苇被风吹着翻起浪涛,芦花被带到空中,又纷纷扬扬落下。芦苇地里有一条大江,芦花落在水面被流水带着往下游漂去。父亲是南方人,他坚信这点,他经过长途跋涉才来到这片北土,始终想不起来他的起点在什么地方。
那是一座大宅院,有好几层,每一层都有好多个房间。宅院里没几个窗口,一股潮湿沉闷的气息在屋内弥漫,潮湿是水泥地板和青砖墙壁发出来的,沉闷则来自楼房里的木家具。腐朽的红木桌椅以及书架因为热胀冷缩发出爆裂的声响,每张方桌后面都有一面明晃晃的圆镜。
一所楼房、一座山丘、一片稻田、一条大江和一片芦苇,构成了好几个记忆碎片。芦苇地里有一条黄泥路,路上有许多大小不一的脚印。野鸭在追逐,灰鹭从芦苇丛中飞出来又钻进远处的稻田。父亲记得稻田里淤泥的气息,他曾沿着田埂奔跑,被藤蔓绊倒摔进稻田里吞了几口淤泥,几天后肚子胀成一个球,大便的时候使出浑身力气才把这些泥土排出来,坚硬的泥土还带着血丝。
我们将父亲抬到医院,急救室的大门关了大半天,医生出来说父亲是睡着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妹妹和母亲都感到欣慰,失眠几十年的父亲终于睡着了。父亲安详地躺在病床上,脸上的皮肤舒展开来,面孔泛起了红光,呼吸均匀。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路,说话要到门外去,担心惊醒了他。窗外下起了雪,轻盈细腻,在街道上飞舞,落到地面就融化了。
母亲和妹妹留在医院照看父亲,我回家给父亲带衣服,他睡着之前只穿一件薄棉衣。漆黑的房子冷冰冰的,父亲一个人住在三楼,他的房间十分整洁,窗口能够看到前方的大街。我在父亲的房间来回走动,心情十分沉重。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来过父亲的房间,有多久没有关心过父亲的生活了,或许我根本就没有留意过父亲以及他的过去。大学毕业以后我和妹妹每天忙着工作,回家吃饭的时间少了许多。我知道父亲有许多心事,以前他跟我们说过一些,那时候我们都还小,没有特别在意他说的话。
我从衣柜里取下父亲最喜欢的那件大衣以及一条白色围脖,衣柜旁边是一个旧书架,上面的报纸都是好多年前的,已经发黄了,父亲一直珍藏着。我在书桌前坐下,一边翻阅这些报纸一边回顾父亲以往的生活。
二
夜里,母亲和妹妹回家了,我留在医院照看父亲,空荡荡的病房里只有一张白色的病床和一张椅子,父亲躺在床上,我坐在他身边。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撞在窗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街边的路灯和树枝挂着晶莹的雪,地面也渐渐被白雪覆盖了。每到下雪天父亲就要张罗着烧水泡身,热水泡烂了一层皮,他用肥皂将那层皮搓掉。
父亲在我们眼中一直是个爱干净的人。大部分时间他都穿着白色衬衫,即便冬天也要穿着整洁的西服,如果天太冷,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才会套上一件黑色大衣。他有一个黑色宽边礼帽,外出的时候他喜欢戴上这个帽子,有时候冷得耳朵红红的他也不愿意换一顶针织帽或者貂毛帽。父亲几乎没有给别人工作过,也是因为怕脏,我们家是母亲一个人撑起来的。我们都不曾怪过父亲,母亲说父亲是南方人,不适合在北方干重活。父亲下雨天从不出门,也是因为怕脏。
近两年父亲变得沉默寡言,有时候他长时间坐在客厅里发呆,有时候蹲在门口看街上人来人往,因为无法睡眠,他的脸很黑,眼珠是黄色的。
父亲睡去的模样显得陌生,咳嗽与叹息不再从他口中冒出,他肯定没有做梦,身体没有丝毫动静。小时候许许多多个夜晚都是我和妹妹躺在床上,父亲坐在身边给我们讲故事。父亲说他从小就喜欢虚构故事,常常在真实与虚构中犯混沌,年纪大了精神衰弱,越是遥远的事情他越不敢确定是否真正发生过。
当周围安静下来,大脑便进入虚构的最佳状态。父亲躺在床上凝望天花板,天花板上陆续出现许多黑点,黑点是故事的主体,黑点像蚂蚁一样在天花板上移动,没有时间,没有方向,故事往往就这样开始了,父亲利用这些故事打发了许多个无法入眠的夜晚。
苍茫的芦苇是父亲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父亲断定自己生自那里,从那里走失。芦苇地的清晨总是飘着白雾,灰鹭单脚站在芦苇的花穗上。小时候的父亲不喜欢穿衣服,光着身体走到厅堂,抬来椅子趴在唯一敞开的窗口眺望门前那片荒野。
父亲胆小如鼠,又对陌生事物充满好奇,他依靠想象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天花板上的黑点无数次虚构出陌生且模糊的景象,后来,黑点构成的画面开始无休止地重复,成为他睁眼看见的噩梦。黑点往往是从墙角开始移动的,越聚越多,在天花板上没有规律地旋转,化成一片芦苇地,父亲在芦苇地里奔跑,一个手举镰刀的女人追在身后。
“可能就是这样走失的。”许多年前,父亲在饭桌上突然站起来说,“那个疯女人追着我,我在芦苇地里越跑越远、越跑越远。”
父亲说他走失的时候应该是春天,楼房的墙壁闪着银光,轻轻一碰,指尖上都是水。木制家具爬满了水珠,变得特别沉,木门已经关不上,而在下雨前关上的木门几乎要和墙壁生长在一起。稻田与芦苇地被白雾笼罩,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燕子在稻田上面穿梭。父亲走到地下室,在黑暗的楼房里摸索,手指碰到了墙壁,墙壁上除了水珠还有毛茸茸的霉菌。父亲摸索了很久,找不到灯台,找不到门,他被困在一条漆黑的没有尽头的廊道里,廊道的两边是高高的墙壁,像一个巨大的盒子,他就在这个盒子里奔跑,然后眼前出现了一片芦苇地,那个疯女人在身后紧追着。
三
窗外明亮时雪已经停了,玻璃窗上爬满了冰花,街上还没有人走动,路灯、树枝、长椅和楼房是黑色的,其他地方白茫茫一片。护士给父亲换了两瓶药水,对着床边的机器记录了数据便出去了。一夜未眠,我疲倦不堪,对着玻璃窗打了几个呵欠,喷出来的白气碰到冰冷的玻璃变成水雾。窗玻璃一面挂着水雾,另一面爬满了冰花,同时承受着两种温度。
父亲说他不知为何会出现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躺在巷子的垃圾堆里。他从垃圾堆里爬起来,许多事情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自己被疯女人追着跑了很远,镰刀似乎已经打在他的后脑勺,脑袋凉凉的,他以为自己死了。街上空无一人,天空布满了乌云,真实记忆便是从那时开始的。
父亲所说的黑水镇位于安徽北部,算不上南方,黑水镇四周都是黄土丘陵,虽然芦苇随处可见,父亲记忆碎片里的大河以及古堡式的宅院并不存在。从黑水镇往南走八十里路才到淮河,一个七岁的小孩不可能跑那么远的路。父亲在垃圾堆里醒来之前肯定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路程,他的记忆才会如此模糊。
我在电脑上搜索过黑水镇,从图片上看那里并不富裕,多是三层高的楼房,各种摊贩挤在路边,街道只留下两个身子的空间给顾客来往。街上撒满了垃圾,路面是砖头铺成的,坑坑洼洼,粗糙的表面被鞋底和车轮磨平了,父亲在那个地方生活了十几年。镇上有一群流浪儿,潮湿逼仄的巷子以及没人居住的烂尾楼是他们的地盘,他们接纳了父亲,在用纸皮铺成的窝里给他留了一块空间。
夜深以后,流浪儿都睡了,漆黑的巷子,臭烘烘的沟渠,老鼠不时在父亲脚边爬过,他心里恐惧,留意着身边的动静,不时有影子从巷口飘过,或许是人,或许只是一只狗。有一天,一个手拿长棍的疯子闯进流浪儿的地盘,父亲站在巷子里惊恐地望着疯子,四肢麻痹无法动弹,木棍打在他的左脸上,父亲倒在地上,左耳出血,耳鸣困扰了他很久,后来他对声音特别敏感,细碎的声响都能被他捉捕到,这种敏感增添了他的恐惧。
巷子里的生活片段占据了父亲大部分记忆空间。黑水镇居民围捕过他们几次,想把他们送去山上的孤儿院,可每次都让他们逃脱了。巷子里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父亲由恐惧疯女人到恐惧围捕。
因为失眠,而且听力灵敏,父亲便承担起晚上放哨的角色。漫长的夜晚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父亲的身体发育得极其缓慢,眼睛四周的皮肤发黑发皱,睫毛也掉光了。尽管父亲的机警能够帮助流浪儿避免被围捕,他们还是每过一段时间就搬到另一个街区去生活,他们讨厌夏天,大雨使他们睡觉的地方变得湿漉漉的,地上的纸皮被水泡烂了,第二天太阳猛烈照晒也难以将地下的水蒸发掉。流浪儿身上长满了癣,从一个地方开始烂,蔓延至全身,体无完肤。父亲是流浪儿当中患皮肤病最严重的一个,他浑身都是血痂,痒得不行,稍微一动就冒出脓液,差点就死去了。跟他玩耍的小女孩背着他离开黑水镇,在山里找到一眼温泉,用温泉水替他擦身,父亲才活了过来。
在山里待了两个月,父亲的病开始好转,身上的血痂掉下以后留下无数个印痕与疙瘩,皮肤绷得紧紧的,父亲不敢伸展身体,担心把薄薄的新皮给撑破了。下山以后他又回到巷子里,躲在书院的窗口下学会了读书写字,随着身体的不断膨胀,烂尾楼日渐残旧,巷子也变得狭窄了,夜晚躺在纸皮上,父亲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或许是因为那场病,他开始害怕肮脏的东西,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属于这些黑暗的巷道,不属于黑水镇。
母亲说,父亲倒下之前好像在写什么东西,晚上他房间的灯一直亮着。母亲知道他晚上睡不着,因此并没有干预他,就让他在那段安静的漫长的时间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在父亲的房间里找了好久,并没有发现他写的东西,书柜上除了报纸还是报纸。
在医院值夜看守父亲的时间里我把父亲收藏起来的报纸都翻了一遍,那些发黄的报纸所记录的是黑水镇自1978 年至今的发展变化,其中有几篇写旧房拆迁以及古楼修复的文章,父亲在上面画了几条横线。我在想父亲是不是在计划回黑水镇?这二十多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北方,或许他真的想回去,但他知道他要回去的并非黑水镇,而是他出生的那个地方,他无法知道那个地方距离黑水镇还有多远。
四
父亲在医院躺了三天三夜还没醒来,母亲把医生叫来,说没痛没病地躺了这么多天,是不是成植物人了?医生把父亲推出去做检查,半天才送回病房,父亲依旧平静躺着。医生说父亲的身体到处都是病,但这些病都不是沉睡的原因,他的脊椎完好,后脑勺也没有摔坏,因此只能给他输液,等他自然醒来。
母亲坐在床边握着父亲的手不停地唤他的名字。司徒两字是他的姓也是他的名。我曾问父亲为何给自己取名司徒?他说记忆中那所宅院里有一块巨大的牌坊,后来他才知道上面写的是“司徒”两字。妹妹站在窗边哭泣。我认为我们不必为父亲感到伤心,他并没有死去,而是陷入了他一直在寻觅的沉睡状态。
天气越来越冷,下了几天的雪,地上、屋顶上早已积了厚厚一层雪。雪后天空放晴,地上的积雪反射太阳光把周围照得亮晃晃的,街道两边,不少人出来铲雪,小孩在雪地上玩耍,梧桐树下站着一个五官不正的雪人。父亲说他在二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杀死过一个人。
长大以后巷子里的流浪儿都有了劳动能力,也出现了利益纷争,闹过几次以后就一哄而散了。父亲跟当初救自己一命的女孩相依为命,没多久女孩外出偷东西的时候从两米高的围墙上摔下,脑袋摔在尖尖的石头上,当场死了。
父亲孤身一人在街头徘徊,夜晚降临以后他走进漆黑的巷子,闹矛盾以后其他流浪儿已经不在巷子里活动了,夜晚寂寞冰冷,女孩的死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那天晚上,他决定杀死记忆中的疯女人,唯有杀死恐惧才能获得自由。
天气寒冷,月光被乌云遮住,为了壮胆,父亲去偷了一瓶酒,他提着酒瓶在梧桐树旁坐下,早上飘落的雪已经融化,积水把地面泡软,泥土像发酵的面团。他大口大口地将烈酒灌进腹中,然后把酒瓶敲碎在树干上,紧紧握住尖利的瓶口。
梧桐树上的积水打在他的额头上,打在身旁的落叶上,打在软绵绵的泥土上,发出噗噗的声响。街头出现一个黑影,父亲举起手中的瓶嘴,绽开的玻璃像一朵带刺的花。黑影靠近的时候父亲猛地站起来,向那人腰间刺去。
父亲晃晃悠悠走进巷子。很快,白光把梧桐树光秃的枝丫照得闪闪发亮。父亲看到手上有凝固的血块,心里发怵,把血块蹭到衣服上,捂着胀痛的脑袋走到街头,看见梧桐树下躺着一个拾荒老人。
五
父亲对自己的姓名、年龄和籍贯一无所知,他被拉去游街,街道两边站满了人,喊着各种口号,父亲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场面,以为自己是要被送去枪毙,呜呜地哭了起来。
游完街,父亲被关在牛棚里,牛棚里一片漆黑,墙壁用粪便扫过,肮脏不堪。地面是潮湿的,用稻草铺成的床已经散乱。父亲重新整理好潮湿的稻草,躺在上面,他不再恐惧手持镰刀的疯女人,疯女人已经死亡。他顾忌把他关起来的那些人会杀死他,那个女孩从墙上摔下死去之前跟他说过,他们没有身份,是这个世上不存在的人,任何人都可以伤害他们,因此他又彻夜难眠。
父亲被安排到采石场劳动改造,身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他的罪名。石山被凿得千疮百孔。男人在岩石上凿,女人们就在下面把大块的石头敲碎挑到外面,外面有车把石头运走。父亲不会使铁笔,满手都是水泡,监管人就派他到女人中间去敲石头,后来又分配他到运石头的队伍里去,把碎石装满车厢然后跟着汽车到各条路段去铺路。父亲对这份工作很满意,他和其他几个人坐在石堆上被车带着到处走。
天气越来越冷,雪迟迟没有来,路边和山上的树光秃秃的,像无数根插在泥土里的鱼刺。两个月后,汽车把父亲载到一个小山村,把碎石卸下之后监管人就把他锁在一个仓库里。仓库里已经关了好多人,父亲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下等开饭,吃完饭或许还会安排其他的工作。他感到精疲力竭,想洗个澡,把身上的灰尘和石屑洗掉,他厌恶身上的脏污。仓库顶端有几个方形窗口,映进几束月光。身边的人埋怨那么晚还没有饭吃,仓库像一个漆黑的洞,里面藏着一群吵闹的蜜蜂。
父亲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眠对他来说是稀有的,因此他记得很清楚,那个沉闷吵闹的夜晚睡得很沉,以至于天亮了都不知道。
睡在他旁边的胖女人死了,她患了瘟疫,尸体被抬到阳光底下,一群人张罗着找来干柴要火烧尸体。父亲站在远处眺望,想不起躺在身旁那个胖女人的模样,脑海里只有她肥大的轮廓。
城里卫生部门派人来给劳改分子检查身体。中午时分父亲被派遣到采石场劳动,坐在巨大的石头面前浑浑噩噩地敲了大半天,手上多处震出血,他已经没有知觉。自己离胖女人最近,为了预防被自己身上可能潜伏着的病毒,那些人会偷偷下毒手杀死他,父亲一整天都在想这件事。
傍晚时分,父亲又被安排去运石头。汽车往小山村奔去,经过一座石桥,只听见一阵落水声,父亲在水面上消失了,夜幕降下来把水面的涟漪抚平。
六
父亲依旧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和妹妹轮流照顾他,给他擦身,喂流食,倒排泄物。他的身体发生了明显变化,死皮一块块掉落,萎缩的肌肉日渐饱满起来,肤色细嫩通红,前来探望的好友都说父亲是返老还童。
我和妹妹给父亲穿上棉衣,带上帽子,推着他到外面去晒太阳。外面雪很厚,不过天气晴朗,没有风,不是特别冷。父亲的脑袋斜向一边,身体往下垂,为了不让他摔倒,我们不得不用绷带将他跟轮椅捆在一起。父亲或许能够感觉到自己正被我们推着走,能感觉到温暖,他的身体在吸收阳光,嘴唇泛起健康的色泽。
江边的景象格外萧条,江面结了厚厚一层冰,行走的人穿着黑色的大衣,脖子跟下巴都藏在领子里,远处有几个年轻人在溜冰。我们将父亲推到江边长椅旁,阳光正好照在他的胸膛上。没多久母亲便来了,披着头巾,提着个银色保温壶,在长椅上张罗着给我们倒热水,然后弯腰去整理父亲的衣服。
“当年你们父亲差点就死在江边了。”母亲将父亲推到阳光更好的地方,然后在长椅上坐下,“那时正值一年里最寒冷的那几天,我和你们外公到野外钻冰捕鱼,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天下着大雪,外公拖着网,我背着一竹篓已经冻成冰条的鱼在冰上走。那时这里还是个破落的小山村,晚上没几户人家点灯。上岸没走几步我被绊倒了,鱼掉了一地。外公一边骂我不中用一边捡地上的鱼,仔细一看,绊倒我的是一个倒在雪地里的人。我们以为他已经死了,外公叫我赶紧把鱼装好回家,才走了两步,你们父亲就喊了起来,他一直喊救命,声音特凄凉。”母亲看着父亲的侧脸哈出几口白气,“那时家里只有两间房,你们父亲在我的床上躺了一个冬天才能站起来走路。他当时像一只快要饿死的猴子,连玉米都啃不动。第二年春天,河里的冰还没融化,上游的水涌到岸上来,整个村子被水淹了,你父亲救了一位干部的女儿,那位干部为了报答他,帮他安排入户,分配住房的时候还给他争取了一套房子。”
母亲用衣袖揩去眼泪,父亲如一个沉重的包袱纹丝不动。江面起风了,溜冰的青年已经上岸,我们推着父亲往医院走。将父亲抬到病床上,母亲捧着他的手,“从没见他这么好看过,看他睡得多沉。”母亲跟我们一样,没有见过父亲沉睡的样子。她从前对父亲充满怨言,说他杞人忧天、胆小如鼠。“你们父亲没有病,他只是睡着了,他太久没有睡了,才不愿醒来,跟医生说说,过年前我们把他带回家。”
医生同意让父亲回家疗养,出院前叮嘱我们按时给他喂食、擦身、活动肢体。我看着病例上父亲的名字从未感觉如此陌生。他过了近三十年没有姓名的生活,后来给自己取名为司徒,出生地写的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北河镇。获得身份证以后,他在身份证上钻个洞套上绳子挂在胸前,夜里双手紧紧握住身份证依旧睡不着。
七
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的那天,我在父亲的床垫下发现了一本黑皮笔记本,这本年代久远污迹斑斑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不工整的字,父亲在那些无法入眠的夜晚断断续续记录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看得我毛骨悚然。以下是黑色笔记本上面的部分文字,日志并非连续记录,有些相隔几天,有些隔了几年,一部分文字已经看不清楚: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1968 年8 月
当我学会写字,过去的事情都记不得了。我还记得那房子、芦苇地还有那个疯女人,可那是什么地方?没有人来找我吗?
没有人。
1968 年12 月
那个女人又来了,拿着一把镰刀,她为何一直追着我不放?为什么?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她就出现了。
1970 年12 月
追杀我的人远不止一个,我已经走了好远的路,这是什么地方?我要去哪里?
我此刻正在一棵树上,和好几只鸟待在一起。
1976 年3 月
我只会越走越远,只会越走越远,我再也回不去那所宅院了,我已经在这个遥远的北方有了自己的身份。我叫司徒,妻子是北方人,儿子和女儿都很健康,他们夜里都不会失眠。
全世界失眠的,只有我一个。
1990 年5 月
又下雪了,今年的雪特别大,下雪天好啊,干干净净的,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气候,我早就适应了,我只是不喜欢下雨,不喜欢幽暗的地方,不喜欢泥泞,那些都会让我想起过去在黑水镇度过的日子。
南方人很少看见雪,曾经一起躲在巷子里的人现在不知过得怎样,不知他们分散到各个地方去了还是依旧留在黑水镇。他们是否记得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那个背我上山的女孩呢?
直至她从墙上摔下死去,我都没有来得及问她。
1993 年1 月
流浪与逃亡的日子无比漫长,可人一旦安定下来,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这段日子,我几乎忘记了过去的那些生活,人都是健忘的,像猫一样,被痛打一顿后很快就想不起来了。可是我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从来都不是能够改变自己或者改变世界的人,我只会被这个世界改变。
难道不是吗?
即便生活看上去毫无波澜,我也无法入睡。
1999 年7 月
我又开始胡思乱想了,都是因为夜太过漫长。我随身带的这张身份证有何用?它能够证明我是谁?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
今天,我又犯病了,但这一次我是清醒的,我不过是想要通过奔跑来找回那些已经不清晰的记忆。
毕竟,我是在奔跑中丢失了自己和故乡的。
2003 年4 月
我到车站打听去黑水镇的车,那人跟我说没有车到黑水镇,人生没有回头路啊,这次我信了这句话。就算我回到黑水镇,能够跑回那片芦苇地吗?很多年前我就尝试去寻找记忆中的那所宅院,那时候都不能找到,如今早已物是人非了吧?
我跟妻子说我想回去。
妻子问我回哪里。
我也不知道。
2011 年9 月
今夜,我还是无法入睡,我尝试了几十年,都一一失败了,我已经忘记了沉睡是怎样一种感觉。不过最近我想通了很多事情,我想我之所以失眠,归根到底还是放不下我南方人的身份。
其实,我就是我,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故乡。
最近,身体特别沉重,走起路来浑身乏力,我知道,我很快就会陷入沉睡。
2018 年12 月
八
我决定去一趟黑水镇。
黑水镇与北河镇相隔两千里,火车要走三十多个小时,父亲走了将近十年。火车越往南走景象就越陌生,爬过开阔的平原,穿过江河湖泊,由白色空间进入绿色空间。父亲行走的画面在我脑海里浮现,他畏畏缩缩、战战兢兢,不敢向人群靠拢,走得极其缓慢,每向前跨出一步都要试探一下脚下是否踏实,仿佛路上布满地雷。有一次,父亲在家门口跟邻居老头说他北上时遇到的事情,他神态茫然,眼睛直直地望着门口的石头,说话的声音特别低沉。他说有一段日子他是住在树上的,白天不敢走路,担心被人追捕,夜里摸黑前行,好几个夜晚累得实在走不动了,看见一棵大树便爬了上去,树叶替他遮风挡雨,他蜷缩在树上过了好几个夜晚。后来他越来越依赖树了,找不到树的时候就惶恐不安。
火车在晚间十点抵达黑水镇,天空下着细雨,刚走出车厢,一股清新冰冷的风扑面而来。出租车司机争先恐后涌上来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问我是否需要搭车。路灯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广告牌各种颜色的光洒在湿漉漉的路面,我提着行李穿过马路朝“天鹅旅馆”走去。
我躺在床上抽了一晚上的烟,黑水镇没有暖气,尽管白天有阳光照进来,空气还是很冰。我在被窝里胡思乱想,生活了二十多年,我不曾想过自己是谁,属于哪个空间,将要面对什么,这些事情父亲纠结了大半辈子。
天将亮时,隔壁房间响起了阵阵摇床声,或许是某对热恋中的情侣昨晚不尽兴,醒来又爱抚一遍。我头昏脑涨,神思不定,突然想到自己已经三天没有睡觉了,但我清楚自己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焦虑。中午是旅馆最安静的时候,不少旅客已经退房。我本打算在这段时间睡一会儿,服务员打开房门来清理房间,将我睡觉的心思打消了。
走到街上,阳光刺眼,寒风凛冽,街边绿化树的枝叶被锯断了,黑色的树干宛如钢铁雕塑。我在街上没有目的地走着,脑袋清醒了许多,身体也没那么疲惫了。拥挤的街道阴沉沉的,街边店铺传来的热量没能赶走冷空气,街道原本是热闹沸腾的,是寒冷的风将喧嚣声抑制住了。不知是楼房过于残旧还是建筑簇拥得过于紧密,黑水镇总给我一种泥泞感。不知走了多久,我来到一座石桥上,石桥并不宏伟,桥下便是唯一一条横穿黑水镇的河——黑水河。
黑水河的水不是黑色的,河水很浅,河床全是黄泥,河两边露出水面的泥土面积比河水的面积还要大,水草萧条但并没有枯萎,各种垃圾被水草拦截在河边。我沿着河水往下游走,小镇城区并不大,我没走多久便来到了郊外。相比城里的拥挤,这片荒地显得更为辽阔。黑水河向东流,郊外的河床尽是些褐色的巨大岩石,露出水面的地方被太阳晒干了。我想河水饱满的时候这些岩石将会被流水淹没,呈现它们黑色的原状,那时才是名副其实的黑水河。
荒野上长满了芒草,尽管是冬天,叶子依旧翠绿,只有叶尖枯烂了,微微下垂。芒草里有许多半陷在黄土里的砖头,我踩着砖头走进草丛,慢慢靠近河边,水的腥味和草的清香混杂在一起。我蹲在草丛里,因为芒草没有我高,不能将我的身体吞没,我想象自己身边的是芦苇,企图体会父亲记忆碎片里的画面。寒风吹着,我留意着身边细碎的声响,虚构父亲在草丛里奔跑的场景。他那年大概六岁,身体瘦小,草丛在他眼中显得辽阔,河流也浩瀚无比,进入草丛以后杂草将他吞没了,他不断回头观察疯女人与自己之间的距离。
父亲的神经一直处于被人追逐的紧绷状态。十二岁那年的一个傍晚,我放学回家后看见父亲在屋后小山丘的松树林里奔跑,嘴里嘟嘟囔囔不知在说些什么,但从他的话中可以听出他的恐惧。他一边跑一边不断回头看,有时候还捡起地上的石头向后掷去,他身后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敢上山靠近他,夜色降临后树林里不再有声音了,父亲在我们睡下后才悄悄进入房间躺下。这样的事情在我十五岁和十六岁时也发生过。事情过去后他的精神往往会好很多,仿佛奔跑只是为了发泄。
天色转变得快。傍晚时分,风凉了许多,青色的鸟儿在露出水面的岩石上跳跃,我沿着黑水河在芒草丛里走了一圈,雾水落下以后温度一下子就下降了,我搂紧衣服往城区走去。回到黑水镇,街灯亮了,我在街上徘徊,心里总觉得有一股气无处释放。
街边招牌上五颜六色的灯光使我眼花缭乱。街对面花店的女孩在整理花枝,枯烂的和老皱的被挑出来扔到路边,来往的人将它们踩烂。我想起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父亲还年轻,母亲托亲戚帮忙给他在牧场里找了一份放羊的活,可是没多久他就抱着席被回来了。我记得当时父亲说他看不了血腥的场面,生病和年老的羊被剥皮肢解后塞进绞肉机里绞成肉酱,只有健壮的羊才能继续在牧场里生存和繁衍后代。当初我们没有太在意他的话,因为他恐惧的东西太多了,原来他爱卫生是生怕自己像枯烂的老皱的花一样被抛弃,害怕像生病和年老的牛羊那样被宰杀。
九
我在黑水镇逗留了几天,查了附近各个小镇的情况,租一辆车去了好几个地方,也向镇上的老人打听了这个地方的过去,还是没有找到父亲的故乡。
往北走的那天又下起了雨,马上就是除夕夜了,人群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堵住了各条街道。汽车已经不能从城中心通过,即便是摩托车也被堵在人堆里不停地鸣笛。雨也没能浇灭大伙儿过节的热情,各种颜色的伞在碰撞,人声从伞下冒出,将雨声淹没。我托旅馆前台向黄牛高价买一张火车票。前台女子回到旅馆的时候身体已经被雨淋湿了,火车票被她从兜里掏出,没有一滴雨水。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黑水镇。”她站在房间里看着我收拾行李。
“父母也在这里?”
“没有父母。”她说话的语气很平静,“我是爷爷带大的,十岁那年他死了,小姨把我带到十四岁,后来她跟一个外地男人走了,我就来这里工作了。”她在沙发上坐下,拿起桌上的烟点了一支。
“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或者离开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我可以去哪里。”
房间里陷入了沉默,她在我背后又点着一支烟,我能听到她吐烟和吸鼻涕的声音,也不好打断她的思绪。待我收拾完毕,她帮我去办理退房手续,然后拖着我的行李往街上走。拥挤不堪的街道寸步难行,摊贩将手推车拉到路上做生意,各种小吃的气味在雨中弥漫。我们没有打伞,低着头挤在人缝里,雨水从别人的雨伞滴落,衣服和头发被打湿了。
“你先回去吧。”我跟她说。
她没有走,手里提着我的行李说要送我上车,“你就让我送送你吧,不收钱。”她的脸色前一秒还是欢快的,马上就变得沮丧了,“两年前有个客人说他要带我走,我当时忐忑不安,既激动又害怕,一整晚睡不着。其实我想过离开黑水镇的,但是我一个人真不知道去哪里。第二天早上,客人好像忘了跟我说过的话,退了房一个人走了。”
人群一点点向候车室挪动,我们很艰难地来到了站台上才相互道别。火车里堵满了人,我费尽力气找到自己的座位。我有种窒息感,宛如被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身上。火车慢吞吞地走,拖着沉重的车厢。我在告别这个小镇,告别那个不知名的女子,有些人就是要一辈子生活在巴掌大的地方,他们哪里也去不了,父亲是这样,那位女子也是这样。
火车艰难地往北走,一路上陆续卸下了许多人和包裹,我又看到了熟悉的景象,银装素裹,四周白茫茫一片,容不下一个黑点。
父亲依旧躺在床上,身上的死皮全掉落了,手臂和脸上的黑斑也消失了,皮肤光鲜有弹性,头发乌黑柔顺。母亲每天早晨推着父亲到江边晒太阳,她坐在长椅上,身边放着个银色保温瓶,对着父亲没完没了地说话。
晚上,我还是会坐在父亲旁边,一遍遍地翻阅他的日志。有天晚上,我趴在父亲床边睡着了,梦见父亲在冰天雪地中奔跑,我听到了他奔跑的时候从嘴里冒出来的话,他高声喊着:“带我走……带我走……”
春节过后气温上升,远处的高山露出了黑色的脊背,地上的积雪也薄了许多。边防军频繁地在江边观察融冰情况,又过了几天,江上响起剧烈的轰鸣,江上的冰块被炸开了,溅到几十米远的地方。融雪的那段日子天空阴沉沉的,不见太阳,到处湿漉漉的。父亲身上冒出了许多水珠,母亲不再推他出门了,她守在父亲身旁给父亲擦身。躺在床上的父亲皮肤苍白,肌肉松弛,像出生不久的婴儿。
沉睡了三个多月,父亲在元宵节过后的第三天停止了呼吸,死得很平静,仿佛是睡够了便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