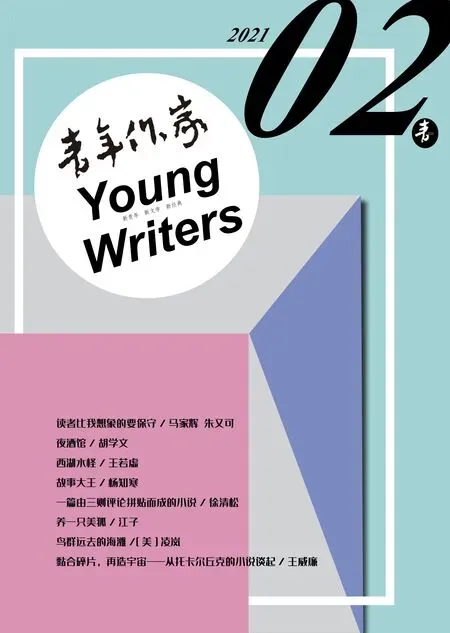向下“开掘”的努力
徐晨亮
或许可以这样解读:杨知寒的《故事大王》写的是故事讲述者的屡遭挫败与小说叙述者的一次诞生。童年的“我”善于复述书本里的童话,被戏称为“故事大王”,这一外号带来的光环与虚荣,因季老师的到来而被碾碎,在她“没有规矩”的课堂上,“我”讲述故事的能力突然失灵;而升入小学高年级后,孩子们一夜长大,学会窥探隐私、编造谣言,刺激因体内秘密力量而躁动的身心,“我”的故事才能随之复苏,却再度受挫于季老师被赶下讲台后蜗居的小屋;二十年后同学重聚,酒精、尼古丁与某些淤积在记忆中的东西,让“我”醉意阑珊,奋力想把那个沉没在往事里的故事,连同其惨烈的结尾,拽出水面,从头到尾讲述一遍。
与这个受挫的“故事大王”不同,年轻的小说家杨知寒似乎不在意还原事物已知的轮廓,更愿意凝视边缘与转角处晦暗不明的部分,再借由叙述的力量,让那些不可见的浮尘凝聚为具体的人形。季老师、小漂亮、郑旺,也属于她笔下常出现的他人眼中“活成荆棘”的异类,浑身芒刺,以致无法凑近,却吸住我们的目光,随之转向那些无法消融于记忆中的画面:“当时是千禧年的下午四点半,夕阳一片浓烈的红黄色,均匀地打在每件物事上头,包括郑旺和小漂亮的影子。它们后来一个踩着一个,直到夕阳褪去……”这样一帧帧剪影,像“我”想象中季老师母子依偎的时刻,有童话的光泽,也如同气息混沌、细节锋利的梦境。
2019 年回答《中华文学选刊》青年作家问卷时,杨知寒曾写道:让人“永远感到迷醉和困惑的一些画面”“恰是吸引我们最初去写作的机缘”“作家将永远仰仗小时候他做过的那些奇怪的梦”“能够从平凡处开掘那么一点不对劲的宝物出来,才使他成为作家,成为时间和记忆里的考古工作者”——本期收入的另三篇小说,或许笔触也有粗率或游移之处,但同样都能看出向下“开掘”的努力。梁宝星《失眠》中,父亲大半生“没睡过几次好觉”,始终没有想起故乡在哪儿;杨萌《小长夜》里的女儿,常有片刻沉迷失神,不知身处现实还是另一时空,由此带给日常若干“细小又恢弘的难题”;于则于《鱼王塘传说》里老人独自枯守,揪心塘里的水连同笼罩于斯的迷雾被抽干后,是否会露出亲人的尸骨与命运不堪的真相。这些纠结与恍惚、怪梦与残念,自成风景,不过,也可能引来批评和担忧:年轻作家由此出发的写作是否过于窄狭、难成大器?
其实,文本中之“所见”与写作者之“所得”常常不能画上等号。并非只有拉开架势写“一代人精神史”或回应现实之必然与应然的作品,才朝向开阔富饶之境。当下青年写作中某些入口看似“小”而“狭”的探寻,分明是被现实中不可见的部分所吸引,他们正在掘进的秘道深处,也许正隐藏着这一代人的宝藏,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亦有可能在过程中浮现。正如梁宝星小说《看不见的大象》里那位科考队长所言:“一个地方的重要性不能只看当下,就像你永远不知道你脚下的沙漠是不是楼兰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