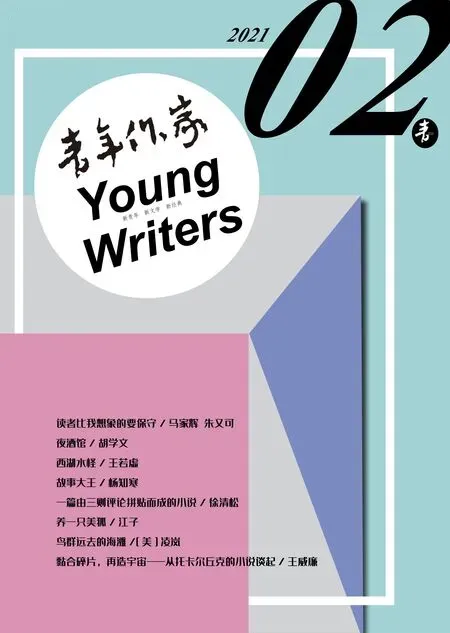读者比我想象的要保守
——马家辉访谈录
马家辉/朱又可
朱又可:你给报纸写专栏,到电视台去做节目、当嘉宾,似乎什么武艺都能拿起来。到快50 岁的时候,你忽然意识到得坐下来,写你一直想写的长篇小说,这是你一辈子似乎唯一有计划想做的事。
马家辉:因为再不写,就来不及了。写长篇小说,对于一个爱文学爱写作的人,是一个永恒的挑战。可能我比较悲观,觉得一过50 岁,看到的跟我之前看到的不一样了。50 岁以前,眼睛看着前面,还觉得我有好多事情可以做。一过了50 岁,眼睛是往后看的,好像觉得前面的时间不多了。
朱又可:你的长篇不是一部,而是“香港三部曲”。
马家辉:是的。第一部写日占时期的香港;第二部写1950 到1960 年代的香港;第三部写1970 到1980 年代的香港,一直写到香港回归。
第一部叫《龙头凤尾》,写的是一个从广州逃亡到香港的黑社会老大陆南才和英国警察张迪臣之间的暧昧故事。出版后,接连获包括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香港红楼梦奖以及南方周末年度好书等18 个奖。
写的时候,我的妻子和朋友,都劝我不要写得太“黄”,我说我不管,由着性子写。令我意外的是,台湾新经典出的繁体字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简体字版,都没做一个字的删节。目前我正在写香港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书还没写完,导演杜琪峰已经买下了这一部的电影改编权。
朱又可:为什么要把故事的时间放在日占香港时期?
马家辉:可能跟我自己做的一些研究有关系。我在学术上面对一个研究主题感兴趣,就是汉奸,比如汪精卫、南京政府,以及香港的汉奸、内地抗战时期的汉奸等等。为此,我看过好多材料,觉得里面的故事,还有他们的心态,很好玩。所以,当我写小说的时候,难免就会把时间放回战争年代。
当然,说远一点深一点,可能也跟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有关系。因为香港一直是一个很暧昧的地方。你看香港所有的电影,都有这种暧昧的性格,每个人都好像很严肃,又很幽默。所以香港最流行的主题是《无间道》。大陆和中国台湾,甚至美国好莱坞,拍《无间道》这种电影,可能都拍不出那种味道。因为那种暧昧,是黑白不分的。根本不需要去分成黑白,这种观念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就抓住了这种感觉,一方面我有研究,看了很多材料;另一方面,暧昧这种性格让我不自觉地把时间的坐标设定在战争年代。
本来我是想写1967 年一个叫金盆洗捻的宴会,一个江湖老大要洗捻,说不再碰其他女人了,只对老婆好,似乎很好玩。可是我写的时候,就觉得只写这个,好像很单薄、很肤浅。如果让金盆洗捻的宴会变得很丰富、很饱满,就一定要把里面人物的性格,还有他们的背景写清楚,一写清楚,难免会把时间从1967 年往前推到1930 年代。结果,我们一不小心,一发不可收,变成写了一个金盆洗捻的前传,写了陆南才从内地来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时空坐标就放在了1930 年代。
陆南才是在战争之后来到香港,混黑社会——他本不想混黑社会,可是因为命运不得不混黑社会。所以还是探讨命运的问题。
朱又可:为什么又要写香港的黑社会?
马家辉 :写黑社会及黑社会与香港的关系,有两项关键考虑。一来因为我成长的背景,接触了许多黑社会人物,他们的故事和传说,让我深深入迷;二来,更重要的是,小说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背叛、忠诚、伤害,为了逼迫出人的抉择,必须把人物安置在比较特殊的位置,例如战争的生死状态,例如边缘人的社会处境,例如男女同志的压抑。黑社会人物正是其中一类边缘,如同妓女、汉奸、草根等。
朱又可:第三部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马家辉:我第三部的开头是这样的:你读过《龙头凤尾》吗?就算没读过,也应该听过。这本书出来之后,我大概拿了18 个奖。也赚了生平最大的一笔版税,我换了一台红色法拉利(我现在开的是保时捷)。
可是有个技术问题要解决,就是要说服我老婆。我跟我老婆说,我要换一台法拉利,我老婆就说:你以前买保时捷的时候,不是说保时捷是你的梦想车吗?我说,是啊,可是做人要往上爬,梦想也要往上爬。周星驰说,人若没有梦想,跟咸鱼没有差别。我老婆没办法,好,给你换。
可是后来我还是没有换,原因是钞票,可是严格来说是我父亲。我以为那书我父亲不看,结果他看了三遍。他找我吃饭,好像很生气,我问他原因,他说错字很多。我父亲以前当编辑,受不了错字。他骂我,说我的情节写得不够彻底。他说你写乱七八糟的东西,网络上一大堆,有什么好玩?
他就说他有一个好故事。我让我老爸告诉我,结果我老爸说,告诉你可以,可是你要给我分钱。他说,你把我家族的事情写了,分我一点版税也对。另外,我答应过你妈,要买一个东西给她,我已经答应她五十年了,现在要做,不做来不及。
我问他,买豪宅还是买钻戒?我爸说,不是,我要买一块墓地给她。我问干嘛要买墓地?他说,第一你妈怕疼,她不想死掉被火化;第二,你妈妈年轻的时候看过命,命书里说她死无葬身之地,我不希望这样。所以要买一个墓地。我觉得很温暖很感人。
之后,我父亲就给我讲了陆北风的故事,就是陆南才的弟弟。我会写陆北风跟他的儿子混黑社会,以及1970 年代整个香港黑社会发展的历史。
这一部我写1970 到1980 年代的香港,一直写到中英联合声明,说香港要回归。这个时代发生了廉政公署反贪,1975 年到1977 年之后整个的天翻地覆。我们今天的香港其实是1970 年代建立起来的。反贪,香港的法制,我们今天所说的还包括福利、房屋、教育、医疗等等,工人最基本的一些照顾,都是1970 年代建立的。
在书房我是最放肆最快乐的
朱又可:我想知道你小时候所受到的家庭教育。
马家辉:非常香港,就是吃喝玩乐。我从小只有一个梦想,赶快做事情来发大财。家人打麻将赌博,嫖赌饮吹都有。我在很多演讲中都提到,我的几个舅舅经常在我家里住。
正经人家的旅行是约去郊游,我的家庭旅行通常都是去澳门赌钱。我爸、妈、妹妹、姐姐约去澳门赌钱。
我父亲在报社工作,他当记者、编辑,后来当了总编辑。可是,他不是文人办报,他对文字没有热情,他就是工作养家,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男人。
我家里就我、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加上爸妈,一共五个人。可是,他把我的外公外婆,还有我妈妈几个不成才的弟弟也接过来住。结果,一家五口变成一家八口,有时候九口,负担多重!房子好小,还是租的,40 平方米住了八个人。高低床,还要两三个人一起睡,可能还要睡客厅,很惨的。
所以我的家庭教养,除了吃喝玩乐、嫖赌饮吹,还有一部分就是非常负责任。你看我的名字,“马家辉”中的“家”,就知道我父亲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所以我有时候会给自己很大压力,对待事情很尽责任。
朱又可:你父亲的职业有没有影响你?
马家辉:他毕竟是在报社上班,小时候我们在家还看到好多笔和稿纸,那个年代我父亲要写专栏赚外快,他写马经,什么乱七八糟的文章都写。我们从小就感觉写作是好东西,拿笔是好的东西,纸是很温暖的东西。可能这对我以后选择方向是有影响的。
我父亲还有一个好玩的故事,这个会写进我小说的第二部。他小时候看相,那个看相的人说,他只能活到63 岁。他60 岁退休了,领了一笔退休金,他就想着,剩下三年我要做什么?把钱花掉。结果到63 岁还非常健康,于是他就去找那个相士问,结果发现那个相士死了。什么时候死的?大概十多年前,那时候相士63岁。
是我父亲记错了,原来活不过63 岁的是相士自己,不是说我父亲。可是我父亲搞错了,结果就在那三年时间把钱都花掉了,现在没有钱,都是我在养他。所以,我现在的命运跟我父亲差不多,就是我要养老婆、小孩,还有我的爸妈,全部是我一个人的肩膀承担。
朱又可:你小说中写的湾仔的故事,那是你小时住的地方吗?
马家辉:是的。那个年代湾仔很重要,好多香港的文人、写作者,都住过湾仔。坦白地讲,因为当时香港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发展起来,湾仔算是比较重要的地方,我在那边长大,一直住到20 岁去台湾。小时候我家对面就是运动场,就是修顿球场。我每天去那边打球、踢足球,看到的都是三教九流的人。
朱又可:你20 岁的时候,是怎么跟李敖联系上的?
马家辉:通过出版社,他那时候刚好在台湾的远流出版社出书,我写信给远流,他们就把李敖的联络方法给我,我就去找他了。他请我吃饭、聊天。
当时我很年轻,做事认真,看了很多有关他的材料,还在他的文字中找出矛盾的地方。有时候他说什么什么,我说不对,明明你以前是那样写的。所以,李敖才跟我说,家辉,以前胡适说我比胡适更了解胡适。我今天说,你比李敖更了解李敖。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李敖的嘴巴毒的时候很毒,甜的时候又很甜。
我印象深刻的是,我20 岁访问李敖,他那时候写了很多文章骂国民党。当时,刚好在台湾发生了一个案件叫陈文成案。他后来回到台湾教书,被发现在台大校园死了,大家都觉得是国民党特务把他弄死的。我记得,那时候跟李敖吃饭,就问他担不担心。毕竟他批判过国民党,又曾经坐过牢,担心他再被抓进去。李敖说,做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求仁得仁,第一只要我不靠他吃饭;第二我不怕被他陈文成(动词),我也不怕被他关,关就关吧。我就很自由,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时候我20 岁,这一段话就一直在我脑海里。
朱又可:当时你还正在台大上学。
马家辉:对。我一年级考上辅仁大学,是天主教的,很舒服的地方。后来一年级暑假,我就转学考到了台湾大学的心理系。心理系是理工科,所以要我修化学、物理、生物学,还有微积分,我毕业拿的是理学院毕业证书。我从小爱看色情杂志,对生物了解很多,所以生物学考得不错,而其他化学、物理、微积分,都是作弊才过的,几乎被退学。
说来也奇怪,那时我刚好出版了李敖研究的书,教我化学的教授刘广定是一个很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虽然是理工科老师,可是他很爱搞历史。于是,我就把这本书送给这位老师,他一看,大学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居然写了这样的书。他就找我去聊天,谈李敖、谈台湾政治等等。于是,我就获得了重考的机会。我的老师爱才,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不过,就要退学了,而我若是被这么好的大学踢出去,会很惨的。他给了我重考的机会,随便给我一个题目,我就乱写一堆,但也给我过了。其实,老师想给你过就可以过的。
所以生命蛮好玩的,幸好我出了本书,也幸好我碰到了一个喜欢历史的老师。但我当时不觉得,好像天经地义。
朱又可:你是从台湾直接到芝加哥大学,后来又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
马家辉:我芝加哥大学毕业之后,回台湾九个月,那时候海峡两岸刚刚开放,我就在电视台工作,带队去广州拍风土人情。台湾的电视台还说叫我演电视剧,我不做,我要去读书。后来,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收我读博士班。可是我读书,不是为了做学术研究。
我知道我没有那个耐性,也没有那个能力做第一流的像余英时、夏志清一样的历史学家。既然我做不了第一流的,那我就不做了。
我喜欢随心所欲,看自己想看的书,写自己想写的小文章。所以,后来就在报社工作,再后来就到大学教书了。大学的环境还是比较自由、比较有弹性的。所以我说性格决定命运。做人很公道,你要获得什么,你就要付出什么。
我现在是助理教授,香港的教授分三等: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假如从开始就想当教授的话,我觉得一点难度都没有。第一,只要你不冒犯、得罪别人;第二,你乖乖地跟着一个前辈做论文、发论文,升等很容易的。可我没兴趣,我不愿意付出那些时间和委屈。
我这个人有个不太好的性格,我非常放肆。所以我没有教授的职称,没关系,因和果,我要承受。
朱又可:放肆到什么程度?
马家辉:拿到博士学位后,当时我刚回到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系一个很重要的教授,搞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动邀请我做论文的评论人,还主持其中的一场研讨会。意思是你搞好关系,可以邀请你来中文大学教书。结果一看他的论文,我真的觉得就是中学生、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水平。
他以为我会给他捧场,结果我在评论上面出言不逊。我讲完之后,那个教授的脸都是黑的,所以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我当时觉得挺爽的,爽完,你当过英雄,就变狗熊了。所以,最后我还是躲在书房写书,在书房我是最放肆最快乐的。
读者比我想象的要保守
朱又可:第一部《龙头凤尾》2016 年出版,又花了四年,2020 年8 月,第二部《鸳鸯六七四》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
马家辉:第二部写出初稿后,前后改了很多遍。编辑说小说的女主人公阿冰“不可爱”,我觉得女人写得不可爱不行,就修改,结果比想象的工程大得多。就像你盖了一座桥,你想修桥的其中一边,结果就几乎往另外的方向修,最后等于另盖了一座全新的桥。
第一部《龙头凤尾》讲述香港黑社会龙头老大陆南才跟英国情报官张迪臣之间的暧昧关系,最后以张迪臣死于日本战俘营和陆南才被盟军飞机炸死结尾。
继陆南才当了帮会老大的哨牙炳“金盆洗捻”(捻,广东话卵的意思)的故事在第一部开了个头,但真正展开是在第二部里。黑社会本来就是黄赌毒,但是,帮会中人的“善良”,却也是普通人该有的善良。我家有个长辈就当过帮会老大,而当过警察的舅舅后来吸毒,因为这种亲切和熟悉,我对“黑社会”没有那么恐惧。不过,相比第一部的“太黄”细节,第二部做了描写上的“减黄”,淡化处理。我不希望那些描述构成了阅读的障碍,还是回到故事回到感情本身。
朱又可:做到了吗?
马家辉:人心中总是有阴暗有光明的地方,所以整个命题就是说我们怎么选择,我们怎么样安顿光明跟阴暗。我们对阴暗的部分承认它、面对它,还是保守它、排除它、压制它。
我的选择是面对黑社会并用小说艺术言说出来。
第一部“龙凤”是“同志”之恋,第二部“鸳鸯”是阴阳相配。作为帮会老大的阿炳跟杀狗出身的阿冰相爱成婚,恰是一对“冰与火”的反差与平衡。在跟上千女人告别的“金盆洗捻”仪式上,阿炳失踪了,几天后尸体被发现于海滩,已面目难辨。其时是1967 年,海面上每天都漂浮着逃港者的死尸。阿炳死后,一个帮会的新时代即将随着1970 年代廉政公署的设立而开始,这将是香港三部曲第三部的内容,止于1997 年香港回归。
帮会就是无间道。香港从开埠以来就伴随着帮会的兴衰起落,二者几乎不可分开,这也是香港文化的“暧昧”之处,没有别处那么黑白分明。我的书名用鸳鸯,也是香港精神的暧昧,在香港喝鸳鸯就是咖啡加茶,那种黑白不分的奶茶。
朱又可:我觉得阿冰是挺可爱的,也可能很好看。你虽然没写她相貌,但是感觉应该是不难看的人。
马家辉:谢谢,读者比我想象中保守。
朱又可:你说读者保守?
马家辉:比我想象中保守,我前面写了什么男同志、女同志,他们都好像——后来尤其是台湾,相对台湾的读者好像还比较保守,很多读者觉得太黄了。内地也有人说这种太黄了什么的。我觉得我并不在意他们的批评,而是说假如因为那个部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太黄,可能影响阅读感觉的话,我就不希望这样子。
朱又可:你的意思是说你后来删了一些吗?
马家辉:删了一些。特别相对《龙头凤尾》来说,描述上淡化了一下。
对帮会而言,江湖就是天下
朱又可:第一卷你写的是从上世纪30 年代到40 年代再到日占时期,就是到战后,写到陆南才和张迪臣死,这个基本上是结束了。第二卷是还往前延伸了一点,然后主要写1967 年。我很想你说一说香港帮会的历史,它和百年香港史的关系是什么?
马家辉:我个人觉得,对于帮会,有不同的角度来界定它,在我看来,帮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帮忙。其实所谓仗义就是帮忙,帮忙不仅是帮别人,也是帮自己。这个精神是从百年香港一直传下来的。我常喜欢讲一个小数字,英国鬼子占领香港之后,那些人很快就跑过来了。那时候,英国人就做人口统计了,英国人要算一下有多少人,背景是什么。没记错的话,大概1840 年代末期,他们的统计是香港有两万五千人,其中四分之三有帮会背景。你想一下这是什么概念?四分之三!
朱又可:除了殖民者以外,所谓的市民应该是很少的。
马家辉 :殖民者不多。那时候英国管治印度,只有几千英国人。香港那时候两万多人,四分之三的话,近两万人是帮会分子。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回到香港的本质了,他被占领、殖民,好多人从四面八方跑到香港来了。到香港后做不同的行业,搬运的、做木工的——还有个很重要的行业是采石。从内地不同省份来的人,潮州人、惠安人、广州人、福建人,甚至更远地方来的人,行业加上省籍,总要互相来支持帮忙。这个地盘是我们的,这个行业是我们的,你们外面的人不能来。或者说来了我们会保护你,可是你要缴一些会费。就像我们去健身房要缴会费,然后才能进去一样。
所以从一开始,帮会的这种帮忙,其实是自利也利他的,透过利他来自利,这种精神香港一直都有。
当然,这种帮会也有为非作歹的一面。可是这种帮忙的概念、仗义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有,所以这种核心精神在香港是很浓厚的。
朱又可:那就是它最原初的意义,那种黑色一开始是没有的,一开始应该就像是行业自我保护的那种组织。
马家辉 :当然它也是非法的,殖民鬼子很早,好像1940 年底已经颁布了什么打击帮会、地下组织的条例。清清楚楚地打击三合会。所以它还是非法的,非法你当然可以打击他、镇压他、抓他。可是英国鬼子很会玩政治,有时候抓,有时候不抓,有时候还利用帮会来管理。
讲文艺腔一点,甚至到我出生成长的年代,1960 年代1970 年代,对帮会其实是没有多恐惧的。当然,当他来侵犯你的时候,比方说卖毒品、抢劫、绑票,那是很讨厌的。可是回想起来,至少一直到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好像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帮会帮忙。
可能因为殖民的时候,殖民鬼子管着你——到1970 年代才有一些所谓的社会福利,之前没有的——你碰到事情怎么办呢?你只有找帮会帮忙。或是说帮会会自己演变出一种秩序。还有一点就是我经常强调的暧昧,是黑还是白,这个东西一直显现在香港的电影里面,对吧?无间道、警匪片什么的,特别能够拍出这种感觉,就像我以前在一些访谈或节目里也讲了,香港人帮助英国鬼子管理控制香港,有些当时就称为汉奸,可其中好多也都是帮会的人,他也是无间道。
像我经常提到一个人叫卢亚贵,他是谁?他基本上是个渔民,也是个海盗,而且他是几个帮会堂口的老大,那时候当帮会堂口很容易,我打个号召,我们朱家堂对吧?才十多二十人就一个堂。然后你可能又跟我合作,就有个朱马会,又是一个堂。所以卢亚贵是帮会老大,可是他也帮英国人来这边买水买粮食、卖鸦片、带路,那就是汉奸。当时的清政府怎么样?把他招安,说你别当汉奸了,你来当个官,给了他一个广东那边的小官。真的有官服、有名号、有钱的。他当官后又说,我在这边没啥用,反正我懂得英文,也跟他们熟,不如你放我回去,我替你们提供情报好不好?这样清廷就放他回去了。
他一回到香港,一方面跟英国人继续做鸦片买卖,替英国人做事,也提供一些情报,也给清政府提供情报,可是他两边都帮,就是无间道。从香港一开埠,就是一个头号的无间道。
后来英国全部占领香港,他就不当清廷的官,当了大财主。英国人也感恩图报,批了很多地给他,他发了大财,跟英国官员勾结,继续做各种毒品、妓女什么的买卖,但最后他破产了、失踪了、人间蒸发了。
朱又可:很好的故事。你能举例说你和一个亲近的帮会的人的故事吗?他具体在哪个方面帮过你?
马家辉:呵,太多了,说两个吧。一个是我的舅舅,以前是警察,抓了毒贩,贪小便宜,自己吸了毒,变成毒虫,进出戒毒所和监牢好多回,很多时候住在我家,经常跟我谈天说地,不断提醒我要好好读书,别像他一样。他说,他没有其他前途了,生命里除了吸毒的片刻能够暂时忘掉眼前,根本没有其他快乐,嘱咐我千万别像他。他又对我说了许多帮会故事,包括帮会中人用的暗语和诗句。有一回,我在学校被欺凌,回家对他哭诉,几天后,他陪我到学校找那群比我高大的同学算账,他也不高,但站在他们面前,气场取胜,讲了一些黑语狠话,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我不羡慕他的帮会背景,但羡慕他的胆色和勇气,以后一直提醒自己,遇到不公平的事情,要挺起胸膛面对,千万别畏缩。多年以后,他跳楼死了。
另一个经历是,有一位长辈是堂口老大,有一段日子,跑路到了台湾,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在他身边,陪同他跟三教九流的人见面,安静地听他如何跟他们对应,许多时候,确是“闲口一句”,令对方甘愿服从。他靠威势,却也靠人情,所谓人情,就是从对方的立场去看,明白对方想要的是什么。钱?权?名?色?他示范了,只要是人便有所欲有所贪,只要针对这些,供其所好,便有话好说了。那是混江湖的技艺,但若用在其他领域,其实也一样,简单来说就是,体贴对方,明白对方,在对方所欲和自己所欲之间,总能寻得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今天你帮忙我,明天我帮忙你,做下人情,便是播种,既是帮会中人的“善良”,也是普通人该有的善良。
朱又可:帮会在不同的时期和当权者的合作有什么特点?比如说早期的港英殖民者与日占时期和日本人的关系,后来又回到英国人的手里。
马家辉:我觉得他们都是做两面人。因为一代一代香港人主要从内地来。你说民族主义也行,他们生活在殖民者统治下,心中还是觉得寄人篱下;可是他们要讨生活,你就看到他们还得跟统治者勾结。但在民族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出钱出力,比如日本鬼子占领香港地区的时候,他们就帮当时的国民政府把留在香港的不管是国民党那边的人还是左翼的人,营救、抢救出来,其中包括茅盾、黄苗子等,都救回内地了。他们也帮中国军队救英国人,还有在日本政府那边做卧底的。所以他们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日本人统治,不管是合法的生活还是非法的生活,他们心中还是有一个理想,那个理想可能就是国家、抗战,或者民族主义,还有民间互相的帮忙。我觉得,可能也只有这样的帮会精神,才能让在一百多年殖民统治下的人活下来,才能够找到各自的空间。就是这样,他们在所谓的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里做他们的事情。
当然有一些是很坏的,他们是帮会的人,也等于是流氓。比方日本人统治的时候,他们就趁机来抢劫,来为非作歹,可是那些人也是被瞧不起的。
朱又可:日本占领香港地区的时候,据说有10 万人的帮会组织,据说他们是帮日本人打英国人的。
马家辉:打英国是不是有10 万人,我也忘记那个数字了。一定有的。他们就帮着日本人。日本人占领广东,占领中国,都有些帮会分子在帮忙。特别是广州。那些人那时候有个称号,叫做“胜利友”,他们所说的胜利是指日本胜利,因为日本打跑了英国鬼子。
这有个小故事,我在《龙头凤尾》写得比较深,在《鸳鸯六七四》里面稍稍有提起。就是当日本人占领了九龙半岛的时候,好多帮会分子都浑水摸鱼,在那边抢劫。香港地区这边还是英国人在管,香港岛的帮会流氓就很不服气,说我们现在要起义,我们要杀上太平山。因为那时候有钱的外国人、欧洲人主要住在太平山,我们要把他们杀掉,抢他们,要报仇,打洋鬼子。英国人都布防了,恐惧起来了,就去求他们不要杀人,怎么求呢?英国的警察高官就找了杜月笙,杜月笙找了他的门徒,门徒就找了那些流氓,结果就有200 个流氓跟几个英国的警官在香港开会。你能够想象那种场面吗?一两百个黑社会的人坐在下面,三个英国警官坐在上面求他们高抬贵手,不要杀人,你们要什么条件来谈判。诱之以利,当然也威胁,说虽然日本人现在很可能占领了香港岛,我们输了,可我们什么时候打回来就难说,假如你们今天不高抬贵手,以后大家就很难看了。谈判结果是,英国警察赔了几万块给那些黑社会。他们也没有几万块钱,是找杜月笙的门徒先借的。后来答应了还,有没有还不晓得。就有这么荒唐的事。那些帮会的人说,我们求财不求气,拿了钱就分一分,也没有去屠杀欧洲人。
反而是日本人统治了香港后,把那些欧洲人关在不同的集中营。那些帮会的人还有帮忙去把他们偷偷救出来的,或是把粮食送进去,也算是仗义了。我小说也有提到,杜月笙讲过两句话,皇帝他们暂时做,可天下还是我们的。
就是说不管日本鬼子还是英国鬼子管着香港,可是天下还是我们的。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朝廷跟天下其实是两个概念,天下有时候也等于是江湖,对于帮会的人来说,所谓天下就是江湖了,江湖就是天下。当然这一两句话是我编给杜月笙的了,就是说他来香港他是青帮,可是他来香港找那些洪门的兄弟,就要打招呼。而且有些兄弟问他杜先生,日本鬼子来了,我怎么办?我要不要走?他就劝他们说,留着吧,做事吧。
朱又可:像你写陆北风,因为战后广州这边要抓汉奸,他就逃到香港。那就是说在香港和广州这边对于汉奸的态度不太一样。
马家辉:在香港,汉奸还是讨厌的,他们在大家心中的感觉不好,形象不好。但没有怎么来追究他们,在香港,倒是没有看到大规模这样做。其中一个理由可能是英国政府都没有追究汉奸。在英国重新占领香港以前,伦敦那边发布命令了,说除犯了战争罪的,其他一律不追究。等于是说不管你那时候是帮日本人还是帮什么人,都不追究。英国政府为什么这样做?我的理解是,原因很简单。假如我帮日本人是汉奸,我帮你英国人做事,我是不是汉奸?其实我也是汉奸,对吧?后来英国人回来了,当时日本人找了一些名流成立了一些委员会,从一个角度来看,等于是汉奸了嘛,等于是伪政府了,可是英国人都没有追究他们,顶多是免了他们的官而已。只是追究了十来个当时替日本人当警察的、当特务头目的人。因为他们杀人放火。民间社会也是,比方说一些知识分子在当时也参与日本人的一些组织,甚至到报纸、杂志当主编,甚至写了一些文章。战后他们不提,大家都不提,继续当名士。我举例好了,一个人叫陈君葆,他好像是港大什么图书馆馆长。他在日本鬼子进城以前花了好大的力气,把港大图书馆里面很重要的书全部装箱辗转运回内地,保留下来,但他还是留在香港,还是在港大教书,好像还继续当馆长。他留有日记,记录他去参加日本人的茶会、酒会、诗会。
廉政公署成立是个分水岭
朱又可:你写的日占时期的帮会和后来你说到50 到70 年代的帮会有什么不同呢?
马家辉:完全不一样了,这个马上就可以谈到我第三部小说的写作计划。因为最关键的是,1974年成立了廉政公署。因为帮会能够壮大,坦白地讲一定跟掌权的人有勾结。他跟身居高位的那一群掌权者勾结,也跟下面的警察警官有勾结。后来廉政公署成立了,不管是警察警官还是黑社会,就面临一个选择了,你相不相信会反贪反黑?
廉政公署成立以前,香港政府也有什么反贪污部门,有反贪污条例,但大家都当做笑话来看,以为不过是又多了一个收红包的部门。但廉政公署是玩真的了,抓、查,结果有好多警察被抓了,黑帮头目也跑了,没跑的也变得低调了。1978 年就发生过一个事情,因为廉政公署抓得很厉害,警察当时被查了好多,人心惶惶。结果警察上街游行,等于是叛变了,几千警察上街游行,还跑去廉政公署门口捣乱,还抓着几个廉政公署里面洋人高官的领带,抓出来揍。
结果英国的总督就宣布特赦。就是说好像1977 年1 月以前的案件,除非已经被举报,已经在调查,否则既往不咎。那很重要,你看那些警察马上请客了,你不觉得很荒唐吗?好了没事了,我马上摆个18 桌、20 桌、50 桌大家吃饭,我以前的贪污全部没事了,因为既往不咎,很荒唐的。可是荒唐是一回事,大家放心了,然后按新的规矩来做事了。
我那时候刚好十来岁,所以记忆很深。不管是警察、黑社会还是民间,几乎不夸张地说,好像一天之间变了天,变成了另外一个香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什么法治精神好像都是那时候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黑社会就不能像以前那么肆无忌惮了。
当然它有其他的方式,比方说香港政府那时候也大展拳脚,所谓10 年新政,从1971 年到1981 年有各种的医疗、教育、房屋、社会福利政策,还填海、移山,开始发展。单香港还有一个地下秩序,比如说有几条街是红灯区;还有那种交通小巴,它有不同的路线安排,背后都有人收保护费。他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第三部小说就是处理这个年代的故事,讲他们怎么介入香港的经济发展、怎么样用非法的手法来经营,跟整个历史紧扣起来。
朱又可:你写到其中的一个帮会头头是在九龙城寨,九龙城寨的变迁是怎么样的?
马家辉:没了,九龙城寨在1990 年代初全部拆掉了,那个城寨很好玩,我们都知道它的历史,三不管,据说清廷租借新界的时候故意要留下这个地方。没记错的话,是李鸿章还是谁说我要留下这个地方,还是我们的。结果那等于是整个黑海里面有了一个白岛,一个区里面有清廷的官,还有清廷的兵,还有清廷的法律。后来清廷倒了,就成了所谓的三不管地区。
因为三不管,好多来到香港混不下去的人,作为一个过渡空间,就在那边。香港的法律也没在那边执行,所以房子大家乱盖,就变成密密麻麻,黄赌毒、吃狗肉,各种事情都在那边,甚至说警察都不敢进去。比方说有些医生从内地来的,他没有资格在香港执业工作,就躲在那边挂牌。当然收费很便宜。后来到了谈判香港回归的时候,就成了中英双方要处理的事情。最后英国人就说很简单,拆掉算了,于是就拆掉了。那里现在是一个公园。可是它作为一个景观,那是非常震撼的,其实蛮可惜的。你想一下地球上假如有一个区,那些楼房密密麻麻到那个地步,你推开你家的窗户,跨腿就可以到别人家,蛮震撼的。
朱又可:在帮助逃港的人当中,帮会起过什么作用没有?
马家辉:有,那是他们发财的时候。他们安排一条龙服务,等于非法偷渡。有些是游泳来,有些爬山过来。当然来到新界,他们要进九龙半岛,还要来香港找他们的亲戚。怎么来呢?要安排交通,安排带路,都是帮会做的。你爬山过来,来到元朗,帮会的人就会接应,要收钱,你没钱付他就先带你去九龙,找你的亲戚,你先给两百块,就要给两百块。当然那时候也有一些浑水摸鱼的,反正就收了钱不带路都有。
可是他们也怕,怕什么?帮会对于暴动没有太大的参与,他们反而是怕,因为暴动也好,反英抗暴也好,他们掌握不了事情的变化。别说帮会了,连当时的英国人都做了几手准备。其中一手准备就是放弃了,觉得解放军会过来接收香港,所以他们就走。所以不管是当时的老百姓还是帮会的人,好多都移民。有一群人那时候发了财,移民后房价大跌,然后他们就买房,当时留下来的就发财了。这是那时候的背景。阿柄就是因为死了两个小孩,然后也觉得差不多了,不想老婆跟另外的女儿也死掉,所以他就走了。
朱又可:你小说设计的金盆洗捻是纯粹的一种虚构吧?
马家辉:我不晓得,老婆她很希望发生,希望老公发生。这种其实认真地说起来,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挣扎。所以我的书名用鸳鸯,也是香港精神的暧昧,在香港喝鸳鸯就是咖啡加茶,奶茶,那种黑白不分。其实这种再推开来也不只是香港,我突然想起周作人有个小文章,大概是说我心中住了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一个是流氓鬼。有时候君子鬼会跳出来,我就是君子。有时候流氓鬼跳出来,我就做流氓了,做坏蛋、做坏事、想坏事。大概等于是一个天使一个魔鬼。这种人心中有阴暗也有光明,所以整个命题就看我们怎么选择,我们怎么样安顿光明跟阴暗。
金庸作品是中华文化的资料库
朱又可:你1997 年进入《明报》做副总编辑,那时金庸先生已经离开,请谈谈你跟金庸先生的交往经历。
马家辉:我和金庸先生在十来次小范围饭局当中见过面,印象中金庸先生话不多。他坐在那边就是听,然后你看他眼睛一直眨眨眨,甚至不会主动点评,要别人来问他。当然那么聪明的人几句话就讲到重点,而且他非常直接,不会拐弯抹角。有几回金庸太太在,他太太和他年龄有差距,金庸在其他人眼中是大作家,在他太太面前,就是小孩了,讲话特别温柔,整个人也温柔了下来。
朱又可:你能回忆一些关于金庸的旧事吗?
马家辉:我先谈我年轻的时候读金庸吧。我就像好多人一样,十来岁开始读他,在我湾仔的家,人很多,躲在角落读。我看好多人都有一种经验,每次一读就一头栽进去,我还记得那种感觉。我因为家里小,比方说只有十平方米,住了八个人,又经常打麻将,很吵。可是每一次读他呢,就感觉整个身边的声音、整个世界都离开我了,或者是说我离开了身边的世界,跳进了他的世界。所以就感觉他的小说,把我从那么吵闹那么不舒服的生活环境里面,拽去了另外一个江湖。所以非常感恩,我最近也喜欢读,他又很好玩。我身边当时有几个老铁,读书成绩很不好,什么科都不好,除了中文还不错。那他们为什么中文不错呢?就是因为喜欢读金庸小说。
这种情况到后来我自己长大为人父母,听到很多,直到今天也一样,一些朋友的小孩,假如中文不好,不喜欢中文,他们都有一个方法说,给他们读金庸。读完金庸就会喜欢两个东西,第一个喜欢中文,第二个喜欢美食。所以阅读金庸学中文这个方法到今天还是有效的。这是我以前从小读金庸的一个经验。我不晓得内地情况如何,香港是这样的,给小孩读金庸,他们就喜欢中文。
朱又可:你跟他在《明报》时期的交往有什么故事?
马家辉:当然完全谈不上交往。1997 年我回《明报》担任副总编辑,那时候《明报》已经不属于金庸了。可是我还是在报社里面听到好多人以前都是跟着金庸工作过的,说了很多金庸的故事。主要还是说两类,金庸就像一个大将军,通常有一个很好的本领,懂得用人。他看到有谁好,他就找来,然后很准确地把那个人放在某一个位置上面,谁替他编辑月刊,谁替他编晚报,谁替他写社论,谁替他管财务。而且他很用心,很温暖。对他喜欢的人才,很有温度,也有很重要的培训。
对普通的员工,他就很苛刻了,甚至连倪匡也说过他不是一个好老板,因为他的薪水比起同行低很多,工作很辛苦。因为他有他的金庸哲学:来我《明报》打工,第一个你可以学到很多,第二个你跟着我金庸工作,是你的光荣,等于是你的红利。所以薪水低,薪水低有什么关系呢?薪水低本来就应该的。
朱又可:是吗?他对员工除了苛刻还有什么?
马家辉:我印象中,大概十年前,有一个以前的老员工也专门写了一本书来骂他,那个书名叫什么“我在金庸手下工作”,或者“金庸是我老板”之类。他作为报社的老板,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报纸是我的报纸。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在报社里面当然没有言论自由,因为报纸就是老板的报纸,我要登什么,我要引导这个舆论方向是什么样,那当然是老板做决策。所以后来,也有很多报社里面的员工因为不认同他的主张,干脆就跳槽了,这是我在报社里面听到的和观察到的。
我去的时候,好像《明报》刚卖了一年多吧,一两年了,所以那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对他来说非常伤心,他卖给于品海,是千挑万选的。他找高层的员工也是这样子。他有一个很喜欢用的方法,就是跟对方一起去旅行,好像现在你要找男朋友,跟他去旅行一样,就在旅途上面观察他。所以于品海为了跟他旅行,带着老婆小孩一起。后来他就信任他了,金庸还把钱借给于品海来买自己的报社,你看他多么器重于品海,多么重视这事情。后来于品海出事了,他就非常难过、伤心。
朱又可:批评金庸的人不少,比如王朔就瞧不上金庸的武侠小说,你怎么看待这种批评的声音?
马家辉:胡适,还有王朔都批评过金庸,他们有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没有很新,就是一般对于所谓俗文学与雅文学的一些争论。不仅对于金庸作品,从简·奥斯丁,甚至狄更斯、莎士比亚,对俗文学的经典化,或者台湾地区说的正典化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的争论。所以对他们的观点,第一觉得没有什么新意,第二他们的观点也太浅了,什么通俗什么浅薄啊这样。我觉得评论小说不是那么简单。
我反而关注的是读者对于金庸阅读的趣味在哪里。为什么金庸能够成为所谓的“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这个部分我觉得有趣,他除了凭丰富的人物、有趣的故事以外,还有什么能够打动一代一代读者,而且每个人都说你不可只读一部金庸,你要么读了就放不下来了,就是一口气把金庸的作品全部读完。
我关心的是,这个动力在哪里,或者说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个“阅读快感”在哪里。我个人觉得,先不管什么我刚刚说的人物的丰富、情节的有趣、历史感等等;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方面是,金庸透过他的文笔、故事、人物,把读者带进一个我们中华文化一直好像很关注的两难困局里面。中国人一直都是两难。从孔子、孟子一直都说鱼与熊掌,舍生取义,这个套在现实里面,就是国家、民族,什么个人、爱情,或者说爱情跟生命的取舍,或者说门派、老师、师傅跟个人的取舍等等这种两难困局。他几乎每一套作品都把不同的人物放置在某个两难困局里面,面临怎么取舍的艰难抉择。
这个两难困局,往往一方面是外面的大道理、大传统、大框框,可能就像我所说的,国家、民族、集体,甚至门派。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个人的欲望,可能是情,可能是权,可能是利,可能是名誉、光荣等等。我经常怀疑,是这种两难处境、两难困局,让大家读得这么过瘾。而且我们都知道,金庸是用中文来写中文,而不像有的小说是欧化的语言、西化的语言。里面写的人物、细节、地方,有人做过对比,小说里面写到很多金庸18 岁以前的成长经验,比方说写他跟他母亲的关系,比方说写他去逃难等等地方;他们把那些经历和小说中一些场景、情节对比,发现其实就是金庸把他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所面对的各种场景、人物,放进了小说中去。
金庸的作品让我们在熟识的文化语境里来面对这种两难困局,让我们感觉焦虑,也跟着里面的人物来做选择。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是阅读金庸最有趣味的一个地方。我感觉,故事看来表面是写这些,其实是通过两难困局来挑战。因为假如那么简单的话,你只要为了什么大道理、大传统,我们就去做事,那太简单了嘛,很好写啊,但不会好看。我们作为一个人,独立的个人,我们会焦虑,我们要违抗吗?我们要顺从自己的爱、自己的选择吗?我觉得这个部分,读起来才是最觉得过瘾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金庸作品跟读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说什么,哎呀,俗啊,人物很片面化,语言很通俗,甚至只要是流行都是错。这是我的看法。
朱又可:你怎么评价金庸这个人的贡献?
马家辉:说到对金庸作品的看法,我觉得虽然金庸作品被称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那我觉得这个共同语言,其实是中华文化价值里面大的资料库,是个database,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
既然是这样的话,金庸很多人物面对两难困局,韦小宝的拍马神功,很多名词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弄成普遍的语言,甚至弄成可以操作的临床医学、临床心理学用语。或许我孤陋寡闻,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人也不多,我觉得可能金庸自己也担心,那么多人读我的作品,为什么好像从不同角度去研究,还是远远不足的。我们都知道,他花了很多金钱跟精神去鼓励支持他的粉丝把他的作品翻译外语,进行研究,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有人说他贪慕虚荣,我觉得一个作家非常在意自己的作品,觉得你们研究得不够,假如你们愿意花时间精力想去研究,我当然支持了,何况我又有财力、又有能力、又有影响力。
这是金庸做人的认真,所以他晚年还去英国再读博士,又有人阴暗地说怎么这么虚荣啊,你学问这么大,成就这么高,还需要这个行头吗?我觉得提出这个批评的人,本身根本批评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