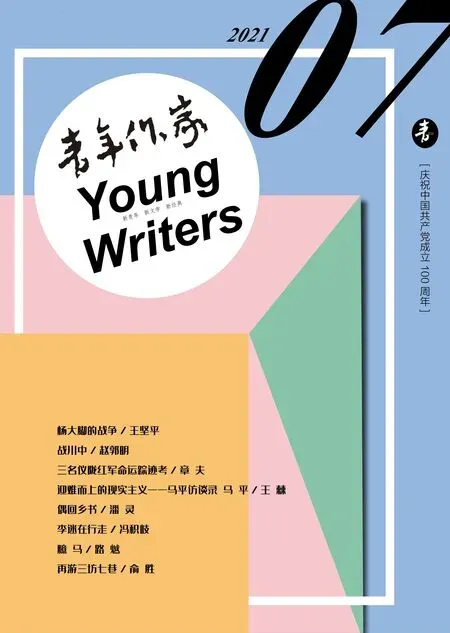新南方写作与黑色浪漫主义者路魆
唐诗人
读路魆的《心猿》《臆马》,我总感觉他是被黄锦树缠身了,每个句子都散发出阵阵南方的湿气和阴气。不对,是新南方!路魆是正宗的广东人,生于肇庆,长于岭南,目前也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最近,岭南等“南方以南”地域的写作有了新头衔,叫新南方写作。不管这新帽子路魆喜欢不喜欢,我读着小说时就特别想给他戴上,而且就像杨庆祥阐述新南方写作时用了黄锦树的写作作为典型一样,我也特别想把路魆的小说风格界定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南方文学风格。
像很多人用后现代主义来理解黄锦树的小说一样,目前人们对路魆小说的认知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前不久路魆发表中篇《暗子图谱》,就被多人评判为后现代主义风格写作。但我始终不愿用“后现代主义”这种被人们使用得毫无感觉的文论概念来界定路魆,我更希望摆脱这些大而无当的概念,而使用一些更具触感的词语来形容,比如阴郁、幽暗、潮湿、诡诞。路魆和黄锦树一样,喜欢写湿漉漉的森林,小说中经常出现乌鸦、黑鸟等既有地域特征又带神秘感觉的意象,包括人物塑造方面的忧郁、怪诞性情和失踪、死亡命运安排,这些都是路魆与黄锦树作品风格上的共性。有人评价黄锦树《乌暗暝》说:“故事多发生在南洋的胶林小镇:移民南洋的华人处在野兽环伺、种族压迫、殖民侵略、认同焦虑的环境中,面临各种形式的离散、失踪及死亡。”我觉得可以换掉这段话中的几个词来概括路魆《心猿》等小说的基本风格:故事多发生在岭南某个靠近森林的荒芜小镇,被现代生活所抛弃的人们处在野兽环伺、精神疾病、残酷野蛮、自我迷失的环境中,面临各种形式的暴力、失踪及死亡。之所以替换掉“移民”“种族”“殖民”“离散”等,一方面是因为路魆与黄锦树身份不同,另一方面也表明路魆这种风格的写作很容易陷入“为风格而风格”状态,毕竟他没有黄锦树身份背后所意味着的沉重历史,但这种历史感的缺乏,是否反过来说明路魆这种叙述风格在美学上的纯粹性?不是因为要负载特殊的历史内容而生成这种幽暗的文学风格,而是因为生存环境和作家独特的创作追求而塑成了这种迥异的美学形式。但是,抛开沉重的历史,路魆身上的黄锦树气息意味着什么?
比如《心猿》,路魆虚构这个故事,纯粹是为了营造一种诡异的美学风格。小说中的马斯布父子以制作蜡像为业,最先是专门替各地博物馆制作那些已灭绝的动物蜡像,后来无意中父子合作制作出一个不存在于现实中的动物蜡像。制作不存在的动物蜡像,这是一件特别艺术的事情。这一偶然事件搅动了父子俩的艺术细胞:“马斯布的父亲决定不卖,他从这种无中生有的虚幻形式中,看到了某种潜在的未来,以及超越常规的乐趣。”从实用、商业化的蜡像制作、过渡并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创造,这对于马斯布父子而言是一个从技术到艺术的境界突破。但同时也带来了危险,马斯布后来接了一个特别艺术的活:制作一个“弥留之际的人”的蜡像。弥留之际的人应该有怎样的表情?这考验着艺术家的想象力,能否制作出来意味着作为艺术家的马斯布是否跨越了人类思维的局限。马斯布为此着迷,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创造活动中,以至于头疼欲裂,猝死在工作台上。“倒下时,他的脸恰好压在雕塑泥上。”马斯布用自己的生命留下了弥留之际的表情。但蜡像制作工作并未完成,为此,路魆让他从殡仪馆中复活归来继续完成了这一艺术创作。以上只是故事的一半,这个故事显然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隐喻。马斯布为了创造出人将死之际的表情、蜡像,这件艺术品本身并无什么可见的社会价值,但马斯布却愿意为之付出生命,且死后还不愿放手,还必须复活回来把它完成。这不就是艺术家为艺术献身的最好隐喻吗?路魆创造这个故事,或许就是在解释自己为何要创造一种绝对纯粹的美学形式。他似乎想要告诉评论家:没有历史感,纯粹形式的美学表达也有生命,甚至可以更有美感、更具魅力。毕竟,我们肯定会慨叹马斯布为艺术献身的精神,也必然会为他最终突破思维界限把一种不可能变成可能致以至高的敬意。为艺术而艺术,怎么就成了问题?路魆用《心猿》反驳了这个时代愈来愈世俗化的文学观念。
马斯布复活回来完成了最后的艺术创造,随后,故事转由“我”这个多年不做手术的尸检解剖助理来讲述。“我”检查马斯布死因时把心脏挖出来且让野猫给吃了,然后马斯布被一道白光给唤醒、自行回家了。“我”为了弥补失误,找到马斯布,又受马斯布父母所托,找了心脏来弥补。开始是找了猪心,于是马斯布变成了猪,随后找了猿猴的心脏来换,马斯布于是变成了猿猴。这后半个故事特别荒诞,与前半个故事的关系可有可无。但路魆显然是不在乎这种故事层面的前后逻辑,他要突出的恰恰就是这种怪诞感和黑色浪漫性。之所以说是浪漫,因为这根本不现实,作家想要表达什么情感,叙事就往哪里去。
不牵涉历史,不在乎逻辑,我们理解路魆的作品时,其实就是直接在感受文学的形式和风格本身。路魆讲述的那些黑色怪诞故事,都是纯粹想象出来的,它们并非小说的核心部件,它们只是作者用以承载美学风格的容器。路魆刻意要把小说的形式和内容颠倒,他排斥讲故事,只热衷于塑造一种独属于自己的美学风格。他不希望他的读者是来听他讲故事的,他的故事内容是很不重要的维度,只是为了一种荫翳的美学风格,他不得不讲出个像那么回事的故事来。路魆的兴趣只在于如何用一种湿漉黏稠而又诗性的文学语言,表达出一些诡异的、阴郁的精神感受,以及烘托出幽暗、暗暝的审美氛围。很多时候,我们对路魆小说的阅读,之所以能够持续至结尾,并不是被小说的故事情节所吸引,而是不自觉地沉浸到作者纤穠语言所营造出的诡异、幽暗审美氛围中——这是真正的沉浸式阅读。这种感觉,有点类似于我们阅读现代哥特小说时的状态,完全被作品中荒芜小镇、幽暗森林、凶恶黑鸟——对,连美好的鸽子都要强调是黑色的——等恐怖意象所塑造的氛围俘获。当然,路魆的语言比哥特小说的文字优美得多。同为90后作家的鬼鱼曾点评路魆《林中的利马》说:“路魆的小说有奇异质感,审美取向多在我们所熟知的世界之外。每次阅读,都仿佛置身于亘古的陌生部落,四周是潜伏的魑魅魍魉。”《心猿》《臆马》也是如此,奇异的质感是语言和叙述,陌生部落是故事环境,魑魅魍魉是形象和氛围。路魆是像写诗一般写惊悚小说,黑色唯美,恐怖魅惑。
为了创造一种美学形式而去虚构故事内容,这当然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叙事。后现代主义要冲击的是一系列“元叙事”,像传统文学叙事相信的内容决定形式,路魆肯定不信这个。在反元叙事层面,路魆似乎又和黄锦树一致了。但同样是后现代、反元叙事,路魆与黄锦树是不同的。黄锦树的后现代里有很多拼贴、并置和后设,以及人们将他视作非主流角色所成就的异质之美。路魆的后现代是美学风格意义上的纯粹性,所以黄锦树更魔幻、更沉重、更压抑,而路魆更黑色、更唯美。黑色与唯美,这其实是很现代的叙述,或者说是最纯粹的后现代美学形式。路魆似乎有一种野心,想通过中国亚热带潮湿荫翳的岭南地域风格来重构西方文艺史上的黑色浪漫主义传统。为此,我们在路魆小说中会感受一些爱伦·坡式的黑色惊悚元素,同时又有浓烈的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味。但是,欧美文艺史上的黑色浪漫主义风格也有他们相应的历史背景,比如早期十八世纪西班牙戈雅的黑色绘画,精神背景是战争和宗教势力的堕落,到19世纪哥特风和唯美主义,历史背景换为野蛮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20世纪的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背后是战争的残酷、是理性发展到极端所带来的压迫和邪恶,为此想用潜意识和梦境来完成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内容呈现。无论哪个阶段,黑色浪漫主义风格都带有明显的批判色彩。如此,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历史感问题,如果在路魆的黑色浪漫风格背后看不到历史感,他以岭南地域文化来重构黑色浪漫主义风格叙事的目的和意义何在?这一问题似乎也困扰着路魆自己,因此他特意虚构一篇《臆马》来专谈“历史感”。
《臆马》的怪诞感和黑色浪漫特征不比《心猿》弱。主人公“我”叫罗波,因为从小和邻居马可一起玩,便被人唤作“马可·波罗”,我就成了波罗/菠萝。我不但名字是植物,脸上还长满了铜绿色疙瘩,跟菠萝外皮的颜色和形状一样。长大后,我被父母赶出去了,他们说我需要历史感。我离开家后,为了获得历史感而选择与马可一起生活。我和马可一起逛旧货市场,我寻找历史感,马可则寻找《特洛伊》电影中的道具铜马。铜马找到后,马可为了报答我,强行拉我去医院治好了脸上的皮肤病。出院后回到家我出于恐惧,砸死了一个一直跟踪我的男人。误杀事件导致我和马可开始做噩梦,我梦见自己是个古代帝王,我的麾下大将与我的妃子私通,于是我将他处以极刑。而马可梦见自己曾是元朝骑兵,最后被皇帝处以极刑。我变得无法分清现实和梦幻,把墙上挂着的商纣王肖像当成是镜子里的自己。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对历史感的辨析:我为何不敢照镜子?我是认同自己手术前的植物面目?还是相信治疗之后的干净脸庞?植物面目背后是古老的铜镜所折射出来的老朽,这充满历史感;但我又不敢去照现代的镀层镜子,不愿意接受新的自己。历史感其实就是认同感。路魆很顺利地把小说的历史感问题转换到了人物的身份认同问题。写作的历史感可信吗?后来“我”父亲告诉我,那面铜镜其实是旧货市场上买来的赝品,也就是说:我被赝品照出来的形象欺骗了,且还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我们的写作亦是,到处都填充着历史素材,可其中会有多少真正的历史感呢?
《臆马》小说最后,马可为了让我看清真实的模样,把我推往厕所去照真正的镜子,但我把马可绊倒打晕,将他藏在了铜马的肚子里。随后,我联系马可的妻子,邀她来看马可送给她的礼物。我们在铜马底下烧火取暖等待马可的出现,一边还讨论起了中国古代刑法炮烙和西方刑法铜牛。当马可妻子意识马可在铜马肚子里时,我告诉她:“你跟妲己一样聪慧。但你当年选了马可,没选我……我真的……难以释怀啊。”马可被我用铜牛方式处以极刑,马可妻子为了救马可拍打烧烫了的铜牛,为此挨了炮烙之刑。可见,我已经彻底陷入了疯狂,已无法分清楚历史、现实和梦境。小说中我——波罗的状态或许就是文学创作的状态。小说创作处理历史,是让历史、现实、神话、想象、梦境等等交相辉映。这种处理方式,并不在乎小说呈现了多少真实历史。正如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这事一般,真假不要紧,但有了这一叙事/文本,它就成了可触摸、可阅读、可想象的精神遗产,自然会与真实/实在发生关系。
路魆利用马可·波罗来讲故事,这让我想起利玛窦。16世纪末,利玛窦曾在路魆的家乡肇庆建立其在中国的第一座耶稣会布道所。据说当年有几位中国士大夫去拜访时,看到布道所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地图上的中国被压缩在右上侧的一个小角落,这让那些士大夫大为惊骇。所谓“大为惊骇”,在那些士大夫那里意味着世界中心的调整,是世界观的撼动。今天,我们读肇庆作家路魆的作品,或许也有一种惊骇感。它不一定影响我们的世界观,但足以撼动我们关于小说叙事的惯常认知。路魆颠覆内容与形式的主次关系,重构小说叙事的历史感和想象力,营造出一种纯粹的美学形式——这是一种属于中国岭南的黑色浪漫主义风格。黑色是幽暗的、阴郁的,浪漫是想象的、诗性的。从黄锦树到路魆,我仿佛看到了新南方风格的觉醒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