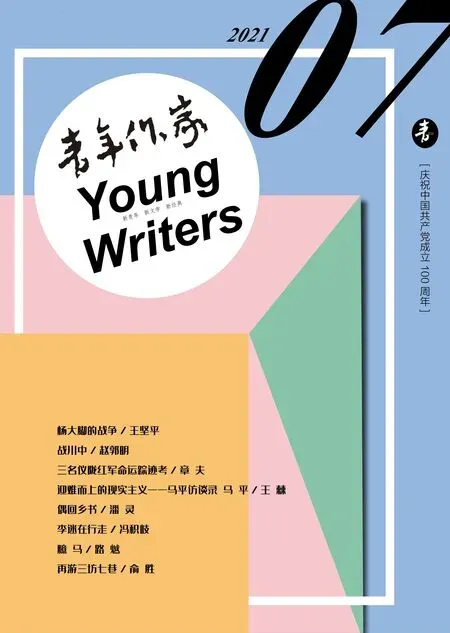红房子
程多宝
一
数年之后,营盘里那一排排迎风立正的红房子,在陈德宝稍一打盹的时候,潜入得有些活色生香。如同操场上的队列,有人一声口令,无声地踢起了正步,排山倒海直扑过来。陈德宝有时不大相信:海市蜃楼,或许就是这种神奇?
于是,陈德宝索性不再睁开眼睛,静等红房子们碾压过来,看似重重地罩住了自己的身子骨,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压迫,反而特别的亲,还有种甜甜的味,吸上一口,以前身上痒得挠不到的地方,居然没了;还有的是,晕晕乎乎的脑子,吸足了氧气似的,精神了一大截。
往往这个时候,多是深更半夜。陈德宝难得一笑,有时笑出声来,离他身边不远处的那张小床上,十回就有六七回,莲子不醒也睁了眼,摸起一件衣裳披着,就着隐约的窗外碎光探了探身子,看到陈德宝还在梦里沉浮,莲子打了个呵欠,原本想钻一回热被窝的念头,说没就没了。
这些天,或者说这些年来,自打男人退伍之后,很少有过睡得这么安实的时候。
类似的梦,有电视连续剧的范儿,没头没尾,又没完没了,来得突然,醒得也惊。陈德宝心有本账。这些年来,最懂自己的除了连长,就是莲子,如同那一排排红房子最让他自己懂得。红房子们时而安分时而沸腾,身架子一律余光标齐,自九里山下快到心窝窝处的那个旮旯,站成直挺挺的三排,每排那么几间平房,如同队列里的士兵肉身,中间隔着缝隙,任风儿肆意游走。这是一排排1970年建设的红墙红瓦。某个双休日,陈德宝难得出一趟大山,返营时过了卫兵把守的营门,从东往西,闭着眼睛数着脚下步子,也能知道自己走到了哪个营连的屋前:电子对抗营、炮兵指挥连、武装侦察连、技侦队、气象室、看守所……最里面的那一排平房,十几间红房子手牵着手的,就是他们的防化营。
红房子与山外相连的,只有那条蜿蜒的山道。所以说,当兵当到了一期士官的陈德宝,退出现役有些年头了,还一度纠缠不清,究竟是先有了这一排排红房子,还是先有这条山路;那一排排红房子,每天早晨如何醒来?是军号声呼唤,还是飞鸟啼叫,或者由着他们的脚步声舒筋活血?
每天清晨,只要不是特别操蛋的雨雪天,雷打不动的,从其中一间红房子里钻出来的陈德宝,还有他们这个连队的百十号人迅速集结,伴随着响雷式的口令,还有一路炸天式的番号,齐齐杀出营门,隔三岔五就来了个五公里武装奔袭。这要是冬天,难得一遇的路人,一度也看不到他们嘴里哈出的热气。
其实,那一口口热气,被一根根长长的象鼻子似的软管,仙气似地回收走了。
新兵下连那会儿,陈德宝惧怕戴防毒面具。本来一大早跑五公里,气就不大顺畅,偏偏嘴上罩着一截象鼻子,这不要命么?可一看到每天跑在最前面的连长,中途不打一个停顿,还时常照顾着体弱的士兵,陈德宝怎不心服口服?后来的陈德宝一抬眼,看到的榜样就是离他最近的连长。
这时的陈德宝,是防化营洗消连一排一班长,他的眼光只要往上一望,越过身子前面的一排长,连长的背影活生生地挡在眼前。这年开训动员之前,指导员突然提拔去了机关,位置一度空着,这么一个大家,只能是连长一肩挑,既当爹又当娘。几个排长,甚至副连长副指导员都为连长叫屈,本来他们也认为这次提拔,轮也轮到连长啦,民主评议票数那么高,怎么又成了备胎?当然,这些只能是私下,像陈德宝这些有些年头的兵,多少也听到一些。只是连长似乎不关心这些,他的大嗓门依旧,早上的五公里越野,出发口令一炸一声雷。有雾的大清早,陈德宝分明看到,山腰间悬浮的几条若有若无的岚丝带,一时也被吓得惊了魂魄,好半天一抖一飘的。
当兵的嘛,从那一排排红房子里出来的,连长就是榜样!哪像阿汪,哪天早上的五公里越野,有个精气神?
阿汪是陈德宝老乡,一个火车皮拉过来的,小时候一个庄子里长成男人模样,哪个不知根知底?只不过阿汪肚子里装了一只倒不完的墨水瓶,人家当年考上了县城一中,眼下正准备报考军校。
“你那个身子骨,三公里都跑不下来,还考什么军校?”陈德宝也替老乡着急,这要是以后成了排长连长,五公里越野啥的总不见少,你不站在前头,兵会服你?
“要是考上军校,为什么还回九里山,戴这个象鼻子?”阿汪的身影一闪而过。
那一排排红房子,忽地朦胧起来。
二
阿汪考上军校走了,转年,陈德宝的一期士官到了最后一年。连长有点难受,话语漏气一般:二期士官,名额紧,怕是……
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一班长啊,哪个不想留你?你听我说……
陈德宝想说点什么,可又没说出来。连长没辙了。他们这个连队,说是特殊兵种,其实那些技术没有多少含量,只不过更为需要的是奉献,甚至是不怕牺牲。陈德宝这样的技术骨干,连队主官哪个也不愿意放人。兵嘛,舍不得离开营盘的多了,这样的连长当起来,那才过瘾。
陈德宝点了点头,剩下的没话了。要说的,去年在红房子里面,自己举着右拳那会儿,兴冲冲地热血往头上直涌,仿佛这一生的事,在那几句话里,什么都交代完了。
“要不,眼下还在队伍上,先探个家?”连长声音低了,目光越过九里山下的那一排排红房子,似乎想要飞越到山的那边。唉,像他这样的兵,这些年耗去了太多,连队又能回报人家多少?趁着穿着军装,老家皖南那一带民风淳朴,以后要是脱了这一身,说不定找对象都困难了。
探家?连长……眼下,还不大想,真的。连长听出来了,他这样的一期士官,一两年内就有探亲假,陈德宝这么些年,印象里只探过一次。那次,听他回连时说,不知怎么搞的,一离开红房子,成天晕车一样,身上还痒得不行,浑身也挠不到痒的地方……
真是怪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反过来了?连长帮他分析,点穴把脉式的那种促膝谈心,最终也没有谈出个所以然。陈德宝回忆了一会儿,说,刚当兵时,戴上防毒面具,气就不大顺畅;一穿上防毒衣,浑身痒得不行;坐上洗消车端起喷枪,“三合二”味道一闻就想吐。怎么一探家,离开这些了,反而成了病怏子。
“三合二”是防化营洗消连战术训练时的一种喷洒试剂,化学成分是三次氯酸钙+二次氢氧化钙,腐蚀性极强,从洗消喷枪里射出来的水流,白白的如同乳浆。初上训练场,好多新兵上车前心里就打着鼓,这么多年,连长第一次听到,像陈德宝这么上瘾了防化洗消专业,还真是第一人。
这么想着,连长更有心了,觉得更不能亏了这个好兵。
“怎么,还没想……结婚的事?”这次,连长等不及了,他有点搞不清这个兵,怎么这么依恋红房子?的确,他自己也依恋着,红房子老是老了点,这么多年冬暖夏凉不说,遇上烦躁的事,走进去再一出门,神了,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
“要是以后,退伍了免不了念想,多拍几张照片就是了。”那时候部队官兵还不准配手机,要不然,可以录个视频。连长只能这么说了,停了停,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像要说的后半截,全在里面了。
陈德宝不是没想过成家,到这岁数,又是热得发烫的身子,白天里顾不得想,夜梦里总免不了。可阿汪临走时说,这些年先别想结婚的事,你看看,连里几位干部,生的都是女孩。
这么一说,陈德宝想起来了,阿汪这家伙有心机,难怪报考军校想的就是离开九里山。可是,陈德宝还是不相信他的这套歪理邪说,年初晋升机关的指导员,嫂子不也生了个带把的?
那个嫂子,陈德宝有点不大喜欢,家属来队了好多次,到头来连人家姓甚名谁也不知道。成天看她烫了个头,伙房里钻进钻出,几乎没空过手;与战士们打乒乓球,争个输赢还掉链子。一比较,还是连长家属小林老师好,暑假里进一趟山,帮兵们补衣洗鞋,有时还补点文化课。那次,连长查铺查哨时才发现,皮鞋下的鞋掌,也让小林老师悄悄拔掉了。
三
陈德宝哪里不想结婚?只是他一心想着,以后要找的那一半,最好像小林老师那样,虽说不一定有小林老师那样美丽、贤惠和高大上,要是一名教师,当然最好。
其实,陈德宝有所不知的是,比他家长还要着急的是自己的连长。连长通过团政治处联系上了陈德宝所在家乡的县妇联。那个叫莲子的女人,虽说不是教师,初次见面时那么一笑,害羞的样子让陈德宝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来,自己的这一百多斤,就交给她了。
那一刻,虽然寂静无言,可陈德宝觉得有些按捺不住的冲动,与自己当年在红房子里吼出的誓言有得一拼。那次,算是两人的第一次约会。周边寂静,似乎听见身上的血液在流淌,还有的正对着两人面前的,那一河嫩得如草芽一样的碧水。莲子想问的话,一如河面上扯起的皱纹,一波一浪地相互推搡着,碎得前仆后继。好端端的,那一排排红房子,远远近近地走着,只一个恍惚,似乎涟漪在走、水草在走,甚至岸上的莲子她也在走,望天望地又望了望人,方知那一刻波涛没走、水草没走,身边的莲子真的没走,是风在走:部队的假期匆匆忙忙,好不容易赶上了训练间隙期,部队上的结婚介绍信都开出来了,要是没啥意见,还等个啥呢?
无声的,对面笑了一下。那一河的水波,突然间红映映的。天上,涌过来一些白云絮絮,像是弹了一床迎亲的棉子,盖天盖地的,没见着一枚刚升或是刚落的日头,哪里来的满天满地的红?
结婚还没一个星期呢,哪知就出了情况。起先一点征兆也没有,就是成天犯困,睡不醒似的,紧接着浑身奇痒难熬,密密麻麻的红点,前胸后背遍及,仿佛夏夜的繁星坠满了一件大袍子,忽地一下披上了身,一汪一片的“青春痘”,夜里抓破了皮,一大早起来淌黄水,没完没了。
更要命的,一开始还不敢对莲子说;幸好,脸上一颗豆儿也没有。要不然,唉,蜜月刚刚起了个头,陈德宝睡觉时再也不敢脱去内衣,甚至一度都不敢贴近莲子白花花的身子。
是不是,九里山那边,有人了?女人担心了,可一想也不对,这样的气话可不能乱说,影响军民关系呢。于是,一转身,又笑了:哪能呢?妇联介绍的,要是不那么优秀,组织上能这样不负责任么?
男人扛不过去了,只好实话实说,必须的:原来,真的不痒,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
还有呢?
头晕,不是缺氧,有点像是醉氧,可能……好久没戴防毒面具,也没有穿防毒衣,更别说五公里越野了。
莲子急了,拽着他进了城,直奔全县最厉害的第一医院,挂了一个挺贵的专家号,检查单子填了一圈下来,啥也没有,各项指标都正常。
这种痒,到底是个啥?新婚小夫妻怎么不急?专家也没了招:再观察一阵子,再说,这……也不是癣啊;头晕乎乎的,要不,歇几天看看?
莲子叹了口气,莫不是,你的魂,落九里山了。听说,那可是个古战场,地底下尸骨成堆。是不是晚上夜哨,遇上什么鬼神了?
以后站岗,要是深更半夜的,那……能不能与别人换换?眼泪汪汪地又补上了一句。
瞎说,怎么还信这个?那怎么成?眼下,还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陈德宝的眼前,似乎那一排排红房子又浮现了,“我宣过誓的,不能不算数!”
“那……假期一结束,还是快回部队吧,去找你的魂。还有,部队医院的专家,本事大些。”送别的时候,莲子的眼泪快要下来了,“只是……夜里,别忘了,托个梦回家。”
四
陈德宝答应了。
睡在红房子里,有时真的有了梦,除了父母亲,剩下的让莲子占满了。仿佛莲子说的每句话都有了灵验,让他没想到的是,正准备忙过这几天去一趟驻军医院,好好的却邪了门:头不晕了,身上也不痒了;更奇怪的是,前一阵子后背前胸上的那些“红点豆豆”不声不响地逃逸了,像是缩进了皮肉层里,挤都挤不出来;原先结痂的那一块块,好端端地成碎片片滑落,还长出了新新的皮肉,摸上去白滑滑的,绸缎一样。
一切都好了。那就听从组织的,复员回家吧。
只是没承想,刚回来时好好的一个人,脚落地没多少天,原先的那两种病根,似乎又扎入了土层吸上了肥料,说发就发了。
还是那种困,还是那种痒。特别是那种痒,莲子寻遍了方圆百里的名医郎中,自己也动上手了,又是熏又是洗,还有热敷加冷冰的。到后来,有家郎中多了句嘴:是不是……干过防化兵,落下的病根?
陈德宝一怔,似乎远处,像是阿汪递了一句话。他们这个营,也有过几名战士得过白血病,还有的是生女孩的确居多,但这么些年那么多退伍兵和转业军官,也没听说有什么事;更何况全营官兵的后代,不也有一部分生的是男娃?虽说他生的是女儿,自己回家后身体有些不适,总不能有了些不顺心的事就缠上部队,那成啥了?那么多战友,也没听连长说起过,有哪个返回部队找麻烦什么的。
但是,自己身上的这个,说病还找不出病因的怪样子,又做何解释?退伍有些年头了,那么多春风沉醉的夜晚,他这么一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不敢与自己的女人搂在一起,大热天的,乡邻面前都不敢光一次臂膀。有几个晚上,莲子柔柔的眼神里,渐生一种油油的坚决,有点像是荧屏上的革命党人。只是到了这个关键时刻,陈德宝还是软了。
尽管,他的身子骨硬邦邦的,内心的炽热特别想拱出一个喷涌的出口,可……他真的怕啊。有时孩子扑了过来,他都有了躲闪,抱的时候想着拉大一些隔空,一度让莲子好生担心,怕男人手臂不稳,这要是一抖散了,孩子坠落下来,那就不敢想象了。
实在是没招了。陈德宝对女人说了句,还是去部队,也别写信打电话了,直接找连长,怎么摊上了这个事,这到底啥个情况呢。
五
记忆里的那道营门,一如当年亲切。只是那些新面孔的卫兵,威严得没法靠近。几乎解释了一箩筐,人家就是不认脸,报上的连长姓名也不管用。原来,这批卫兵是留守值勤的。陈德宝哪里知道,盘踞在九里山下的这支部队划入了军改行列,他的连长眼下成了新近合并的某集团军防化营营长,而且新营区远离了这片红房子,搬到了山那边。
连长,你恐怕没有想到,你的一班长病成了这个样子?进不了那一排排红房子,陈德宝只得在营区外面转了半天,时不时地往里眺望一眼,让他没想到的是,有位卫兵心软了,一个电话,连长赶了过来。
老营房,那一排排红房子,现在空着,不住人了?陈德宝敬礼的右手,好半天也放不下来,到底叫您什么呢?连长,还是营长?
那就,喊一声老连长?咱还是一家人嘛。
连长你哪里老?你真的不老啊。说是这样说,陈德宝有了哽咽:老连长,当年最听您指挥的那个一班长,实在没办法,给你丢人了。
哪里的话,这不到家了吗?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营长这么一说,陈德宝心里软活了。那一排排红房子又一次罩住了他,原先一班住的那间屋子,空空的没了人影,还好,床板啥的没有挪位。这阵子,部队刚刚搬迁,新营区万事俱备,这边的营具倒是省下了。那晚是个夏夜,营长请了假,陪着他住进了红房子。一宿的漫长时光,陈德宝没了睡意,班里八张空空的床铺,他每张床上挨了过去,每次睡了一个钟头就挪一下身子,以前在家动辄的犯困居然又没有了,身上也没见一处痒着。
奇了怪了,第二天一大早,营长把他留给了营区卫兵,还交待说:陈班长从老家过来一趟,几千里的不容易;他要是想进红房子回连队看看,尽量行个方便,那是我们永远的家。
营长的意思是,部队刚搬进新营区,等忙过这几天,再陪陈德宝去治病。陈德宝应了,虽说与卫兵班一起搭伙,晚上也有了自己的床铺,特别是一放眼就能看到老连队那一排排红房子,要是实在想得急了,还可以走几步过去看看。这些天,他就随着卫兵班重温军营生活,不仅叠被子,开党小组会,还记了许多笔记;就是每天早上戴防毒面具的五公里越野,因为训练装备缺乏而无法进行,其他的倒是回炉了当初的兵营时光。
几天过后,营长转了过来,说是带他去看病。陈德宝居然一惊,这才想起,差点把治病这一茬忘了。这几天,他一点也没犯过困,身上哪里也没痒过。刚来时满身直淌黄水的那些地方,全都结了痂;以前结痂的那些,如同刀刮鱼鳞似的一片片落了。等陈德宝脱下内衣,营长这才发现,他的背上黑黑白白的,像是套了一身无形的迷彩服。
日怪了。见到营长的陈德宝,像是一条上岸时张着嘴的鱼儿,倏忽一下跳进了河里,说不定这么一眨眼,激流都追不上他。
六
现实摆在眼前,那就是不能离开红房子。陈德宝回家之后,没多少日子,那些原来的病根,在他身上复活了。
从这年开始,一连几年,他每年都要回一趟九里山,只要进入了红房子,或者说哪怕就是转几转,整个人啥事没有,就像高原海拔上吸了氧似的。可这样下去,怎么办呢?有次,营长沿途找了过来。那是个早晨,陈德宝一人在那条小路上折返跑,像是计算着五公里越野的路程。营长赶到时,正听着他扯着嗓子,面对群山呼点全班战士的姓名。
总不能带一身防毒衣回家?营长像是想起了什么,咕噜了一句。
哪能啊?脸红红的,尽往下低:防毒衣,防毒面具,那是部队装备,战士的第二条命啊。
那怎么办?营长真的没招了。
连续多年的治疗,陈德宝一时成了贫困对象,等到精准扶贫全面铺开,刚一见到自己的包保干部,还没等开口介绍,对方冲过来,一声大喊,两人抱住了。
新来的扶贫书记,正是阿汪。阿汪转业了,这次主动包保的村子,正是自己的老家。
这下好了,有了主心骨,一旦痒得受不了或是困得不行的时候,阿汪就陪着他,有时看鸟也能看上半个钟头。那一只鸟,又一只鸟,齐齐地往西北那边一头插了过去。
也只有莲子知道,那是九里山营盘的大致方位。
撑了这么些年,莲子耗不住了,她敢打赌,说陈德宝摊了鬼神,一度她还想着找巫师作法,陈德宝恼了:乱扯什么,扶贫先扶志,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你知道么?红房子里,我与汪书记,那可是宣过誓的!
可是,这一大堆,有哪本管用?那次,莲子有些失态,她一扬手,白花花鸽子似地飞落一地。阿汪看清楚了,那不是鸽子,是这些年陈德宝积累下来的多家医院的病历。
阿汪说了个点子,还是要向老部队再次电话求助,得到的反馈是:九里山下的那片营区,那一排排红房子立正的地方,被南京一家开发商相中,准备建造住宅小区;考虑到创建双拥城,开发商顺带建几幢经济适用房,只要九里山下当过兵的,都可优惠购买……而且,已经丈量过地皮了。
“那楼,盖那么高?”陈德宝急了,听阿汪说起的楼层,快耸到云层里去了,兵们要是望一眼楼顶,大檐帽的护带要是不拉下,一阵风过,军帽要是滚下山坡,那真是恼人的事。
“也不知,副团长有没有提醒兵们?”陈德宝嘀咕了一声。这么些年下来,连长成了营长,又成了副团长,小林老师早就随军,成了驻地一所名校骨干老师。
再次见到陈德宝的时候,副团长犯难了。他倒是有了个想法,要是能让陈德宝第二次当兵,这个病会不会断根呢?可是,这样的念头对于一个副团长来说,落实起来,有点不大现实了。
现实的想法,还是阿汪提出来的,老营院不是搞房地产开发么?可否请部队出面,让陈德宝找份活干,只要能看到红房子就行。说不定在那一排排红房子旁边待一阵子,这病就断根了呢。
莲子认为,阿汪书记说得有理。这趟九里山之旅正好暑假,莲子有些不放心,带着孩子跟了过来。现在的村子,青壮年男子齐齐进城打工,自家田地租给种田大户,有个零碎的农事,阿汪书记也能组织党员骨干照应。
“治病么,客气个啥?咱是老乡,战友呢。”阿汪又补了一句,“退伍老兵的困难,就是我们支部的事。”
这次,看看能不能多待些日子?“顺其自然,也不要成天想着。有枣没枣打一竿,权当回趟娘家。”送别陈德宝夫妇的时候,阿汪又剧透了一个事:他的一个哥哥是开发商,要是能在咱们村里也造几间九里山下的那种模样的红房子,这个病会不会渐渐好些?
只怕……再造的,那些复制品,没了那个味,心病还是要用心药治啊。阿汪又一次否定了自己:按理说,我也在防化洗消连当过几年兵,怎么啥病没有?唉,陈德宝当年要是生个男孩就好了,等以后到九里山附近的营盘当个兵,最好当个军官,这样他夫妻俩也能来个家属来队,有理由往九里山多跑几趟。
七
那一排排红房子,可能要拆了,要不要过来一趟?电话是小林老师打过来的,“要是过不来,我们多拍几张照片,再拍一段视频?”
那几天,看到陈德宝的病似乎又犯得厉害,莲子还是心软了,连忙替丈夫买了火车票。等到那一排排红房子再现眼前,天色有些黑了。好在卫兵们熟悉了,由着他进了门。红房子里的那些房间,哪间他不记得?特别是连史陈列室那间,也就是军人委员会开会的地方,还兼作俱乐部之用。好多年前的一天,时令上与现在差不多,那天的这间屋子里,他高高举起右拳,跟在入党介绍人后面,宣誓之声言犹在耳。
“防化营洗消连一排一班班长陈德宝,向您报到!”好久,他才下了狠心,坚决地走出了红房子。快要走出营区门口,眼帘里看到有人迎了过来,晃动在左右肩膀上的肩章,是耀眼的两杠两星。
副团长,哦,不,老连长,您怎么也来了?。
两人折了身子,回望着暮色里的那一排排红房子。许久,副团长说了一句:
答应我,以后,就……别再想红房子了,行不行?
陈德宝说:好。
又转了个身,敬礼,右手还没放下,一个拥抱,两人箍得紧紧的,陈德宝感到了,有几根肋骨,隐隐痛。
陈德宝又说,老连长,你答应我,往后……你也不想。
副团长点了点头,想了想,又摇了摇头。营盘铁打兵似流水,虽说军改之后,这里的营盘也成了流水,可是——这里曾经有过的,那可不是简单的几排红房子。那些如风的往事,早就深入骨髓里面,怎能说不想就真的不想啊?
好的,我答应你,我的一班长,以后,我们都不要想了。
是,老连长,我也不想了。
有风吹过,天色暗得厉害,视线有了些模糊。夜深了,浓浓的,让陈德宝望不见副团长的脸,副团长一时也看不清他的身子。只有夜风知晓,此时的他俩,眼角里都滋出了一种叫泪的液体,顺脸颊往下蠕动,久久地没有坠落……
渐渐地,陈德宝有了呜咽。没办法,实在是憋不住了。
副团长像是听到了,可是他不想说,就这么由着他。九里山的风,一到夜里,就特别尖,扯来扯去的时候,哪回不是粗粗的嗓子?哪张青春的脸也让这家伙刮得粗糙着,皱巴巴的。
陈德宝的呜咽,渐渐放荡。这次,身旁的副团长分明听清了,可又一度听不真切内容。他想扭过头去,看一眼当年的一班长。等副团长转过身来,却没想到九里山下这漫漫夜色,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合拢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