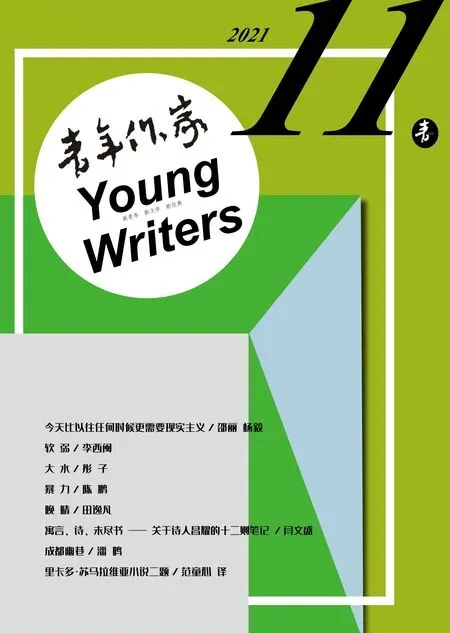晚 晴
田逸凡
半晌午的太阳正要滚烫起来。挂掉电话,我并不是太着急。看树冠的时候,树叶一直在摇摆,但人走起来却觉得空气安安静静。树叶有一面是油亮油亮的,一层灰毛的另一面总是被树顶的风翻出来,让疲倦的人看了感到更加疲倦。出门的时候抽了几张湿巾攥在手里,以备不时擦一下鼻沟什么的。偶尔刮一股热风,脸上的油珠儿唰的一下就冒出来了。
假设幼儿园小李老师的电话晚来两分钟,我可能就和双双一起来医院了,也不至于到现在还联系不上双双。我的确记得当时正纠结要不要去帮一下双双,就快要决定了,裤兜里一阵猛烈的振动打断了我。电话里传来一个女孩儿的哭声,但我是电话那头一言不发的男孩的父亲。
我儿子现在情况不太妙,颅内有瘀血。有两条路可走。直接开颅手术的话,医生说儿子这个年纪,大概率会影响智力发育。第二条路就是等到后天,北京的专家坐诊,有不开颅的技术,但是儿子在等待的这两天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这必须和双双共同决定。我无论如何联系不上双双。
双双创办的辅导班第一天开学。这段时间已经忙得她团团转。如果儿子没出事的话,我可能就去帮她了。本来也没以为儿子出事。小李老师电话里说的是我儿子在玩蹦床的时候,把一个女同学磕到了。我从电话里也听出事情应该不是很严重,只是需要我陪同去医院检查一下。小女孩的母亲态度不太好,一头大波浪跳来跳去。只是皮外伤,脸上蹭破一丁点儿小皮,抹几天芦荟胶之类的就会好的。医生给小女孩上了碘伏,其余连药也没开。我让儿子向同学和阿姨道歉,那位母亲只是礼貌地说好的,全程几乎没有看过我,一直抱着闺女问东问西。她走的时候高跟鞋要把地板敲碎似的。小李老师建议先把孩子带回家,下午再来学校。
回家的路上,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儿子在后座上抱着我的腰,头贴在我身上,手插在我的口袋里。我问儿子,玩蹦床怎么会磕到同学呢?以后小心点啊,磕得严重了就没今天这么简单了。儿子没说话,我感到他的脑袋暖暖的。我耳边的风呼呼的,看着电动车的电格,希望能撑到家。路两边的每一棵树都好像高温烤架,疏疏密密地穿着知了。接近正午,太阳的炙烤已经非常狂暴。它们疼啊,所以它们叫。我顶着一张油脸,难受得要命。
停下车子,我才发现儿子睡着了。平时这个时间也不会犯困的,他经常拒绝午睡。我抱着儿子进了家门,放到床上。想问问双双回不回来吃午饭,她没接电话。我先给儿子炒了一盘干豆皮,热了一下早上熬的粥。起来吃饭啦。我摇了摇儿子。儿子半睁开眼,几乎是眼白,迷迷瞪瞪的。太困了,爸爸,不……困……不吃。我这才发觉不对劲,抱起儿子冲下了楼,急忙打上车。
我在车上拍打他的脸蛋,捏脚底,掐腋窝。我努力不让儿子完全睡过去,虽然不知道这些方法有没有用。我不断问他,儿子你想想,当时你怎么磕到同学的?你有没有摔倒?儿子别睡,儿子别睡啊。司机看我这样,自然也在车流中见缝插针,油门踩得一惊一乍的。我感觉不是在坐车,而是自己跑着去的。急诊门口我差点绊倒。我太着急了。
真是祸不单行。我终于打通双双电话,她已经在来医院的路上了。她说,我今天一直尿血。她还不知道儿子在重症监护室。
大夫对我说,两条路都有一定风险,医院尽全力救孩子,但你要尽快决定。
双双来到医院,那神情就像是已经知道了似的,其实是尿急。她这段时间顾不得喝水,今天开班又格外忙,火气一下子上来了,尿路感染。尿路感染的人一直有排尿的感觉,压迫感很强,尿频尿急,而且带血。她去完一趟厕所,我看她那样子真不忍心现在和她商量儿子的事。但没办法,陪她挂完号,我就说了。双双吓得要哭了出来。
她久久凝视着我。那双眼我不敢看,只记得两条细长锋锐的眉毛。医院的大厅里相对嘈杂,但我还是听到双双微微颤抖的呼吸。我明显感到她几近崩溃的情绪。她除了做儿子治疗方案的抉择,大概还在心里咒骂我。你怎么看的孩子?是啊,虽说儿子应该是在幼儿园出的事,但在这个三口之家内部,相当于双双把儿子委托给了我,出了问题自然首先责怪我。她事业心太强,接送儿子基本都是我。我甚至觉得现在是在某种制度之下的协作,譬如婚姻制度,而不是我们作为一对夫妻、一个男孩的父母来共同面对生活。就像法律,只有权利和义务,没有冲动和感动。
相比之下,我缺乏上进心,看上去是个闲人。我在一所中学教物理,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工资,稳定的工作时间。双双和我在同一所学校教书,但她不是正式的,工资很低,也不能评职称。她筹办校外辅导机构,我从一开始是抵触的。本质上我不喜欢折腾,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其实夫妻各有各的事业,本不该相互干扰。但我们都在教育行业,怎能没有交集?而且对于大多数家庭,一个成员的工作似乎必然要取得其余成员的支持。也因为这事,我和双双已经很长时间不和谐,更别提做夫妻之间那种事儿了。
我一直认为房事是夫妻和睦的最根本来源,起码对于能行房事的人来说。那次她很晚才回卧室躺下,我翻身把她压住。刚进去,没几下,她一下推开我。我当时似乎瞬间失去了什么,摸了摸下面,像一根冻坏的茄子。那天晚上我左躺右躺睡不着,就下楼了。
我们住在中学校园里面,教师的周转房。下来就是大操场,其实环境很不错。一盏探照灯挂在教师居民楼上,操场上彻夜通明。至今我也不知道学校为何这样做。我沿着塑胶跑道走啊走。
这里的夜晚并不太黑,天空脏脏的。记得小时候,世上的什么就是什么。月亮就是月亮,星空就是星空。黑夜就是黑得那样纯粹,连明澈的月光也不会刺破那份厚重的黑。跑道中间的圆形草地像被打上聚光灯,万豸竞跃。有个搞前卫艺术的日本女艺术家,她的名字很符合这种意境,叫“草间弥生”。一只黑影在草地边缘窜动,那草高出它半头。我大略一看,是只刺猬。跑道对于刺猬大概是个封闭的圆环,它时而停下张望,寻找圆环的缺口。或许它根本不想加入进来。如果我们都是楚门,它找到了圆草地的边界,试图冲出来。我呢,我可能还没意识到自己是楚门。那晚回去之后我做梦,梦见刺猬在草地上唱歌,一首蒙古族民歌。
“那木汗,那木汗,你远在天边却近在我眼前……”
双双不必住院,每天来医院输液就行。但她身体很虚弱,辅导班那边只能我过去照看。我一下子忙碌起来,几边来回跑。儿子和双双的医院这边,我完全陌生的辅导班那边(而且我作为公职教师在那边还有一定风险)。还好,中学已经放暑假,省去了请假的麻烦。除此之外,还有小李老师和儿子同学家长——那个大波浪。陪你闺女去看那么点皮外伤,结果我儿子却是重度昏迷。儿子在幼儿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得去跑个明白。
我们的原则是保证儿子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尽量不开颅。脑出血已经停止,但还是有再次出血的可能性,而且瘀血在颅内压迫时间越长,危险越容易发生。所以我们决定,先密切观察等待,一旦有危险迹象立即开颅手术。我们当然希望儿子能撑到北京专家来坐诊,颅外抽出瘀血,不影响智力发育。
我必须,看到当时的视频。我见到小李老师和园长,这样说。
实在抱歉,我很理解您的心情,但我们学校不允许家长随便调取监控。园长十分冷静。
随便?什么叫随便?我儿子躺在ICU,你觉得是随便躺进去的吗?!
您先别激动,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发生了什么,即使您亲自看了,也不会使孩子的病情好转。所以,请您也理解我们,我们也是依法依规办事。
具体的原因我可以向您说明。小李老师接过园长的话。
走出园长办公室,小李老师一直跟在我后面,不敢轻易追上我。我质问她,到底有没有看见当时的情形。她还是摇头,说确实没有,发现时就看见女孩子在哭,其他小朋友向我指责你儿子。我请她联系女孩子家长。
还是那个大波浪。远看就像金色的厚厚麦浪,就是阳光也数不清有多少根头发,太阳公公也被晃吐了。她化的妆比上午在医院更浓艳了。上午作为赔礼道歉的一方,女孩子的检查费用是我出的,我还买了一支双双常用的一款芦荟胶送给她。但现在我们成了受害方,我自然也要她承担一定医疗费用。我说至少出我儿子一半的医疗费用。
这位父亲,我来学校见您也是出于礼貌,因为这本身就是讹诈。您怎么知道您儿子出事是因为我女儿呢?或许您儿子是在家或别的时间出事,您不知道,而正好赶在今天中午发作,您就认定是我女儿的事了呢?
我讨厌这个女人一贯的礼貌。但我不得不忍受。小李老师告诉我,要想查监控,只有教育局规定的两种情况。一是公安立案,一是两个以上孩子的家长联名提交申请。流程就这样,没办法。校方当然不建议报案,而我也并不想。报案是最坏的选择,我希望自己查清,和对方家长私了。毕竟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事情,起诉学校也不至于。看起来大波浪不会轻易和我联名“上书”。时间不早了,我得赶在放学之前出现在双双的辅导班。便留了她电话,匆匆离去。小李老师送我出校,我将上车时,她似乎要说什么,但又没说。
辅导班临时只开数英物理化几科。原来的宣传单上说明了开设有许多兴趣班,报名的有多有少。少的暂缓开班,一是租的场地腾不出太多教室,二是怕还不够开老师工资。多的也没开,主要因为很难找老师。比如报名最多的作文班,在外面请专业的太贵,许多人拿着省级国家级作协证,工资绝不松口。双双曾鼓励我去教作文,把我吓了一跳。公职在身倒是其次。我是喜欢写点东西,但我毕竟是物理老师。这要让家长们知道了,怎么交代?双双说,教得好了家长就认可,慢慢也就不在乎你是物理老师了。我坚决没答应。双双说,从提议办班你就反对我,请你代课不愿意,那你倒是帮我联系几个老师也行啊,你整天写写写,也没认识几个写作的朋友!
我有时看着双双特别累,也很可怜。她居然没遇上一个可以和自己共同奋斗的伴偶。我既这样想着,又不愿意受她感染、也充满激情起来。
房管局来的那天,我和双双在废旧的种子站等着他们。种子站搬走之前,听到消息的双双就想买下这栋楼和院子。我们没有那么多存款,而我轻易不敢贷款投资,很快种子站就落入了别人手中。双双只好向房东交年租。房管局的人在几处承重点和有楼板的地方,刮开灰白的墙皮,拿机器怼上去,挨个测验。最后的结果是C级楼房,不允许使用。
我本应该高兴,C楼不满足办学条件,正好可以由此打退堂鼓。可这时我也鬼迷心窍,觉得办班可能来钱快,竟一时脑热提起了双双的姐夫。他是大老板,人多路子广。双双为我突然的上进很是欣慰,也觉得找姐夫能办成,便催我赶紧给姐夫打电话。我遇到求人办事就犯怵。我说你姐夫你问。她急了,骂我一通。她的意思还是我不顶事,要老婆求人办事,还不让姐夫笑话了去?
我靠!我恨了自己一下,一脚跺向刮开的墙壁。墙皮哗啦啦掉下来一大堆,裸露的钢筋水泥和层叠的石灰像一张狰狞的脸,恶狠狠瞪着我。
姐夫在电话里问起我,双双说,他呀,现在办学太麻烦,正忙呢。我听见气不打一处来,把茶杯往茶几上重重一顿,还是没发泄出来,兀自坐下喘着粗气。后来忘记发生了什么口角,我差点动了手。当时双双呛得我不行,我噌地站了起来,同时右手停在半空。她倒退两下,用一种惊恐而陌生的眼神盯着我。我恨不得将那只停在半空的手扇到自己脸上。
我从没打过人,上学时连架都没打过,又怎么会打老婆?双双哪错了?她巴竭着办班,不是为了这个家吗?不是为了儿子吗?我怎么会举起巴掌呢?就因为她说我不顶用,不是个男人,有文凭没本事?可她是谁,她是双双,我的老婆。老婆骂你什么不行?老婆在家里怎么数落你,你能受不了,举起巴掌呢?我他妈是个什么东西?
姐夫把房管局某领导约到包间。领导朝姐夫笑,身上每个毛孔都咧开嘴笑。领导与姐夫握手,恨不得连双脚也抬起来表达敬意。他毕竟是个县局里的小领导,姐夫这样的大老板找他办事,似乎给了他很大自信。他可以安排施工队帮我们加固楼房,费用可以由房东承担。然后他说,检测数据上也可以活动一下的。双双忙说,没问题,该活动的您尽管去活动,放开了去活动!我陪着说是啊是啊,跟着双双举起酒杯。喝酒的时候我瞄了一眼姐夫,他好像一直在观察我。
有一晚在家,我看到我的脸映照在厨房洗池上方的玻璃窗中。洗池里,水花吹着泡沫。洗池快满了,我仍然让它继续流,害怕水龙头关上后恐怖的安静。我想起一部老电影的一段长镜头:循着嘈杂的流水,岸边出现了自杀者的尸体。从全景到中景,除了水声,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听不到脚步声、衣服摩擦的窸窣声、人们交头接耳的声音,只有流水在叙事——这样交代一具尸体,简直比任何台词、任何配乐都意味深长。玻璃窗中我的头发该理了,睡觉压得变了形。阴影之下我的腮头还是隐约有些坑洼,额头左上角新冒出来一颗红鼻子痘痘。
那些日子我书都看不下去。下了班只有儿子可供我忙活。我经常没话找话,双双并不搭理,有时还会过度解读,再呛上几句。去楼下操场上散步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常常是在深夜失眠的时候。我再没有找到刺猬。我在操场上吟唱起曾经梦见的蒙古族民歌,却只会那一句。“那木汗,那木汗……”慢慢地直到唱出泪来。
医院的凌晨,天亮得很晚。走廊一头的窗子正对西关村,整齐的红瓦浸泡在深蓝的空气中,显得露气凝重,一如深秋。这是夏日里唯一清爽的时辰。在下面绕着医院走了一圈,我的背上却沁出了汗珠。儿子住院的第二天,依然是焦灼的等待。我们已经拜托医生,请北京专家明天首先治疗我的儿子,算是医生帮我们插队了。双双七点半去辅导班,八点零几分就回来了。儿子在医院,她根本无心工作。我约了大波浪九点在一家离医院不远的咖啡馆。
大波浪这次的妆容比较淡。我甚至怀疑她是否习惯在上午化淡妆,下午化浓妆。她带来了一点礼品看望我儿子,也是她的礼貌使然吧。我说,这些奶、补品,你看我儿子这样怎么吃呢?我是想讥讽她,但她似乎比昨天多了几分歉意。她丈夫稍后也会到咖啡馆。她今天寡言少语,说等她丈夫来,让我们男人商量。
我让她想喝什么尽管点,但她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不要点甜品吗?我把菜单翻到有卡布奇诺和马卡龙之类的那一页。大波浪身材偏胖,而且女人基本都喜欢甜品吧。她如此矜持,已经超出了礼貌的界限。我也陪她喝白开水。
她丈夫坐到她身边的时候,我抬头,惊呼起来。是你?!这个男人叫李义山。我们曾是中学同学,初中还是高中,不记得了。我们多年没有联系,他现在穿着十分得体,寸头也很干净,我不知道他做什么。不过看见他,我没心思打听太多,认为老同学一定会同意联名写申请。
李义山替我点了杯黑咖啡。我说,干脆现在就起草,然后我们一起去幼儿园查监控。他从桌子对面伸出左手,按住我的手腕,示意我别着急。他并不像大波浪昨天那样冷漠和决绝,但不希望联名调取监控。
他说,你是老师,应该也懂,现在学校的监控和公安系统是联机的。
我立即明白他的忧虑。监控在各学校公共区域全覆盖之后,公安可以随时查看学校实时录像。录像管控变得十分复杂和严格,也就是说,家长申请查看学校监控,学校同意后,也要报备公安部门协同监督。一旦录像中有对李义山女儿不利的画面,考虑到我儿子的病情和高额费用,公安很有可能介入调查。所以,李义山表示,他不会拒绝支付医疗费用或者赔款,但尽量不要将公安牵扯进来。
李义山冷静地考虑我能理解,赔钱是小事,一旦公安进来,他的家庭以及幼儿园方面都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可是我又能怎么办?我把黑咖啡一口喝下去。不查监控,不报警,你让我上哪查去?李义山,要是现在躺在ICU里的是你女儿,你还这么冷静吗?我说就算真有什么,我作为受害方,可以要求公安不立案。李义山却说,你就没想想其他办法——咱孩子班主任老师,你真觉得她什么都没看到吗?
小李老师?她要是看到了怎么会骗我呢?
大波浪自始至终没说话。我怀疑大波浪知道什么,而且极有可能在昨天下午我走之后,通过小李老师知道的。今天是由李义山来提示我的。我很难相信小李老师会骗我。我又隐约看到过,昨天园长找机会和小李老师单独说话,也或许没看到,发生在我去之前。
我的脑子一片茫然。只要小李老师在我们面前证明我儿子出事和李义山女儿有关,李义山就会愿意答应赔款。李义山也表示,既是老同学,就算和他女儿无关,他们夫妻也会尽力支持我儿子治疗,而且借此再续同窗之谊。那我还有调查真相的必要吗?
咖啡杯中残余几道深棕色痕迹。咖啡馆里除了很小声的古典音乐,就是把我耳朵灌满的蝉鸣。这是夏季最有穿透力的声音,钻入层层墙壁,飞奔于条条街道,甚至将整个夏天都穿透了。
我是在一次家长会上和小李老师相识的。
开会时我全程走神,一散会就机械地走出教室。有个人叫我,我回头一看是儿子的班主任。我以为是要交流儿子的情况,对于这些我仍然提不起兴趣,那会儿我正构思着一篇写了一半的小说。这位老师却说,请问您是作家吗?我打了个激灵,什么?她说她从大学期间就常看一些文学杂志,到现在还在坚持阅读,看家长名册时看到我,感觉熟悉,在某些杂志上见过。我说我不是作家,我是物理老师,写小说是业余爱好,没发过几篇,还能被你看到,十分荣幸。
之后,我有了人生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文学迷妹,她让我叫她小李。我还是带上“老师”二字,表示尊重和距离。双双不懂文学,我又不善交际,从来也没遇到一个和我聊文学的人。她喜欢写作,从没得到指导,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发表,时不时从微信给我发来最近的习作,期待我的点评。
我在文学方面一直是自卑的。上学那会儿,我也是文学青年,有一个激情狂热的作家梦。我还曾拿着一摞诗去印刷厂印书,那人告诉我,自费一千块钱给你印上三本。我攒的零花钱不够,便对那人说,你们错失了一名杰出的诗人。后来我才知道,我找的那个印刷厂——我是按照中学作业簿上的地址找的——根本不会出版书,只是一个负责包揽教育局业务的私人作坊。上大学后,到处乱投,一个未中,后来渐渐失去信心。有个我当年颇不以为意地写网络同人小说的师姐,后来跟网文公司签约,现在发达了。
考上物理教师之后,我还没有完全死心,终于有一篇很短的散文发表在了县作协的内刊上。拿到样刊那天我战战兢兢,不知道怎样告诉双双和同事。后来放平了心态,三三两两的也在一些稍微大型的刊物上发表了文字。但又一直羞于自己的职业和作家差别有些大。谁知道我这个满口受力分析和电学公式的物理老师,也曾狂热地阅读萨特和加缪,崇拜略萨和加博,效仿塞林格和契诃夫?李义山按理说也会记得当年的我吧,见了面他会不会问我还在写作?
从小李老师这里,我慢慢找到自信,有时会飘飘然。每次接送儿子或幼儿园举办活动,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和小李老师聊几句。我比她年长不少,可能在一旬以上。我很庆幸,我讲的笑话总能让她开心。那笑声是发自肺腑的,来自一个真诚的姑娘。这种感觉就像你站在真正的草原中间,或站在一条恢宏的瀑布面前,那是真真切切的美,不带一点修饰。现在我和双双之间,甚至有时需要不那么情愿地互相附和一下,我真觉得可笑。和小李老师的结识,让我觉得年轻许多,好像回到了大学时代。
北京专家的团队没让我们失望。从脑外抽出积液,只用了半小时不到。儿子完全脱离生命危险,意识渐渐清醒,只是还需要住院观察、调养。
双双输液总是在傍晚六点左右,这是医生的要求。儿子住院第三天,手术成功,也是双双输液最后一天。我陪她坐在输液区的绿色躺椅上,背对着巨大的落地窗。我问双双还记不记得我们那个和一位古代大诗人重名的、共同的男同学?双双思量一会儿,说,小李杜!我们回忆起中学的事情。其实在那时,我和双双也不熟。李义山和我们都认识,却也不是很要好的朋友。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当年要好的同学,现在基本都失去了联系。能在这座城市遇到中学同学,甭管认不认识,也都是缘分。只是通过这种“事故”,平添几分恼人的滑稽。这几日十分闹心,此时倚着这傍晚的西关美景,和双双毫无顾虑地聊一下少年。这让我记起有一年,我们三口在江南度过暑假。
梅雨过后,天快要黑下来时,一个久违的晴天。原来夕阳一直在山的后面,溪的源头。我记得儿子曾在一次作文中写道,“江南小镇上的小朋友受够了没法晒衣服的日子,去教室里偷了老师的黑板擦来,一位电工爸爸扶着长长的铁梯,让孩子们爬上去把西天擦了个干净。夕阳一下子笑了。”他的语文老师用红色波浪线划出了这些句子,写上了大大的“Good”,还在最后一句批注“学习成语‘笑逐颜开’”。我当时骄傲极了,几乎要哭出来,不愧是我儿子!
不消说,西关村整齐的红瓦此刻一定佛光普度,善哉美哉。夜晚那只会唱歌的刺猬,循着一些奇妙的东西——你永远不知道刺猬会发现什么——来到西关村,歌起那首蒙古族民歌的另一个汉译版本。
“那么静,那么静,连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向双双吟诵起唐朝李义山的诗句: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
正说着,今朝的李义山携大波浪来到医院,找到我们,手里提着更多的礼品。大波浪不知何时与双双熟络起来,两人握着手说话。李义山把我叫到一旁,塞到我手里一张银行卡……
我终于还是没去质问小李老师。儿子住院后,小李老师代表幼儿园来看望了儿子。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在微信上给我发作品。后来我忽然看到一家市级刊物某期有了她的名字,立即向她发出祝贺,渐渐恢复了我们的文学交往。我儿子上小学之后,她告诉我,我儿子和李义山女儿是抱着从蹦床里“飞”了出来,摔在地上,我儿子在下面,应该磕到了脑袋,而李义山女儿的脸,其实是跌在我儿子身上,被纽扣蹭破的。儿子还大致记得当时的情景:李义山女儿越蹦越高,好像控制不住了,惊慌之下抱住我儿子,我儿子被带飞了。儿子写了一首关于那次飞行体验的诗,我为儿子浪漫的生命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