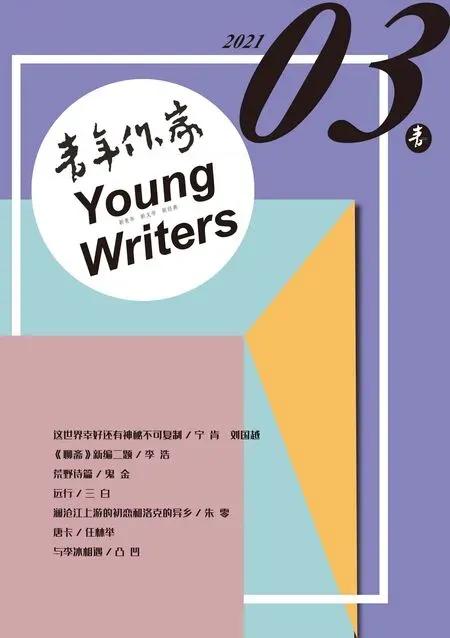橡皮擦
沙 爽
午夜失眠,随手翻翻微博,见《科技日报》登出了一则简短新闻,说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万有与伊鸣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可以精准“删除”动物的特定记忆:
该研究在两个不同的实验箱里诱发大鼠对箱子的恐惧记忆,进而将基因编辑技术与神经元功能标记技术结合,通过对特定印记细胞群的基因编辑精确删掉大鼠对其中一个箱子的记忆,而对另外一个箱子的记忆完好保留。
这一天是2020 年3 月24 日,日本正式宣布将东京奥运会推迟至一年后召开。意大利、美国和西班牙的新增病例持续攀升,中国大部分城市大中小学的开学日仍遥遥无期,整个世界沦陷于新冠病毒带来的恐慌之中。微信朋友圈里,有人开玩笑说,应该把这一年从历史纪元中删除,这样东京奥运会仍可以在2020 年如期召开,人们也不必为虚度的一岁而焦虑不安。短暂的莞尔之余,面前仍旧是阴沉凝滞的漫长时间。疫苗虽已进入实验阶段,但真正应用于临床,至少要等到一年以后。两三百年来,现代医学原本一路突飞猛进,不仅放言要攻克癌症和艾滋病,还要让纳米机器人深入人体,随时修补所有被衰老和疾病损害的器官……谁能想到呢,小小的一个病毒,便狠狠击中了现代医学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这样的日子里看到这样一则新闻,真是让人心头五味杂陈——如果删除记忆是获得重生的唯一方案,当瘟疫结束,曾经在悲伤、恐惧和绝望中苦苦挣扎的幸存者,会不会宁愿删除关于这场瘟疫的全部记忆?
如果我们的海马体能够自行辨识记忆的类别就好了——如果是愉快的记忆,就将它们输送往大脑皮层进行备份;反之,与痛苦有关的记忆将被永远封存在海马体内,等待另一个新生事件取而代之。事实是,人体确实拥有类似机能,一只隐形的橡皮擦,早已被造物植入我们的体内,用以擦除所有痛苦和不堪的往昔。肉体经受的剧烈疼痛,在经年之后将会变得隔世一般模糊。但是,此类记忆一旦被输送入大脑皮层,它就会变成一块巨大的、吸饱了雨水的海绵,阴郁、沉重,不堪触碰。当人们经历战争、恐怖袭击、强奸、重大交通事故等等事件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约七成的人会通过自身调节逐步恢复正常心理状态;而余下的两到三成人群,则坠入与此相关的漫长噩梦——医学上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因之而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病例,至少有万人之巨。曾经遭遇过的灾难画面一遍遍在脑海中重演,使他们夜夜难以入睡,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一点点稍大的声响,就足以让他们受到惊吓,甚至看到摩天大厦也会惊惧不已……记忆造就了一座人生炼狱,将许多人囚禁其间,而刑释日遥遥无期。
怎样才能让大脑删除苦痛,以补救被无形鬼魅所损毁的人生?
最早剪辑人脑的尝试,大约发生在古埃及。在一小部分埃及木乃伊中,尸体头盖骨上钻有奇怪的小洞。这种治疗癫痫病的古老手术早已失传,以致后来者不得不查阅大量资料,以了解这些小洞到底所为何来。
到了19 世纪末期,为了治疗精神类疾病,医生们开始尝试对大脑进行手术。施术对象除了人类,还包括家犬和灵长类动物。1935 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神经精神学会上,约翰·富尔顿和卡罗尔·雅克布森发表报告,提到他们对黑猩猩实行两侧前连合切断术后,黑猩猩的攻击性行为减少了。在此基础上,葡萄牙医生安东尼奥·莫尼兹发明了脑叶白质切除术,用以治疗包括精神分裂症、抑郁症、严重强迫症以及一些被人们认为有精神疾病征象(如喜怒无常、具有暴力倾向)的人。经过手术,这些患者确实大都变得温顺驯良。莫尼兹因此获得了1949 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脑叶白质切除术曾经风靡一时,从20 世纪30 年代到50 年代,短短二十年间,仅在美国,就实施了四万到五万例。但因之而起的质疑也从未止息。50 年代前后的一项调查表明,大约有三分之一做过脑叶白质切除术的病人,术后病情并没有多少变化;另外的三分之一则比术前有所恶化,变得更为冲动,甚至丧失了部分人性和社会性。也有的病人在经过手术后失去了精神冲动,表现出类似弱智和痴呆的迹象。一些文艺作品也以此为题材,比如电影《飞越疯人院》,影片的主角、热爱自由且充满反叛精神的迈克·墨菲,被强行施行了脑叶白质切除术,就此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在迈克·墨菲的感召下重新唤醒了生之希望的“酋长”,忍痛杀死迈克,逃出疯人院。
在日本,曾经发生过一桩轰动一时的“脑白质切除术谋杀事件”。
该事件的主角名叫樱庭章司,出生于昭和四年(公元1929 年),是一位成绩斐然的业余拳手,为人富有正义感。除了擅长运动,樱庭章司还勤于学业,自学英语并考取了正式的翻译资格,并立志要当一名作家。
年轻的时候,樱庭章司曾经做过土木施工员,为了保护被欺辱的同伴,他痛打过小混混,也曾涉嫌以暴力手段抗议老板的不当行为。以上这些都构成了他的“前科”。后来他开始写作,成了当红的体育作家。有一次,在赡养母亲的问题上,他与妹夫发生争执,盛怒之下,他捣毁了妹夫用来展示玩具的玻璃橱柜,因此再次被捕。医院对他的易怒型性格进行了精神鉴定,随后以检查肝脏为名,对他实施了脑白质切除手术。作为出院的条件之一,他被迫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
(4)热量分配:三餐热量分配一般为1/5,2/5,2/5或1/3,1/3,1/3或四餐1/7,2/7,2/7,2/7。三餐饮食内容要搭配均用,每餐均有糖类、脂肪和蛋白质,且要定时。可按病人生活习惯、病情及配合治疗的需要来调整[3]。
术后的樱庭章司,无缘无故出现了癫痫症状。而意欲的减退,使他的书写能力陡降到了从前的五分之一。有一天,他在窗前眺望落日美景,却发现自己的内心竟已不再为这世间的美好动情。自此他决意要杀死那位为他手术的医生,再自杀谢世。某日他服下巴比妥,来到医生家中,但碰巧医生外出,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杀死了医生的妻子和岳母。
樱庭章司被捕之后,法庭对他进行了医学鉴定,确认他患有脑萎缩和髓液循环障碍,同时还发现了当年手术时遗留在他脑子里的止血夹。
受到此案启发,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岛田庄司创作了《溺水的人鱼》,讲述了天才的游泳选手阿蒂娜在胁迫和欺骗之下,被切除了脑叶白质,由此失去了运动能力,不得不在轮椅上度过了痛苦的后半生。促使樱庭章司下定复仇决心的那个黄昏,也被岛田庄司移植到了小说之中:
这是在欧洲大陆可以看到的最后夕阳,眼前是一片金光灿烂的大海,间或也能望见星星点点的渔火……可是,望着这一切,阿蒂娜全无赏景之心,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以前,每当她看到这种夕阳西下的美好光景,总是惊呼赞美,欢呼雀跃。眼前的阿蒂娜简直成了一个木偶。
以脑叶白质切除术来改变某些人类天性的尝试宣告失败之后,医生们转而求助于药物治疗和其他更精确的脑外科手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对自我肉身的探究可谓巨细靡遗。科技的飞速进展也鼓励了科学家的野心,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也更为精细,对“记忆操纵”的研究,便是其中之一。
2014 年,荷兰科学家宣布,他们成功采用电击疗法删除了人类大脑里的指定记忆。医生借助电休克机等特殊仪器和设施,在短时间内,以适量的弱电流刺激患者脑部,从而引起脑神经内部发生综合作用,达到局部治疗的目的。
从2016 年开始,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阿兰·布鲁奈特博士和他的搭档们,则尝试使用降压药普萘洛尔,为六十名受试者进行每周一次的治疗,每次治疗时间为十分钟。在六次治疗结束后,有三分之二的患者病情有所改善,虽然不能称之为完全清除痛苦记忆,但病人此前的睡眠不良、过度警觉、记忆闪回等PTSD典型症状,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
在此之前,美国佐治亚医学院研究小组曾经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的科学家共同合作,从小白鼠大脑中成功分离出记忆分子。他们在试验中将小白鼠放到一个房间里,播放一段录音,然后反复对小白鼠进行电击,使之对这个房间和声音产生痛苦的记忆。然后,他们将小白鼠再一次放到这个房间,并播放让它感到恐惧的录音,同时给它注射被称为CamKII 的蛋白质。此后,当小白鼠被重新放回到同样的环境中并播放同样的录音时,则不再因恐惧而颤抖。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如果我们试图删除一段不愉快的记忆,需要在同时回放痛苦的记忆或恐惧的情况下,注射这种CamKII 蛋白质。
当时出于好奇,我查阅了资料,了解到基因编辑的一些皮毛知识。当HIV 病毒攻击人体时,它主要以CD4+T 细胞为目标,必须在细胞表面找到一个叫作CCR5 或CXCR4 的受体,这个受体相当于HIV 病毒进入人体的“入口”。但是对CXCR4 进行编辑可能影响到胚胎的发育,而且多数HIV 都是通过CCR5 受体进行入侵的,所以CCR5 受体就成为基因编辑的最佳选择。贺建奎团队正是敲掉了CCR5 基因的32个碱基,使其蛋白无法正常穿膜表达于细胞膜上,病毒也就无法找到这一“入口”进行入侵。不过,基因编辑存在出错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基因突变,对新生婴儿产生无法估量的伤害,也有可能产生新的疾病隐患。而且基因一旦被修改就无法恢复,这种隐患会伴随人的一生,并被遗传给子孙后代。
后来,坊间传出贺建奎被捕的消息。南方科技大学也发表公告,解除了与贺建奎的劳动关系,并终止其在校内的一切教学和科研活动。一桩疯狂的科学事件似乎就此画上了句号。然而,作为一个懵懂的凡人,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应用于人体的基因编辑究竟在多大尺度上为法律所允许——如果将基因编辑作用于胎儿属于非法行为,那么,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删除特定记忆,其应用对象到底仅限于实验室动物,还是终将在人类中推广实施?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出于对个人隐私的维护,我们不可能追踪这对婴儿的未来。基因编辑究竟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如何确认其对艾滋病终身免疫,这一切都将成为悬念。半世纪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留下的阴影并未散尽,考虑到人类记忆的复杂性质,实在远非小白鼠可以比拟——以基因编辑技术操控记忆,将为人类带来福祉还是灾难,我们完全无从预知。
有几次,朋友在网上向我借钱应急。第一个反应当然是担心遇到了网络骗子,于是请对方拨打我的电话,然后随口问了两个问题。这些问题不会见诸于任何正史和野史,也无法凭借搜索引擎找到答案。它们是在多年的交往中,我与友人共同经历的细枝末节。如同在忘记某个密码的时候,系统据以确认操作者系你本人的提示问题:“你最喜欢的老师的名字?”或者,“你小学同桌的名字?”它们是游离于公共记忆之外的私人印记,而只有这样的印记,才可以证明你是你。这人世的深情,恰是建筑于我们彼此间共同拥有的点滴回忆。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人生之所以让人哀怜,是因为先于肉体,他们与亲人内心的环扣已经提前脱离。我们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个全然空白的世界,仿佛一切被强光飘过,回首时空茫一片,连脚下的路也接近虚无。
在韩国电影《我脑中的橡皮擦》里,当秀真的记忆力日渐衰退,那个隐形的橡皮擦不断擦拭掉她脑中的一切印记,深爱着她的哲洙说:如果记忆离开了,还会剩下灵魂。秀真说:不,如果没有了记忆,那么灵魂也就不存在了。
果真如此,当未来医学真的可以删去那部分痛苦的记忆,此后的人类,是否仍可以拥有属于个人的完整灵魂?或者是,在完整与欢愉之间,我们将如何决定舍此取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