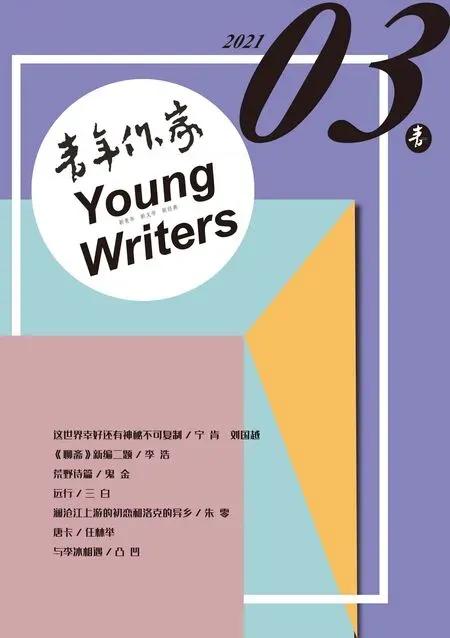鬼
三 白
Paula 要求和我上厕所时,我才认识她没多久。那天她穿了件白色吊带裙,边缘脏得泛了黄,胸口点缀着番茄汁和芥末酱,她拉着我的手,讲她那重复第十一遍的鬼故事:有个叫玛丽亚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去不返,她为了报复他,就把自己的孩子吊死在厕所中。可她后悔了,哭哭啼啼,从此以后,她就到处寻找和她死去的小孩长相相似的,把他们也吊死在厕所中。
哦不,这是最新版本,我第一次听到的故事不是这样的。女人是叫玛丽亚,丈夫也确实离家出走了,但孩子不是死在厕所,而是死在河里,女人也跳进了同一条河。Paula每讲一遍,背景都要适应环境做些改编,如果我们在操场,孩子就是从滑梯上摔死的,如果在饭厅,那就是被人用土豆泥噎死的,每一遍她都从“这是一件真事,是小时候妈妈告诉我的”讲起。
Paula 是墨西哥人,和我们学校三分之一的小孩一样。后来她告诉我,她爸妈离了婚,爸爸搬出了房子,她和兄弟姐妹都跟着妈妈住,也和三分之一的小孩一样。我其实是个转校生。二年级的时候,妈妈说要带我去个很远的地方,那里有个自由女神,有条名叫“华尔”的街。来了以后,我很快又上学了,学校建在马厩旁,人们每天早上要从马厩里拉出一辆观光车,把黄色的粪便运到城市各个角落。
起初我连拟声词都听不懂,唯一听得懂的就是笑。这些小孩格外能笑,教室里,饭堂里,操场上,到处都散落着他们的笑声。但Paula就不爱笑,也不怎么说话。我认识她是半年以后了。这半年里我的英语突飞猛进,已经到了能独立完成作业的程度,就只剩一个毛病:不怎么开口说话。妈妈听了班主任的反馈,回来很着急,她说这孩子没什么毛病,就是有点木。
半年后的一节数学课上,老师把四加五用阿拉伯数字写在黑板上,我想都没想,脱口就是”nine”,被旁边的女孩听见了,她意外地兴奋,使劲对我说say it,say it!又看我没动静,她就直接指着我大声对老师说,she knows it!所有的目光于是转向我,老师善意的,同学好奇的,还有女孩炙热的,都像烟头轮流烫在我身上。尤其是那个女孩,她的目光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我当时想不出来,只觉得脸红羞愤悔恨,斗争许久才终于说出个响亮的“nine”。说完以后,教室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那节课后,女孩告诉我,她叫Paula。Kay—la,她再次说道,好像生怕我听不清似的。
从此我不得不感谢她,那次尝试彻底敞开了我的交流之门。Paula 和我越来越熟。她长了一头马鬃的头发,皮肤眼睛头发都是棕色的,鼻子上架着一副厚重的紫框眼镜。我终于弄清了,原来她奇特的目光跟这副眼镜有关,别的眼镜把眼睛缩小了,她的却放大了好几倍。从外面看,她整张脸的比例就像只苍蝇,而且和苍蝇一样,她四肢纤细,和体形极不相称。
我很快发现,她在班里除了我就没别的朋友了。她从不听讲,手下压着伪装成笔记本的速写本,一到上课就在上面涂涂画画。一旦被老师叫起,她就支吾着乱说一气,等同学笑完又接着画,这次用手臂遮挡着,像怀里藏了个小孩,这下所有人都看清楚了她私底下搞着什么名堂,几节课下来,她去了老师办公室。其实老师拿她也没办法,这里的老师拿谁都没办法。
有一次,Paula 被叫走时,本子落在了课桌上。那是长方形的木桌,所有人围成一圈坐,坐在Paula 旁边的同学碰巧翻看了速写本,这就免不了让它绕桌子一周兜个圈,等Paula 回来时,笔记本已经落到Eddie 的手里,他是个红发男孩,脸色粉红,布满雀斑,他一脚踩在椅子上,对面的Stasia 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扎成马尾的金色洋葱圈在她身后玲珑地晃着。
“看她画的,馊得像她裙子上面的芥末酱!”
Eddie 说完,深深地为自己的睿智感动,趁Paula 走来之前,他赶紧把本子传给了“老大”John。John 佯作还给她,等她一出手他就抽回去,然后再伸,再抽,这么来回逗了两下,他直接冲出教室,跑进走廊,Paula 在一片喝彩中追了出去。我出于好奇,也跟了出去。他们绕着走廊周旋了两圈,John 故意跑慢,让Paula 追上,然后他闪身向旁边一跨,躲进了男厕所。Paula 立在外面,看John 把速写本悬在垃圾桶上,眼看着要松手,上课铃敲响,他遗憾地把本子甩在垃圾桶旁边,自己回去上课了。
她就那么呆呆地站了一分钟,腿太细了,两根火柴棍直戳戳地杵在地上,有两滴水珠“啪嗒,啪嗒”地落在旁边。后来她自己捡出了本子,我陪她回了教室。
我也看过她的画,都是些骷髅、木偶,还有披头散发的女鬼。它们太逼真了,甚至连阴影都画到了位,每一页翻过去都让我毛骨悚然。我印象非常深的有一位老人,他的一只眼没有上下眼睑,惊恐地张成圆形,后来我在学校阅览室里的一本简版《泄密的心》里看到了一模一样的插图,画的是故事里那位暴毙的、长着秃鹫眼的房东老头。
那天中午,我第一次和她一起吃饭。她说她给我讲个鬼故事,是真事,就发生在她的家乡,是小时候她妈妈给她讲的。我问,真是真事?她说,真的,千真万确。我非常激动,倒不是当了真,而是加深了VR 体验。Paula 说,从前有一个女人叫玛丽亚,我打断她,从前是什么时候?很久以前吗?她非常意外,好像从来没被打断过,仔细想了想说,大概十年前吧。我说好,继续。她又说,她很漂亮,我又问,有多漂亮?她说,她有贝儿公主的头发,哈利·波特的绿眼睛,安吉丽娜朱莉的身材和灰姑娘的水晶鞋。她看上去一点不讨厌被打断,还大受鼓励,自觉地挑染起故事里的所有细节。我发现这样下去她永远也讲不完了,就不再打断她,改用一种有限的专注来倾听。
她整整讲了两天,眼睛里前所未有的狂热实在有点过头了。你知道吗?她说,玛丽亚的指甲有这——么(她比画着)长,上面滴的全是小孩子的血。你知道吗?被捉的孩子要被吊在一根红绳上。她什么时候都在说,课间,午休,体育课,不光是我,其他人也惊奇,班里学习最好的Caron 几次停下手里的剪纸作业来听,我看着Paula 饱含感情几乎热泪盈眶,只想和她永远分开,我还亲眼看见Stasia 冲我们的方向翻了个为时两秒的白眼。
吃饭的时候,Paula 要等所有小孩都去了操场,才肯把盘子里最后一丝土豆泥打扫干净。自从发掘了讲故事的乐趣,她对食物和画画再也没兴致了。放完盘子,她又要拉我一起上厕所,我没有立刻答应。我似乎本能地懂得女孩子一起上厕所包含着多么严峻的象征意义。才两三天,我和她的关系已经到了要做”闺蜜”的程度吗?可我那么无助!她是股神秘的大力,把我从漫无边际的孤独里拉出来,又把我投入另一口井里。
以后,她就是我的闺蜜Paula。班主任对我们的配对大为赞赏,一有小组活动就把我们分到一起。John 的党羽们看Paula 竟然有了伙伴,不再好当面拿她开涮,偶尔经过她的座位,只会从她背后吹上一句“玛丽亚今天又吃了谁啊?” Paula 根本不会理他们,她已经找到了真正的知音。你要是见过玛丽亚那双眼睛!她颤抖着说,仿佛经历着一场地震,你要是见过,你这辈子都不敢盯着别人眼睛看了。有天夜里,我梦见我在沼泽里下陷,四围的枯树上挂着我熟悉的脸,老师的、Stasia 的、John 的,还有Paula,她的眼睛比平时还要大上一倍,眼珠子上翻。我拼命往芦苇丛里游,刚碰上硬地,沼泽里突然伸出个什么东西,一把把我拖回了泥潭。
醒来时我还记得,抓住我的是玛丽亚那只白皙滴血的手。
我不是害怕,我真不害怕,对于这个,我起码能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那天我们照例吃完饭去上厕所,那是一楼没翻修的老厕所,设施陈旧,除非是真内急,没人会来。路上Paula还在说,从前有个女人——我马上打断她,她叫玛丽亚,她的丈夫抛弃了她,她一气之下在厕所里吊死了孩子,所以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就会被吊死,是的,我知道了。我一口气说完,Paula 先是沉默,又着急地说:“不是这样的。”可她半天说不出是什么样的,好像丢了剧本,直到撒尿的时候都没说一句话。我心里暗爽了一把,尿也撒得格外快,出来时她才刚蹲下没多久,我就守在外面,用脚踢厕所的门玩儿。
这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厕所的最里间,那个长期停用、被胶条封死的陈旧隔间的门开着,我一踢这边的门,那里也动一下,轻轻的,幅度很小,咿——呀——咿——呀——我怕听得不真切,想让Paula 快点尿完,可她今天就像喝干了一座水库,没完没了。我不再踢门,把它关好,那边的门竟还在动。紧挨着门边的墙上,在我们谁也够不到的高处有一扇狭长的窗户,像一道眯缝的眼睛,为这间阴湿的屋子增添着嘲讽的采光。
我没注意到Paula 出来。她拍了下我的肩膀问,你干什么呢?
我指给她看。你看,那个门是不是自己在动。
她像株濒死的植物尝到了新鲜的雨露,两眼发光,肌肉紧绷。是玛丽亚,玛丽亚找我们来了。
哦,是吗。我沮丧地说。
你听!呜——呜——就是她的声音。
你看见上面的窗户了吗?是那里的风把门给吹开了。
那也解释不了门为什么开着。这门以前是封死的。
这下我没得说了。我恼怒异常,非要证明给她看。我走到门前,故意不去看门上那几个歪歪扭扭的“抱歉,已停用”,一脚踹开了门,咿——呀——我几乎等着一个女鬼冲出来把我扑倒,可我还没来得及闭眼,门就已经大敞了,在门回落前的一瞬,整间屋子静得像间墓室。
Paula焦急地问:“怎么了?你看见什么了?”
我突然抱着肚子开始笑,什么也说不出。Paula 跑过来,我为她把门顶开。原来墙上挂着女鬼的地方,现在挂着一把灰蒙蒙、丑兮兮的墩布,上面一只巴掌大的蜘蛛网已经茁壮地成长起来。墩布旁挂了一把竹条扫帚,中间顶出一只圆头蘑菇,遗世独立。马桶被胶条封着,周围堆着其他清洁用具。
看见了?我说,看清楚了吗?
她还不罢休。厕所为什么会有两个工具间呢?那边不是有一个吗?
我耸了耸肩。谁知道,这是旧的,那是新的,有新的不用旧的,这有什么。
她又和自己斗争了一下,最后说,不,这是玛丽亚吊死孩子的那间屋子。
这种无端的日子只有向前看才显出一点起色。老师发布郊游通知的时候,关于郊游计划的讨论立刻充满了整间教室。在那些草地野餐的热烈争执中,John 是最冷静的,他翘着椅子,两手抱胸,超然世外,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渗着那句还没说出的“fucking idiots”。Stasia 在抱怨她买不到的新款机械狗。今年郊游也太早了,她说,我什么都没准备。
就连Paula 都忘了她的故事。她说她那天要带上妈妈做的玉米片配辣番茄,到时候和我一起吃。我很高兴,觉得和她亲近了些,中午上厕所都没那么不情愿。那里的工具间在我们“探险”的第二天就重新被胶带封上了。
到了郊游前一天,节日气氛已经白热化,教室一分钟都安静不下来。Paula 早上没来,到了第二节课也没来。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和其他人一起陷入无可救药的倦怠。中午,我一个人下楼吃饭,端着盘子在食堂那几张拉帮结派的长桌前犹豫了很久,最后坐到了Caron 对面。她高挑壮硕,面颊红润,像个姐姐,总爱一个人吃饭。
我坐下时,她抬头看我一眼,问,今天Paula 怎么没来?
我摇摇头。
她咽下肉丸子,又问,明天想带什么吃的?
我说,金枪鱼三明治。旁边的日本男孩听了使劲点头,我也是,他说,嘴边顺势还流下一股番茄油。
Caron 想了想说,我会带一小盒pizza,你们可以和我一起吃。
她吃饭很快,几下把盘子刮干净就走了,胳肢窝下夹着本厚厚的“大人书”。她走了后,日本男孩说,Caron每天中午都去阅览室。我问,真的吗?真的,他说,她挺厉害的,不是吗?
我看着他诚恳地抬头,一短根意面还友好地挂在他下巴上,突然觉得明天Paula要是不来,情况也不会那么糟了。
郊游当天,我一大早斜挎着午餐包来了学校。用上这个午餐包是这次出游的最大目的。我求妈妈照着Stasia 那个睡美人的包也给我买了一个。我在里面规规矩矩地装好一个金枪鱼三明治、一杯可乐、一小包薯片,装好背在身上,又老想把它取下来摸一摸,好像怎么放都不得劲。我是最早在操场上集合的几个小孩之一,我亲眼看着同学一个个到齐了,而Paula却不见踪影。当老师开始点名了,我已经站到Caron 身后,这时候却见Paula 急匆匆地从门里跑来,那一刻我的心情几乎是失望的。她跑到队伍前,到处张望,看见我冲她招手,老半天才挤过来。挨近了,我发现她脸上、胳膊上多了几道紫红印子,而且两手空空,连个塑料袋都没有。
我窘迫地问她,你昨天怎么不来?
因为磕了。
你怎么什么都没带?
出来的时候忘了。
我本来还想问问玉米片的事,可她的表情看起来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件事。
出发后,走过马厩,四月的河风渐渐吹来晴天的迹象,John 像只金丝雀那样把口哨吹到了后排。路上,Paula 和我说,她爸爸不见了,我问什么叫不见了,她说就是找不着了。我说,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事。她说真的,怎么没有。她又说,她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有个姐姐和毒贩私奔了,弟弟经常不回家。她说她妈妈的奶子有皮球那么大。我说我没见过毒贩,只见过她妈妈的奶子,只有水气球那么大。她说,嗨,那太小了,你是没见过大的,有人长得比田纳西的西瓜还大。我说怎么可能,没那样的人,她说是真的,千真万确。
我们逐渐看到了河流的影子。它像蓝天跌落地上的碎片,在城市的远角神秘地闪着。拐过一些弯,走过几条街,我们爬上一阶狭窄的石砖楼梯,那里的入口写着“欢迎来到布鲁克林桥”。
Paula 忽然捏住我的肩膀,你看这个牌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不等我反应她就说,我们进入了亡灵之国。
我不理她。沉默的策略似乎抓住了她的大软肋,从进入甬道以后,她就一直没说话。等我们从里面钻出来,再一次被阳光浇透了身子,她才又找回自我,慢腾腾地说,玛丽亚会把长得像自己的孩子推下水里。
前方耸立着一座巨型的桥塔,用古老石砖垒砌而成,从它身上延伸出的钢索交织成网状,把行人的通道完整地包裹起来。行道下方是车道,车道外,密林样的楼房渐渐稀疏,过渡成一片盈盈的晶蓝。
哇,海!我激动地说。
是河,Paula 说。
老师在桥塔的地方停下来,指着拱墙上的纪念牌,嘴巴飞舞,声音大半被河风卷走了。我们站在末尾听得异常枯燥,我手握栏杆,脚踩横梁,使劲一抬,上半身就能探出栏杆外了。我像个大人一样弯着腰,忧心忡忡地欣赏风景,让河间的清风舔过我的脸颊,感受发丝被掀起的优美动作,就好像自己是刚被王子吻醒的睡美人。
我看见远处的河上有座小岛,我想象着椰子树、金沙滩、白房子和马尔代夫。那些我没去过没经历过的迅速融在一起,从岛上飞来一束光,我第一次感到庞大的未来带着它的无限可能性在美好地向我招手。这感受那么浓烈、直接,不再是通过大人的媒介,而是赤裸地向我袭来——我突然涌出一股压抑不住的表达冲动,想把此刻的心情准确地描绘出来。
你知道那座岛上有什么吗?Paula 的声音突然从背后飘来,把我吓了一跳,我竟然忘了她的存在。那是被玛丽亚杀死的孩子们埋葬的地方。
你这人真恶心,我小声说。
你说什么?
我改了主意。我说,Paula,你相信你说的话吗?
当然!
但你说的话没一句是真的。那些故事不是真的,玛丽亚不是真的,鬼也不是。
是真的,我都说了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她听起来好像急了——因为本来就是啊!
我不急着理她,有意显得大度。我把肩上的背包取下来,拿在手上抚弄。我单手握着肩带,小心地让它垂到铁栏下,来回荡悠,在疾行的车辆上空昭示着我的优越。然后我说,怎么证明是真的?
Paula 很久都没吱声。我担心她生气了,跳下横梁,回头看看。
我一转过来,尖叫就卡在了我的喉咙深处。一双硕大的、超自然的眼睛,眼皮外翻,布满青紫的蜘蛛网状的血丝,填满了我的视野,还在缓慢向我逼近。
我的身体奋力后仰,耳边呼啸着风,这时我才意识到身后彻底的虚空,吓得掌心流汗,我觉得手上有什么东西滑落,却来不及看,头已经磕在钢缆上,痛得我睁不开眼。等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双手抱着钢缆,身体安全地倚在栏杆上——我太矮了,只有半个胸部露出栏杆,根本掉不下去。
Paula 笑得肩膀都在抽搐。你看,她说,你还说不是真的,你都害怕啦。
没有!我不顾一切地喊着,我没害怕!你无不无聊啊!
可我忽然想起了什么,赶紧又把胸部贴紧了栏杆。在我的视线下方,在车道的正中躺着我粉色的睡美人,粉色带子四仰八叉地散落在马路上,像散落的骨和肉。一辆汽车驶过,轮胎边缘撞飞了睡美人,它在空中滑出一道弧形,卡在右侧栏杆的缝隙间挣扎片刻,终于撒手滑向了水面。我以为自己听见了一声震耳的“噗通”,接着归于沉寂。
我回头看看Paula,看见我的仇恨映在她眼底,让那张太阳暴晒的无辜又抱歉的脸畏怯地变了形。
这是我倒数第二次跟她正面接触。以后无论她做什么——说对不起,在我面前哭,向老师告状——都没效果。老师在一趟数学课后把我拉到了一旁,因为那节课是小组活动,而Paula 整节课都泪流不止,我在她面前高效完成了两人份的课堂作业。老师私下问我,你为什么对她这样?我傲慢地咬紧嘴唇,一声不吭,可她又说,嗯?你说为什么呢?我只好说,她老编些无聊的鬼故事。老师说,那你可以请她别讲了,干嘛要冷落她?她眉头一皱,皱出两杠人道主义的责备,似乎等着我开口,又似乎在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她的胜利是无疑的,和蔼是铁腕的。她毫无悬念地听我答应好要向Paula 道歉。等她一转身,我昂首走过Paula 正在淌泪的地毯。
我不是稀罕这么个包。妈妈两天后就又给我买了一个,被我扔在一边,碰也不碰。我是觉得从前的什么柔软东西在那天被碾碎了。
我和日本男孩组了个小团队,每天中午跟Caron去阅览室读书。我在这里遇见了真正的“鬼故事”:《鸡皮疙瘩》的全套丛书和简版爱伦坡短篇故事集。Caron 说,有不懂的随时问她,她那广阔有力的低音就像个码头,让所有停靠的人都心安舒适。我的英语一下子飞越了几座山峰,老师看在眼里,说不出表扬,也说不出责备,从此她的眼睛从我身上掠过,像掠过空气。
John等人又重拾了旧业。他们说, “Paula,你的玛丽亚怎么不出来吃人了?” “今天的小Paula 又哭了几个池子呢?”自从我和Paula 断交以来,从没正眼看过我的Stasia,突然在体育课上邀我加入他们的抓人游戏。我欣然接受,故意要做给Paula 看,但即使这样,她在报复我的路上仍不动摇。没错,在我看来那是恶毒的报复,她公开展览她的眼泪,无处不在,在教室里哭,在饭堂里哭,在操场的滑梯上哭,就连厕所的隔板里也传来她的哭声。我走到哪里都能“不经意”地撞见她。
Paula 终于放弃是在一个炎热的五月星期一。从那天开始,我再也没见过她。一连两天,我身上清爽,心情放松,已经闻见绿宝石的夏天从五个街区外的游轮夹板上扇来香草冰激凌的味道。星期三中午我倒完饭,刚要返回,路却被人挡了下来。我先看到的是熟悉的开胶球鞋,接着那件终年不换的白色吊带裙绝望地映入眼帘。
我问她,你要干嘛?
Paula 一把攥紧了我的手腕。过来一下,我给你看个东西。
我想拔出来,但怎么也拔不动。
求求你,她说,就一下下,你会喜欢的,就一下嘛。
我还在犹豫。她又说,求你了,并直勾勾盯着我,晃眼。
周围已经有人在回头看了。我想马上离开,又拔不出手,被她硬生生拽着钻进人群。经过我吃饭的座位,我示意坐在凳子上等我的Caron 和日本男孩,让他们先去读书。
我们进去时厕所还是没人。Paula 松开我,跑到最里间,一把拉开门。
我走了,我说。
等一下!她像是用生命喊出了这个词。求求你,你闭眼,大声数到三十,然后把门打开,一定不要走哦!
这可真蠢!我开始数,一,二,三——咚、咚,有人踩在马桶盖上——十,十一——叮呤咣啷,剧烈响动——十六,十七,十八——她的呻吟——二十三,二十四——
Longyi!
我回头,Caron在门外,身后跟着日本男孩。Longyi,她说,你干嘛呢,我们走吗?
我红了脸。我不是说不用等我吗?
我们没懂你什么意思,看你往这边走了就……你尿完了?
我啊,我回头看看工具间。它静悄悄的,了无痕迹。尿完了,走吧,我说。
到了阅览室,我什么也看不下去,盯着《鄂榭府崩溃记》里的玛德琳插画,“玛德琳”有时候变成“玛丽亚”,那些复杂的线条开始自己游动、重组,纸面上浮出Paula 的脸,翻到下一页,还是她,再下一页——我疯了,把书合上。
下午进教室,我一眼就发现Paula 不在。我坐下来,觉得屋里比以前空旷。教室的门敞开着,穿堂风洪水般地灌进来,我抱紧胳膊,把头埋在桌上。上课铃敲了,老师还不进来,满屋子都是嗡嗡声,我时不时地要睃一眼走廊。
远远地,一个人影迅速扩大。我的身体反射性地弹起来,心好像跳在嘴里。有人说:“嘘!”班里当即安静了,下一秒,班主任出现在门框里,气喘吁吁,手里拿着一叠作业纸。我失望地趴回去,身上打了个寒战。
不好意思,她说,刚刚有点事耽误了。
她跳过点名环节,马上投入讲课,声音湍急,里面杂着些还没平复的喘息。整节课,我只听见她莫名其妙的声音在我上空盘旋,越来越快,越来越热,热得要沸腾。相反,室温却在下降,嗖嗖的空气袭进我的卫衣。我好像发烧了,脸上发烫。
咦?班主任的叫声好像从井底传来。怎么多出一份作业?咱班不是来齐了吗?谁不在?
静默似乎持续了有一个世纪。这时候John说,Paula,是Paula 不在。
班主任问,有人知道她在哪吗?
没人再发言。
她跑出去,丢下我们,没等她回来,班里已经起伏着剧烈的人语和笑声。外面下起雨了,雨点突然砸到窗户上,往下流的时候形成好几股。仿佛扒着玻璃窗的一根一根手指。
你怎么了?Caron 的声音吓了我一跳。她看上去很关切。
啊,没事。说完,我觉得不够诚恳,又添了一句,我肚子疼。
她教我撑不住了去跟老师说。一声迫近的闷雷缓慢裂开,激越的情绪触电般地传遍教室。话语声和笑声都不自觉地放大。这时候班主任出现在门口。她谁也没看,径直走向了我。
跟我来一下,她说。
我站起来,眼睛发黑,被她领去了办公室。其他老师见我们进来,齐刷刷地抬头,又把眼睛低下,只留耳朵。班主任绕到自己的桌位,站着问我:
你这两天见到Paula 了吗?没有。
今天你见过她吗?
没有。
她锐利地看了我一眼,我感觉自己的脸红了。她面无表情,但眼角嘴角的每根纹路都袒露着对我的厌恶。
她问,你知道她可能在哪吗?
不知道。
她看着我,沉默了。这不足半米的距离,她用权威把它浸透了,她拿捏它、拉伸它,把我的身体扯成橡皮筋,几乎接近极限。
好了,她忽然说。“啪”的一声,我的身体归了原位。你回去吧,她说。
回到班里,整间教室沦陷在暴雨的兴奋中,没人看我。哪里似乎不对劲。我坐下来,为我刚才冷静卓越的表现感到惊奇。
Caron 问,你跟老师说了吗?
我扭过头,发现她还是那么担忧地看着我。我说,没有,我好了。
她抬起一只眉毛,不大相信,我等着她审问我刚刚谈话的内容,可她马上低下头,缩进她的书里。为什么?为什么她不问?其他人也是,为什么他们绝口不提那个名字?他们兴致勃勃地说着雨,好像这辈子第一次见雷雨,除了雨什么都没意思。他们的笑声升高,变细,磨在我的神经上快要断了。班主任又进来,她连“安静”都没说,脸上弥漫着不安,似乎只有半截神志还在教室里。她说最后一节课不上了,让我们安静地等她带队下楼。
可铃声响了她也没回来。其他班的学生陆续撤了,走廊上出现两名警察,衣服里像藏着个人肉搏斗机。过了会儿,他们也走了。
忽然,Caron 扣上书,眼神变得奇怪,闪电照得她脸时明时暗。她的嘴唇动起来,默念着什么,我凑过去听,一,二,三……
我大吃一惊,水杯“啪”地倒了,水从里面涌出来,我感觉脸上的血被挤干了。
你在干嘛?
她非常迟缓地看过来,聪明的灰眼眸子落在我身上的一刹那,我知道她知道了,我发誓,她绝对知道,她当时什么都看见了,一清二楚。
她回过神来,对我说,我?没什么,我在数《格林童话》有多少故事死了人,却被篡改了。
一,二,三……我噌地从座位上跳起,她诧异地惊呼,你怎么了?
我去,我去上个厕所。
我摇晃着走出去,感觉被她那双好奇的大眼睛从后面盯着。没人拦我,我身后,笑声已经声嘶力竭。楼道黑得像地洞,没一个人,我扶着墙,漫无目的地下了楼梯,脑袋空了,但腿自动就知道该往哪里走。
我终于走到大厅。最后几个学生坐在板凳上等着被家长接走。大厅连着食堂,墙上的红漆反着阴雨的光。我腰一软,几乎要坐到地上,可腿还自己动着,寻着一个声音——不,我看故事看疯了!但我没疯,我知道那全是假的,我必须证明。她不在那里,她回家了,去游乐场滑滑梯了,或者磕了,明天就会来,身上多出几块疤。她以前不也消失过吗?没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走得快了,走快了就不怕。
我在门口停顿了一下。我知道厕所里没人。
深吸一口气,我走进去。本来采光就差的厕所,这时漆黑一片,但满屋的白墙、白门、白地砖却隐隐地反着光,像个得意的眼色。我的眼睛紧盯着最里的隔间,只能辨出个大概轮廓。
这时候,一道闪电照明了我的整个视野。我那双早有准备的眼睛在一秒钟断续的通明里确认了门上的那条缝!
我走过去,走到它跟前,门上那几个幼稚的字体依稀可见,每个词都像在嘲讽我,尤其是那个扭捏的“抱歉”,它是一声尖利的、放肆的、恶作剧式的嘲笑。抱歉,抱歉,Sorry,抱歉。那个词在放大、膨胀,要挤出门框把我吞掉了。我赶紧用一只脚踢开它,那一声咿——呀——,被一道劈在头顶上的巨雷淹没得无声了。我迅速地抽出脚,生怕被什么捉住。
我的眼睛落在了墙上。
我最先看到了墩布。它稳稳地倚在扫帚旁,坚硬的线条清晰可见。取代它,挂在墙上的是另一庞然大物,把隔间凌乱的空间填得满满当当。就在这时,又一道闪电劈来,一切都清清楚楚!她就在那里,她的头发、指甲、白裙子、光溜溜的两条腿,还有眼睛,苍蝇状上翻的眼睛大半已脱出眼眶,它们在那一瞬,绕着那根拴在墙上的红绳子转动,机械的,迟疑的,缓慢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