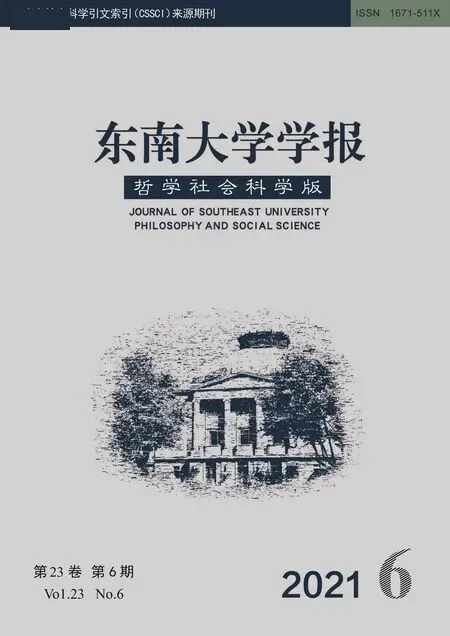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拓展与转型
王菡薇,杨 峰
(1.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2.南京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一、引言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对国际、国内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外文化交流、碰撞日渐深化,“留学潮”兴起,国人开始主动向外国学习,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自觉肩负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国文化的重任,以谋求民族复兴。在现代美术思想观念的冲击下,中国美术的范畴被重新定义、分类。中国美术史的发展不仅充分接纳西方的美术思想,亦逐步消化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美术史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更深刻地影响着当下中国美术的发展。
近代中国美术史学的兴起与西学东渐的大势及中国学术文化体系的转型密不可分。中国美术史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美术思想双重影响下,渐以自觉、自尊的态度基于开放性、多元化的视角或立场,用现代学术视野,重新审视和整理中国美术发展历史,开拓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路径。相关学者已经开展了诸多综合性的梳理和研究。薛永年的《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较为全面地检视、考察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历程,指出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历经了改步变古、推陈出新、交流开拓等阶段,形成了既不同于古代,也有别于外国的特点,左右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全局与大势。陈池瑜的《中国现代美术学史》从中国现代美术学的思想文化背景、现代美术思潮、美术理论、美术史研究等方面,系统梳理和考察20世纪中国美术史发展历程。陈振濂的《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运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日本模式”,以及近代中日绘画间交互性影响。曹贵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考察了日本模式、德国模式、苏联模式、传统模式影响下中国美术史学研究成果。乔志强的《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史研究》全面梳理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以及发展历程,认为中国美术史的发展伴随着西学的引进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出现,从微观上经历了初创期、风云突变期、一元发展期、多元开放期。
总体而言,目前学者们针对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拓展与转型问题的专题研究尚没有形成直接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以涉及的局部问题为对象开展的研究,呈现出成果虽较为丰富但相对分散的特点,对涉及其中的社会、文化层面的互动关系缺乏系统性的专门研究。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从艺术社会学的视角检视考察近代中国美术史学与社会发展、政治文化变革的互动关系,以及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发展、演进历程。
二、近代中国传统美术史研究发展路径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巨变期,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事业大兴,同时在近代留学潮流的促动下,新式知识分子不断涌现,促使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等逐步踏上近现代化的征程。中国传统史学深受西方现代科学、思想文化的影响,逐步摆脱封建史学观的束缚,掀起“史学革命”的潮流迈向近代化的“新史学”,促使中国传统史学学术发展体系进一步发展。
晚清时期,日本近代史学的先觉以及作为中国“西学东渐”的重要窗口,促使中国的文化形态、学术研究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深受日本学界的影响。其中运用现代美术史观、治史方法研究中国美术史,日本学者首开先河,“1901年,大村西崖《东洋美术史》第一次系统研究中国美术史内容;1909年,内藤湖南主持《中国绘画史》讲座,但当时不形成著作;1913年,中村不折、小鹿青云《中国绘画史》成书,开创了中国绘画史研究的新局面”(1)陈振濂:《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169页。,随着中日文化交流向中国输入以及中国近代美术史学研究的开启,这些著作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借鉴。
民国初期,浓厚的美术史学术研究氛围、众多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参与以及各类美育机构、美术社团、刊物之间的良性互动,促使中国美术史研究、撰述逐步脱离于传统史学研究体系,形成日渐独立化、科学化、体系化的知识系统。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晚起与滞后,使得众多中国新式知识分子自觉肩负重振中国美术的兴起重任,谋求中国美术史学研究的近现代化,基于近代美术史学科建制、近代美术考古学的建立、发展,通过融合中西美术史观逐步尝试整理、研究中国美术史。
1917年,姜丹书(1885—1962)所著《美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虽受到日本治史方法以及西方美术史的影响,但其所秉承的宗旨是振兴中国艺术文化以及培才育人之重任。此书填补了中国美术史编著的空缺。全书短短二万余言,是因教学急需而编撰的著作,尤为注重其综合性以及普及意义。其书编著受篇幅限制,重在广博且精核,虽存在部分史实撰述少有根据的缺憾,但是突破了中国传统美术史的史观,独具通史性、科学化、体系化的史学观念以及意识。
姜丹书早年长期接受传统教育以及新式学堂教育,深受日本、西方的学术文化影响,援引日本、西方美术史家的先例,将美术划分为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美术四大类,通过综合性的汇类,囊括诸种美术门类的起源与发展,重新审视美术史的性质、意义以及美术发展与社会政教、文化之间的关系,表露出一种求“全”的整合观念。“所谓全,一方面是指力求触及美术的各个品类,另一方面又要顾及美术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立体的关系。”(2)孔令伟:《近代历史科学对民国时期中国美术史写作的影响》,《新美术》,1999年第4期,第24页。
姜丹书所著《美术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美术观念、美术教育的影响。继之后的陈师曾(1876—1923)所著《中国绘画史》更是依据中村不折、小鹿青云《支那绘画史》增补而成,两书在分篇、用词、史观等方面基本一致,陈师曾章节中对中村不折著作内容略有调整,但反而在主次分明上不如原有著作。陈师曾此著为中国第一部绘画史,近代中国绘画史研究在起步即被笼罩在“日本模式”之下(3)陈振濂:《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176页。。与之同时的潘天授(1897—1971)的《中国绘画史》亦是仓促编译而成,而非创新性写作,余绍宋评其书乃是译述而成。“审其内容,实译自日本人中村不折、小鹿青云之《中国绘画史》,增补之处极少,其章节亦大体相同。题为编纂,不若题作译述之为愈也。”(4)余绍宋编撰:《书画书录解题》,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以陈师曾、潘天寿为代表的中国美术史家置身于近代中国美术史学的开创阶段,其著作深受日本学者的影响,虽然皆为沿袭、模仿之作,但对于促进中国美术史研究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作用。
1926年,滕固(1901—1941)所著《中国美术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书是较早通过吸收融合西方美术理论贯通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全书二万余言,运用进化论史观,“欲推论沿革,立为假说”(5)滕固:《中国美术小史⋅弁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页。。其书虽篇幅较短,将中国美术发展分为生长、混交、昌盛、沉滞等四个阶段,叙述建筑、雕刻、绘画等美术门类,但删繁就简,尤重考证,并注重运用新兴史料来阐述中国美术史,初具史论意义。“引人瞩目之处,在于顺应了时代潮流,吸收了学术新机,在有限的史实梳理中,突破了明清书画史家热衷于记载生平和作品流传的局限,以建筑、雕刻和绘画为范围,写出了一部有见解而非仅史料的中国美术通史,对上古至清代美术的发展脉络与因果联系做出了前人所无的阐释。”(6)薛永年:《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薛永年卷》,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312页。
1929年,郑午昌(1894—1952)所著《中国画学全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书依据中国绘画发展演变的时代特色,结合各个时期思想、文化以及政教与绘画的关系,将中国画学史划分为实用、礼教、宗教、文学化等四个时期,并以朝代分章,下分概况、画迹、画家、画论等小节(7)郑昶:《中国画学全史⋅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0页。。其书撰述体例完整、精研博讨、取材精审、史论结合,兼具综合性与史论性,具有美术史家个人才识、眼光。“吾国自来无完全之画史而叙述画史,尤以通史体例为宜。通史前无作者,最近始得陈师曾及潘天授两编,然师曾之书纯系学校讲义,非其著作。天授之书,则大半译自日人,非其心得。惟此编独出心裁,自出手眼,纲举目张,本原具在,虽其中不无可议,实开画学通史之先河,自是可传之作,余于吾国画学、画事,时有论著,颇欲汇集之为中国绘画通史一书,今得是编,可以搁笔。”(8)余绍宋编撰:《书画书录解题》,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以郑午昌为代表的近代美术史家具有现代化美术史观、深厚的传统美学史识以及融贯中西学术文化的史才,在坚守与变通、创新与融合的过程中,深刻拓展了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理路、视野。此后如李朴园《中国艺术史概论》(1930)、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1) 、秦仲文《中国绘画学史》(1934)、王钧初《中国美术的演变》(1934) 、史岩《东洋美术史》(1936)、俞剑华《中国绘画史》(1937) 、冯贯一《中国艺术史各论》(1941)、胡蛮《中国美术史》(1942)、刘思训《中国美术发达史》(1946)等,“叙史”类著作日渐兴盛,促使中国美术史的撰写形式逐步由单一模式走向多元发展,综合性与史论性的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撰述日渐兴起,成为现代中国美术史研究基调。
三、留学潮流与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的中国美术史研究
19世纪下半期,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但此时强调务实,且条件艰苦,留学生大多出生平民之家,少有涉及美术专业。至19世纪末,开始出现中国留学生赴外学习西方艺术,“第一位赴外学习美术专业的留学生李铁夫;最早走出国门,系统学习外国舞蹈艺术的裕容龄”(9)刘青弋:《裕容龄:身体的自由和束缚的博弈——影响20世纪中国舞蹈的早期留学生研究系列之一》,《当代舞蹈艺术研究》2017年第2期。。由于广东地区在清代时期便有着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是中西交汇的前沿阵地,中国最早一批的留学生多来自广东,而广东输出的海外华侨此时多聚集于美洲,这使得在20世纪初先后有梁銮、刘博文、赵雅庭、黄潮宽、朱炳光、余本、李秉、关金鳌、陈锡钧、陈瑞璋、关墨园等人选择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修习西方美术。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后民主与科学思想进一步传播,出国留学的条件更加便利,留学热潮日渐兴盛。
在民国初期,关于中国传统书画受到青年画家的质疑,他们在新文化的熏陶之下,渴望学习和引进西方美术以改造封建思想,大批的青年画家怀着对西洋美术的热情,踏入异国他邦,寻求拯救民族美术的良方。他们的主要学习对象,早期多倾向于邻邦日本,稍晚则集中在欧洲的法国。时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1868—1940)十分重视美术对国民思想改良的影响,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10)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34页。、“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11)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61-362页。等观点,推动了美术留学的发展。
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等各方面深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12)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9页。由于日本西化的成效显著,并且中日文化一脉相承,国情民俗相近,地理交通、语言交流便捷,日本成为国人接触、学习西方工业文明的重要渠道,先效仿日本再转入西方学习成为当时最好的选择。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中国留学生将日本看成学习西方的捷径,中国青年奔赴日本学习西方绘画,在日本间接地接受了西式的美术思想,“1906年前后约10年的时间当中,仅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多达两万余人”(13)陈瑞林:《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中国近现代引入的西方美术史论多转载于日本,现代意义上的“美术”一词以及众多的美术术语,最初也是受日本影响翻译成汉字的。可以说,日本早期留学生不仅拓荒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亦为大规模的美术“西行”铺平了道路。赴日留学的美术生以辛亥革命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辛亥革命前,出现了李叔同(1880—1942)、陈师曾、高剑父(1879—1951)、何香凝(1878—1972)等美术先驱,他们在接受西方美术思想的同时也将时间大量投入到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活动之中,因而对于西画的训练仍处于初级阶段。作为留学的拓荒者,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对中国美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02年,陈师曾携弟陈寅恪(1890—1969)东渡日本留学,虽然不是美术专业而是博物专业,但留学生涯使得他能够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传统书画,他回国后投身于美术教育事业,出版了《中国人文画之研究》,其中包含自著的《文人画之价值》与翻译的大村西崖所著《文人画之复兴》两篇文章。他参与发起“中国画学研究会”,并以独到的眼光鼓励齐白石对中国传统书画的创新。与陈师曾为好友的李叔同,在1905年自费赴日本,翌年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1911年李叔同归国,先后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与柳亚子(1887—1958)等人创办文美会,刊行《文美杂志》,并培养了丰子恺、吴梦非、潘天寿等民国美术史的众多名家。
辛亥革命后,赴日学习的艺术青年则以更加纯粹的目的走出国门,他们多报考正规的美术学院,回国后成为现代美术教育的中坚力量和民国的书画名家。在20世纪初,中国美术史上的著名人士几乎都曾去日本或长或短的考察学习过,如:金城、姜丹书、吕凤子、汪亚尘、俞剑华、江新、徐悲鸿、刘海粟、张大千、林风眠、常任侠、郑锦、潘天寿、傅抱石等等。
近代早期致力于开拓美术领域研究的中国美术史家注重引进、借鉴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成果,在美术史分期、编撰体例、撰述模式等方面深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民国初期,限于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的荒芜,受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影响,部分有识之士主动翻译日本人著作,以启迪和活跃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
1928年,陈彬龢翻译大村西崖的《东洋美术史》的中国篇成书《中国美术史》(14)[日]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陈彬龢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4页。,继之后,郭虚中以增进国人对于中国绘画研究的兴趣,进而开拓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为目的而翻译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中国绘画史》,成书《中国绘画史》(15)[日]中村不折、小鹿青云:《中国绘画史》,郭虚中译,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第2页。。大村西崖、内藤湖南、中村不折等日本学者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长期影响国内美术史研究与撰述,但亦不乏多数居于日本民族本位主义者,贬低中国文化、歪曲事实的现象,傅抱石对此警示中国学者在引用日本人著作时应有选择性的吸收,不要被他们误导,“他们研究中国美术,出于民族的夸张,往往不惜歪曲正确的史实,把中国说的无甚希奇,虽然连这无甚希奇的,他们本国也还是指不出来。他们对于中国美术的观念,是把古代的抬上天,说是如何如何的灿烂伟大,再说几句类似恭维而实际气愤的话,最后就离不了‘现在的中国有些什么呢?’这是日本一般的学者对中国美术乃至一切文化见于文字的公式。所以我们引用日本人的著作,应该警惕着这一点”(16)傅抱石:《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叶宗镐选编:《傅抱石美术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傅抱石曾多次赴日学习,其所形成的对于日本学者著作应辩证性看待的思想与呼吁,说明了近代中国美术史家已经开始逐步摆脱完全因袭、模仿日本学者的美术史观、治史方法、研究模式,日渐形成力主重塑中华民族本体地位下中国美术史研究。
与赴日留学的阶段性相似,辛亥革命前的欧洲留学仅有星火出现,而蔡元培曾在1907年游学欧洲4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为其后来强调美育思想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后,东渡日本和西行欧洲的近代留学潮开始兴起,20世纪20年代起,陆续有赴欧洲留学生学成归国,他们也像许多留日学生一样从事美术教学或开办美术学校。另有一批曾在日本等国留学的美术生为了接近更加正统的西洋美术,也转赴以法国、德国、美国为主要目的地的欧美地区进行深造学习,近现代美术史上的著名美术家中有大多数曾在法国学习。例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周轻鼎、汪亚尘、庞薰琹、常书鸿、刘开渠、颜文梁、王临乙、吕斯百、吴作人、傅雷、王子云等。
赴欧美留学生归国后,在中国美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亦促使近代中国美术教育、思想以及美术史研究日渐深受西方美术理论、思想以及研究模式的影响。以滕固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美术史家早年赴日留学,后受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又转赴德国留学,受西方美术学界流行的风格分析法的影响,并尝试通过西方现代艺术史研究方法撰述中国断代绘画史,“滕固创造性地把图像学方法和风格学方法、内向观与外向观方法、科学与审美方法结合起来,形成既吸收西方研究新方法又契合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方法,具有深刻的洞见,对于今天的艺术学研究有借鉴意义”(17)谢建明、徐习文:《论滕固构建艺术学科的思想》,《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54页。。1933年,滕固所著《唐宋绘画史》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它是立足于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格局,吸收西方现代艺术史研究方法,融合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创造性地运用风格分析法,来观照、阐释中国绘画史。“绘画的——不是只绘画——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Stilentwicklung)。某一风格的发生、滋长、完成以至开拓出另一风格,自有横在它下面的根源的动力来决定。”(18)滕固:《唐宋绘画史⋅引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第3-4页。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激发部分有识之士主张学习俄国革命经验。随着苏联的成立以及局势稳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注意力逐步从法国转向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复兴中国,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亦逐步在中国内地传播,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发展。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以及美术发展方向由此开始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以胡蛮为代表的中国美术史学者赴苏联学习,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并尝试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美术史,具有显著的前瞻性、先觉性。
1942年,胡蛮所著《中国美术史》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作者云其“是依照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的启发,把我过去十年间用一部分时间所研究的中国美术遗产问题和新美术运动的方向问题加以系统的整理”(19)胡蛮:《中国美术史⋅序言》,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年,第3页。。这是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中国美术的著作,开辟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新篇章,且长期被运用于实践教学,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美术教育以及美术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美术教育、美术发展以及美术史研究随着西学东渐以及留日、留欧美、留苏潮流的先后兴起,先后深受日本、欧美、苏联的影响。“前清那些学堂,譬如是先河;民国以后那些学校,譬如是后海;看今后的发展情况,将要扩海而成洋了。若以吸收外来的要素而论,先受日本影响最大;后受法国影响最大;近年加受苏联及东欧民主国家的影响最大。”(20)姜丹书:《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1页。赴外留学的新式知识分子逐步成长为美术界新兴力量,通过融合西方美术理论以及治史方法重新审视、阐述中国美术发展历史,不断拓宽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视野和路径,多元化中国美术教育以及美术史研究逐步确立并日至成熟,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实行现代化转型。
四、近代中国美术本体地位下中国美术史的重塑与建构
中国美术史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束缚下长期居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范畴,使得近代中国美术史长期落后于日本、西方,且深受日本学者以及西方美术史理论、研究范式的影响。近代中国美术学科建制的初立以及留学潮流的兴起,一批深受日本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美术史学者以积极、崇拜的态度学习与接受外来学术文化,开启了中国美术史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化转型。
民国初期,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日益严峻,国人长久以来的民族自信心和优越感受到了冲击,迫使中国人开始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而主动向西方学习,伴随着中西文化合流,西方现代美术理论与研究方法被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加以借鉴,用之改造中国传统美术史的分类方法以及研究模式。面对中国美术史学研究滞后的现状,近代中国早期的美术史学者主动引进、效仿甚至因袭日本以及西方的学术研究,以补足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荒芜状态,出现了以西方美术史观、研究方法为主,甚至全盘西化的研究模式。
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尊心、责任感以及现实的中国美术教育需求,使近代早期中国美术史学者实现了从引进到超越的转变,中国美术史学逐步从引进与模仿、固守与创新中向近现代化转型,进而建构了中国美术本体地位下本土化、独创性研究。
民国早期的中国美术史学者似乎长期处于一种“矛盾”心态,现代学术思想下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落后现状,使得其人只能效仿外来文化,而立足于中国美术本体地位的自觉又促使其人力主重构“自叙”地位下的中国美术史,以高扬民族艺术、文化,重塑国人文化自信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主流地位。
在近代早期中国美术史家姜丹书、陈师曾、潘天寿及至滕固等学者的广泛实践与开拓下,近代中国美术史学开始依托模仿、借鉴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编著体例、研究方法逐步过渡至重塑与复兴中国美术史本土化的主体研究地位,直至以郑午昌为代表的中国美术史家突破传统绘画史叙事方式,注重史论结合,形成了由国人撰述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著。
郑午昌所著《中国画学全史》历经近九年方才问世,著论长达35万余字,开启了中国画学通史之先河,同时郑午昌所开启的以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从中国传统绘画内部出发,统合西方现代学术方法为辅的研究范式,促动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转型。郑午昌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立场以及世界美术发展历史,重构中国艺术在东方以及世界中的地位,划分世界美术发展系统为二,将中西并列,中国为东方统系之集大成者,肯定中国绘画作为东亚文化的源头以及在世界美术中占有主流地位。“世界之画系二:曰东方画系,曰西洋画系。西系萌蘖滋长于意大利半岛,分枝散叶,荫蔽全欧;近且移植于美洲,播种于亚陆。东系渊源流沛于中国本部,渐纳西亚印度之灌溉,浪涌波翻,沿朝鲜而泛滥于日本。故言西画史者,推意大利为母邦;言东画史者,以中国为祖地,此我国国画在世界美术史上之地位”(21)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页。。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以及竞争意识,促使傅抱石坚定中国绘画独具民族性的信心,亦应由国人来担任研究主体,极力倡行重建中国美术本体地位下的本土化叙史,进而重建中国美术研究领域的主体地位。“只要不糟塌自己的天才,努力学问品格的修研,死心踏地去钻之研之,其结果,最低限度也要比隔壁老二强一点。”(22)傅抱石撰:《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导言》,南京:南京书店,1931年,第4页。
自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深刻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革,李大钊、郭沫若等较早尝试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美术史具有借鉴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行者,胡蛮深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进而形成了唯物史观与治史方法,开创性地运用唯物史观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透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阶级斗争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美术的演变与发展。“美术的创作和美术的理论是有血肉关系的。要想获得正确的美术活动的方向和美术创作的方法,就不能不研究本国的美术的源流变迁和它的发生发展的规律,这就是说,必须批判地接受历史的遗产。……另外还有一种偏见,好像和那思想正相反,说‘中国一切落后’说‘中国一切都应该效法西方文明’,……最后一种偏见,是‘穿着洋服拜菩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内容,也就是‘中西艺术之调和’的新形式。而这种偏见恰好正是前种偏见的总和。”(23)胡蛮:《中国美术史·序言》,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年,第1-3页。
胡蛮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中国美术本体地位,严厉批判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中所存在的局限于庸俗化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中西调和等思想下追求固步自封、崇洋媚外、中体西用等等偏见和研究模式,明确了坚守以中国传统美术文献以及现存的和新兴的考古实物、历史遗迹等文化遗产为根本,进行综合研究、科学分析的史观与治史方法。胡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史观、治史方法与社会发展、时代思潮紧密相关,开启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新方向,亦成为20世纪中后期重要的研究方法。
在近代社会发展大势下,以姜丹书、陈师曾、潘天寿、滕固等为代表的早期先行者,不断开拓中国美术史学研究视野、路径,促使中国美术史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而以郑午昌、傅抱石、胡蛮为代表的美术史家,坚守中国美术主体本土化研究立场、治史方法,以促动近代中国美术文化的崛起日渐成为共识,而中国近代美术史研究亦逐步从模仿转向独创,多元化美术史观和研究范式被广泛的吸收和应用,中国美术史研究亦脱离了从传统学术体系下边缘化地位,成为一门“显学”,开创了中国美术史学发展的新局势,奠定了我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的基调。
五、结语
中国古代有关美术史的记载、撰述繁多,但一直束缚于封建政治制度以及传统道德价值评判标准的窠臼,长期附会于史学撰述的范畴,美术史的撰述实落于传统史学的学术生态之中。近代社会变革以及中西文化合流促使中国美术史研究开始了转型。西方美术思想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整体潮流传入中国,受日渐高涨的文化自知与自觉的影响,中国美术史学研究脱生于“史学革命”浪潮,伴随着美术学科的建立而发展,“留学潮”之后,留学归国的新式知识分子逐步成长为中国美术界的新兴力量,他们引入和借鉴国外的美术理论与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美术史,不仅拓宽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视野和路径,亦形成了多元化中国美术史研究文化情景,逐步实现了向现代化形态转型,中国美术史学学术发展体系日趋现代化。以郑午昌、傅抱石、胡蛮等为代表的中国美术史家在强烈的民族情感以及现实的本土需求促使下,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综合现代学术思想以重新审视、阐述中国传统美术的发展历史,进而重构中国美术史的“自叙”地位,在“综合性”与“史论性”的观念影响下,中国美术史研究日臻完善与成熟,并奠定了中国现代美术史学的发展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