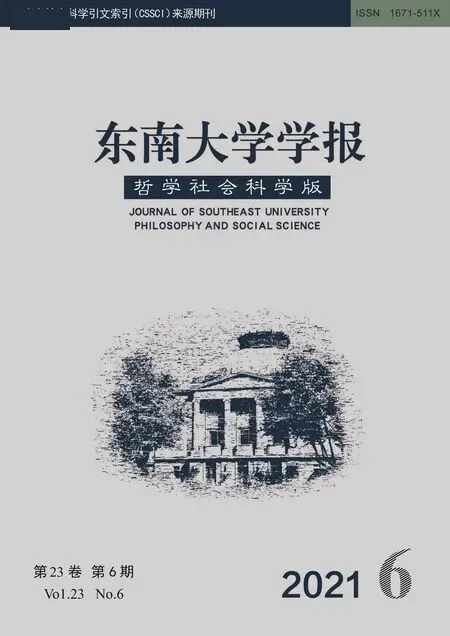总体流、反阐释与形象化
——论詹姆逊的后现代媒介观
黄 擎,张 隽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作为当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k Jameson,又译詹明信、杰姆逊、詹姆森)的媒介思想却长期受到学界忽视,可谓是詹姆逊研究中的一大盲点。实际上,媒介问题在詹姆逊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其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每一个时代都会孕化出一种得天独厚的媒介形式。以文学为代表的印刷媒介在整个现代主义时期一直是文化的主要传播形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媒介活动的样态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以电影、电视、视频为代表的可视化媒介完成了对印刷媒介和语言中心的颠覆,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出类拔萃的艺术形式”。
詹姆逊本人曾形容媒介问题就像是一个索引,将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精神”以一种凝缩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因此,对詹姆逊的媒介思想中的后现代性进行追问,不仅能为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多维度接受与阐释提供一种可行的路径,也能为当代媒介思想史领域提供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资源与比较视角,拓宽我们对当今媒介环境的理解。鉴于詹姆逊的媒介思想很多时候不是显在的,而是零散且细碎地编织在其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片段中。本文将从詹姆逊的相关著述中钩沉出他关于媒介的思考,从媒介编排、媒介生产、媒介传播这三方面对其展开论述,并就其中所包孕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做出说明。
一、观看的暴力:媒介编排的总体流
一般而言,媒介生产者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源于受众对其所生产的内容的直接消费,另一部分则来自流量变现(诸如接收广告投放等形式)所带来的收益。因此,在内容生产之外,积累用户数量与保持用户黏性自然而然地成了媒介生产者所关注的焦点。这也是詹姆逊媒介思想的核心议题,他用“总体流”(Total Flow)来揭示当代媒介以流量为重心的运作模式。总体流是詹姆逊在雷蒙·威廉斯“流程”(Flow)概念上发展而来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制作人员将看似互不相关的内容通过一定的技巧进行编排,使某一媒介上一定范围的内容组接成具有内在连续性与统贯性的序列,从而将用户“锁定”在该媒介,并尽可能延长用户使用该媒介的时间。需要指明的是,这里的连续性与统贯性并不表示总体流遵照的是完整严密的线性逻辑,而是以片段式的转喻与联想为组织原则。也就是说,总体流之下的各媒介文本的联系是松散的、开放的,它们不具有明晰的前后一致性。
那么,如何解释在内容之间植入与插播的广告呢?尤其是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观众都会在广告期间选择切换频道。就此而论,广告难道不是对总体流自身的一种干扰与阻碍吗?詹姆逊认为广告看似是在节目的“自然断点”时出现,实则在节目制作时就已被纳入考量之内。他试图提醒我们,广告这种规律性、周期性的中断与其他文化活动的终结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广告并不真的意味着观看行为的终结,它不同于戏剧或歌剧的落幕,也与电影的结局存在极大的差别,用詹姆逊的话来说广告只是“去洗手间或者动手做一个三明治的时机”(1)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 p.70.。这表明总体流允许观众短暂的离开,但只要观众再次将频道切换回来,总体流的策略就取得了既定的目标。
当然,媒介生产者也会提前准备好“保险”措施。他们会将稍后播放的节目内容的精华部分单独剪辑出来,制作成预告片,并在广告开始之前进行播放。预告片中通常会出现信息密度极大,充满感官刺激的镜头,以此充分激发观众对于随后将要播出的节目的兴趣,从而提升观众对于该频道的黏性。可以说,每个节目从早期的策划到最后的播出,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广告的播出时机。例如电视在播放一部电影时会均衡有致地将其切割为几个部分,并在这些切割处填充短暂的商业广告与节目预告。由此,原本不相连属的电影与广告开始结合为一,最终汇集成有计划性的总体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节目表已经整个改观了,各种自成单位的系列性节目,由彼到此,犬牙交错,真正的流程,真正的‘广播’,从此就出现了”(2)[英]雷蒙·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冯建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114-115页。。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不论在电视还是其他影音媒介中,我们总是会频繁地收看到预告片。
电视毕竟只是一种单向度的传播,节目表是事先编排好的,一个节目只能在既定的时刻播出,并不能按照个体受众的意愿进行随意的更改。詹姆逊注意到录影带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并加剧了总体流效应。随着电磁技术的商用化,录影带变得唾手可得,观众即想即看的需求得到了满足。观众花费在电视机前的时间急剧增加,对于电视的依赖性与成瘾性也在不知不觉间被培养了起来。对此,詹姆逊不无同情地说道:“录影时代无助的观众被牢牢地锁定,被机械地整合、被中性化,就像先前的摄影对象一样。”(3)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p.73-74.录影带所带来的总体流总是令我们对电视欲罢不能,观看的暴力也就此滋生。
然而,总体流所带来的成瘾机制远不似表面看起来的那样简单。阿多诺在讨论流行音乐时曾提出作为大众文化的流行音乐之所以拥有广大的受众,根本原因在于其既能够带来刺激又不用耗费精力(4)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On Popular Music, Simon Frith and Andrew Goodwin, On Record: Rock, Pop, and the Written Wor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263.。但在总体流的操纵下,当代大众使用媒介的时间出现极大的延长,如何协调刺激与劳神的问题愈加尖锐。詹姆逊也认为电视虽然能够令我们感受到放松与陪伴,但“电视的这些特性也会起到抑制神经系统的作用,它容易带来长久性的无聊,强迫性的重复甚或是麻木感”(5)Fredric Jameson, The Ancients and the Postmoderns,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5, p.240.。换句话说,大众文化的情节套路在不断重复中导致了总体流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媒介在标准化、模式化、同质化的生产中,必须针对受众心理做出对应的调整。对此,詹姆逊以电视剧《火线》(The Wire)为例,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为我们剖析媒介如何摆脱总体流下“审美常模”(Perceptual-AstheticNorm)所造成的困扰。
在形式上,《火线》的编导一直有意拖延该剧的进程与结局。自2002年第一季首播至2008年第五季完结,这个系列剧前后绵延了6年之久,且每一季的播出是以一周更新一集的方式进行。詹姆逊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欲望与满足就像是钟摆的两极,每当欲望满足时,便会觉得空虚无聊。连续剧的形式恰好能够充分地延宕欲望的满足,正如詹姆逊所言,“这种内容层面上的矛盾影响了形式本身——电视连续剧——因其不会以完全的满足感结束,我们便会对后续的收看充满动力,并期待更精彩的剧情进展”(6)Fredric Jameson, The Ancients and the Postmoderns,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5, p.243.。在该剧中,不管谁被绳之以法,新的毒贩总是会卷土重来,借助故事的历史性重复,《火线》没有真正意义上闭合的结局,总体流也就能一直持续下去。
就内容而言,《火线》的剧情则总是在不经意间掺杂着乌托邦蜃景。其实早在经典好莱坞时期,詹姆逊就发现类型电影中充斥着大量补偿性的“梦想成真和慰藉”。在《火线》中,“非直接的愿望满足”这一传统成功延续了下来。《火线》的每一季都直击一个具体行业或群体的痛点,并塑造出一个乌托邦式的“英雄”人物。虽然他们的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但詹姆逊却认为《火线》“出人意料地描述出在现实对乌托邦加以围剿前,乌托邦总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实现突围”(7)Fredric Jameson, The Ancients and the Postmoderns,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5, p.254.。在这里,电视连续剧的重复性被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功能所遮蔽,成了像流行音乐一样的社会黏合剂,修补了社会关系。
媒介编排的总体流同时也关涉到后现代主义一个核心的问题,即主体的消逝。詹姆逊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便是“作品”(Work)与“文本”(Text)的对立。在詹姆逊看来,现代主义从始至终都在追寻所谓的“审美自律”,投射在创作层面便是如指纹般的个人风格。每个现代主义作家都力求在创作时烙印下自己“可见的签名”。这也使得现代主义时期的作品像莱布尼茨所谓的“单子”那样,具有高度的独立自足性。在广播与电视问世之前,所有传播系统中的主要项目间总是保持着离散的状态。例如一本书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单元,我们阅读它时并不会牵涉到其他的文本。再如我们观赏一出戏剧,这出戏剧有着确定的演出时刻与地点,从而使得我们的观看体验形成了一个闭环。
到了后现代主义时期,总体流使得我们很难单独地去谈论一个具体的媒介“作品”,而是只能称其为“文本”。“文本”不再是封闭的、自律的,而是开放的、他律的。一个“文本”不再是具有鲜明辨识度的原创,而是对既有“文本”的回收、重组与拼贴,呈现出具有复杂指涉关系的互文性。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连续接收多个“文本”时,知觉、记忆总会受到其前后“文本”的干扰与扭曲,从而使得所有的发现变得面目全非。这是因为尽管“文本”内容各有不同,但当代媒介以总体流的方式将这些“文本”内容都整合了起来,内容与内容已经形成了经验“共同体”。在总体流的统辖下,将它们切分成独立的单元然后进行分析与评论的可能早已被抹除并驱散。
综上所述,总体流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动因,它是流量经济模式下媒介之间相互竞争、争夺用户的结果。对于媒介生产者来说,想要获得更丰裕的收入,就必须尽最大可能地“抓住”用户,方能最终实现流量转化。这也是威廉斯与詹姆逊所共同持有的观点。但与威廉斯不同的是,詹姆逊并不满足于对总体流进行简单的政治经济学描述,或者说仅仅将其视为提高用户黏性、增加使用率的一种手段,他转而将总体流置入后现代语境中,揭示出总体流在运作时必然会将媒介的历时编排转译为一种共时系统,而该系统显然并没有为作者与受众的主体预留位置的打算,任何试图在总体流中找寻作者风格与文本个性的行为注定要以失败告终。我们有理由认为,詹姆逊的探索为总体流注入了更为深刻的理论内核,提升了总体流的阐释效力。
二、意义的消解:媒介生产的反阐释
詹姆逊曾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篇纲领性的文章中提出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症候便是深度模式的消解。正如苏珊·桑塔格主张后现代作品的本质在于体验而非阐释,我们在接受过程中更多的是要去感知作品本身所带来的刺激与体验,而不用刻意去追寻隐藏在表层之下的意义一样(8)[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3-15页。,后现代理论谱系整体呈现出鲜明的去阐释化态势。受该思潮的影响,发轫于现代主义时期的辩证法、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及符号学等阐释理论均招致不同程度的质疑与诟病,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后现代理论场域中也受到严重的挑战。
对阐释的排斥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也渗透到具体的媒介生产中。如果说无深度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主导文化逻辑,那么当代媒介中的录影艺术就是这个逻辑最有力、最具原创性的形式。詹姆逊以一卷名叫《异域国度》(AlienNATION)的录影视频为例向我们说明此点。该作品由来自芝加哥艺术学院的爱德华·兰库斯(Edward Rankus)、约翰·曼宁(John Manning)以及芭芭拉·莱瑟姆(Barbara Latham)三人联合制作完成。
从视听语言的角度来看,这卷录影文本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高密度的意象材料,在短短的29分钟里,就出现了30余个视觉性的意象材料。画面急速的闪切、背景音乐无规则的变换都给观众带来一种时间上的急迫感。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过量且急速流动的视觉与听觉能指。这也带来了时间体验的延长,正如詹姆逊所感受到的那样:“这卷29分钟的录影带比任何故事片中同等时长的片段都长得多。”(9)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Or,The Cultu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79.二是形式的解构。我们很难在《异域国度》中辨认出类似开端、发展、冲突、解决、结束等常规的叙事形式。例如最后的湖滨一景,看似是该卷录影带的结尾镜头,但这里的结尾只是一个空洞的视觉讯号,它不具有任何的结构性功能。因此,詹姆逊指出,湖滨一景在此只是形式的残余,或者说,它是一种对已经消失的形式作用的模糊记忆。按照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的看法,故事就是一系列幕的组合,故事的发展是从一个情境到另一个情境的变化,而结尾作为发展的最终情境,必须是绝对且不可逆的(10)Robert Mckee, Story: Substance, Structure, Styl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 New York: ReganBooks, 1997, p.41.。然而在《异域国度》中,前后画面间根本就不具有线性的因果关系,也不具有连贯的情节,甚至都构不成罗伯特·麦基所谓的“故事”,因而也就不存在结尾这一说法。
对于《异域国度》的上述两个特征,詹姆逊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它们所带来的反阐释性。我们根本无从回答《异域国度》的内容在传达什么意思,也无法解释《异域国度》的形式到底想要表现什么。但詹姆逊的讨论并没有就此戛然而止。相反,正是在不可阐释之处,詹姆逊看到了阐释的必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是“任何不需要解释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亟待解释的事实”(1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是什么阻碍了对《异域国度》阐释的可能呢?詹姆逊认为是充斥在该录影视频中的“符标”(Logo)及其运作模式。詹姆逊是这样定义符标的:“符标就好像广告形象与品牌名称的混合体;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已经被转变成一个形象、符号或标志的品牌名,这些形象、符号或标志以一种类似于互文的方式在其内部承载着对早期广告的整个传统的记忆。”(12)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85.也就是说,符标实质上是一种剔除了所指的符码,它无法提供除了自我指涉之外的任何意义。符标不局限于视觉性的图片与视频,同时也包括语言性的文字与听觉性的音乐。据此,《异域国度》中出现的自动扶梯、服装店的人体模型、《零怪兽》、迪斯科乐等等片断均可包容于符标的范畴之下。
符标之所以具有反阐释性,与它的运作模式有密切的关系。根据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符号由代表项(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与解释项(Interpretant)组成(13)Charles Sander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s2, edited by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2, p.274.。解释项是对代表项做出解释、说明的符号,它与代表项实际上共享一个指涉对象。一个符号在成为代表项的解释项的同时,也存在着另一个解释项对其进行解释与说明的行为。换言之,代表项与解释项是两个本质和功能相同的符号,代表项是先发的、主导的,解释项则是继发的、从属的。凭借解释项的不断增殖与延宕,符号在三元间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闭环,意义也就此形成。
然而,符标间的运作模式颠覆了皮尔斯的符号学。詹姆逊指出符标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一个单独的符标能够以运作主题的身份保持优先性;一个符标作为另一个符标的解释项的情况不仅仅是暂时的,同时也会在未经注意时发生改变;在我们必须面对的永不停歇的转换运作之中,我们的两个符标以一种令人困惑且近乎永久交换的方式占据对方的位置。”(14)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87.具体而言,《异域国度》的镜头就是一种符标的位移与迭代,符标每时每刻都处于变动中,当一个符标成为解释项的瞬间,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符标已经生成并开始顶替前一符标,导致没有一个符标能够长久地占据代表项与解释项的位置。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本雅明对于观影体验的描述,电影的画面总是处于流变不居之中,每当观众试图用眼睛捕捉或是定格画面时,画面早已出现了切换。观众对此只能以“涣散”(Distraction)的方式进行接受(15)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London:Fontana Press,1992,p.231.。
詹姆逊进一步指出,在文本的各种媒介要素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往往会改变甚至消解单一媒介要素的原始意涵。这是因为符标并不孤立地存在,符标间的关系是共时的而非历时的,而这种共时系统使符标的表意功能发生了异化,就像詹姆逊所发现的那样,“似乎毫无疑问,时装模特或是一系列人体模型的形象在与科幻电影及其各种(视觉的、音乐的、文字的)符标的力场交汇时被强力而粗暴地改写了:在这一时刻,时装广告中那熟悉的人类世界变得‘疏离’了,而现代百货公司则像任何一个遥远行星上的异域风俗那般怪异与可怖。”(16)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88.符标的共时性使得录影带文本就像是呈现在我们感官下的万花筒,令我们无法从中指示出可资辨识的意义或指涉物。
除此之外,符标的运作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媒介文本主题化(Thematization)的可能。在詹姆逊看来,“主题化就是指文本的一个要素、一个成分被拔高至中心思想的地位,并且在这一基础上成为一个具有更高荣誉的候选项,即作品的‘意义’”(17)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91.。可是符标的不断流动从根本上阻断了主题的抽离与提取。即便我们从某一符标中解读出具有指涉性价值的隐喻,这个符标也只是众多符标中的一个,它出现的瞬间便被淹没与消融在符标流之中。
实际上,以录影视频为代表的媒介生产的反阐释性与后现代主义有深层的同构关系。受到德勒兹的启发,詹姆逊曾以符号受阉割的过程来喻拟文化分期。他假定前资本主义社会所使用的语言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与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一种物化的力量也随之产生。该力量驱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使用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包含了意符、意指以及指涉物的完整的符号语言。这个语言体系投射着“一个外在的、真实的世界,一个向外不断延伸的、可以衡量的世界”(18)[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84页。。文学与科学都想要用说明性的语汇去描摹、表征这个新的外在的客体世界,现实主义便就此产生。随着物化的力量进入符号语言内部,指涉物从符号语言中剥离了出去。符号语言与客观世界拉开了距离,并因此获得了否定与批判的力量,这正是现代主义的生成背景。当物化的力量进一步加强时,它又渗入了意符、意指之间。在消除了意指(意义)之后,剩下的就是意符“纯粹而无目的游戏”。此时的符号语言只能以拼贴的方式转换既有文本的片段,试图从中识别出潜在的意义注定是一种徒劳。反阐释性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症候,而当代媒介文本可以说是这一症候最有力的表征。
三、现实的消亡:媒介传播的形象化
我们知道,不同类属的媒介形态具有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詹姆逊正是通过对收音机与电视的区分来开启他关于当代媒介传播特质的思考。收音机在20世纪曾一度成为欧美家庭中的主导媒介。此后,得益于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视在20世纪40年代后开始普及并逐渐代替收音机成为欧美日常家庭生活中使用率最高的媒介。詹姆逊指出电视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电视的出现,可视化的广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广告及广告形象这一问题就成了我们所称的后现代主义的中心问题,因为电视广告以其速度之快和效果之好完全突破了旧有的广告形式”(19)[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7页。。电视广告之所以能够引起詹姆逊的强烈关注,并被置于后现代主义话题的中心,其根本原因在于电视所带来的广告传播方式的变革,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电视广告的形象化对于当代媒介传播的深刻影响。
詹姆逊为何会对媒介传播形象化的问题如此关注?这与他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形势判断是分不开的。詹姆逊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时期,经济活动的重心已然从生产转移到了消费。资本主义的影响力不再止步于经济领域,而是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渗透与扩散。文化这一从未受到资本浸染的飞地,如今也再难以“独善其身”,彻彻底底地被商品规律所同化。詹姆逊指出,“在这个新阶段中,文化本身的范围扩展了,文化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是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在购物中、在职业工作里、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在为市场生产产品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中,甚至在每天最隐秘的皱褶和角落里被消费,通过这些途径,文化逐渐与市场社会相联系。”(20)[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媒介传播融汇了资本与文化,并在二者间搭建起了相互转化的链路,完全可称得上是后现代主义的技术典范。
与此同时,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商品大多采用流水线式的集成化、批量化生产,这就导致相同类别的产品具有同质化的倾向,如何在消费者中取得辨识度因此成了一个大问题。詹姆逊以香烟为例向我们说明此点。他假设有五家香烟厂商,在工艺水平持平的情况下,所制造的香烟无疑是大同小异的。任何一家厂商想要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就必须先说服消费者自家的香烟味道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完成对产品的差异化处理。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詹姆逊告诉我们,这涉及广告的运作机制。他认为广告的目的在于给产品或品牌生产出一种形象,除了使用功能之外,还会与某种观念捆绑。如此一来,消费就不单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同时也是为了获得某一象征性的附加意义。
在鲍德里亚那里,上述过程被指认为商品或消费的符码化,商品与商品之间甚至组成了符号矩阵,形成了一条互相指涉的暗示意义链(21)[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与鲍德里亚不同,詹姆逊注意到的是文化的审美或是高雅属性无疑会成为提升商品附加意义的绝佳手段。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着形象生产,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在今天,形象就是商品,这就是为什么期待从形象中找到对商品生产逻辑的否定是徒劳的原因,最后,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美都虚有其表,而当代伪唯美主义对它的青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策略而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源泉的原因。”(2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7页。正是文化的商品化导致了形象的大量生产。在这一过程中,一种经过精心剪裁的形象制成品通过当代大众传媒这个加持装置迸发出了数倍的潜能。媒介成了资本用文化包装商品,将消费伪装成文化活动的同谋。
伴随着形象的大量生产与传播,问题也随之产生,那就是社会和世界的非真实化。正如詹姆逊迫切想要告诉我们的那样,“这就是真正的形象社会时期,从此在这个社会中人类主体面临每天超过一千个形象的轰炸”(2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3页。。形象看似是对社会现实忠实的复制,但也正是在这种机械性的复制中,受众承认和接受了媒介所创造的非真实化的社会现实。在詹姆逊眼中,形象就像是陈列于展览馆中的蜡像,其内在的真实性已被掏空,只能以仿拟的、人造的硅胶面貌示人。也就是说,形象虽不等同于虚构,但它却是通过将缺席表现为在场的方式来同化现实。最终,现实被吸收进形象里,而我们只能在形象的包裹下看到似是而非的残余。
个人终端媒介的普及无疑加剧了媒介形象与现实世界关系的改变。电视、电脑与手机等电子媒介在令我们在获取外部信息更加便捷的同时,也使得我们与现实世界间的距离感进一步消失了。原本宏阔的、立体的、复杂的外部现实全都凝缩到了我们眼前的屏幕上。我们所观看、所了解的不过是一种经过加工的平面化的屏幕现实。现实不再具有即时即地性,而是被本雅明式的“展示价值”所裹挟。肖恩·霍默在评论詹姆逊相关研究时曾点明:“电视为交流网络和计算机空间的新世界提供了完美的形象,在这个世界里,孤立的个人被塞进了他们自己的控制面板,并远离了与现实的任何接触,除非现实在他们面前的屏幕中被模仿,仅此而已。”(24)[英]肖恩·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孙斌、宗成河、孙大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由此,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被转化为无数的形象,一切都只在形象中存在,一切也只能在形象中被感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理解了詹姆逊何以认为对于美国国内民众来说,越南战争本质上是一次电视事件。
形象还通过对无意识的入侵来改造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当代广告显然深谙此点。詹姆逊指出广告想要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就必须与消费者的欲望相吻合,但广告不仅仅是直接与消费者的表层欲望对话,它同时也必须在深层或是无意识层面的欲望上发挥作用。这些深层欲望往往具有普遍性,如独立自由、生活幸福、青春永驻等等。广告的惯用伎俩便是将这些普遍的深层欲望以形象化的方式嫁接到自己所推广的产品上,通过许诺一种虚幻的精神满足感来引诱消费行为,而“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在这种乌托邦式的状态下改变了、变形了”(25)[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8页。。在广告的推波助澜下,形象为现实世界加上了一层滤镜,同时也成了一道隐形的幕墙,人与世界被分隔两端。长此以往,我们的对现实的感知能力必然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钝化,转而对媒介制造出的蜃景顶礼膜拜。
我们不难发现,詹姆逊对于传播的形象化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还接续了鲍德里亚对当代消费社会与拟像的思考。传播的形象化是媒介技术发展的社会转化,更是金融资本收编文化生产的必然结果。正是资本逻辑对文化领域的全面渗透,导致了形象的大量生产与制造。与此同时,与传播的形象化接踵而至的是现实世界的消亡。传播的形象化压迫甚至直接挤占了现实世界在媒介中的存续空间。受众接收到的只是一种现实世界的“摹体”,媒介传播的本真性也就无从谈起。
整体观之,詹姆逊的媒介观是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判之上,但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基础视作上层建筑的直接决定因素,詹姆逊认为经济基础只对上层建筑施加最终决定作用。换言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有时并不具有直接的交合性,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众多中介层面,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影响必须经由中介层面的传导方能实现。媒介恰好正是这样一种中介,它能够为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模式提供有力的说明。因此,詹姆逊的后现代媒介观的立论基础很多时候并非纯粹的技术决定论或是技术本体论。相反,他更多的是将当代媒介视作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的再生产工具,所关心的也是晚期资本主义以何种方式通过媒介来操纵、控制我们的文化活动乃至日常生活,而媒介又以何种方式回应晚期资本主义的诉求。就这一层面而言,詹姆逊的媒介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丰富与发展,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社会的适用性与言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