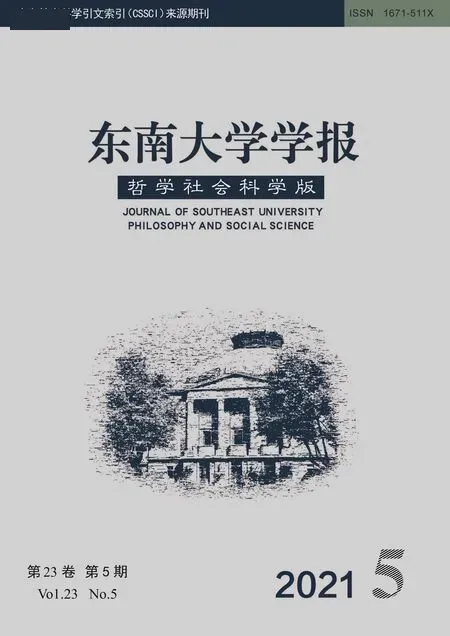无声者的生态悲歌
——读《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
陆薇薇
(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初版于1969年)是日本作家石牟礼道子(1927—2018)《苦海净土》三部曲(1)《苦海净土》三部曲由《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1969)、《神灵的村庄》(2004)和《天之鱼》(1974)组成,本文着重论述第一部《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下文简称《苦海净土》。的第一部,在其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苦海净土》曾荣获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文学奖及大宅壮一纪实文学奖,同时也是池泽夏树编撰的《世界文学全集》中唯一收录的日语作品。
如池泽夏树所言“水俣病的苦痛是全人类巨大的财富”,石牟礼书中对于人类文明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思考颇具当代价值,近期被作为日本生态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介绍到我国。例如,杨晓辉在《日本当代生态文学研究》中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对苦海净土这一标题的意象、行文中方言的意象及作品中人物的意象进行了阐释,展现出作品的生态意境(2)参见杨晓辉《日本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3年。。刘利国等在《论石牟礼道子的生态创作意识》一文中从生态批评视角对作品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剖析了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及表现形式(3)参见刘利国、祝丽君《论石牟礼道子的生态创作意识——以“苦海净土”三部曲为例》,《日语学习与研究》2016年第6期。。
对环境问题的深省无疑是贯穿这部作品的主旋律,然而,石牟礼的生态思想还蕴含着更为深邃的内容。从历史和社会语境看,水俣病发生在其家乡,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之一,作品创作时期正值日本妇女解放运动的萌芽期,她与同时期的几位女性作家都曾加入谷川雁的“同好村”(4)同好村(サークル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九州地区及山口县为促进地域及职场间的相互交流而成立的矿井劳动者自立运动共同体。1958年,谷川雁、上野英信、森崎和江等创办了同名期刊《同好村》,有200多名成员,石牟礼道子为其中一员,该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是日本战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过短暂的共产党员史。这些经历让石牟礼对社会弱势群体格外关注,因此,《苦海净土》不只是单纯的环境挽歌,更是为“无声者”而颂的生态悲歌,体现出作者女性主义意识、后殖民主义意识、当事人意识与生态意识的融合。我们只有在这些意识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动态把握石牟礼的思想,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这部作品。
一、纪实还是虚构?——“道子体”的创造
文学作品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形式是内容的载体。在探讨石牟礼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意识之前,先论述一下这部小说中颇具特色的文体。《苦海净土》中石牟礼共使用了三种文体:“以第一人称‘我’展开的叙述(旁白);夹杂着水俣方言的口述(独白);医生的诊断书和政府机关的报告书。”(5)[日]上野千鹤子:『おんなの思想』,东京:集英社,2016年,第45页。看似不可通约的几种文体被石牟礼道子巧妙地组合在了一起,渡边京二称之为“道子体”。
“道子体”中最受关注的是患者及家属夹杂着水俣方言的口述部分,金井景子指出,“道子体”类似于近世人形净琉璃(6)净琉璃是日本传统艺能之一,人形净琉璃(也称文乐)及古净琉璃的表演比起“唱”来说更注重“说”。或可以追溯到中世的古净琉璃,尤其是患者的述怀,相当于艺能中最精彩的部分,娓娓道来,扣人心弦(7)[日]金井景子:「『偿い』を问う—水俣病と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の半世紀—」,『学术研究(国语·国文学编)』2010年第58号。。患者及家属的口述如泣如诉,赋予作品极强的代入感,从而获得极高的赞誉。但这极其细腻而真实的笔法,却又让众多读者误以为这些内容全都是石牟礼道子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是其对患者话语的忠实记录,所以作品出版翌年即荣获“第一届大宅壮一纪实文学奖”。石牟礼谢绝了该奖项,因为“《苦海净土》并非边听边写的记录,甚至不能算是报告文学”(8)[日]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 わが水俣病』,东京:讲谈社,2004年,第368页。。
如果说《苦海净土》不是纪实文学,那么它是虚构的作品吗?作品中患者在自己破旧的小屋里、医院的特别病房中,向“我”(作者)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事实上,石牟礼确实于1959年起与水俣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赤崎觉一起走访病患家庭,倾听他们的遭遇。环境伦理学家鬼头秀一在《来自环境破坏的相关言说现场》一文中强调“倾听”的重要性,他认为倾听意味着接受讲述者的全部,是接近水俣病患者的重要手段。记录和表达是倾听的延续,土本典昭、佐藤真用影像的方式加以记录,而石牟礼道子则用文学的形式加以表现(9)[日]鬼头秀一:「环境破坏をめぐる言说の现场から」,饭田隆、井上达夫、伊藤邦武,等编:『岩波讲座 哲学8 生命/环境の哲学』,东京:岩波书店,2009年,第162页。。所以,石牟礼首先是一名倾听者、观察者,其次是一名记录者,继而才是一名创作者。
可以说,“道子体”是一种既非纪实也非虚构的文体。纵观世界文坛不乏纪实与虚构的对立统一之作,例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然而石牟礼的文体有其特殊之处,它具有“凭依”的特征和方言的魅力。
“凭依”一词指灵魂的附身,石牟礼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诉说着患者真实口述以外的内容,却让读者感觉那就是与水俣病相关的真实,所以被文学评论家们称作拥有灵力的“巫女”。这种灵力实则是一种极强的亲和力。身为一介主妇的石牟礼,融入患者当中倾听他们的心声,无论在作品里还是现实中,患者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阿姐”。正如渡边京二所说,石牟礼的文体“历经了诗的洗礼”(10)[日]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 わが水俣病』,东京:讲谈社,2004年,第386页。,这种亲和力与文学根本之所在的“诗情”是一致的,体现出作者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情感。
水俣方言是“道子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苦海净土》中患者的独白与其说是水俣地方语言及风土人情的真实反映,不如说是打上了石牟礼道子个人烙印的文学再现。石牟礼之所以使用方言进行叙述,不仅因为方言是具有当地浓烈地方特色的文化表征,还因为方言是水俣人话语权利的象征。北美民俗学家亚伯拉罕曾指出:人类的成就来源于人类在群居交际场合作出的创造性的方言回应。这是我们应对那些让我们束手无策的力量的手段(11)Abrahams Roger D,“Phantoms of Romantic Nationalism in Folkloristics”,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993,p.5.。为了对抗日本政府、对抗水俣病元凶的日本窒素公司,《苦海净土》中方言的使用是不可或缺的,也只有这样的“道子体”,才能承载起石牟礼对近代文明的质疑和对弱势群体的关爱。
二、女性主义视角的生态批评
日本社会长期受到父权制的影响,文学界也不例外,女性想要在文坛“发声”极为艰难。当我们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梳理战后日本文学史时,无法忽略“同好村”的森崎和江、石牟礼道子等几位女性作家的重要地位。
石牟礼曾把同好村创始人谷川雁(12)日本诗人、革命家,崇拜毛泽东思想,并植根于日本本土凝练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理论及方法,对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翼阵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终极思想,对谷川的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最终,她并没有止步于谷川的思想。在创作《苦海净土》的同时,石牟礼与女性史学家河野信子一起撰写日本女性史奠基人高群逸枝的评传,高群的著作促使石牟礼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她写下了与谷川思想的诀别之言:“我们,不,至少我,已决定不再与男性(男权)世界对话……男权支配下的遗语,不论是多么进步的男性来使用,终究会受其思想根基所限。”(13)[日]石牟礼道子:『最后の人——诗人高群逸枝』,东京:藤原书店,2012年,第316页。
在《苦海净土》中,石牟礼成功塑造了山中皋月、坂上雪、杉原百合等女性形象。尤其是第三章坂上雪的口述《雪女的见闻记》,为石牟礼最早创作的一个部分,1960年曾以《奇病》为题发表在《同好村》上。
处于日本女性主义思想萌芽期的女性作家,认为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带有东方主义的意味,她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分娩的主题,以示与男性作家的区别。例如,森崎和江如此描述自己的经历:“我将生孩子时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快感据为己有这一事实着实令人恐惧;我害怕直面那一刻所拥有的女性性心理的傲慢,便将丈夫也叫到了分娩的现场。对于分娩的快感、对于虽似绞肉之痛一般却由此而生的快乐、对于与生命的产生相伴随的几近死亡的自我消费式的性高潮,我完全知晓。”(14)[日]森崎和江:『第三の性——はるかなるエロス』,东京:三一书房,1965年,第62页。然而,石牟礼笔下的坂上雪却因为水俣病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不仅她本人深受病痛的折磨,“全身的痉挛让她感觉万物都在摇晃”,“说话断断续续,难以与人交流”(15)[日]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 わが水俣病』,东京:讲谈社,2004年,第148-149页。,而且由于水俣病极强的遗传性,她腹中的婴儿也不幸感染上胎儿型水俣病,被迫堕胎。
我住院的时候,被迫流产了。那时真的好反常。
屋外一片漆黑,送来的饭菜里有条鱼。我那时刚做完手术,感觉那条鱼好像就是我那死而复生的孩子……
……这次得了怪病医生说要保大人,用机器把宝宝从肚子里取走了,我看见宝宝的手脚在朦朦胧胧地动。一想到这事我真是羞愧极了,我对不起他。现在我呆呆地望着那条鱼,就像望着我那孩子……
我努力去抓盘子,可是一用力痉挛就开始加剧。盘子和筷子碰在一起叮叮作响。筷子刚夹起鱼就又掉了。我一个人乱作一团。我的孩子从饭桌上逃走了。(中略)
不要逃,我现在来吃掉你(16)[日]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 わが水俣病』,东京:讲谈社,2004年,第157-159页。。
世界各国的女性运动与各国的文化土壤密切相关,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向‘母性主义’倾斜是日本女性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母性主义’与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孕育的万物有灵论的心性不乏相通之处”(17)[日]井上洋子:「『ゆき女きき书』成立考ー石牟礼道子とフェミニズムー」,佐藤泰正:『フェミニズムあるいはフェミニズム以后』,东京:笠间书院,1991年,第42页。。女性“生”之哲学与日本传统自然观紧密相连,在日本传统自然观中,自然是“生”成的,而非西方世界般由神所“创”造。与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的主客二元对立不同,“生者是主体,而被生者不仅是客体,同样也是主体”(18)[日]田中晃:「日本的自然观としての连续观」,『思想』1939年2月号。。正因为日本传统自然观中自然既是客体,也是主体,所以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荣的存在。坂上“生”的痛楚与辛酸是近代文明的恶果,是对环境污染的控诉,而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恰是人类本身。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毁灭了自然的“生”的能力,这种行为终究反作用于自己,令人类自身丧失了“生”的权利,坂上的悲剧旨在提醒世人时刻自省自己的行为。
另一方面,虽然坂上被迫流产了,但她历经了怀孕的部分过程,看到了孩子手脚朦胧的动作。在这一过程中她已生成了母性意识,这种意识使得她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与孩子关联的整体。坂上幻想着孩子就是那条鱼,要将他吃掉,实则是希望从母子分离的状态回归到母子结合的状态。“完全行使‘单个的我’这一权利并非女性的最终目的”(19)[日]森崎和江:『ははのくにとの幻想婚』,东京:现代思潮社,1970年,第254页。,相对于男性的“一代主义论”(20)“一代主义”一词出现于森崎和江的《第三性》一书中,她认为相较女性而言,男性注重自身的独立性,缺乏代际意识。,女性特有的“生”的体验让其真切感受到生命的延续性,引发了其对代际关系的思考,这种意识与我们当下所说的环境代际责任具有相同的指向。当我们不仅考虑本代人的利益、代内的环境正义,而且将下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身体健康及公平享有生态资源的权利纳入到环境伦理考量的范畴,就会自觉维护地球的生态环境质量。如此,石牟礼女性主义意识和生态意识的交融构成了《苦海净土》的第一乐章。
三、平民视角的生态身份认同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现代化之路,政府积极引进西学,构筑起所谓的官方学术体系,而普通民众则被定位成“无知”的存在。依据米歇尔·福柯的知识与权力之连带关系的言说,知识与权力相互作用、相互建构,知识产生权力,权力生成话语,而这一话语是压制了部分话语的特权话语。可见,日本社会曾呈现出“官(有识、有权)与民(无知、无声)”的二元对立格局。为了打破由前者主导的知识体系,柳田国男及其弟子创建了令“常民”(21)基本等同于平民。在不同历史时期柳田对于常民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但关注底层民众的视角贯穿始终。幸福的民俗学。为了对抗强势话语,谷川雁等人为平民设立了同好村。石牟礼颇受谷川雁思想的影响,对平民生活极为关注。
在《苦海净土》中,石牟礼进行了生态身份认同的建构,这一建构是在平民视角下完成的。所谓生态身份认同是指“在与自然的多样性关系中把握到的各个人的自我概念”(22)Thomashow Mitchell,Ecological Identity: Becoming a Reflective Environmentalist,Cambridge, MA:MIT Press,1995, p.3.,表现出自然环境与人的价值观、行为、自我认知的相互影响。构建一个人身份认同(identity)的要素包括语言、民族、国家、文化、宗教、性别等等,生态身份认同(ecological identity)概念的提起,意味着在既有的诸多要素中添加了“环境”这一内容。《苦海净土》中的“环境”是水俣,水俣是石牟礼的家乡,位于九州熊本县的最南边。该地区西临不知火海,海产丰富,本是风光明媚、清朗闲适之所。“除了每年一两次的台风,汤堂部落总是被一个小小的、波澜不惊的海湾围绕着。泛着微波的汤堂湾上漂浮着小船和沙丁鱼篓,孩子们光着身子玩耍嬉戏,他们时而在船和船之间跳来跳去,时而‘扑通’一声扎进水里。”(23)[日]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 わが水俣病』,东京:讲谈社,2004年,第10页。石牟礼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深深的地方依恋(topophilia),然而她并没有通过与水俣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获取自己的生态身份认同,而是将关注点放在经营着日常生活的普通水俣人身上。
环境文学研究者结城正美归纳了美国与日本生态文学作品中构建生态身份认同时存在的差异:“在美国生态文学中,具有一种强烈的‘我’和自然相对、进而在与自然这一‘他者’或‘异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深化环境意识、获得生态身份认同的强烈倾向;然而,(在日本生态文学中),石牟礼却一直以现代化过程中被排挤、被忘却的非现代的世界观为立足点,对生态身份认同进行探究。换言之,在石牟礼的作品中,鲜有作者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对立的景象,或者毋宁说,她所关心的是那些以土地为生的人们。”(24)[日]结城正美:「<庶民の文化>とエコロジカ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生田省悟:『「场所」の诗学』,东京:藤原书店,2008年,第44页。在水俣的普通渔民身上,石牟礼找到了构建生态身份认同的路径。
《苦海净土》中,江津野老人对年轻时的生活进行了追忆:“鱼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上天无偿赠予我们的礼物,我们取一日之需渡过该日。没有比这更奢侈的了。”(25)[日]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 わが水俣病』,东京:讲谈社,2004年,第220-221页。而坂上雪如此回首往日的美好,这是《雪女的见闻记》中的经典段落。
船上的生活真的很好。
乌贼可不讲情面呢,一抓上来就冲着我们“噗噗”地喷墨,那个章鱼呢,章鱼真是个可爱的家伙。
章鱼要用章鱼罐来捉。章鱼的脚牢牢扒住罐底,向上翻着眼珠,就是不出来。你看,等你(跟罐子一起)被捞到船上你还不是得出来,快点出来吧。就是不出来吗?不管我怎么说它就是不出来。我咚咚咚敲了敲罐底,它还跟我撒起娇来。我也没辙了,只好拿鱼捞网的手柄捅了捅它的屁股,哎呀,出来了,好家伙跑得真快,八只脚交替而行,一点儿都不会打结,跑得真带劲。我也不甘示弱,船翻了也不怕,拼命地追,总算把它装进篮子里,继续航行。它又从篮子里爬了出来,正襟危坐在篮子顶端。你瞧,你已经上了我们家的船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别斜着眼睛瞄我耍小性子。
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吃的鱼或是海里的其他物产。那时的日子真好。
船,已经卖了(26)[日]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 わが水俣病』,东京:讲谈社,2004年,第154-155页。。
通过他们的口述,我们可以窥见水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日本人与自然共生的思想根植于万物皆有灵的原始信仰(27)[日]鹤见和子:『内发的发展论の展开』,东京:筑摩书房,1996年,第188页。,古代日本人从森罗万象的自然中感受到巨大的力量,相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中均宿有灵魂,将自然作为崇拜的对象。这种信仰的背后隐藏着日本人对于自然的双重情感,即对自然的喜爱之情和敬畏之意。水俣人曾经拥有的美好的日常生活里,充满着这种信仰与情感。他们与大海极为亲近,享受着自然的馈赠,却深感自身的渺小,心怀感恩之情,只取“一日所需渡过该日”。他们与乌贼、章鱼追逐嬉闹,用传统的章鱼罐(28)章鱼的身体没有保护壳,除捕食时会来到沙地外,其余时间多躲在岩石里。利用章鱼的这一习性将章鱼罐置于沙石中,章鱼会将其作为藏身之所,一旦进入罐中便很少会再逃走。比起常见的撒网捕捞来说,章鱼罐的捕捉方式效率较低,但不会造成章鱼身体受损。方式来捕捉章鱼,虽缺乏效率却在不知不觉间维护了生态的平衡。从水俣人这种与现代“格格不入”的行为中,石牟礼感受到了智慧的光芒。她说:“看上去没什么学问的他们,却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天地之真理、生活之伦理的方式。他们向日月水土问询,用五官来解读,不依赖书本,而通过日常生活来领会。”(29)[日]石牟礼道子:「乳の潮」,色川大吉:『水俣の启示·下』,东京:筑摩书房,1983年,第342页。《苦海净土》中的人们在经营日常生活时获得了生态身份认同,而石牟礼则从这些前辈那里学到了与土地亲密相处的方式(30)[日]结城正美:「<庶民の文化>とエコロジカ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生田省悟:『「场所」の诗学』,东京:藤原书店,2008年,第44页。,完成了自我生态身份认同的建构。
水俣病不仅威胁着普普通通的水俣人的健康和生命,还使他们平凡和谐的日常生活灰飞烟灭。如上文所述,《苦海净土》是一部通过“道子体”描绘的半纪实小说,对于作品中所描绘的平民的日常点滴,我们需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把握:一方面,石牟礼道子与柳田国男等民俗学者有着相同的平民视角,她是日本文学史上首位清晰地刻画了平民经验世界的作家,但与柳田等人从外部进行研究不同,同为水俣人的石牟礼着重从内部进行书写,通过她的作品,“被描绘成能够从外部加以观察的平民世界(world)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转变成生动鲜活的真实世界(cosmos)”(31)[日]渡边京二:「石牟礼道子の时空」,石牟礼道子:『不知火——石牟礼道子のコスモロジー』,东京:藤原书店,2004年,第181页。。石牟礼深谙水俣的地域文化,所以她勾勒出的生活场景颇具真实感。另一方面,这些生活场景也存在虚构的成分,因为“只有从现代制度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从内部描绘平民的世界”(32)[日]结城正美:「<庶民の文化>とエコロジカ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生田省悟:『「场所」の诗学』,东京:藤原书店,2008年,第49页。。虚构的世界属于那些无声的人们,是作者对抗现实世界的武器。
可以说,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平民是被边缘化的他者,为平民而歌,是要向世人展示被现代文明夺去的人与自然亲缘的关系,并重塑被知识暴力排挤了的价值观。石牟礼构建生态身份认同的过程实质也是展现平民文化生活的过程,而“对于平民文化的关注,是实现当下所倡导的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具体化路径之一”(33)[日]结城正美:「<庶民の文化>とエコロジカ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生田省悟:『「场所」の诗学』,东京:藤原书店,2008年,第54页。。
四、患者的当事人主权意识
水俣病是经济至上主义的恶果,是人类史上首例因环境污染物进入食物链而引发的疾病。患者的中枢及末梢神经受到水银的侵蚀,出现四肢麻痹、精神迟钝、视力衰退、口齿不清等症状,严重者会痉挛抽搐、神经失常、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然而更为悲惨的是,被贴上“水俣病患者”标签的他们,遭受着社会上的种种歧视,隐忍着种种不公。如书中所描述的,“我又不想得这种怪病,为什么好像特殊展览品那般被大家嫌弃?被指指点点地说怪病、怪病的”(34)[日]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 わが水俣病』,东京:讲谈社,2004年,第164页。,“大学医院的医学系好恐怖,放着巨大的砧板,用来摆弄人的砧板”(35)[日]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 わが水俣病』,东京:讲谈社,2004年,第180页。,等等。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当时水俣病患者普遍面临的状况,所以水俣病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苦海净土》中石牟礼对这些“无声”的水俣病患者进行了当事人主权意识的建构。“当事人”这一概念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残疾人自立生活运动中。残疾人无法独立完成吃喝拉撒、外出、与人交流等行为,需要向他人寻求帮助,这使得残疾人本人的意愿有可能被家人、医生、志愿者等操控或者扼杀。21世纪以来,当事人的内涵不断扩展,残疾人、女性、老年人、孩子、病患等被剥夺了自主意志的社会弱势人群开始发声,力图改变社会中的不合理。当事人主权以人格的尊严为基础,原本使用于国家间的“主权”一词在这里表示对自己的身体及精神所拥有的不可侵犯的自我统治权、决定权,当事人主权表明了这样一种立场:我是我的主权者,不允许除我以外的任何人——国家、家人、专业人士等替我决定我是谁、我的需求是什么(36)[日]中西正司、上野千鹤子:『当事者主权』,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第3-4页。。在《苦海净土》中,我们可以看到水俣病患者与医生、社会间的矛盾冲突,他们的当事人主权意识通过“道子体”跃然纸上。
当父亲、姐姐及身边熟知的人接连住院却客死院中后,山中九平拒绝入院。
“我不去,会被杀死的。”
“被杀?说什么呢,没那回事儿。是熊本大学赫赫有名的医生来给你看病,不会有事的。叔叔陪着你,不怕。”
“我不去。去了就被杀了。”(37)[日]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 わが水俣病』,东京:讲谈社,2004年,第31-32页。
山中九平的言语间充满着对医生、医院的不信任,他认为去医院将面临被杀死的结局,而远离医院反而可以摆脱被杀的命运。
仙助老人也同样拒绝去医院,甚至不愿被当成水俣病人,他说:“说什么呢?什么水俣病?我祖上世世代代都没听说过这种病。……俺可不想去医生那儿丢脸。”(38)[日]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 わが水俣病』,东京:讲谈社,2004年,第67页。
山中九平及仙助老人的反抗,体现出“我的需求我最清楚,所以我的事情由我决定”这一当事人主权的核心内容,旨在对抗社会上蔓延着的“你的事情我最清楚,我来帮你做出最佳决定”的专业人士至上的观念,而读者也跟随着当事人的话语,不断反思怎么做对于患者来说才是最好的。
对于患者当事人主权意识的建构还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提出,“人通过自我定义才能成为当事人”(39)[日]中西正司、上野千鹤子:『当事者主权』,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第196页。,也就是说,并非只要是水俣病患者就是当事人,只有当其意识到身为水俣病患者所直面的问题,并将其作为自身的问题看待,才能够“成为当事人”。在《苦海净土》创作初期的1959年,罪魁祸首的日本窒素公司与水俣病患者互助会之间签订了极其不平等的《赔偿金协议》,窒素公司只赔偿死者30万日元,丧事费用2万日元,支付健在的患者每年10万日元,未成年人3万日元,并附加了“今后即便知晓病因是工厂废水也不再追加赔偿”这一霸王条款(40)[日]金井景子:「『偿い』を问う—水俣病と石牟礼道子『苦海净土』の半世紀ー」,『学术研究(国语·国文学编)』2010年第58号。。随着《苦海净土》创作的进行,作品愈发与患者靠近,逐渐激发起现实生活中患者对抗主流政治、揭露犯罪企业恶行的斗志。
《苦海净土》的创作是作者与患者共筑历史的过程。“田野作业中所涉及的访谈并非单纯的采访者(听众)从被采访者(讲述者)那里单方向的听取现实,而是两者在交相互动之中将现实形塑而出,即共同创造现实。田野中的民众所叙说的话语实际上是根据田野工作者的发问而作出的回复;同时,田野工作者的话语也是从被采访者的话语中被引导出的结果。在对话之中共同无意识地构建出语境,从中所展现出的现实不得不认为是具有可变性的被创造的概念。”(41)[日]菅丰:《民俗学者的田野介入与社会现实的再建构》,邢光大译,《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在创作的过程中,石牟礼道子与患者相互影响。于作者而言,她在患者的影响下顺利完成了创作,并投身于水俣病运动的社会实践中;于患者而言,他们在作者的影响下“成为当事人”,站出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在《苦海净土》出版的1969年,水俣病患者互助会将日本窒素公司告上了法庭,拉开了水俣病运动的序幕。1970年,患者和家属反对政府的补偿方案,来到窒素公司门口静坐。除“诉讼派”外,水俣病患者互助会中还诞生了“自主交涉派”,以川本辉夫为首的自主交涉派于1971年冲进窒素公司东京总部,与社长岛田贤一直接交涉。终于在1973年,熊本地方法院以有违社会秩序、社会道德为名否决了1959年的《赔偿金协议》,患者胜诉。之后,1995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水俣病最终解决方案》,并于2009年出台了《水俣病特别措施法》。“当事人运动不仅会改变当事人本身,还拥有变革社会的力量”(42)[日]中西正司、上野千鹤子:『当事者主权』,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第148页。,《苦海净土》不仅是一次文学创作,更是一次社会实践、一场与患者共同开展的社会运动。
本文重点论述的是《苦海净土》三部曲的第一部《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从副标题“我们的水俣病”,不难看出石牟礼与水俣病患者共苦共悲的决心。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她已不再是他者,而是同样成为当事人,并通过《苦海净土》的创作获得了成为当事人的正当性(legitimacy)。同时,《苦海净土》这篇檄文的出现,使水俣病开始逐渐为人所知,石牟礼的当事人意识与生态意识的交织将这曲悲歌演绎到了高潮,并对救济患者、造福水俣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结语
韦清琦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在不同的批评语境下是以不同的面目出现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批评所要解构的男权中心、西方中心、人类中心都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其堡垒。”(43)韦清琦:《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笔者赞同这一观点,《苦海净土》中石牟礼道子所展现出的女性主义意识、后殖民主义意识、当事人意识,与其生态意识具有相同的指向,均以消除逻各斯中心主义、构建和谐社会为旨归。
《苦海净土》这曲悲歌以环境公害病为出发点,完成了对该时代“无声”的人群——女性、平民、患者的主体性建构。“因为的确有感而发,才能将长期以来弱者受到欺凌所产生的各种念头付诸笔端。这不仅仅是一种怨忿,更是在对表达方式加以锤炼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普遍性相关的书写”(44)[日]池泽夏树:『池泽夏树の世界文学ワンダーランド』,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9年,第14-15页。。无论是女性特有的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还是平民日常生活中蕴含的生态智慧,抑或是水俣病患者被激发出的当事人自主意志,石牟礼的作品对弱势群体身份和文化的重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而重构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驱逐二元对立中强势的另一方,而是要打破所谓的二元对立格局,展示世界的多样性,实现不同群体的共生。《苦海净土》不仅将其被创作、被消费的社会语境中存在的现实问题鲜明地展现出来,作品本身更成为社会运动的一个篇章,成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诚然,当前社会已不再是作品中的语境,生态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当事人研究等等都已成为我们熟知的字眼。然而,随着世界格局的日新月异,我们身边也不断出现新的问题。继“9·11恐怖袭击”、“3·11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我们又遭遇新冠疫情的袭击,而日本政府更是一意孤行地主张将核废水排入大海。当我们对人类的近代文明进行反思,对日本政府的无耻行径进行批判时,可以从《苦海净土》这部作品中找到种种启示。犹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底层人能发声吗?”令人振聋发聩,《苦海净土》这首镇魂曲,至今依然时刻提醒我们不断自省生活的方式,不断关注弱势的人群。当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当无声者都能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平等地生存于这个世界时,“苦海”也就成了“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