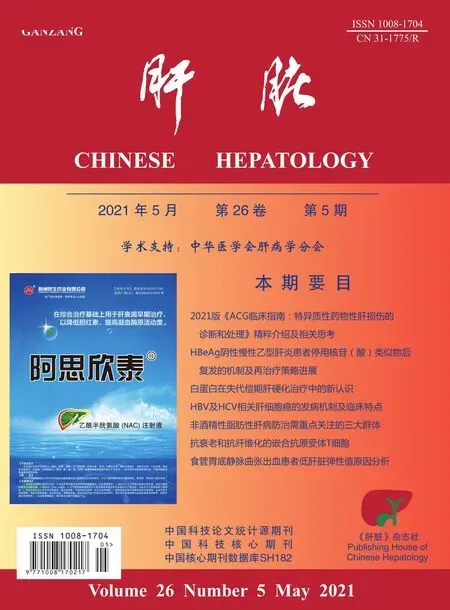HBV及HCV相关肝细胞癌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特点
王铭杰 张欣欣
乙型肝炎病毒(HBV)及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是全球范围内导致肝细胞癌(HCC)发生的主要风险因素。慢性病毒感染引发炎症及肝脏损伤,并进一步促进肝纤维化,最终导致HCC。在HCC的疾病进程中,宿主、病毒及环境因素三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在临床实践中,如何实现高危人群的早期筛查、及时抗病毒治疗及精准的抗肿瘤治疗?本文将对HBV及HCV感染相关的HCC发病机制及临床诊疗进行总结及探讨。
一、HBV及HCV相关肝癌的发病机制
慢性乙型肝炎(CHB)和慢性丙型肝炎(CHC)患者在肝癌发病机制中存在着诸多相似和不同。两者在宿主免疫应答中存在一定相似性。对于病毒感染而言,宿主免疫是一把“双刃剑”,其在控制病毒感染的同时,也发挥了促进肿瘤生长的作用。
HBV和HCV所致的肝细胞损伤大部分由宿主免疫反应介导[1]。例如在早期免疫应答中,CD8+T细胞通过直接损伤病毒感染的肝细胞并分泌干扰素和肿瘤坏死因子来抑制病毒。然而有研究证实,肝脏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也能够降低机体的抗肿瘤活性。例如,调节性T细胞、肝窦内皮细胞和肝星状细胞都能导致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2]。天然免疫在通过干扰素和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抑制病毒的同时,也会引发胞嘧啶脱氨酶家族基因表达[3]。该家族基因APOBEC3A和APOBEC3B能够降解HBV cccDNA[4]。然而,胞嘧啶脱氨酶的表达也能够促进HBV的免疫逃逸和促进肿瘤体细胞突变的产生[3]。此外,慢性炎症所导致的细胞损伤能够加速肝细胞再生[5],而肝细胞再生和氧化应激则会进一步加重细胞DNA损伤和突变累积[6]。随着宿主免疫系统的逐步激活,免疫激活期的CHB患者发生肝癌的风险要高于免疫耐受期患者[7]。HBV和HCV的组装和成熟都发生在内质网中。研究表明,大量的表面抗原(HBsAg)可在感染肝细胞的内质网中积聚,激活肝细胞的未折叠蛋白反应通路(UPR),导致DNA损伤和基因组的稳态失衡[8]。HCV RNA在内质网中的复制及病毒在内质网膜上的锚定,同样可以激活肝细胞UPR,进而导致肝纤维化和HCC[9]。
在慢性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癌的发生过程中,HBV和HCV存在诸多共同的机制和途径,但因病毒本身属性和宿主免疫反应不同又存在致癌机制的不同。HBV是一种嗜肝、部分双链的DNA病毒。HBV DNA序列可以整合到肝细胞基因组中,成为肝细胞及其祖细胞的永久组成部分,整合后可诱导基因组的不稳定性并破坏抑癌基因,从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另外,一些证据表明,HBV具有直接致癌潜力。例如,HBV感染原代细胞后,可上调参与细胞周期的宿主因子表达,包括PPARA、RXRA和CEBPB等[10]。其次,一些HBV蛋白被认为是潜在的“病毒癌蛋白/ viral oncoproteins”,可以直接驱动HCC,包括HBsAg、核心抗原(HBcAg)和X蛋白(HBx)等。HCV是一种嗜肝、正链RNA病毒,具有高度的序列异质性。作为一种RNA病毒,HCV不能整合到基因组中。然而,慢性丙型肝炎可以通过激活炎症和毒素反应途径促进肝癌的发生。HCV的基因产物(包括HCV核心蛋白、核心E1-E2、NS3和NS5蛋白等),已被证明可产生活性氧(ROS)或改变肝细胞miRNA表达,导致肝脏炎症和损伤[11]。此外,丙型肝炎还与肝脏铁沉积有关,铁沉积的增加也可促进ROS的升高和HCC的发生[12]。
二、HBV及HCV相关肝癌的临床治疗特点
临床上,适时给予病毒性肝炎患者合理的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增强病毒特异性T细胞功能,改善肝脏炎症水平,进而降低HCC发病风险[13- 14]。研究表明,CHB的抗病毒治疗可使相关肝癌的发病风险降低50%以上[15]。近年来,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的广泛应用使得CHC的有效治疗成为可能。有专家提出假说,抗HCV过程中激发的免疫炎症反应可能会攻击肿瘤,溶解肿瘤的过程反而促进了肝癌的发展进程。但后期已有研究显示,HCV清除后的全因死亡率和偶发肝癌的风险都是下降的[16]。
对于治疗前已经是进展期肝纤维化的患者,HCC风险会随时间而继续增加,因此需要进行密切监测,规范的随访有助于HCC的早期诊断。美国肝病学会指南建议有肝癌高发病风险的患者,每6个月需进行一次肝脏超声检查和(或)甲胎蛋白水平检测[7,17]。是否发生肝硬化,是判断肝癌发病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在肝硬化患者中,肝癌风险每年增加3%~8%。AASLD指南建议,对于亚裔和黑人男性的HBV感染者,应从40岁开始进行肝癌筛查,女性患者筛查从50岁开始[17]。
除外抗病毒治疗,其他临床药物包括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对于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癌也具有明确的预防和(或)治疗作用。研究发现,服用阿司匹林可显著降低CHB或CHC患者发生肝细胞癌的风险[18]。可能的机制是阿司匹林抑制肝脏中的致病性血小板聚集[19],具体机制需要更多的研究证实。阻断免疫调节途径或免疫检查点可以安全、有效地重新激活免疫系统对特定类型肿瘤的杀伤作用[20]。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作为一种抑制受体,在多种免疫细胞表面均有表达。研究显示,无论是病毒源性(HBV、HCV)还是非病毒源性的肝细胞癌,阻断PD-1药物的治疗有效率为15%~20%[21]。这些药物在阻断PD-1途径的过程中可激活抗病毒相关的免疫反应并诱导肝细胞损伤。例如,在一些HBeAg阴性的CHB和CHC患者中,PD-1阻断后会出现ALT升高[2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抑制剂可以抑制肿瘤血管生成,是常用的抗肿瘤药物之一。最新的一项III期临床试验显示,与索拉非尼相比,联合使用VEGF抑制剂和PD-1阻断方案,可使病毒性肝炎相关HCC患者的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率显著提高[23]。但需要注意的是,两个治疗组中有超过50%的患者出现3级或4级的不良反应,这表明在进行肝细胞癌的治疗前,需要充分评估患者的肝功能储备,并通过抗病毒治疗减少病毒因素诱发的肝脏负担。
综上所述,病毒、宿主和外界因素都是影响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癌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临床上肝硬化患者诊断不难,但具体要采取哪些措施来预防肝硬化患者发展为肝癌,仍是临床医生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其次,肝癌的发生虽然是由多种基因突变共同促成,但目前还不清楚具体是哪个关键位点的突变不可逆转地导致肝癌的发生。
对于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癌诊疗的研究,除了抗病毒药物治疗外,未来的治疗方案可以考虑针对早期癌症的驱动基因或逆转肝纤维化等方面。肿瘤细胞的基因筛选可以将基因改变与肿瘤发生、药物敏感性等重要表型关联起来,更好地促进治疗方案的选择和优化。因此,通过肝癌动物模型及人类癌症数据库结合的方式筛选肝癌驱动基因,可实现靶向基因筛选和治疗的目的。此外,临床风险预测模型将成为未来肿瘤研究的重要领域,大规模的GWAS和多组学研究,将有助于发现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癌高发病风险的基因位点及生物标记物,极大提高早期肝癌的诊断效能,使更多的患者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