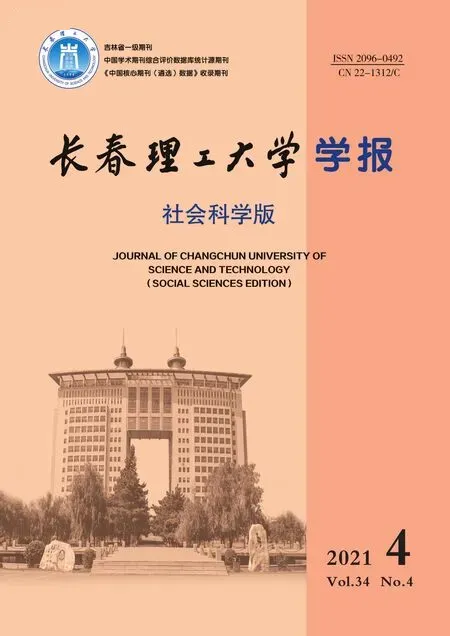认知语法视角下《葬花吟》英译研究
曾 妍,钱建成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一、引言
《红楼梦》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是明清小说中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红楼梦》创作令世人赞叹的一大特色是它的诗化魅力。[1]作者以诗为文,以诗人的眼光、诗歌审美观,甚至是诗歌创作思维完成这部小说。[2]诗歌的使用和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整个故事情节的联系都非常密切。一首诗歌常常会与一个人物的命运发展密切相关,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3]由此看来,诗歌在《红楼梦》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葬花吟》是《红楼梦》诗歌中的杰出代表,是其中为数不多的长篇诗歌。从体裁上讲,是七言歌行;从题材上看,则属于落花诗。[4]它勾画出林黛玉纷繁复杂的精神世界,奏响了她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曹雪芹以它塑造林黛玉这一艺术形象,并表现其性格特征,为探讨曹雪芹笔下宝黛悲剧提供了重要线索。[5]因此,《葬花吟》对于整体把握、深入解读《红楼梦》,尤其是把握宝黛悲剧这一主线,理解林黛玉的身世遭遇与内心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红楼梦》作为我国浩瀚文学作品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受到国内外文学爱好者的广泛关注,更有许多学者、译者竭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这部凝聚作者无数血泪的优秀文学作品。迄今,《红楼梦》已有三个全英译本:邦译本(英国传教士Bramwell Seaton Bonsall翻译的“The Red Chamber Dream”,于20世纪50年代末完成,但出版之际因企鹅出版社发布霍克斯的翻译计划而未能真正面世)、霍译本(由英国汉学家、牛津大学讲座教授霍克斯与其女婿闵福德合译的TheStoryoftheStone,由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出版)和杨译本(由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和其英籍夫人戴乃迭合译的ADreamofRedMansions,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全译本结构完整、前后连贯,选择全译本的《葬花吟》英译进行对比研究更具有信服力,因此本研究将选取《葬花吟》霍译本和杨译本为语料进行分析。
二、文献综述
《葬花吟》英译对比研究主要可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为基于翻译理论的译本比读,涉及的翻译理论有“三美”(形美、音美和意美)理论[5]、生态翻译学[6]等;第二大类为基于语言学理论的译本比读,涉及系统功能语法[7]、对比语言学理论[8]、认知语义学[9];第三大类研究借鉴文学理论,如从叙事学角度进行译本比较研究[10]等。
Pym认为,“基于文学理论和基于语言学的描述性研究方法遭受批评,因其过分关注文本和系统而非人们及其行为”[11]。以前《葬花吟》英译对比多囿于对文本的解释性研究,较少依据文本考察译者的认知状态。刘云虹和许钧指出,“一处看似简单的习语翻译涵盖了翻译理论、文本意义、风格、形象等与翻译行为密切相关的内容,其中折射出的是文学翻译的诗学特征,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立场与选择”[12]。文本能够反映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立场与选择,上述文献也大都能从文本回归到译者本身,但是关注力度欠缺。以刘肖杉为例,作者完成对《葬花吟》形、音、意三美的对比赏析后,总结为霍氏的“变通”和杨氏的“直译”。[5]这是作者综观霍、杨译本后对译者立场与选择的整体概括,但译者的认知状态和认知行为贯穿整个翻译过程并实时发生改变,概括性的总结与翻译过程的连续性不对等,因此并不足够涵盖并清晰阐释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认知状态与认知行为。
“近年来,随着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和认知文体学的发展,为考察和透视翻译文本中体现的主体的认知状态和认知策略提供了可能。”[13]认知语法恰似一把利刃,其视域下的识解维度能够帮助我们实时追踪译者的认知状态和认知策略。此前已有认知语法应用于翻译研究的案例:谭业升基于认知文体分析框架,对《红楼梦》霍、杨译本展开批评性的描述和解释[13];乔小六从语义框架、焦点与背景、详略度、视角、象似性等五个维度分析《红楼梦》第一回四个英文译本[14];ElżbietaTabakowska从详略度、射体-界标和视角三个识解维度分析Emily Dickinson 所作的一首英文短诗(迪金森 328)[15]。由于文本是译者认知结果的直接呈现,因此我们可以借助认知语法的识解维度追溯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认知状态和认知行为。
本文拟以详略度、突显和视角三个识解维度考察《葬花吟》霍、杨译本,旨在回答三个研究问题:(1)《葬花吟》霍、杨译本在三个识解维度上有何不同?(2)《葬花吟》霍、杨译本在三个识解维度上所表现出的差异体现了译者翻译过程中怎样的认知状态与认知行为?(3)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认知状态与认知行为反映了译者怎样的翻译风格?
值得指出的是,张军平也探讨了《葬花吟》英译本的视角转换[10],但其关注的是英译本整体人称视角的变换,而认知语法视域下的视角识解维度涵盖范围更广,“包括时间、认识、文化语境和空间位置”[16],可用于解释《葬花吟》英译本中更为细微的视角变换。
三、理论介绍
认知语法模型认为,语言并非独立存在的体系,在不涉及必要认知处理的情况下无法被描述。语法结构无法构成独立的形式体系,也无法构建独立的表征层次:语法结构本质上具有符号性,为概念内容的架构和规约符号化提供支持。词汇、词形和句法共同构成符号单位的连续统一,分析语法单位时不考察其语义值就如同编写字典时删除词条意义一样,毫无意义。[17]所以,“意义和语言形式有着固有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14]。
意义并非存在于客观真实中,而是存在于认知处理中。[18]语言表述的意义并非只有其形式激发的概念内容,识解概念内容的方式也同样重要。[19]因此,即使描述同一客观情景的表述也会存在意义上的差别,这取决于识解这一客观情景的方式。[18]Langacker借用视觉隐喻阐释概念,认为概念内容是所观察的情景,识解是观察这一情景的特定方式。在观察某一情景的过程中,我们实际看到的取决于我们观察的仔细程度、我们关注的对象和我们进行观察的位置等等[19]55,分别对应下文的详略度、突显和视角。
详略度指的是对于描绘的情景所能达到的精确性和细节化程度。[19]55人类在认知过程中,面对同一个情景或事体,可以从不同精确程度和详略程度来认识和描述,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识解。[14]如描述温度时,人们可以说“凉爽”,也可以选用其他详略度依次升高的表述:“十几度”“18度”“18.5度”。高度具体的表述在描绘某一特定的情景时非常详尽,具有高分辨率,而详略度低的表述会使我们受限于粗泛的描述,其低分辨率只能展现大致特征和整体结构。[19]55
突显指的是语言结构中呈现出的多种不对称性。[19]66描述一种关系时,其组成成分得到不同程度的突显。最突显的组成成分被称为射体(trajector),是被定位、评价和描述的识解实体。射体给读者的印象是这场关系中最受关注的焦点。一些其他的组成成分经常作为次焦点被突显,即界标(landmark)。具有相同概念内容、描述相同关系的语言表述会因射体/界标选择上的差异导致意义上的差异。[19]70如下例,由于问句已经将“lamp”设定为需要定位的对象,所以只有选择将“lamp”作为射体,即(i),才是恰如其分的回答。
(1)(a)Where is the lamp?
(i)The lamp(trajector)is above the table(land⁃mark).
(ii)*The table(trajector) is below the lamp(landmark).[19]71
视角对于空间描述至关重要,并且视角依赖于说话人的相对位置和观测点。但是视角也存在于非空间域中,即我们所持视角基于我们的知识、信仰、态度和时空位置。最接近于视角的认知特质可能是哲学概念——“情景性”,即我们存在于世界的某一位置,这一位置在识解意义上具有非常广泛的范围,包括时间、认识、文化语境和空间位置。[16]体现视角的语言形式包括语义反义(如behind/in front of或under/above)、人称代词或指示代词、语法时态以及能体现认识转换的词汇等。[15]如下例,(a)中体现的是说话者的视角,(b)中体现的是外部观察者的视角,(c)中体现的是思考者的认识视角。
(2)(a)A bird came down the walk.
(b)A bird approached the poet.
(c)A bird inspired the poet.[15]
四、霍译本和杨译本对比分析
《葬花吟》共52个短句,下文在认知语法关照下,从详略度、突显和视角三个识解维度对两个版本的译文进行分析。
(一)详略度
原诗(句序5):闺中女儿惜春暮,
霍译:The Maid,grieved by these signs of spring’s decease,
杨译:A girl in her chamber mourns the passing of spring,
原诗(句序6):愁绪满怀无释处,
霍译:Seeking some means her sorrow to express,
杨译:No relief from anxiety her poor heart knows;
此例中,霍译描述“闺中女儿”因何愁苦的详略度高于杨译,而杨译描绘“闺中女儿”愁苦程度的详略度高于霍译。霍译相较杨译在描述愁苦原因时多加了“these signs”用于指代上文落花与落絮等意象,这反映出英文重形合的特点,霍克斯作为英语国家的译者,将这一点诠释得很好。霍译紧接着用一个现在分词短语做伴随状语——正是因为需要排遣忧愁,所以才有接下来“Has rake in hand into the garden gone”的结果——逻辑关系通过语言形式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说明霍译注重目标语读者的需求。但是霍译只提到需要找寻方式排遣忧愁,读者又如何知道忧愁的深浅程度呢?因此其描绘愁苦程度的详略度不如杨译忠实于原诗的表述:“闺中女儿”的愁苦已经到了无法排遣的程度。杨译忠实于原诗的表述也更符合原诗后续发展:直到最后主人公也未能通过葬花这一行为排忧解愁,反而是愁上加愁愁更愁。
原诗(句序13):三月香巢已垒成,
霍译:This spring the heartless swallow built his nest
杨译:By the third month the scented nests are built,
原诗(句序14):梁间燕子太无情!
霍译:Beneath the eaves of mud with flowers com⁃pressed.
杨译:But the swallows on the beam are heartless all;
此例中,霍译描述燕子“香巢”的详略度高于杨译。值得注意的是霍译和杨译均选择了定冠词特指燕子,“在英语这样的语言中,认识视角大多可以通过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对比体现”[15],这表明两位译者均认为燕子对于女主人公来说是熟知的事物,但二者在单复数形式选择上又有不同,霍译选择单数形式,而杨译选择复数形式,这也决定了二者描述“香巢”的详略度有所不同。当镜头拉近对准一只燕子时,燕子巢穴的位置与构成材料自然能清晰地一览无遗。而当镜头拉远对准一群燕子时,观测者便只能看到巢穴的轮廓。那么两位译者的译文为何会呈现如此差异呢?笔者猜测,霍译是为了借用形单影只的燕子呼应女主人公的孤凄悲凉,而杨译则是为了突出所有燕子对花的无情抛弃,对应下句物是人非的苍凉。
(二)突显
原诗(句序1):花谢花飞花满天,
霍译:The blossoms fade and falling fill the air,
杨译:As blossoms fade and fly across the sky,
原诗(句序2):红消香断有谁怜?
霍译:Of fragrance and bright hues bereft and bare.
杨译:Who pities the faded red,the scent that has been?
此例中,霍译和杨译在第二句的射体/界标选择上均与原诗不同。人在感知世界时最优先的感官应当为视觉感官,加之前句“花谢花飞花满天”是视觉景象,为使前后更为连贯,所以原诗将“红消”放置在第二句句首作为射体。与颜色凋零的视觉冲击相比,嗅觉上的“香断”感知并没有那么迅速,因此作为界标。霍译为了押头韵(bright-bereftbare),调换了“红消”与“香断”的顺序,也因此改变了二者的突显程度,破坏了与前句的连贯,略显突兀。杨译虽通过将“红消”置于“香断”前赋予“红消”更高的突显程度,但“红消”与“香断”在第二句中均为界标,作射体“Who”的陪衬。杨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译者认为此句虽表面写景,但实际突出的是观景之人,观景之人的心境融于所观之景,伤景即是观景之人的伤情。
原诗(句序49):试看春残花渐落,
霍译:As petals drop and spring begins to fail,
杨译:See,when spring draws to a close and flow⁃ers fall,
原诗(句序50):便是红颜老死时。
霍译:The bloom of youth,too,sickens and turns pale.
杨译:This is the season when beauty must ebb and fade;
原诗(句序51):一朝春尽红颜老,
霍译:One day,when spring has gone and youth has fled.
杨译:The day that spring takes wing and beauty fades
原诗(句序52):花落人亡两不知!
霍译:The Maiden and the flowers will both be dead.
杨译:Who will care for the fallen blossom or dead maid?
此例中,霍译对“红颜”和“人亡”的突显强于杨译。这四句诗是主题凸现和情感抒发的关键,诗人借落花、残春自喻,表现了“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奈与痛苦,充满了悲剧色彩”[4]。原诗第49和50句中三个意象的先后描写顺序为“春”“花”“红颜”,杨译的排列顺序忠实于原文,霍译的排列顺序则为“花”“春”“红颜”(排列顺序是前后两句押尾韵的结果),花落是春残的原型表征,而红颜老去,逝去的青春就如留不住的春天一样,霍译的排列更具层级性,更能体现出“红颜”作为射体的突显程度。52句中,霍译调换了原文“花落”和“人亡”的位置,将“人亡”放置句首作为射体,这虽然失去了与前句“春尽”和“红颜老”的呼应关系,但也表现出译者突出主题的强烈意愿,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译者对于女主人公悲惨命运的同情。
此外,中文重意合,因此原诗描写对象的排列顺序并不会过多地影响读者对其主题的理解,而英文则不同,语言形式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读者对于诗歌的解读,加之目标语读者不熟悉此类借物喻人的手法,所以有时需要译者更为直接、清晰地传达原诗所表现的主题与情感。
(三)视角
原诗(句序11):桃李明年能再发,
霍 译 :Next year,when peach and plum-tree bloom again,
杨译:Next year the peach and plum will bloom again,
原诗(句序12):明年闺中知有谁?
霍译:Which of your sweet companions will re⁃main?
杨译:But her chamber may stand empty on that day.
此例中,霍译选择了参与者视角,而杨译选择了旁观视角。通过采用第二人称称呼女主人公,霍译自然而然地引入了一个参与者,他似乎就站在女主人公身侧,感受着同样的景象,观景之余与女主人公直接对话,一个看似不经意的问句直戳女主人公内心,道尽无数悲凉。杨译采用第三人称,变原诗问句为陈述句,似一个冷眼旁观的看客,冷静地陈述明年春季必会出现的场景,即“桃李再发”,冷漠地预测明年“闺阁已空”的悲凉,这恰恰营造了一种孤凄的氛围,使读者的视觉范围中只有形单影只的女主人公和她未来的凄凉结局。霍译借参与者之口旨在主动、直接地描述原诗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而杨译看似冷漠无情的客观叙述却也暗含深深的无可奈何与凄凉。
原诗(句序28):冷雨敲窗被未温。
霍译:While a chill rain against the window falls.
杨译:Cold rain pelts the casement and her quilt is chill.
原诗(句序29):怪奴底事倍伤神?
霍译:I know not why my heart’s so strangely sad,
杨译:What causes my two-fold anguish?
原诗(句序30):半为怜春半恼春:
霍译:Half grieving for the spring and yet half glad:
杨译:Love for spring and resentment of spring;
此例中,霍译和杨译均意识到原诗从观察到反思的视角转换,也均在译文中体现了这一视角转换,但霍译的视角转换似乎更为明显。从前句对周围环境的描述过渡到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杨译选择了与原诗相同的自问自答形式——寂静冰冷的夜晚,女主人公独自蜷缩在被窝里,忽略周围的一切,只安安静静地同自己对话,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完成了外部世界到内心世界的视角转换。霍译直接选用陈述句,以“I know not”这一表述清晰地划定了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界限,直接明白地告诉读者到此已经进入了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杨译的自问自答固然也能体现视角的转变,但此种情况下的现实世界与内心世界毕竟会有部分穿插重叠,相比之下不及霍译清晰明了。这也再次表明霍译更加注重语言形式对于诗词的阐释。
五、结语
本研究以认知语法为视角,从详略度、突显和视角三个识解维度对比《葬花吟》霍、杨译本,发现霍译和杨译体现了不同的识解方式,总体上霍译更注重目标语读者的需求,而杨译更忠实于原文。
霍译在详略度的识解操作中反映了霍克斯作为英语国家的译者对于语言形式的重视;在突显的识解操作中反映了其注重体现诗歌的音韵美与彰显原诗借物喻人的手法;在视角的识解操作中反映了其重视直接向目标语读者传达原诗意境。
杨译虽也体现了自己的理解与考虑,但其更注重保持原诗风貌,相对霍译变动较少,而且大部分变动基于诗歌留白。“诗人可以在每一行中留下空白,等待读者填补或将其具体化。译者有时正是利用这一空间进行阐释,在将原文中的空白具体化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理解赋予译文的表现形式。”[10]所以总体上忠实于原文的杨译也会在诗歌留白的空间内展现自己的理解,如“梁间燕子太无情!”一句中“燕子”采用的复数形式与“红消香断有谁怜?”一句中对“Who”的突显。
综上,笔者认为,霍译像酒,入口即热烈,译者通过自己的理解,将原文的意境直接明白地呈现给读者;而杨译像茶,入口平淡,杨译对原文的忠实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翻译过程中意境的损耗,但是需要读者细细品味,才能在平淡之后品出原作独有的清香。
——以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为例
——以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