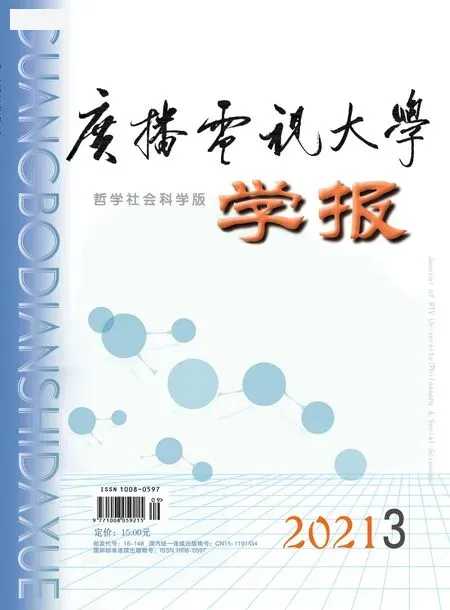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的乌兰牧骑精神传播
——基于《红色文艺轻骑兵》叙事特征的分析
乌琼芳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1957年6月17日,第一支乌兰牧骑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从此,中国内蒙古大草原上,红色文艺轻骑兵的旗帜就一直在飘扬着。2018年初,作家阿勒得尔图在行程几万里、采访几十只乌兰牧骑近百名乌兰牧骑新老队员之后,完成了报告文学《红色文艺轻骑兵》,发表于2019年第2期《人民文学》“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选作品”专栏,把60年的历史浓缩在纸面上。基于扎实的采访,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都是富有独特性的个体和更具乌兰牧骑精神共性的群体。作品的叙事特征让阅读者与《红色文艺轻骑兵》的情感互动、认知互动在人性闪光点上、环境特殊性中、具体历史情境里不知不觉生成。本文就《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的叙事特征进行分析,以阐释该作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为乌兰牧骑精神传播所做的贡献。
一、内在逻辑故事化,让国家意志更见温情
“民族大团结”“民族大家庭”的民族政策理念是中国共产党100年来一以贯之的。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内蒙古自治区,1956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甘肃省的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地区最终完成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任务,“结束了三百多年来内蒙古民族被分割的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辉煌胜利。”[1]“周总理说,恢复内蒙古原有区划,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内蒙古和内蒙古人民的关怀。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的统一,要按照‘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积极推进。”国家让更多蒙古族合于地域,更要让内蒙古人民暖在心里,“周总理对乌兰夫说,建立一支相应的队伍,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丰富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周总理强调,要进一步探索适应广大牧区分散生活的文化活动形式。”[2]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乌兰牧骑成立了,这也注定了乌兰牧骑的使命及使命的实现方式必然有国家的高度、生活的深度和草原的广度。文中的一个小故事,就已经体现出来这三个维度了:在草原深处,六十多岁浩日勒老人生平第一次看演出,晚上两位演员睡在她的蒙古包里:
她借着微弱的灯光,颤颤巍巍地走到蒙古包的西北角,打开箱子,拿出一块月饼和一把红枣。月饼和红枣几近风干,这是老额吉的全部珍藏。老额吉把珍藏拿出来,有如把一颗滚烫的心捧在她俩面前:“孩子,吃吧!走了一天的路、演了一晚上的节目,累啊!额吉心疼你们哪……”
精神满足之后最容易产生融在血液中的情感,乌兰牧骑队员身负国家对包括蒙古族牧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深情,国家视角的民族关怀就是少数民族视角的国家认同。
《红色文艺轻骑兵》用历史细节说明,乌兰牧骑精神也不是限域于内蒙古的。
1960年6月1日,在北京召开为期十一天的全国文教群英会,会议间隙,周总理详细听取乌兰牧骑队员的汇报后,称赞乌兰牧骑是草原上的一面红旗,并指示在场的《中国戏剧报》记者进行采访,1960年6月30日出版的《中国戏剧报》上刊发《草原上的一面红旗》,这是国家级报刊第一次报道乌兰牧骑的先进事迹,具有里程碑意义,也可以说是乌兰牧骑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观摩会演和乌兰牧骑全国巡演的前奏。
1964年,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对乌兰牧骑队员说,“中宣部肯定了乌兰牧骑是为农牧民服务的一个很好的组织形式,乌兰牧骑解决了‘为什么人服务、拿什么东西服务’的根本性问题。”乌兰牧骑队员荷花在接受作者采访的时候也说:“我们那个时候下乡,不是蜻蜓点水,不是浮光掠影,不是走马观花。让去哪儿就去哪儿,让干啥就干啥,像军人似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嘛!”
八十高龄的策仁那德米德是在额济纳旗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休的,纳森说:“不叫策主席,老人家不高兴呢!”在姑姑跟前,纳森永远是一个爱开玩笑的孩子——看起来是玩笑,却将老人内心的情感逻辑传递出来了。当年刚刚两岁的策仁那德米德跟着家人在中蒙边境放牧时,突然被全副武装的蒙古边防部队掳到蒙古境内,十六年之后才回到祖国怀抱。所以,今天老人不是在意行政职务,而是这个职务背后,有着一位颠沛流离于异国他乡又重归故里之后的老者对国家的深度认同,也许老人要紧紧握住这种只有国家才会带给她的心理安全感再也不肯放手。
1973年乌兰牧骑在“人烟稀少、文化匮乏、地处偏远”的赛汗乌力吉公社宝力格浩特演出结束后,牧民们说:“在台上你们是演员,在台下你们是社员。我们打心眼儿里喜欢你们哪!”《红色文艺轻骑兵》中类似的细节比较多,这是对现实的尊重,更是对乌兰牧骑精神的情感解读。乌兰牧骑队员“自认为是社员”那是组织行为的目标,而社员们认为乌兰牧骑队员“是社员”则是至高的评价,这种评价放在乌兰牧骑的发展历史上,就是闪烁着光芒的“初心”。使命在,初心在,今天的内蒙古,草原深处的牧民、大山深处的农民不仅仅需要参与生产的“社员”,更需要服务于生产生活的“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员,而今天的“乌兰牧骑+”正是乌兰牧骑精神的完美承传。
艺术发展逻辑的故事:凸显了乌兰牧骑家庭化承传的薪火之力以及“反观式”的创新活力。“讲故事”是《红色文艺轻骑兵》重要叙事方式,其中“乌兰牧骑家庭”的故事以极具说服力的艺术传承逻辑、精彩的细节提升了乌兰牧骑精神的传播力。
1940年春夏之交,色·普日布(前文策仁那德米德的哥哥)一家在中蒙边境放牧时,突然被全副武装的蒙古边防部队掳到蒙古境内,没有任何理由,事先也没有任何征兆。……在远离祖国与故土,举目无亲的境况下,色·普日布一家开始颠沛流离的苦难时光。……色·普日布在做零工、打松子、挖芒硝中渐渐长大,也渐渐显露出吹拉弹唱的艺术天赋。一九五三年……色·普日布就被招聘到地方政府的文化机构,从事群众文化辅导工作。……他用长调苍凉而悲怆的拖音、颤音、滑音来抒发内心的情感。
一九五六年九月,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和蒙古国的多次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在蒙古高原颠沛流离十五年的三十户、一百零五人,终于能够回到祖国怀抱了。
阿拉善旗委宣传部领导召见这位归来的游子并委以重任,让他负责和组建阿拉善旗乌兰牧骑,色·普日布的艺术天赋得以拥有发挥的广阔空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茫茫的戈壁上没有铁路也很少有公路,交通极为不便。色·普日布骑着一峰红驼,穿行在沙漠与戈壁之间,大海捞针般地寻找着能歌善舞者。
同样的艺术载体,在中国可以跨越万水千山踏实地进行精神的融合,但跨出一线国界虽有相同的艺术却是孤独的、无法兼容的,所以流浪于蒙古国时色·普日布只能是以蒙古族长调寄情,回到祖国之后却是充满了艺术创作激情。色·普日布兄妹两人都成了乌兰牧骑队员,“从舞蹈演员、舞蹈编导到副队长、队长,一路走来,我心中的榜样和楷模就是普日布老师。”现任额济纳旗乌兰牧骑队长雷东香如是说。娜仁图雅和她的八个孩子各有长项,都是乌兰牧骑队员,他们的“家庭乌兰牧骑方阵”曾一度成为内蒙古春晚电视观众心中的一道音乐风景线。乌兰牧骑队员爱敏那的父亲哈斯巴根和母亲萨仁高娃都是西乌珠穆沁旗乌兰牧骑队员,他是在乌兰牧骑大院里长大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乌兰牧骑的孩子”。因为生在“乌兰牧骑之家”,爱敏那对乌兰牧骑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父母的言传身教、情感启蒙,家庭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为乌兰牧骑艺术的传承、精神的发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红色文艺轻骑兵》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乌兰牧骑精神的家庭故事,还讲述了更多的创新故事,在更深层次挖掘并呈现了乌兰牧骑的艺术发展逻辑。巴林草原“舞神”巴达玛在1975年“临危受命担任了巴林右旗乌兰牧骑的第七任队长,他明白使乌兰牧骑焕发生命力尤为重要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面对下乡知识青年的拒绝,他最终用精神动力和艺术魅力共同促生了他们的内生动力,扩大了乌兰牧骑队伍,在人才选拔、人才引进、队伍传承等方面将发展逻辑言明,发展逻辑支撑的是乌兰牧骑生命力的持续性。而在2003年,锡林郭勒乌兰牧骑队长孟玉珍启动关于三千孤儿的舞剧《草原的记忆》的创作,承担剧本创作的是国家一级编剧王晓岭,导演为获第五届中国艺术节文化导演奖的国家一级编导邓锐斌,他们以“反观视角”从更深层次理解蒙古族音乐,反倒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诸多蒙古族元素。从草原戏台到剧院舞台,从偏重白描化生活的再现到融进生活血液般的艺术表演,贯穿始终的是生长在国之沃土中的蒙古族文化。
二、内在精神符号化,让民族味道更浓厚
从叙事特征的角度看,将内在的乌兰牧骑精神进行外在的“符号化”表达,是显而易见的。所谓符号,就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3],而符号化——可以是文字式的,也可以是情境式的——则是被感知的意义有着公认的客观所指,且所指是唯一的,就像茫茫草原上一支举着印有蒙汉双语“乌兰牧骑”字样红旗的队伍,所指的就是红色文艺轻骑兵,不用言说,只要看到这支队伍呈现的情境,且有着相应的认知框架,就不会出现认知偏移的情况。
写出民族符号里的家国情怀。乌兰牧骑是一支文艺轻骑兵队伍,其内含的精神传承至今并将被继续发扬,首先应该被强调的是国家的意义,《红色文艺轻骑兵》正是传递出了这一重要价值所在。
“好来宝”这三个字已经是蒙古族传统艺术形式的符号之一了,是大约形成于公元十二世纪前后的蒙古族曲艺形式,200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就意味着这种艺术形式在国家的保护之下,传承会有更大的推动力量。在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之后,队员瓦·钢宝力道便创作了好来宝《乘爱起航》,表达队员们的心情——显然基于被国家关怀的蒙古族民众的情感已然熔铸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可谓是我增加你的内涵,你滋养我的根系,中华民族的情感纹理也因此更丰富多彩。而在1984年10月1日,参加国庆大典的“乌兰牧骑彩车”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以国内视角看,乌兰牧骑已经被确认为鲜明的内蒙古符号,而从国际视角看,乌兰牧骑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符号之一,她是民族的,更是国家的,才是世界的。当富有少数民族色彩的符号融入国家气质之中,生成符号的土地上的人们,会有更强的国家认同心理,会有不接受任何辩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红色文艺轻骑兵》对乌兰牧骑精神的传播价值也就水到渠成地实现了。
环境符号衬托出乌兰牧骑精神中的坚韧品质。“达赖却尔济庙和阿其图乌拉之间横亘着漫漫沙漠。走进沙漠,气温骤然升高,平时精神抖擞、仰天嘶鸣的高头大马此刻耳朵全都耷拉下来,汗如雨下”——《红色文艺轻骑兵》中多处环境描写都表现出了符号性特征,“沙漠行走”“草原驱车”“驼铃”“勒勒车”“几十里路才能碰到一座的蒙古包”,标志性元素综合成了内蒙古自然环境的符号性特征,牧民散居于草原,无论草原多深,住在其中的牧民都是党和国家要温暖到的,带着牧民熟悉的艺术形式,乌兰牧骑穿沙过草奔向牧民,而牧民牵马拉驼前来迎接,最坚韧的品质与最淳朴的深情相遇、相融。在物质贫乏的时代,精神的满足比较容易获得,但在草原深处,在沙漠腹地,骨子里热爱歌舞的蒙古族牧民,因为散居且流动生活能够与他人彼此赋力的机会太少了,获得专业水平艺术表演的审美满足、精神满足尤其非常难的,乌兰牧骑队员肩负国家使命在典型的牧民生存环境中,不因行路艰难而却步,他们抵达并奉上贴地气的表演,足以让乌兰牧骑精神中的坚韧品质赋予牧民热爱生活、热爱国家的力量了,更何况还常会遇到牧民生病无法就医,乌兰牧骑队员就策马夜行于“无路”的草原去请医生,三十多里路“一个人、一匹马行走在寂寥空旷的草原上,着实疹得慌”,直到听到狗叫才安心些——草原谚语是“有狗叫的地方一定有人家”,战胜恐惧是因为心里惦记着生病的牧民,无论什么时代,只要真的“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有坚韧的品质,乌兰牧骑精神的时代价值也在这里。
在蒙古族特色鲜明的艺术符号中写出乌兰牧骑忠于艺术的创作精神。乌兰牧骑首先是“文艺轻骑兵”,与人民群众形成沟通的首先是艺术表达。这个原创力强大的团队忠于艺术,确实是“扎根生活沃土”的。1947年两位乌兰牧骑队员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在草原深处完成了人生第一次接羔,在母羊羔羊的咩咩声中、在草原上世代相传的《劝奶歌》引导母羊给羔羊吃奶的“台古”声中,“大羊不再躲闪,小羊含住乳头。看到这情景,费宝金眼里闪烁着泪花,一支舞蹈的轮廓在脑海中形成。《接羔舞》风靡草原,草原是《接羔舞》的生活源泉和艺术源泉。”如此沉浸于生活的回馈,才让艺术创造的灵感迸发,打造出了“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艺术精品。还有基于生活中的“挤奶”劳动而创作的《欢乐的挤奶员》、因为沉浸于牧民老人聚精会神地下着蒙古象棋——莎特尔而精心打造的群舞《蒙古莎特尔》等舞蹈精品,都是源于生活的艺术进而在“舞台”上与观众形成深度共情,乌兰牧骑队员在生活与艺术的互动中滋养着艺术创作的新鲜的血液,在牧民与队员的情感共济中让乌兰牧骑扎根于生活越来越深,“枝干”越来越茂盛。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她为草原深处的牧民建立的乌兰牧骑队伍也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乌兰牧骑精神也感染了中国大地,“每个乌兰牧骑人都能够讲出许多生动的故事。但最为根本的是,乌兰牧骑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乌兰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草原文艺轻骑兵”。可以说乌兰牧骑的成立是国家领导人高屋建瓴又基建草原之举,只有这样在全局之中才会探索到更多的发展空间,才会避免因盲目而损失成长的力量、因方向偏离而损耗成长的空间。《红色文艺轻骑兵》以全景视角为读者呈现了牧民与演员的精神共济——不只是给牧民带去精神享受情感寄托,也让自己获得了净化内在精神的营养。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回信中说:“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红色文艺轻骑兵》就是在帮助读者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中,读懂乌兰牧骑队员的精彩故事,认识乌兰牧骑的红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