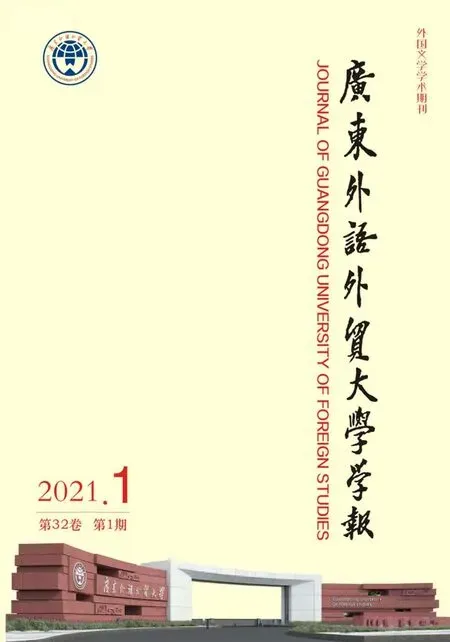俄国形式主义文学伦理学再评判
陈礼珍
引 言
俄国形式主义被视为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开端,对结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符号学等文艺思潮有直接影响。在20世纪初期,俄国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在此大的历史思潮下,文学批评界力图超越庸俗社会学,重新评估传统文学价值体系,形式主义批评应运而生。形式主义批评在整体上强调文学自律性,试图采取科学和客观的方法研究文学,将文学从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语境中抽离出来,专注于文学形式本身,反对从道德和伦理角度阐释文学作品。形式主义使文学批评的重心回归文本,对20世纪现代文论的发展演进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然而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片面强调文学形式,将文学跟现实割裂开来,否定文学的教诲功能,忽视文学和文本背后的复杂伦理规范,并未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文学意义产生的机制,也未能真正发现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形式主义的反道德批评
20世纪初形式主义、新批评的兴起使得伦理这种文本外因素被淡化而凸显文本自身的艺术价值,直至80年代,伦理因素重新得到重视(钱丽雯, 2019: 78)。要想真正把握形式主义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所在,必须还原历史现场,回到那些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形成时候的历史空间,将它们置于当时的伦理环境,唯有如此才能理解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做伦理选择的艰难情境。伊格尔顿将1917年定为文学理论进入快速繁衍变化的时间起点,标志性事件是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作为手法的艺术》(ArtasDevice)一文(Eagleton, 1996: ix)。确切而言,形式主义的真正缘起并不在此。早在1914年,什克洛夫斯基出版的小册子《词语的复活》就被视为“这个流派的第一个历史文献”(巴赫金,第二卷,1998:7:1)。1915年和1916年,雅格布森领衔的“莫斯科语言小组”与什克洛夫斯基领衔的圣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OPOJAZ)相继建立,成为推动俄国形式主义思潮兴起的两大源头。这两个学术组织之间合作密切,共同出版了三本学术论文汇编:两辑《诗性语言理论研究》与一辑《诗学:诗性语言理论研究》(Kolesnikoff, 1993:53)。“莫斯科语言小组”和“诗歌语言研究会”试图发现文学文本区别于其它语言文本的特质,进而洞察文学发展的内在机制,但是他们在诗歌的审美功能和文学艺术的自律问题上各执一端,充分展示出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异质和复杂特性。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在肇始阶段就走上了一条反对文学伦理阐释的道路,聚焦于文学的语言材料和审美维度。
俄国形式主义不同阵营对文学形式各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基本打着改革俄国历史文化学派的旗帜,将注意力放到语言和修辞之上,将文学隔绝于社会、历史、道德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之外,态度鲜明地反对将文学视为道德的容器或表达形式。形式主义思潮秉持的立场实际上是反对道德批评而且反对教诲论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初期勃兴于苏联,这个过程有着特定的历史土壤和伦理环境。什克洛夫斯基1917年发表的《作为手法的艺术》通常被视为形式主义思潮起源处的标志事件。那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二者相伴而生,应该引起深思。除什克洛夫斯基之外,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主要倡导者还有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艾亨鲍姆(Boris Eichenbaum)和托马舍夫斯基(Boris Tomashevsky)等人。在形式主义思潮诞生之初,什克洛夫斯基、雅格布森和艾亨鲍姆等人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人,他们带着叛逆和颠覆的激情对文学进行革故鼎新。“诗歌语言研究会”成员大多数都是布尔什维克。什克洛夫斯基(1997:80)曾说道,“我们是革命的制造者,革命的儿女”。《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发表以后曾多次重印,然而什克洛夫斯基都不曾对其进行修改,他给出的理由是:“并不是因为这篇文章多么正确无误,而是犹如我们之用铅笔写作,时代是用我们来写作的”(什克洛夫斯基, 1997: 83)。形式主义思潮于20世纪初出现于俄国,这是时代造就的结果。然而形式主义者的革命热情在文学领域内产生的理论思想却并不符合当时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列宁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的俄国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在苏联成立以后更成为压倒性的统治力量。
托洛茨基在1923年出版的《文学与革命》中对形式主义展开了激烈批评,正式拉开了苏联官方主流思想界批判形式主义思潮的序幕。托洛茨基从学理出发对形式主义进行批判。1924年以后,苏联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和时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布哈林等人对形式主义发起批判,卢那察尔斯基将形式主义视为逃避主义和颓废运动,他严厉驳斥形式主义者只关注文学技巧和文体而脱离政治与生活的做法,申明“真正的艺术都是意识形态的”(Erlich, 1980: 106)。1925年6月18日,俄共(布)通过《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形式主义被划归到反革命分子的行列,因而遭到大面积的批判。在当时国内政治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下,雅格布森流亡到捷克,什克洛夫斯基和艾亨鲍姆等留在国内的形式主义者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主动或被动地开始自我反省和忏悔(杨建刚,2012)。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语言学转向的大历史背景下,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以叛逆者和颠覆者的形象崛起于20世纪初的俄国思想界,创新性地提出众多批评理念和概念术语,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因为政治姿态和学术理念不容于当时苏俄当局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遭到严厉打压。“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形式主义在苏联被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形式主义’通常被当作侮辱性质的词语来称呼文学批评家、作家和艺术家”(Kolesnikoff, 1993: 57)。俄国当局对形式主义的批判持续了十多年,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国内政治形势的高压之下,形式主义思潮逐渐偃旗息鼓。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而言,以什克洛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思潮从萌发和壮大到挣扎和溃散的发展历程值得深思。形式主义各种流派在文学批评实践维度用一种反伦理的姿态演绎出一系列颇有新意的文学理论,这个流派之所以在十余年间迅速消失,不仅是迫于当时苏联特定的政治环境,它忽视伦理因素和拒绝道德评判所造成的明显理论缺憾也为自己招致众多尖锐批评,这个历史境况不得不察。
文学性与文学的伦理本质
在勘探俄国形式主义的思想渊源时,我们应当从内外两个角度考察它诞生时候的历史现场。就外部的理论脉络而言,学界普遍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是源于西方哲学美学思潮,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而在当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俄国内部的本土因素:“他们一方面同俄国文艺学学院派,同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有血肉联系,一方面剧烈反对俄国文艺学文化历史学派忽视审美特征,将文学史等同于文化史、思想史;反对革命后将文艺学等同于政治、经济,等同于生活的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程正民,2013)。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极其关注语言和文学的独立性。他们认为组成文学文本的语言文字迥异于日常生活语言,这种具有诗性的文学语言区别于其它语言的特质被称为“文学性”(literariness)。“文学性”这一重要的形式主义概念由雅格布森在1921年的“论艺术中的现实主义”(On Realism in Art)一文中提出。雅格布森以此强调文学语言的诗性功能,围绕诗性和文学性来讨论文学语言问题,引起俄国文艺界的高度关注。在形式主义理论视域下,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文学性并不能简单地从文学文本推导而来,而是文学文本类属的一种特定内涵和功能。弥尔勒认为“文学性本质上并不是文本的属性,甚至不是文本可以使用的特殊手法,而是文学系统本身的属性,是后来结构主义者用来称呼不同文本之间互文性关系的那种属性”(Milner, 2002: 99)。形式主义试图对文学性做出一个本质主义的抽象,想从万千鲜活丰富的文学文本中提炼出一种可以界定文学的独特属性。这种抽象与索绪尔对语言所做的抽象有些类似,都是将语言和文学作品视为一种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作为语言体系存在的,是共同体成员都认同的某种契约”(聂珍钊,2019)。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深受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将文学隔离于历史具体性和伦理体系之外,无法超越上升到哲学高度,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文学语言跟生活语言的真正差异。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试图从文学作品中提取出文学语言独有的“文学性”,这是一个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理论抽象行为,将文学语言视为孤立的语言文本,脱离了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历史语境和话语实践过程。批评界早已公认“文学性”这一形式主义概念过于抽象,理论内部含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在实际层面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形式主义研究仅仅关注文学的内部而完全忽视文学的外部研究,将文学视为一种独立的固化存在物,这无疑是有失偏颇的。周小仪(2003)指出,“没有一个抽象的、永恒的、客观的文学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的文学性”。文学不仅无法离开具体历史实践,作为一种话语行为和消费活动,更无法摆脱伦理环境和各种复杂的伦理关系。
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作为审美主体,他们参与的写作与阅读活动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事件,文学作品是人这个行为主体的产物,期间必然涉及意义生产、价值判断以及文学作品和世界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写作和阅读是一个言语的交往和对话过程,所有的一切都无法脱出伦理的范畴。“对文学的基本评价不仅要看文学作品是否带来快感或者审美感受,而且更要看文学作品带来的快感和审美感受是否符合社会或人类所共同遵守的伦理和道德准则”(聂珍钊,2014:103)。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的存在物,试图脱离伦理而对文学抽象出一种非伦理的永恒本质,这无异于在根源上对文学本身进行架空和釜底抽薪。形式主义聚焦于文学作品语言材料的构成形式,割裂形式和内容的有机关系,将文学隔绝于社会之外,脱离于言语交往过程和伦理之外,当然也就无法真正揭示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陌生化与审美过程的非道德评判
俄国形式主义者将“形式”上升到本体论高度,试图建构文学的自律性。如果说“文学性”是他们在为文学构建一种独立的形式精神,那么“陌生化”就是达成文学性的重要途径。什克洛夫斯基在1917年发表了《作为手法的艺术》,被称为“形式主义的宣言”(Eichenbaum, 1965:113)。什克洛夫斯基(1997:10)在文中对“陌生化”进行了详细论述:“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陌生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些,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在论述“陌生化”概念时,什克洛夫斯基强调的是人们对艺术的感知过程,奇异的艺术形式可以打破平庸语言表达方式带来的自动化效应,给审美主体带来新鲜的体验。形式主义最注重艺术成形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力,对艺术作品本身反而不甚重视。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审美和体验过程是一种鲜活生活经验和想象力的交流传递,陌生化的效果固然可以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但这只是手段方法,而不是最终目的。俄国形式主义者试图从感官和经验的渠道去把握文学,在审美范畴上,他们“对美的界定及其方法都与康德不同。它带有经验主义美学的性质,因为经验主义美学就是把审美感觉经验作为出发点,或者说从审美感觉经验上去把握美的特征和规律”(陈本益, 2003)。俄国形式主义者只谈审美体验、诗性语言和形式特质,忽略了文学是道德的产物这个事实。“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产生的目的就是源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教诲,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文学缺失了教诲功能,即伦理价值,文学的审美价值则无法存在”(聂珍钊,2013)。文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道德教诲,作为一种带有公共属性的实践行为,文学不可能只是一种单纯的精神形式,而是有着具体而丰富的伦理内涵。
什克洛夫斯基在艺术形式和审美新体验方面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至少可以追溯到1914年发表的《词语的复活》,他要做的是使早已失去活力的“僵死的”词语和“坟墓”中的语言再度复活(什克洛夫斯基,1993:25)。陌生化理论将文学技巧抽离于伦理环境和伦理关系之外,具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道德规范具有超越时空的基本稳定性,同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文化中又会有演变和变异,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又是民族文化跨越时空的心理沉淀。语言和文本经验是表达伦理关系的载体,他们通过各种互文关系跟历史和文化进行回应和互动,同时又不断产生出新的话语。什克洛夫斯基等人在圣彼得堡成立“诗歌语言研究会”之际,巴赫金也来到圣彼得堡读大学。巴赫金曾撰写多篇文章与形式主义“对话”,对俄国形式主义思潮表明了批评的姿态。巴赫金(1998:91)指出了作者在文学艺术作品创作过程中同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审美与伦理关系:“在史诗中,特别在长篇小说中,有时也在抒情诗中,主人公及其感受,他对事物对情感意志的总体取向,并不是直接地就取得了纯粹审美的形式,而是首先受到作者的认识和伦理的界定;换句话说,作者在对其做出形式上的直接审美反映之前,先要在认识伦理上做出反映;然后再把认识伦理上经过判定的主人公,从纯粹审美方面加以最终完成”。巴赫金用清晰而深刻的语言概括了文学阅读活动中审美和伦理认知上的发生过程,指出伦理对文学意义生成所起的重要作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审美只是文学的作用之一,“文学的美仍然是伦理的美”(聂珍钊,2018)。
什克洛夫斯基重视文学作品(审美对象)本身形式结构的构成方式和表述方式,完全忽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方面。“陌生化”手法的使用确实可以产生新奇的效果,延长读者的感知和审美过程,对提升文学作品的文学特质有较为直接的功效。然而在深层次意义上,什克洛夫斯基颠倒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将“陌生化”手法本身作为追求目标,而无视这个手法所指向的终极意义。巴赫金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中对俄国形式主义思潮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批评,其中一条便是批判它创立阶段就无法摆脱的虚无主义倾向:“形式主义在这个时期制定的基本概念——玄奥的语言、奇异化(陌生化)、手法、材料——都彻头彻尾地贯穿着这种消极的虚无主义的倾向”(巴赫金,1998:186)。经过“陌生化”手法处理的文学作品可以重塑审美快感和更新人们对生活的感知,但这只是途径而不是最终目的,这个行动最终指向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文学作品给人带来的解放,使之通过阅读叙事或抒情性质的文字得到审美快感,接受道德教诲,进而在生活上达成愉悦和幸福。从根源上来说,“俄国形式主义的‘纯形式’文学本质论基于康德美学。但这种‘纯形式’概念是依据感觉(‘陌生化’感觉)经验来确定的,因而剥离了康德美学‘形式’概念中的主体性意蕴”(陈本益,2003)。离开主体和历史来谈论审美感受与形式,不谈伦理,这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伦理取向。
形式主义的自我修正与文学的伦理属性
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诗就是受阻的、扭曲的语言”(什克洛夫斯基,等,1989:9)。以他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借鉴语言学的系统,创造出精确的术语,高扬文学的独立原则,试图建立一门研究文学的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艾亨鲍姆在1924年发表的《谈谈‘形式主义者’的问题》文章中曾有过明确表述,他指出形式主义思潮所讨论的问题“涉及的不是研究文学的方法,而是建立文学科学的原则”(艾亨鲍姆,1998:206)。在这个宏大愿景下,俄国形式主义有着鲜明的学术主张,那就是强调文学的自主性,这是形式主义思潮的一个核心主张。最有代表性的论断是什克洛夫斯基宣称的“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Shklovsky, 2005:22)。什克洛夫斯基等人在形式主义思潮运动早期阶段的理论推演都显得偏激和极端,这跟写作时候的具体历史环境有关。什克洛夫斯基对十月革命持反对态度,他曾于1918年在圣彼得堡策划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暴动,并为此短暂流亡乌克兰。他们展开论战姿态,于内是为了反叛与超越批评传统,于外是为了反对俄国当局政治力量对文艺界的直接干涉。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个著名论断遭到尖锐批评。1919年,青年巴赫金(1998:2)在自己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艺术与责任》结尾处说道:“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托洛茨基也从马克思主义以及政治立场角度批判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个论战口号,在1923年出版的《文学与革命》第五章“诗歌的形式主义学派与马克思主义”中专门驳斥了以这个论断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纯艺术论(托洛茨基,1992:152)。汤普森指出,“艾亨鲍姆在20世纪20年代写作的论文中一直声明形式主义完全独立于任何哲学和美学理论之外,因此(苏联主流思想界)将形式主义划为唯心主义的控诉不能成立”(Thompson, 1971:29)。事实上,不仅文学无法完全独立于生活之外,形式主义理论或思潮亦无法完全独立于哲学、美学理论和伦理学之外。
什克洛夫斯基(1977:3)在1925年出版的《散文理论》前言里说明了自己为何专门研究文学形式的变化问题:“在文学理论中我从事的是其内部规律的研究。如以工厂生产来类比的话,则我关心的不是世界棉布市场的形式,不是各托拉斯的政策,而是棉纱的标号及其纺织方法”。该书出版以后,巴赫金专门发表了书评,批判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个论断。巴赫金(1998:27)指出“织布的方法与总体技术水平和市场形势紧密相关,前者取决于后者”。巴赫金不仅从伦理哲学的高度对审美过程做出精彩论述,而且在回应俄国形式主义者的重要观点时经常举出实例,针锋相对地批判什克洛夫斯基等人忽视历史具体性和伦理关系的缺陷。
晚年的什克洛夫斯基撰写了多篇文章,反思和修正自己的“陌生化”理论,其中论述较为集中的是1982年的《散文理论》。什克洛夫斯基(1997:80)在《散文理论》中全盘否定自己早年主张的文学理念:“我说过,艺术是超情绪的,艺术里没有爱,艺术是纯粹的形式。这是个错误。”什克洛夫斯基(1997:82)在文中继续修正自己关于艺术和伦理之间的论断:“不向艺术里注入意义——这是怯懦。所以,颜色的斑点应当先散开,后再组合——但不是像镜子一样。我曾经写过,艺术无恻隐之心。此话激烈,但并不正确。艺术——是怜悯于残忍的代言人,是重新审理人类生存法则的法官”。什克洛夫斯基青年时代和晚年对待艺术和道德态度的剧烈转变是俄国历史形式和政治权力改造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对形式主义主张的扬弃。
不仅什克洛夫斯基本人的文学形式与伦理观在不同时期有过明显转变,在文学史观上,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思潮阵营中间其实也有分化,并非所有理论家都只关注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和形式,而完全忽视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等外部因素。俄国形式主义思潮由不同学派和集群构成,它们“彼此共同致力于语言艺术形态解析而建设‘科学化’的文论,”交汇成一个共同的文论流派,这个流派高扬文学的独立地位,这个群体兼容并包,多元共存,“正是由于他们的共同奋斗,俄罗斯文论在二十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终于完成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范式的第一次大转型”(周启超,2001)。“俄国形式主义的历史表明了这个流派内部的一个明显转变:从前期的共时研究转向后期的历时研究,从孤立、静止地考察文学语言文学技巧的特征,转向将文学形式放在历史过程以及文学的和文学外的系统中动态地加以把握”(陶东风,1992)。对雅格布森和什克洛夫斯基等早期形式主义者来说,他们有必要对文学形式的重要性进行绝对化,以此宣示与旧的批评传统决裂,进而创立一种新兴的文学思潮。到了形式主义思潮后期,不少俄国形式主义者也充分觉察到这一观点的偏颇,从而开始回归文学的外部研究,对文学形式和文化语境进行折衷处理,比如说“像日尔蒙斯基、托马舍夫斯基(还有梯尼亚诺夫)都不同程度地肯定了文学演变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关系”(陶东风,1992)。雅格布森、什克洛夫斯基和艾亨鲍姆等人在早期研究中将形式主义研究推到了极致,而且他们的贡献最大、理论观点最具辨识度,所以学界在讨论俄国形式主义思潮之时,通常只集中讨论他们这几位典型代表的早期理论。
结 语
在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上,俄国形式主义具有开创新风的作用,将研究重心聚焦在文学作品本身,专注于讨论文学的形式,试图建立独立的文学科学。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的“形式”“文学性”“陌生化”和“诗性语言”概念高度提纯了他们的文学主张,因此引来批评和非难。艾亨鲍姆早在1925年发表的《形式主义方法论》长文中就指出过这个问题:“非难他们根本原理含糊不清或粗枝大叶,非难他们对美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一般问题漠不关心”(艾亨鲍姆,1998:211)。其实形式主义运动持续了20多年,从早期到中后期的漫长过程中,其主导研究方法经历过重要的改变与进化,这一点通常为学界所忽视。艾亨鲍姆(1998:243)在此文结尾处曾对形式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十年间(1916-1925)所产生的变化和影响进行了全面论述。从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朝结构主义理念靠近的趋势。跟其他任何文学思潮一样,俄国形式主义流派一直都在不可避免地接受苏联政治和历史带来的巨大塑形力量,不断主动和被动地演变发展。然而总体上说,经典的形式主义批评理念基本都是拒斥对文学进行伦理评判,试图在文学文本身上找到文学的本体意义和存在目的。形式主义者对文学进行了人为切割,将它放置在伦理的真空里,忽视了文学与人之间的历史关系和联结力量。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顺应了西方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大潮,推动了俄国和西方文学批评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具有无可替代的进步意义。但是它完全抛弃伦理立场和道德责任的批评理念,极大地压缩了文学的阐释空间,损害了文学丰富性,使文学和文学批评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俄国形式主义者以颠覆传统批评观念的姿态出现,倾其所能地强调文学的意义。形式主义仅仅关注语言内部的技巧和规律,试图摆脱伦理来谈文学,排斥一切外在伦理因素。形式主义思潮诞生了一系列形式主义批评概念,产生出源源不断的理论内聚力,一致向内的理论冲动致使外在研究变得贫乏,巨大的压力差最终导致了形式主义文学运动的坍塌。否认文学的伦理因素,否认文学的教诲功能,就是对文学进行釜底抽薪。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初始理论诉求是为文学取得独立地位与合法性。这或许是他们始料未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