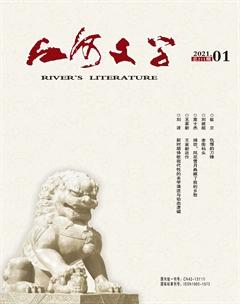日常生活诗学的再出发
何方丽
当“第三代”诗歌美学式微,诗人们纷纷转向时,于坚表现出了对日常之诗的坚守,这让他在1990年代末的论战中自然地成为了“民间写作”的发言人之一。1990年代是于坚的写作“更注重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的时期”,他相继创作出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0档案》《飞行》等诗,1999年创作的《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也是能体现于坚诗学理念的代表之作。从1980年代开始,一直到新世纪的诗歌创作,于坚所引发的争议从未停止过,其中最为突出的争议就在于他诗歌中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对“拒绝隐喻”这一诗学命题完成程度。关于日常生活,反对者往往针对其诗歌中的琐碎和庸常展开批评,而支持者则认为于坚诗中的日常才是真实的生活。无论“拒绝隐喻”能否真正实现,1999年的于坚在论战中依然未改初衷,他的写作始终在他预想的轨道中前行。
一、看见和说出:词与物的对应
“看”作为于坚体察事物的基本方式,被广泛地运用于他的诗歌创作中。“看”对于坚的意义不只在于诗歌方面,也在于他的生活方面。由于药物原因,于坚五岁时便失去了部分听力,初中毕业之后工厂的轰鸣加重了他的听力问题。用于坚自己的话来说,他拥有了“一双只能对喧嚣发生反应的耳朵”。后天原因导致的听力不足成为了于坚“看”的生理原因,毕竟当他能听到森林里各种生命的歌唱时,他与这些真实声音之间隔着人造的助听器,可取走助听器,他就只能听到世界的喧闹,这或许是于坚并不信任声音的原因之一。相反,通过“看”,诗人能够在自身与各种生命和事物的物质形态之间建立最真实、最直接的联系。
但“看”是每一个拥有视力之人的本能动作,真正让“看”成为于坚诗歌特色的原因在于,于坚长久以来形成的极具个人化特征的“如何看”。于坚与生活处在同一平面,他平视整个世界,即使是观察从天而降的一滴雨,他也拒绝俯视,他的视线与这滴雨水的运动轨迹始终保持着一致。“快乐的小王子自己为自己加冕/在阴天的边缘轻盈地一闪/脱离了队伍成为一尾翘起的/小尾巴摆直了又弯起来”,只有将视线紧贴这滴雨水,诗人才能真正把握这滴雨时刻变换着的形态。对那只飞翔的乌鸦,于坚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平视的视角是于坚之“看”的特点之一,让他看到的“物”更加真实。同时,于坚的“看”注重细节,他能通过“看”捕捉到那些细枝末节但往往至关重要的细节。“小雨点终于抢到了一根晾晒衣裳的铁丝/改变了一贯的方向横着走/开始吸收较小的同胞/渐渐膨胀囤积成一个/透明的小包袱绑在背脊上”,于坚对雨点的描写反映了他对细节、表象和局部描写的迷恋。细节、表象和局部的特征符合“看”的常理,目光所及乃是个体选择之后的结果,加上视域有限,“看”这一动作不可避免的具有个人性和局限性。但于坚将“看”这一行为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目的是为了掀开所有的遮蔽,看到一个真真切切的“物”。柄谷行人研究了日本文学对风景的“发现”,于坚所做与柄谷行人所言的“发现”在本质上无异,只是于坚“发现”的是生活中被文化和话语遮蔽的风景。
通过“看”这一自觉而非本能的行为,于坚找到了他诗歌中的“物”。于坚试图通过诗歌还原“物”之存在的客观与真实。因此,用何种词语“说出”自己所见之物就成为了于坚诗学的另一个重要命题。由于诗歌的最终呈现由词语完成,词语是诗人所见的书写对应物。这里涉及到了思维和词语的复杂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每一个词语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逻辑,或者说每一个词语都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索绪尔认为词语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能指是词语所代表的的抽象概念;所指是具体的事物。在于坚看来,由于知识谱系、文化隐喻的影响,事物已经被文化符号所遮蔽,作为符号的词语已经不止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而被赋予了固化的象征隐喻,例如看到“月亮”这个书写符号,人们所想的不止有它的能指和所指,还有诸如思乡、纯洁、悲欢离合之类的隐喻和象征,这同样是对词语的一种遮蔽。因此,去蔽、归还事物以澄明由此成为他诗歌的任务之一,而这对词语本身而言也是一种去蔽。
为实现上述任务,于坚在“说出”(其实是用词语写出)所见之物时,对词语的运用有较高的要求。名词是他诗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实词,从他的诗歌题目如指人的《罗家生》《主任》《小丽的父亲》,指物的《停车场上春雨》《铁路附近的一堆油桶》《篱笆》《0档案》等等。名词表示人、事物、地点或抽象概念的名称,于坚诗中的名词具有更为明显的特征。具体来看,他多使用具体名词,如雨滴、乌鸦、篱笆、星星等等,对于抽象名词的使用他显得尤为谨慎。在评价《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问题时,指出它不如《寻找失去的时间》,原因是“年华”不具备“时间”的中性,因为于坚认为普鲁斯特是在对无意义的生活进行回忆,因此,中性的“时间”就更符合作者的原意。为了还原一个本真的物,于坚在运用名词时会尽力规避诸如“时光”这类具有情感倾向的名词。这样做的结果是于坚用他的语言建造了一个零度情感的词语现实,但就像余华的零度写作一样,作者的冷静和客观并非意味着不能给读者带来精神的情感冲击,相反,这种冲击力往往是巨大的。1988年于坚认为好诗的标准是具备“一种冷静、客观、心平气和、局外人式的态度”,1999年,于坚这样说出一滴雨的一生“它的时间就是保持水分直到/成为另外的水把刚刚离开咖啡馆的诗人/的裤脚浅湿了一块”。可以看到,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于坚始终在冷静、客观的写作道路上前行。
动词是于坚诗歌又一特色鲜明的骨架,于坚是用词的高手,这一點毋庸置疑。还是从诗歌题目入手,《在云南省西部荒原上所见的两棵树》《事件·铺路》《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上教堂》《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我看见草原的辽阔》,以及1999年创作的《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等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这些诗题中的动词都为及物动词,这与于坚历来被人称道的“及物写作”似乎存在某种关联。“及物”这个词语本身就要求动词带“物”来完成一个动作,如此,这个动作是有对象的、具体的。及物动词的使用使于坚的诗歌有一种在场感,这对“说出”一个“物”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关涉到诗歌的可信性,也就与读者的信任相勾连。“盘峰论战”时,“民间写作”攻击“知识分子写作”的弊病时,就指出“知识分子写作”背离了读者,无法赢得读者的信任。还是以于坚对雨点的“说出”为例,“小雨点终于抢到了一根晾晒衣裳的铁丝/改变了一贯的方向横着走/开始吸收较小的同胞”,通过这些精细的及物动词,我们看到于坚捕捉的是瞬间的变化和细微的动作,一种在场感就自然出现了。
及物动词和中性名詞(在于坚这里,名词确实有中性和非中性之别)的运用让于坚在“说出”的时候拥有了具有个人特色物质基础,如此,在解决了“如何看”和“以何说”这两个核心问题之后,于坚实现了词与物之间直截了当、简单真实的对应,剩下的就是诗歌内部的事了。
二、如何“反对隐喻”:诗与思的逻辑
在中国古典诗歌这里,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而段被大量运用,诗人们常常用一个词或短语描写常见的一种物体或概念,而用以代替另一种物体或概念,在暗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时,获得诗学效果。叶维廉指出“中国的‘比强调类同与协调,使喻意和喻旨化而为一”,古代诗人们在江水与时间、鸳鸯与爱情、驼铃与离别等等事物和概念之间建立了隐喻关系,并借此抒发个人情感,隐喻是意象赖以形成的基础。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修辞的手段,也是一种思维的方式,“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隐喻这种思维模式的作用。在朦胧诗时代,为扩大诗歌的张力和想象力,诗人们普遍采用意象堆积的方法进行创作。当创造新的意象成为一件难事,不少诗人开始照搬已有意象,使朦胧诗在思想和语言上都趋于僵化。1990年代以来,“后朦胧诗”写作继续在隐喻和象征的轨道上前行,加上解构主义思潮在中国日渐成熟,于坚提出了“拒绝隐喻”的诗学命题。于坚指出“汉语的能指系统却很少随着世界的变化而扩展,它的象形会意的命名功能导致它只是在所指的层面上垂直发展,所以它的能指功能不发达”,当数量有限的汉字循环反复地承载着各个时代的所指、意义、隐喻和象征,汉语的能指功能逐渐丧失,汉语以及诗歌的活力也就逐渐暗淡。“盘峰论战”中,于坚、谢有顺等人毫不犹豫地将“知识分子写作”惯用的隐喻和象征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
作为一个诗学命题,“拒绝隐喻”首先在于坚思想的层面得到了重视,出于理论构架的需要,于坚写了大量的文字进行阐释。“在五千年后,我用汉语说的不是我的话,而是我们的话。汉语不再是存在的栖居地,而是意义的暴力场”,于坚的诗学命题首先从语言的积弊入手,他试图清理的是积累了五千年文化的语言,以回到汉语的源头和本源性的神性,他将此称为语言神性,“拒绝隐喻”就是在语言神性的基础上对诗歌写作提出的要求。由此,他认为“拒绝隐喻,就要回到指向存在的写作,让词自己说话。这是基于对汉语的信任,汉语是存在性的,不是工具性的”。面对一个被文明和文化所遮蔽的世界,诗歌有责任让事物从隐喻系统中抽身,成为独立自主而非被纳入文化系统的存在。在于坚看来,诗歌无疑具备这种去蔽的功能。当然,于坚并不简单地将诗歌作为一种为事物去蔽的工具,因为他从未放弃过对诗性的追求,读于坚的诗,依然能从中感受到语言的美感。当他冷静客观地描述一滴在空中不断转换形态的雨点,由名词和动词带来的语感和画面本身就构成一种美,只是这种美并不绚烂,而更接近日常。虽然由于“每个字词下面都隐含着一个地质构造”(罗兰·巴特语),“拒绝隐喻”从理论上来看有其无可规避的悖论性质,但于坚“拒绝隐喻”以对事物去蔽这一行为,对我们重新认识一个事物有着重大意义,这个意义是认知层面的,更是思维层面的。
虽然于坚自己也承认“隐喻从根本上说是诗性的。诗必然是隐喻的。”但即便他对拒绝隐喻的悖论性心知肚明,他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始终在自觉地“拒绝隐喻”,因为他拒绝的是那些已经死亡或者僵化的喻体,他也不否认自己的创作是一种新的隐喻:“在隐喻死亡地方,隐喻诞生了”。1999年创作的《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这首诗歌就体现了于坚对“隐喻”的拒绝。在以往的诗歌中,雨大都同离愁别绪以及生命和希望相关,巴山夜雨和随风入夜的雨基本成为这两类隐喻的代表。此外,洗尘除垢也是雨被构建出的一大功能,“渭城朝雨浥轻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北岛的《雨夜》仅仅将雨作为一个孕育着明早“血淋淋的太阳”的背景。可见,绝大多数时候,雨都是作为集合概念出现在诗歌中,诗人往往忽视了雨是由雨滴构成这一事实。因此于坚从题目开始就在与“诗人”划清界限。借助这首诗歌,诗人试图以雨滴还原雨的本质。“哦下雨啦/诗人在咖啡馆的高脚椅上/瞥了瞥天空小声地嘀咕了一句/舌头就缩回黑暗里去了”,在这里,于坚其实描述了诗人面对雨已经失语的事实,而他的写作实践就是要通过观察,重新找回对雨的发言权。当雨滴在铁丝上,“它似乎正在成为异类/珍珠葡萄透明的小葫芦”,于坚拒绝以往的隐喻,用比喻形象地描绘雨滴的形态,虽然喻体皆常见之物,但通过他的诗歌我们发现了雨滴更多的可能。虽然于坚的主观愿望是拒绝隐喻,但就像他自己所言,他已经开始了另外的隐喻。“它还没有本事去选择它的轨迹/它尚不知道无论如何选择/都只有下坠的份了也许知道”,雨滴在此被带入了一个更为宏大隐喻之中。从离开潮湿的云到最终终结于诗人的裤腿上,雨滴也经历了生命的开端和结局,并且,它也无从操控自己的命运,即使不断变换形态,也曾在空中旋转跳跃,在铁丝上充盈膨胀,但它仍然无法摆脱最终的命运,宿命因此成为一个更大的隐喻。其他诗歌像《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啤酒瓶盖》等诗也是对“拒绝隐喻”这一理念的实践。
对于于坚“拒绝隐喻”在理论和事件上出现的悖论,学界大都对此予以包容和理解,当然也不乏批评者,比如姜涛就认为于坚喊出“拒绝隐喻”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一种发明,其目的在于文学史。历时地看,于坚的创作从对朦胧诗的反抗开始,而“后朦胧诗”中的文化、知识、象征和隐喻一方面与于坚的创作理念相左,一方面确实有损于诗歌对接日常和生活的本质,因此于坚提出“拒绝隐喻”于公于私都有助于1990年代诗歌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三、继续在分歧中坚守“非诗”的写作
有论者指出,1990年代不是诗的年代,也是一个不需要诗人的年代,“一切都物质化、市场化了,商品就是上帝。精英与大众失去了界限,精英文化的荣光不再。对于曾具有独特个人深度和个人魅力,曾属于社会精英、顶尖知识分子的诗人,大众悄然拒绝,至多保持一种疏离、漠视、敬而远之的态度。”,市场经济全面展开后,诗歌的确在1990年代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和精神氛围,在一个“非诗”的年代,诗歌变得安静了,诗歌到底该何去何从成为了诗人们自己的事情。于坚选择了一条“非诗”的道路,他从语言表达和结构技巧等方面来突破诗歌的既有陈规,也在姿态上表现出了对“知识分子写作”那种满是“文化腔”诗歌的反抗。陈超从诗歌接受的角度出发,认为“对于现代主义诗歌得到普遍认同的‘间接化的表达方式(暗示性、隐喻性)而言,于坚诗歌语言的‘直接化表达方式,在特定的写作语境中有着‘反诗的性质”。此处讨论的“非诗”涵盖了陈超所言的“反诗”写作,还包括对于坚诗歌中的非诗歌因素方面的探讨,如他对技术的迷恋、对叙事快感的追求等。
“盘峰论戰”反映出的分歧和矛盾在1998年左右就已经开始显现,当“知识分子写作”方面以相对的优势开始构建“90年代诗歌”时,他们实质上表现出了对“第三代”诗歌那种口语化、日常化写作的轻视。这对始终在生活现场的于坚而言,是一种无意的挑衅。不过,即便是在遭受质疑和忽视的处境中,于坚依然在坚持他的“非诗”写作。1999年创作的《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也具有典型的“非诗”特征。
题目中“诗人的范围以外”开宗明义,于坚旨在写一首“非诗”的诗歌,不过诗歌开篇似乎就能确定“诗人”的具体所指。“哦要下雨啦/诗人在咖啡馆的高脚椅上/瞥了瞥天空小声地咕噜了一句/舌头就缩回黑暗里去了”,1991年欧阳江河创作了诗歌《咖啡馆》并在此后的时间里获得了相关批评家的认可与推崇。“咖啡馆”和“高脚椅”这个意象事实上暗指以欧阳江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因为此二者是明显的舶来品,于坚不止一次地驳斥“知识分子写作”对西方资源的依赖。如果仅凭“咖啡馆”和“高脚椅”还不能确定于坚反对的“诗人”所指(毕竟未被“民间写作”批评过的女诗人翟永明也曾写作《咖啡馆之歌》),那“舌头”的出现是又一例证。早在1998年年初,于坚就发表了长文《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在文中,他攻击了与口语写作相对的普通话写作,认为普通话写作对应舌头的硬、紧张和窄的状态,并认为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是普通话写作的一部分,并使普通话“在书面语和形而上的传统反向上更适应某种现代性”,与国际接轨则是现代性之一。当于坚笔下的诗人将舌头“缩”回去,就证明了诗人的诗歌之舌僵硬而紧张,无法面对雨。到这里,可以看到,于坚基本旨在写一首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或者说他在以这首诗反对“知识分子写作”。此外在这首诗中,“诗人”不关心雨点这等小事,而关心更大的事件、关心女读者,于坚认为我们的诗人在反抗嚎叫之后变得合法而登堂入室,并“用唯美的笔为读者签名/拼命地为自己抓住一切”。说这首诗是一首讽刺之诗一点都不为过,因为诗中充满了对“诗人”的鄙视,尤其是当他们竟不能言说一滴雨。可见,于坚“非诗”写作的内涵之一便是“非”“知识分子写作”之诗,在这里,“非”有否定和反抗的含义,而“诗”也特指以“知识分子写作”为代表的非口语写作。
“非诗”的另一层含义则类似于形容词,表示于坚诗歌的一种特征和状态。《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这首诗有两条明显的线索,一是雨点的一生,一是诗人的活动,二者互相交织,并且于坚以雨点的活力和多样的形态反衬了诗人道貌岸然的状态。双线交织就避免了对雨点一生进行单纯的平铺直叙,这有利于诗歌内涵的丰富性。于坚认为,诗歌、小说、散文等文体已经被硬化,因此提出了另外一种自由的“散文化写作”,他认为这种写作“可以是诗的,也可以是小说的、戏剧的”,作为这些文类的一种集合,“散文化写作”是于坚“非诗”写作的重要部分。例如,诗人在“观察雨点”时,就有散文、小说、戏剧等方面的元素。如由诗人至雨再至幼儿园孩子的场景转换就有戏剧特征,而诗歌中不时出现的哲理性思考又有散文的特色,“在滑近地面的一瞬(事物的本性/总是在死亡的边缘上才抓住)/小雨点终于抢到了一根晾衣裳的铁丝”,括号内的独白就是散文笔法,至于线索和叙事的讲究则来源于小说写作。在这种“散文化写作”中,于坚让他的诗歌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诗歌,《0档案》《飞行》等诗都具备这种特点。
在一次访谈中,于坚指出他理解的诗歌更加广阔,“不以所谓优美、抒情、想像力丰富、有深度这些通行的标准为尺度”,于坚的口语写作似乎天然与优美绝缘,《0档案》中的罗列就更与抒情无关,但需要指出的是,于坚的诗歌依然充满想象力,也有一定的深度,只不过他的深度不是源于语言的迷宫,而来自思维和技艺的锻造。作为一个认为“在写作中,形式感是第一的”诗人,于坚绝对不会追求传统意义上语言的美感,因此,他的诗歌中也不乏庸俗、冗赘的语言。这也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后期,于坚在获得广大读者的时候却较多地受到评论家指摘的原因之一。
于坚的“非诗”写作既是作为一个动作反对那些“装腔作势的伪诗”,也作为一种风格成为于坚诗歌写作的亮点。口语和他自己所言的“散文化写作”目标为他“非诗”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指明了一个方向。在世纪末的论争中,于坚依然坚他的“非诗”写作,并在新世纪写作中国继续践行。评论家陈超用“返诗”来描述于坚“反诗”的本质,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从1980年代以来,于坚始终坚守在诗坛,他的反叛和创新都是为了诗歌本身。对于坚而言,他的写作仅仅是为了诗歌。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1978年以来当代诗歌批评与诗人创作的互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D029)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