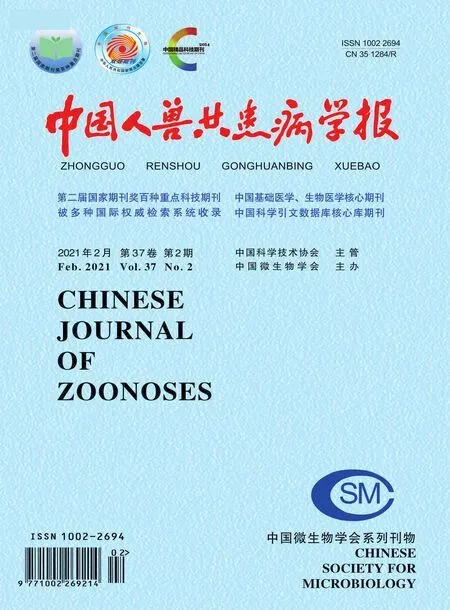一起由产气荚膜梭菌和肠聚集性大肠埃希菌共感染导致的聚集性腹泻事件病原学分析
张 爽,张巍巍,李 颖,马红梅,冯宝立,张茂俊,陈 倩,王丽丽
产气荚膜梭菌(Clostridiumperfringens,C.perfringene)是一种条件致病菌,能引起人类气性坏疽和食物中毒等疾病。该菌可产生至少16种毒力因子,包括α-ν 12种毒素、肠毒素、溶血素和神经氨酸酶[1],其中肠毒素(CPE)和β2肠毒素与胃肠道疾病密切相关[2-3]。肠聚集性大肠埃希菌(EnteroaggregativeEscherichiacoli,EAEC)是5种致泻性大肠埃希菌中的一种,曾在世界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引起散发或暴发流行[4-7],易感染营养不良儿童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8]。EAEC在本地区散发病例中广泛流行[9]。
本研究对2018年北京市一起腹泻暴发事件中分离到的C.perfringens和EAEC进行病原特征分析,为此类混合感染暴发事件的实验室应对提供经验。
1 材料与方法
1.1材 料
1.1.1样本采集与流行病学调查 2018年5月7日北京市某医院肠道门诊接诊9例以腹痛、腹泻为主要症状,有共同就餐史的学生患者。所有病例均来自一个学生团,该团共15人,其中学生14人,生活老师1人,共有9名学生发病。该团成员均于5月6日晚18点在新疆乌鲁木齐就餐,晚20点乘飞机至北京。首发病例发病时间为5月7日早3点,末例病例发病时间为早8点,流行曲线为单峰曲线,呈点源传播特征。我们采集全部9名病例粪便样本送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测。
1.1.2试剂与仪器 麦康凯琼脂(MAC)、胰胨亚硫酸盐环丝氨酸琼脂(TSC)、哥伦比亚血琼脂(北京陆桥);细菌 DNA 提取试剂盒(德国Qiagen);细菌、病毒实时荧光 PCR 检测试剂盒(北京卓成惠生及青岛中创);普通PCR反应液体系液(日本TaKaRa);限制性内切酶XbaI、SmaI(美国NEB);革兰阴性需氧菌药敏检测板(上海星佰);脉冲场凝胶电泳仪(美国Bio-Rad);细菌鉴定仪Vitek2 Compact 3.0(法国梅里埃)。
1.2方 法
1.2.1病原体分子筛查 应用北京卓成惠生公司的五种致泻大肠(货号A211L)、沙门氏菌(货号A2060)、志贺菌(货号A2070)、空肠弯曲菌与结肠弯曲菌(货号A2242)、副溶血性弧菌(A2050)、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货号A2593)、札如病毒/腺病毒/星状病毒(货号A2723)以及青岛中创公司的产气荚膜梭菌(产品编号ZC-RT-PCR-046)荧光定量PCR检测试剂盒对9份病例粪便核酸进行常见的肠道病原筛查。
1.2.2细菌分离培养和毒力基因检测 粪便样本接种MAC琼脂,37 ℃培养24 h,从平板挑选10个可疑菌落进行5种致泻性大肠埃希菌毒力基因鉴定[10],通过荧光定量PCR检测escV、eae、bfpB、stx1、stx2、lt、st、invE、ipaH、aggR、uidA、astA、pic等基因判定所挑菌落是否为EPEC、STEC/EHEC、EIEC、ETEC、EAEC中的一种;采用倾注法将粪便接种TSC琼脂,37 ℃厌氧培养24 h,挑取10个黑色菌落进行牛奶发酵等C.perfringens确证实验[11],采用普通PCR方法对鉴定为C.perfringens菌株进行6种毒力基因检测[12]。
1.2.3EAEC菌株的耐药性检测 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进行抗生素敏感试验,依据CLSI M100-S28判定耐药、中介、敏感。抗生素包括青霉素类:氨苄西林(Ampicillin, AMP)、苄西林/舒巴坦(Ampicillin/Sulbactam, AM);一代头孢:头孢唑林(Cefazoin, CFZ);二代头孢:头孢西丁(Cefoxitin, CFX);三代头孢:头孢他啶(Ceftazidime, CAZ)、头孢噻肟(Cefotaxime, CTX);碳青霉烯类:亚胺培南(Imipenem, IMI);大环内酯类:红霉素(Erythromycin, ERY)、阿奇霉素(Azithromycin, AZM);四环素类:四环素(Tetracycline,TET);喹诺酮/氟喹诺酮类:萘啶酸(Nudic Acid, NAL)、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 CIP);氯霉素类:氯霉素(Chloramphenicol, CHL);氨基糖苷类:庆大霉素(Gentamicin, GEN);磺胺类:复方磺胺(Trimeth-sulfame, SXT);测试抗生素共计包括7大类15种(青霉素类、头孢类和碳青霉烯类均归为β内酰胺类)。
1.2.4菌株分子分型检测 菌株分子分型使用脉冲场凝胶电泳方法(PFGE),其中EAEC使用XbaI限制性内切酶进行酶切,电泳条件:6.76~35.38 s,19 h;C.perfringens使用SmaI限制性内切酶,0.5~40 s,19 h;两种方案均以沙门菌H9812使用XbaI酶切后的片段作为分子量参考标准。PFGE图谱应用BioNumerics 7.6软件进行聚类分析。
2 结 果
2.1病原初筛、菌株分离及毒力基因检测结果 9份病例粪便核酸中,6份样本astA+(EAEC),8份样本cpa+(C.perfringens),5份样本混合阳性。6份astA+样本中分离到6株EAEC,且astA+;8份cpa+的样本中分离到8株C.perfringens,其中2株cpa+/cpe+,6株cpa+/β2+,且8份样本C.perfringens平板计数值均>106cfu/g,见表1。

表1 细菌分离培养、毒力基因和PFGE检测结果
2.2分子分型结果和抗生素敏感性检测结果 如图1所示:6株EAEC被分成2种带型,其中1株为E1带型,另外5株为E2带型,E1与E2带型相似度为70.7%。如图2所示:8株C.perfringens被分为3种带型,其中6株(所有cpa+/β2+菌株)为相同带型C1,2株cpa+/cpe+菌株为2种不同带型(C2和C3),C2、C3与C1不成簇,位于另一分支,C2、C3相似度为81.8%。6株EAEC呈现2种耐药表型,与PFGE带型分布特征一致,其中5株E2带型菌为AMP+CAZ耐药;1株E1带型菌为AMP+AMS+NAL+SXT多重耐药。

(注:如图所示,本事件中分离到的6株EAEC菌株中有5株同源性高达100%,另有1株与其他菌株同源性为70.7%)

(注:如图所示,本事件中分离到的8株CP菌株中,6株β2毒力基因阳性的菌株聚为1支,同源性为100%;另2株cpe毒力基因阳性的菌株聚为1支,同源性81.8%;2支基因分支间的同源性为54.5%)
3 讨 论
C.perfringens在美国作为排在第2位的食源性致病菌[13],却多年在国内零报告[14-15],这可能是腹泻暴发疫情中未将C.perfringens纳入检测范围所导致。本事件对病例粪便进行了多种常见病原的实时荧光PCR检测,与分离培养起到互相验证作用。该方法值得在暴发事件中广泛应用。9名病例有共同就餐史,发病潜伏期为8~14 h,既符合致泻大肠埃希菌导致食物中毒8~44 h的潜伏期特征[16],也满足C.perfringens导致食物中毒8~24 h潜伏期特征[17],同时8个病例粪便C.perfringens计数均>106cfu/g,与文献[18]报道符合,不同病例粪便中分别分离到同带型EAEC和C.perfringens,因此本次腹泻暴发事件可能由C.perfringens和EAEC混合感染导致。
文献报道,CPE肠毒素是引起食物中毒和非食源性人类胃肠道疾病的重要原因[19],β2肠毒素与人类胃肠道疾病紧密相关[20]。本事件中分离到的C.perfringens均携带cpe基因或β2基因,且β2+菌株为同PFGE带型,说明病例可能被多克隆C.perfringens感染,但实验者针对每个病例分离的C.perfringens仅保存1株,这可能是个别病例分离株带型不一致的原因。所有患者(9名)可疑暴露餐次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因此无法对就餐场所环境和疑似污染食品进行采集,最终导致无法完成食品-环境-病例的完整溯源。C.perfringens导致食物中毒是否存在多克隆感染值得在今后的工作中持续关注。建议进行C.perfringens相关暴发实验室分析中应挑取并保存多个单菌落,更易于识别患者可能存在的多克隆感染。
EAEC是小儿腹泻感染的最常见病因,发展中国家食品中EAEC有较高检出率,而且也存在无症状感染者[21-22]。本次事件有6例患者粪便标本分离到astA+的EAEC,虽然菌株aggR-,仍从病原学上支持6名患者有EAEC感染。6例患者分离到的6株EAEC菌株中,有5株菌PFGE带型相同、耐药表型相同,进一步说明患者可能存在着相同克隆的感染。5株PFGE为E2带型分离株仅对AMP+CAZ耐药,与北京市致病性大肠埃希菌耐药谱存在一定差异[23],这个克隆的菌株在腹泻患者的感染特征有待于未来进一步地监测和分析。
本次暴发事件中,有5名患者的粪便样本检出2种病原,推测可能是2种病原同时污染食品。该结果提示我们在进行实验室病原检测分析时,应该尽量全面地筛查有可能引起腹泻症状的各个病原,包括致病细菌和病毒。筛查病原的覆盖面增大后,可以使我们的实验室病原检测结果更为准确、可信,也可以将检测结果更好地服务临床的治疗工作。类似的多病原混合感染造成的食源性暴发事件在之前也有报导,这更加提示我们在应对食源性疾病暴发实验室分析过程中进行多病原筛查的重要性。
利益冲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