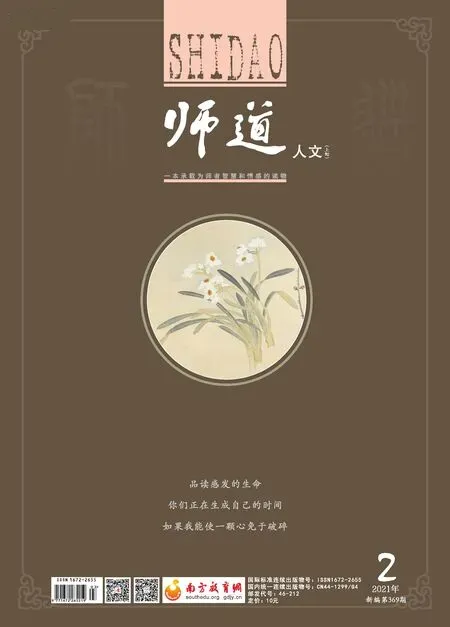你们正在生成自己的时间
傅国涌
蓦然回首, 国语书塾童子班开课已经三年了。
三年, 时间悄悄地来, 悄悄地去, 没有声音, 没有颜色, 也没有气味。 但我们 “与世界对话” 的课堂有声音、 有颜色、 有气味, 我们一同行过的万里路有声音、 有颜色、 有气味, 你们的笔尖流出的是声音、 颜色和气味, 你们演过的戏也有声有色有味。
虽然我们抓不住时间, 时间却天天抓住我们。 三年, 不急也不慢, 那些时光已凝固成我们共同的“国语书塾时间”。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这个说法何等奇妙, “人不只是在时间里,他更会生成时间。 石头、 植物和大多数的动物, 则只在时间里, 它们并不会生成它。”
过去的三年, 我们与世界对话, 生成了自己的时间。 在垃圾时间的重围之中, 我们真实地拥有了自己的黄金时间, 虚空的时间因为我们饱吸人类精神的雨露而变得充实。 你们的想象力、 审美力、 思想力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看着你们不断地突破自己, 你们的世界一天天扩大, 我为你们感到高兴。
你们在 “国语书塾时间” 里,一起读出来、 背出来、 写出来、 演出来、 走出来, 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 每一天都有新的喜悦。 我曾推荐你们读智利诗人聂鲁达的 《疑问集》, 在 “与牛对话” 一课, 我上课时提到了其中一句诗: “你有没有发现秋天/像一头黄色的母牛?”四年级的徐未央受到启发, 当晚写出了非常精彩的习作 《是它, 踏出一个秋天》。 在 “与日出对话” 课后, 五年级的赵涵读到了聂鲁达的诗句: “今天的太阳和昨日的一样吗? 这把火和那把火不同吗?” 为此激动且不无懊悔地说, 要是早点读到这句诗就好了, 她的习作 《日出说》 就会有更好的思路。
回望过去的时光, 我首先想说的是——国语有种。 你们读过美国作家梭罗的 《种子的信仰》, 这种子就藏在人类有文明以来留下的最珍贵的精神宝库里。 三年来, 我们一起读世界, 读东, 也读西, 正是古今中外的经典读物日复一日将你们带进了一个个崭新而奇异的世界。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又关注东欧文学和思想的景凯旋先生 (他也是国语书塾的导师), 曾跟我说起波兰诗人、 1980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切斯瓦夫·米沃什晚年的一首诗 《礼物》:
多么快乐的一天。
雾早就散了, 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的上面。
尘世中没有什么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人值得我去妒忌。
无论我遭受了怎样的不幸,
我都已忘记。
想到我曾是同样的人并不使我窘迫
我的身体里没有疼痛。
直起腰, 我看见蓝色的海和白帆。
他说: “这不就是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吗? 似乎中西文化长期分开后, 两个古老源头又汇在一起了。”
我还是第一次读到米沃什的这首诗, 非常欣喜, 说了一句: “从个体的存在着眼, 东西相通。 可惜陶渊明抬头所见的是山, 山是自然, 也是阻隔。 米沃什看见的是海, 一望无际。 这里是否又有了东西之别?”
见山, 更要见海。 我们不能只读中国书, 这将限制自己的视野,从一开始, 国语书塾 “与世界对话” 的课堂就是古今东西兼容并蓄, 我推荐给你们的书目也是东西并重。
阅读名篇佳作已成为许多童子的日常功课, 从文学到科学, 从历史到艺术, 有的童子甚至开始接触哲学。 在 “与世界对话” 每课一两万字的阅读材料之外, 有的童子还读了大量课外书, 写了不少读书笔记。 特别是付润石, 他啃下了德国诗人歌德的大部头 《浮士德》, 以自己的思路重新改编了其中几个片断。 他读塞万提斯的 《堂吉诃德》,与金庸的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 还写过读书笔记。 他读 《胡适文集》,被胡适续写的 《西游记八十一难》吸引, 动手改编成了近六千字的六幕短剧, 融汇了他接触过的希腊悲剧风格和他从古文中吸收的语言精华, 读来荡气回肠, 而并不显得生硬。
回望2017 年10 月7 日, 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八, 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席卷而来, 我们的第一课就是与 “天下第一潮” 对话……
三年来, 不少童子背出了60篇古文名篇, 背出了普罗米修斯、哈姆雷特、 浮士德等经典独白, 好几位童子一年就背出了40 多篇古文名篇, 甚至有人一年就背了60 篇。
国语有种, 这种子来自 《诗经》 《楚辞》、 唐诗 宋词, 来自《古文观止》, 也来自古希腊悲剧、但丁、 歌德、 莎士比亚他们; 来自“种豆南山下” 的陶渊明, 也来自种豆瓦尔登湖畔的梭罗。 只有东西汇通才能滋养一个处于开放时代的少年。 我不相信人类可以退回到地理大发现之前相互隔绝的时代,“种子的信仰” 毫无疑问要建立在世界视野之上, 而不是回到古老封闭的状态, 拒绝普世的文明资源。
“秋菊有佳色”, “不是花中偏爱菊”, 这菊花不仅为陶渊明东篱下所采, 被唐宋诗人反复吟咏, 也出现在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 《花的智慧》 中。 我仍记得 “与菊对话”那一课, 你们最初读到这些语言时的惊喜——“一个神秘的声音为时间和空间发出同一口令, 最漂亮的女士, 虽然身处不同国度、 不同地区, 都会同时接受并遵循了这道神奇的圣旨。” “最漂亮的女士” 就是菊花。
正如我们 “与红叶对话” 时,向往的不只是杜牧的 “霜叶红于二月花”, 更有梭罗的红枫——在那个山坡上升起它猩红色的旗帜,“也许现在我们可以完全读懂它的名字, 或者说, 它的红色标题。 它的美德——而非罪恶, 同样是猩红色的。”
源自东西方的种子在你们的心中酝酿、 发芽, 最终也化作你们自己的母语。 国语书塾是一个作坊,你们一起读、 背、 演、 走、 写, 这是一个类似酿酒的过程, 所有吸收的资源在你们心中起的是化学反应。我相信种子, 相信时间, 种子在时间中会发芽, 长大, 开花, 结果。
想起三年前你们初来国语书塾, 那时候你们下笔无神, 笔下流出的文字真的没有声音、 色彩、 气味, 许多童子甚至每个句子都是不通的。 时间终将教你们明白, 你们没有辜负时间, 也没有辜负种子,种子的信仰如此确定, 你们等到了自己的时间, 生成了自己的时间。
其次, 我想说——国语有路。所谓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是不能割裂开来的, 科学家、 教育家竺可桢先生曾写过一篇 《旅行是最好的教育》, 在他之前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有类似的说法。
国语书塾从一开始就重视行万里路, 还曾给部分童子、 家长颁发过 “行万里路奖学券”。 2017 年11月, 我们与富春江对话的课堂就在桐庐富春江畔的桐君山和严子陵钓台, 你们在山水之间的兴奋和激动, 我至今难忘。 从那时以来, 三年间, 我们循着 “寻找中国之美”这条线, 先后到绍兴、 北京、 南京、 无锡、 西安、 嘉兴、 海宁、 雁荡山等地, 《寻找中国之美: 少年双城记 (北京、 南京篇)》 已于今年4 月问世, 其他几本也将陆续出版。 我们的 “寻找世界之美” 系列从希腊、 意大利到法国、 比利时、荷兰、 德国一路走来, 已定下行程的葡萄牙、 西班牙之行因突发的疫情而中断, 计划中的英国之行也暂时不能启动。
最初跟随我一起行万里路的童子们, 翻开你们在游学途中留下的习作, 令我感慨不已, 你们用脚步丈量世界的同时, 对世界的理解也渐渐加深。 希腊归来, 冯彦臻在《希腊组曲》 中写过这样一番话:“我猜蓝色的爱琴海是动的, 表面上看上去波澜不惊, 其实爱琴海就如同神们的游乐场, 热闹非凡。 但水中的秘密只有鱼儿们知道, 我并不知道蓝色水中的秘密。” 在荷兰,我们一起读 《安妮日记》, 刘艺婷的习作 《我叫吉蒂》, 以日记本的口吻, 讲述安妮在那间不见天日的密室里的梦想与希望。 德国游学途中, 金恬欣在席勒的花园房子课后, 写了一篇 《席勒的彩虹圈》,席勒的人生也如彩虹, “他画了一个圈, 圈进了七彩, 圈进了世界历史, 也圈进了席勒永不枯竭的灵感。”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芬奇小镇, 付润石第一次突破了自己, 写出了一篇八百多字的 《寻找》, 托斯卡纳的阳光和蓝天, 橄榄的清香, 百合花一样的空气, 将他带到四百多年前达·芬奇的时代, 他在小镇的钟声中仿佛遇见了少年达·芬奇。 意大利文艺复兴之旅成为他成长的关键。 等到去年8 月德国游学归来, 他写出了洋洋洒洒四千五百多字的 《德意志如是说》。
今年夏天, 我们在绍兴上过“与故乡对话” 一课, 在读鲁迅的《故乡》 时, 我说了一句, 也许在少年鲁迅的心中, 少年闰土就是他未曾到达的远方。 我们还读了胡兰成 《今生今世》 中节选的一段文字: “又有经商的亲友……他们是来去杭州上海路过胡村, 进来望望我们, 这样的人客来时, 是外面的天下世界也都来到堂前了。” 金恬欣当场完成的习作 《黑白片》 就有这样一番话:
黑白电影模糊的镜头中, 似乎还有一个有些质朴的乡下男孩, 他叫闰土。 闰土实在是一个见识多广的人, 他见过海边的贝壳, 守护过西瓜。 在儿时鲁迅先生的眼里, 闰土就是未曾到达过的远方, 他来了就是外面的天下世界都到堂前了。
这就是好的母语, 从不同的地方借来的两句话化成了她自己的。
在 “与鲁迅对话” 课上, 我们读了画家吴冠中的短文 《鲁迅故乡》, 其中说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小桥——大弧线, 流水——长长的细曲线, 人家——黑与白的块面”。 又读了另一位画家陈丹青的讲演稿 《笑谈大先生》, 其中说鲁迅的样子好看。 “这张脸非常不卖帐, 又非常无所谓, 非常酷, 又非常慈悲, 看上去一脸的清苦、 刚直、 坦然, 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
何牧真的课堂习作 《故乡》 有一个奇妙的结尾: “在一个江南水乡, 弧线、 曲线和黑白的块面交错、 变化, 变为一张脸, 刚直、 清苦、 坦然。”
她几乎天衣无缝地将吴冠中关于绍兴和陈丹青关于鲁迅的两个描述融合在了一起。 弧线、 曲线和黑白的块面, 她是借来的, 刚直、 清苦、 坦然, 她也是借来的。 但借得恰到好处, 就是好。
2020 年7 月 底, 在 雁 荡 山 游学的第一课是 《文言雁荡与白话雁荡》, 赵馨悦的习作 《荡石》 这样开篇: “不论是 《红楼梦》 中那块宝玉, 还是担中玩具, 这块石头仍在荡漾。 从玉清宫的木纹中开始,时间从宋代开始。” 最后说:
在每块石头中可以长出羽毛,荡来, 是文言, 荡去, 是白话。
雁荡山, 风流的雁荡石不穿衣服, 但个个都触着每寸光阴成了黄金。 雁荡山, 荡了千年的美, 开在杜鹃花中。 雁荡山好美, 身在其中我不复存在。
这样的母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从国语书塾的课堂上, 从万里路上慢慢长出来的。 赵馨悦来国语书塾两年后才开始爆发, 大胆想象, 小心落笔, 她从李白的 “雪花大如手” “燕山雪花大如席” 得到启发, 却写出了更为大胆的 “雪花大如地球”。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三年来, 种子就是这样在你们的生命中发芽, 然后从你们心中流出的不再是机械、 呆板、 无趣的母语, 而是鲜活的、 生气勃勃的母语, 即使还很稚嫩, 却不再庸俗。
最后, 我要说的是——国语有戏, 不仅是与角色相遇, 在不同的角色中每个人将遇见自己, 发现自己身上更多的可能性, 这种力量一旦被激发出来将是神奇的。
国语书塾自开班以来就十分重视戏剧表演, 每次游学都会选择一部戏剧作品, 让你们到相关的历史人文现场演绎。 2018 年2 月的希腊之行, 在三千年前建造的圆形大剧场朗诵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独白, 只是一个开始; 8 月的意大利之行, 在威尼斯演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第四幕; 9 月的北京之行, 在老北大红楼演绎沙叶新的 《幸遇先生蔡》 第二幕和第五幕第六场; 12 月的南京寻梦之旅,演绎了 《桃花扇·余韵》 ……这年寒假, 我们专门邀请致力于大学校园戏剧三十多年的黄岳杰教授开了戏剧表演选修课, 排练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 《青鸟》 第三幕第四场《夜之宫》, 在随后的法国、 比利时、 荷兰之行中, 我们专程去了梅特林克的故乡根特, 在梅特林克博物馆演绎了 《青鸟》 ……黄岳杰教授还在雁荡山给部分童子排练过《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2019 年春天, 国语书塾请黄岳杰教授开了 “朗诵与表演” 必修课, 内容涵盖哈姆雷特、 李尔王、浮士德、 普罗米修斯的经典独白等。 8 月的德国之行, 你们在魏玛演绎 《浮士德》, 歌德的作品从此进入你们的生命中。 10 月的嘉兴之行, 在翻译家朱生豪故居的庭院里, 你们演绎了 《哈姆雷特》。 10月7 日, 在国语书塾两周年分享会上, 你们又将 《浮士德》 《青鸟》《荆轲》 演绎了一遍。 12 月国语书塾的秋季休业式以 “像云一样思想” 为主题, 童子们演绎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 《云》 ……
2020 年1 月, 黄 岳 杰 教 授 又开了一期 “朗诵与表演” 选修课,给部分童子初步排练了沙叶新的《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 第一幕。7 月, 国语书塾绍兴之行, 童子们去了蔡元培故居, 再次演绎 《幸遇先生蔡》, 许多童子脱颖而出。
三年来, 我看着童子们在戏剧表演中不断地突破自己, 收获了自信和母语学习的一个重要途径。 你们平时的习作, 甚至对话都流露出你们演过的剧本给你们带来的影响。
国语有种, 国语有路, 国语有戏, 三年的儿童母语教育实验, 让我和这个时代的儿童有了真实的生命连接, 这是我在五十岁之后的选择。 我把这个小小的实验概括为“三百千万” 四个字, 就是 “三年百课千人万里”。 如今第一批来国语书塾的童子, 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的学习, 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后来的童子也正在成长之中。 我又一次想起胡适先生喜欢的这句话:“要怎么收获, 先那么栽!” 相信时间会见证一切, 你们已经生成或正在生成的时间, 不会被风吹走, 而会留在生命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