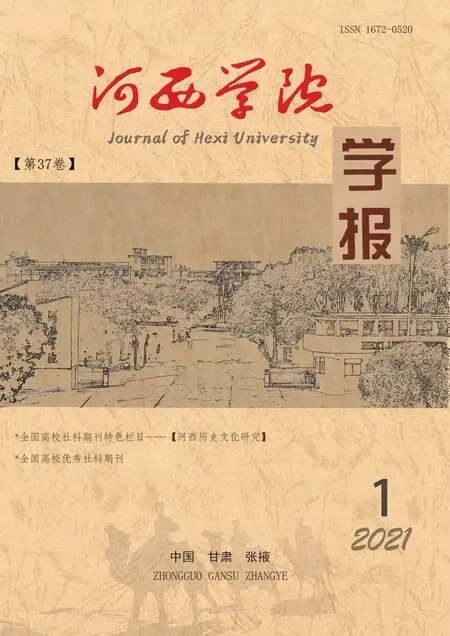马蹄寺石窟群探疑
朱瑜章 朱希帆
(河西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马蹄寺石窟群位于张掖南部祁连山下的临松薤谷及大都麻河山谷中,由北向南迤逦约30公里,由千佛洞、马蹄寺北寺、马蹄寺南寺(胜果寺)、上观音洞、中观音洞、下观音洞、金塔寺七处佛教石窟组成,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文献资料记载的缺失和当代记述的笼统或错讹,马蹄寺石窟的开凿、造像等方面至今仍存一些疑点。本文拟在考据、实地勘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石窟群六个疑点作以探解。
一、“神骥蹄迹”究竟是什么?
马蹄寺因“神骥蹄迹”而得名。这个“神骥蹄迹”现镶嵌在编号为8 号窟的马蹄殿内地面上(图1)。但面对这个“神骥蹄迹”,观瞻者恐怕都心照不宣认为,这个“神骥蹄迹”很可能是后来人为凿下镶嵌进去的,不可能是原始的“神骥蹄迹”。即使有一个原始的“神骥蹄迹”,由于年代久远,早已不知去向,怎么可能保存到现在?
关于原始的“神骥蹄迹”,历来有二种说法:

图1 马蹄殿马蹄印迹
一种说法是成书于明万历年间,刊行于清雍正年间《甘镇志》的记载:“马蹄山,城南一百里,岩石间有神骥足(迹)在焉,故名。”[1]这是最早关于“神骥蹄迹”的记载。但这个记载很笼统,“岩石间有神骥足(迹)”,是山崖、山顶的岩石还是山谷的岩石?这块有“神骥足(迹)”的岩石去向如何?“神骥足(迹)”是什么年代踏下的?印记有多大?都语焉不详。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甘州府志》基本照搬《甘镇志》的说法,说“临松山,城南一百里。俗名平顶山,一名马蹄山,岩石间有神骏足迹”。[2]在另一处则明确记载说:“马蹄印迹在山顶左。”[3]另一种说法是当地藏族民间的口头传说,说藏族的先祖神人格萨尔王骑着神马到过马蹄山一带,他的坐骑在山上踏下了一个蹄迹。还留下了一个“剑劈石”的神迹,至今矗立在山下。藏族的这个神话明显有附会之嫌。马蹄寺在唐宋时期是汉传佛教之地,元代藏传佛教进入河西,马蹄寺逐渐演变成了藏传佛教之地,于是就有人附会出了格萨尔王坐骑留下蹄迹的神话传说。
“神骥蹄迹”是虚妄的,不能把神话当作事实。但不能因此否认“岩石蹄迹”的客观存在。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岩石蹄迹”应该是一种自然现象,即所谓“石瑞”、“石字”。所谓“石瑞”、“石字”,就是石头上出现了某种瑞相图案或文字形象。其文化渊源要追溯到魏晋时期。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援引《魏氏春秋》《搜神记》《汉晋春秋》记载,魏明帝青龙年间,临松薤谷一带曾出现过“石瑞”、“石字”,“苍质白章”的石头上面关于“马”的瑞像和文字最多:“有石马七”、“马自中布列四面”、“大金马一匹在中”、“系五马”、“龙马”、“其文有五马象”、“其一有若马形而不成”、“为十三马、一牛、一鸟”、“马象皆焕彻如玉”等等。[4]其中马的图像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显然就是“神马”留下的印迹,“神马”自然是从天上下凡的。后来可能又发现了有马蹄印迹的石瑞,于是就衍生出了天马下凡在临松薤谷的石头上留了蹄迹的神话传说。马蹄寺“神骥蹄迹”的神话就这样产生了。
魏晋时临松薤谷发生“石瑞”、“石字”的神奇现象,很多人认为虚妄荒诞不可信。诚然,古籍中的记载难免有夸张之嫌,但“石瑞”“石字”却是客观存在。一场大雨引起山洪暴发,山崖断裂,大石被冲出谷口,河床下面被淹埋的大石头也被冲刷出来,这就叫“开石”;人们发现整体苍色的“开石”上嵌入的白色或其它颜色的石质线条和花纹恰巧构成某种山水花鸟动物图案或文字形象,认为这是上天降下的瑞相,称其为“石瑞”。马蹄寺的得名,剥去笼罩在它身上的神奇光环,其真实原因则有其科学的依据。
二、郭瑀最初在哪里开凿石窟?
马蹄寺石窟群是佛教圣地,几乎人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在临松薤谷开凿石窟的是前凉时期的河西大儒郭瑀。据《晋书》记载: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荷卒,瑀以为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服重,盖圣人谦也,遂服斩衰,庐墓三年。礼毕,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5]
郭荷是张掖的一位经学大师,隐于张掖北部的东山。敦煌人郭瑀远道来张掖“师事郭荷”,而郭荷对郭瑀也不吝赐教,“尽传其业”。经过在郭荷门下的潜心苦学,郭瑀“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成为继郭荷之后河西一代经学大师。郭荷身后,郭瑀从张掖北部的东山迁徙到了张掖南部的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临松薤谷,由发源于祁连山的雨雪水冲刷成的几条山谷河道组成,即今马蹄河谷。郭瑀来到临松薤谷,一方面“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修身养性,这是典型的道家做派;另一方面在这里招收后学,设帐讲学,著书立说,“弟子著录千余人”,可以想象当年临松薤谷一带师生济济一堂,书声琅琅的情景。
郭瑀在临松薤谷“凿石窟”招收弟子讲学,亦即办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石窟”学校,弟子多达“千余人”。这“千余人”应该是招收的历届学子总数,不可能是一次性在临松薤谷“石窟”学校注册的弟子人数。即使一届学子有几十人或上百人,这些人在临松薤谷的“石窟”学校要学习,还要吃、住,必须有一个比较大的场所才能解决“办学”的问题,而史书上这方面的详细记载阙如。
考察今之马蹄寺石窟群,远在东南部几十里外的上中下观音洞、金塔寺因地处偏狭,交通不便,完全可以排除在郭瑀讲学场所之外。剩下的就是千佛洞和马蹄寺北寺、南寺。千佛洞毗邻山门,前临马蹄河,进深短,场所小,现存石窟都比较小,距离“临松薤谷”还有约十多里路程,却跟山外的俗世很近,不适合做修道讲学场所。下剩的只有南部的马蹄寺北寺和南寺了。南寺又叫胜果寺,殿宇建在薤谷一山洼间,西南是云杉林,只有靠北的山上有一些石龛石塔,没有开凿成形的石窟,也不可能是郭瑀开凿石窟讲学的地方。那么,可以确定当年郭瑀开凿的石窟就在今天的北寺无疑。
北寺开凿在一座南北走向面东的红砂石山崖上,现存5层窟龛,有编号的洞窟9个,大小窟龛30个,为历代开凿而成(图2)。一层较大的石窟有7号窟站佛殿、8号窟马蹄殿,其中7 号窟站佛殿石窟规模最大,深33.5m,宽26.3m,高约15m。可以推知,当年郭瑀率众弟子首先应该在站佛殿所在的山崖下面开凿石窟,作为讲学的场所。北寺一层的众多石窟可能就是在当时陆续开凿的。本来是儒学、道学的讲习场,后经历代开凿扩大,成了国内单体面积最大的佛教窟殿。

图2 马蹄寺北寺外景
当然,也不排除当年郭瑀一边率众弟子开凿石窟,一边在山崖下面建起一些土木结构的房屋做校舍之用的可能性。临松山上遍布松树,就近伐木比较便利;但不宜在山上取土制土坯。因为一者山坡上石多土少,二者土性松软,腐殖质多,不能作制土坯之用。建房所用土坯,还得到十多里外的山外取土制做,工程量很大。当然,也可以建造一些小型的木石结构或纯木板房的房屋。木石结构即框架用木头构造,墙用石块垒成,但这种房屋冬天很冷。相较之下,恐怕还是开凿石窟比较便利。石窟所在的山由红砂石组成,开凿相对容易些,还因为石窟冬暖夏凉,适宜人居住。更因为郭瑀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认为住在石窟宜于修炼。
郭瑀对他带领弟子开凿的临松薤谷石窟情有独钟。当他在临松薤谷设帐讲学声名鹊起时,引起了前凉政权的瞩目,前凉国主张天锡曾派使者孟公明持节修书从武威到临松薤谷征召郭瑀,而郭瑀不为高官厚禄所动,“瑀指翔鸿以示之曰:‘此鸟也,安可笼哉!’遂深逃绝迹”[6]。孟公明拘其门人,郭瑀不得已被逼出仕,至凉州,值张天锡母卒,郭瑀借机还于临松薤谷继续隐居、讲学。
郭瑀的大弟子刘昞,字延明(一作彦明),敦煌人,是继郭瑀之后的另一河西大儒,其著述颇丰。刘昞年轻时曾跟随郭瑀在临松薤谷就学,因人品优秀,学业突出,被郭瑀选为快婿。刘昞学成后出山入仕,被西凉国主李暠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西凉亡,刘昞又被北凉沮渠蒙逊征为秘书郎,沮渠牧犍尊为国师。北魏灭北凉后,将大量的河西人口迁往平城,刘昞因为年老,被批准留在家乡。晚年的刘昞又回到年轻时曾受业的临松薤谷,“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7]。“韭谷窟”即临松薤谷石窟,“韭谷”,即薤谷。
三、“站佛殿”,还是“藏佛殿”?
上文说到当年郭瑀很可能首先在今编号为7号窟所在的地方开凿洞窟,后经历代开凿扩大而成为马蹄寺石窟群中最大的洞窟。当地的人们过去都称此殿窟为“站佛殿”,今天仍然叫“站佛殿”。可是,现在洞窟门口的解说文字上说“又称藏佛殿”(图3)。一个洞窟怎么会有两个名称呢?

图3 站佛殿简介

图4 站佛殿内重新塑立的站佛
考“站佛殿”的命名,是因窟内前殿原有一尊高大的释迦佛站立塑像而命名。这尊站佛足立地面,头顶窟顶,高约15m。张掖市内大佛寺有国内最大的卧佛,山丹土佛寺有国内最大的坐佛,而马蹄寺站佛殿的站佛堪称张掖地区最大的站佛。称“站佛殿”,可谓名归实至。这尊站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被人为毁坏,荡然无存。近几年又重新塑立起来(图4)。上世纪八十年代给马蹄寺石窟编号命名时,新的站佛还未塑立,命名者根据当地居民口头说法将7号窟命名为“藏佛殿”,“藏”读为zàng。还请人题写了匾额(图5)。“站佛殿”为何改称“藏佛殿”呢?很可能是方音的讹读加宗教的演变造成的。原来当地有方音把舌尖后音“zh、ch、sh”读为舌尖前音“z、c、s”,把“站”(zhàn)读为“zàn”;方音中又“an”“ang”不分,于是就把“站”读为“zàng”;又因马蹄寺是藏传佛教之地,于是就依“zàng”的读音题写为“藏佛殿”。可能是因为文物管理部门后来觉得搞错了,90年代后文物普查时又恢复为“站佛殿”,并重新编写了洞窟介绍,可是在文字介绍中还是加上了“又称藏佛殿”这样的话语,且有人变读为“藏(cáng)佛殿”,并解释说因为殿内藏有佛像而命名,这真是多此一举!总之,“站佛殿”是原名,名副其实,“藏(zàng)佛殿”、“藏(cáng)佛殿”都是以讹传讹,以讹写讹。佛教寺窟的命名解说多有此类错讹情况,例如民乐童子寺曾讹传为“洞子寺”,临泽仙姑寺讹称为“香古寺”,都属以讹传讹以讹题讹,必须加以辨析,返璞归真。

图5 “藏佛殿”匾额
四、站佛殿的明代进香题记有何史料价值?
笔者在多次考察中发现了马蹄寺北寺7号窟即站佛殿内的一处残存的明代题记。此题记位于前室大厅西北角一个已被毁的佛龛底座下面,背景为一幅残存的1m×2.4m壁画,壁画年代不详,可能为元代或明代早期所画,画面内容已经漫漶不清,其中一只神兽爪和上部的粗墨线条比较清晰(图6)。壁画上面几乎写满了从明代万历年间到崇祯年间香客们题写的进香记录。下面分区块录入并作简说。
(一)左下部大字体题记
左下部大字体的题记有9行(图7),从字体看,应为同一人所书写:
普山寺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山丹衛信官章應龍
劉氏進香一次
萬曆□□□年六月二十九日
山丹衛信官章應龍
劉氏
男章光國
□解氏進香一次

图6 站佛殿前室残存明代壁画及题记

图7 壁画左下部题记
按,这是明万历年间山丹卫信官章应龙两次携家人到马蹄寺朝圣进香留下的题记。山丹卫,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徙陕西行都司治甘州,领卫十二,山丹卫为其一。[8]信官,古代官员祈祷神灵时表示虔诚的自称。山丹卫官员章应龙第一次携妻刘氏到马蹄寺进香的时间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九月二十三日,“□氏”依第二次题记“刘氏”可确定章应龙的妻子为刘氏。第二次去马蹄寺进香的时间是“万历□□□年六月二十九日”,年份字模糊难辨,“信”字后面漶漫不清的字应为“官”字。这次是携妻刘氏、儿子章光国、儿媳解氏一同进香。两次进香的题记依次排布在一起,由此推测第二次进香的时间跟第一次进香的时间应该相距不远,有可能是万历二十四年或二十五年,因为如果两次题记的时间相距过大,第二次题记的地方就有可能被别人所题占用。两次题记均用毛笔书写,大小一致,字体一样,应为章应龙本人亲自题写无疑。又,“普山寺”三字为何与后面的两次题记隔了一段空档?很可能是在第二次题记之后章应龙要补题“普山寺”,因题记右侧有一些别人留下的小字题记,故避开小字题记,在右侧空白处补题了“普山寺”。
(二)左上部较大字体题记
此处题记共9行(图8):
山丹衛香客
賈美 何氏
男賈光耀秋保子
崇禎元年六月二十四日
近香五次平安
□□□王□近香三次
□□□

图8 壁画左上部题记
李家保近香
□□趙氏
按,前5行为明崇祯元年(1628)六月二十四日,山丹卫香客贾美,携妻子何氏和两个儿子到马蹄寺进香的题记。大儿名贾光耀,二儿尚小,还没起学名,乳名“秋保子”。进香的目的显然是祈求佛菩萨保儿子平安。另外的题记为王□、李家保所题。“近香五次”、“近香三次”,是前后到马蹄寺进香的次数总和。“近香”即“进香”,“近”字为一些文化程度低的香客写的别字。
(三)中下部题记
壁画中下部较大字体题记共6行(图9):
楊應□上香□次
楊應文上香□次
雷□□上香□次
□□□上香□次
葛□上香□次
葛林上香二次
按,此当为一组6 人同时结伴到马蹄寺上香题记。杨应□、杨应文为弟兄二人,葛□、葛林亦为弟兄二人。其具体上香时间缺。
(四)其他小字体题记
1.右上角似为二句诗,或为对偶题记(图10):
馬蹄靈山是□□
古來顯就□□□
2.右下部小字隐约不清,能基本识读的3行是(图11):
崇禎六年二月□日
秦□□王服

图9 壁画中下部题记

图10 壁画右上部题记

图11 壁画右下部题记

图12 “普山寺”右侧题记
□□到此上香
3.在大字体的“普山寺”右侧,有1行小字题记依稀可以辨认(图12):
崇禎九年六月初一信官侯廷上香六次
下面有“马蹄寺”三字。4.在大字体的“普山寺”左侧,有5行小字题记依稀可以辨认(见图7):
賀□恩進香伍次
□相朝五次
涇陽縣衛□□蘆堽 姚深 陳奉
標兵營家丁湯□科場遇□□
三十二年六月十二日近香
按,“家丁”非指富豪家看家护院的仆役,而是“标兵营家丁”,古代将领在正规军队外私人组建的亲信精锐部队中的军人亦称“家丁”。“三十二年”前缺年号,考“万历”帝在位48年,之后的“泰昌”帝在位仅一个月,“天启”帝在位7年,“崇祯”帝在位17年。而所有题记均为“万历”“崇祯”年间所题,由此可以基本确定此题记时间应为“万历三十二年”。
5.在上面“标兵营”2行题记的下面,又有3行题记(见图7):
甘州左衛都司什字□□
崇禎四年六月十八日進香
□□□
6.画面上还有4行藏文题记,截图以备考:

小结:将以上明代题记综合起来看,虽然为香客们随手题写的进香记录,字体大小有别,书写工整与潦草不一,但这些题记仍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首先,从题记中得知马蹄寺还有一个别名“普山寺”,这在《甘镇志》《甘州府志》及其他书籍、文献中都没有记载。“马蹄寺”应该是原名、俗名,明永乐十四年敕赐“普观寺”[9]。“普山寺”或为民间将“普观寺”改造而成的别名。
其次,从题记中可以看出,明代万历年间到崇祯年间的六、七十年里,是马蹄寺香火很旺盛的一个时期。人们进香的时间多为一年中农历六月、九月份,六月初三是护法韦陀菩萨圣诞日,六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成道日,九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出家日,九月三十日是药师佛圣诞,在这些佛教节日前后香客们纷纷前往马蹄寺朝拜进香。香客中有官员,也有“标兵营”的军人,更多的是普通民众;有单独一人前往进香,也有携家人一同前往进香,还有几个朋友相约一起去进香;有本地民众,也有外籍人士;有汉族信众,也有藏族信众。尤其是那句“標兵營家丁湯□科場遇□□(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十二日近香”题记,让人感到新奇。一位张掖标兵营“家丁”,可能在参加武举科场考试中遇到了挫折,于是专程来到马蹄寺朝拜进香,以祈求佛菩萨保佑下次科场考试能有好运。从中可窥见明代中后期河西地区佛教信仰的普及程度及各色人等的社会心理状态,是研究丝绸之路佛教史及明代社会心理的珍贵资料,从中也可窥见马蹄寺历史的一个侧面。
第三,从众多的明代题记中可以看出,当时马蹄寺寺院的管理还是比较松散,香客们可以随手在壁画上书写题记,这显然是对壁画的一种破坏,但当时似乎没有人来制止这种不文明的涂鸦行为。当今社会所诟病的一种不文明陋习,就是一些人喜欢在旅游地随手书写“×××到此一游”,原来这种陋习由来已久,从古到今陈陈相因,要杜绝也绝非易事。
五、“三十三天”开凿于何时?
马蹄寺3号窟俗称“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是佛教用语,佛经中说须弥山顶中央为帝释天,四方各有八天,合起来共三十三天。马蹄寺3 号窟实际上是一组洞窟集群,该窟有5 层,地面距第5 层共42m,共开凿21个窟龛,从外观上看,犹如一座宝塔(见图2)。从第1层到第5层,仅靠一山崖内开凿的石洞甬道连通,甬道呈“之”字形。笔者在考察中发现了甬道内一处石刻题记,位置在第一层到第二层甬道左壁上,约1m2。由右到左,依次阴刻了3行字(图13):
造主人楊□
大明成化十年五月
初十日造
按,“造主人”姓名为“楊□”,“□”字为“金”字旁,右边的字符磨灭难以辨认,疑为“鈌”或“鈇”,不能确定。
石刻题记左侧上部刻三个“大”字,下面刻一树,疑为神话中的扶桑树,也可能是佛传神话中的菩提树,树顶有两只左右对称神鸟。题记右侧刻一站在莲花座上的菩萨(图14),洞壁上还有石刻佛塔二座(图15),石刻仙人像一幅(图16)。从洞壁上的凿刻线条印迹及佛塔凸出的形制看,石刻题记、菩萨、神树、佛塔、仙人应为开凿石洞的同时一次性凿刻而成,不可能是后来补凿的。
题记中的“大明成化十年五月初十日造”,“造主人杨□”提供的信息十分重要,它有助于我们搞清楚马蹄寺三十三天石窟开凿的很多疑点。

图13 甬道左壁石刻题记

图14 甬道左壁石刻菩萨

图15 甬道左壁石刻佛塔

图16 甬道左壁石刻仙人像

图17 三十三天窟龛题记
首先,过去对三十三天石窟开凿于何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根据这个石刻题记,可以基本确认马蹄寺三十三天石窟开始开凿的时间为明成化十年(1474),此后的若干年内连续开凿并最终落成了三十三天5层21个窟龛。笔者从三十三天第三层的窟龛壁上发现了一处题记,上书:“弘治四年六月十七日左衛百戶陳宣”(图17)。说明三十三天甬道、窟龛从开凿到造像全部完成,很可能就在从成化十年(1474)到弘治四年(1491)近二十年的时间段内。二十年时间乍看起来有点长,但这项巨大的佛教工程确实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甬道内比较狭窄,不可能容纳很多人一起施工,因此进度很慢;洞窟、佛龛开凿好了,还要抹浆、打底、造像、上色、画像等,所以,开凿并落成三十三天用了二十年左右时间应该是可信的。从北朝十六国时期的前凉河西大儒郭瑀最初开凿洞窟起,历经北凉、北魏、隋唐、西夏、元、明、清,历代都有洞窟开凿。马蹄寺石窟的开凿前后延续了一千多年时间,堪称中国佛教石窟开凿史上历时最长的佛教工程之一。
关于“三十三天”的开凿年代,学界倾向于元代,主要证据为窟龛内有的造像、壁画有元代风格特点。如杜斗成先生认为三十三天佛龛“四壁为元代影塑千佛或壁画,有的壁画为明代重绘”。[10]最新出版的“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之《马蹄寺石窟》在“马蹄北寺石窟”的文字介绍中说:“洞窟均开凿于元代。据现存于各窟内的造像、壁画特点分析,大多是元代作品。”[11]所谓造像、壁画有元代风格特点,也就是有藏传佛教造像、壁画特点。窟内壁上的千佛和壁画有元代风格,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元代所绘,明代的画工依照元代的风格所绘完全有可能。更何况明代的马蹄寺实际上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杂糅之地。据《甘州府志》记载,明永乐十四年马蹄寺敕赐普观寺,佛教造像“至明始著,番僧至五六百人,人知其为甘郡第一丛林”。[12]这里明确说佛教造像“至明始著”,并没说“至元始著”;而且明代马蹄寺常驻“番僧至五六百人”。现存甬道和窟龛的文字题记均为明代所题,未见有元代的题记。所以明代开凿的窟龛造像和壁画有藏传佛教风格特点是很自然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元代开凿了二层以上至三十三天的窟龛,原先自下而上由栈道相通,后来窟体外部坍塌后栈道也随之被毁,所以又从内部开凿了“之”字形甬道。[13]这种说法令人怀疑。其一,没有任何关于元代开凿石窟和石窟坍塌的文献资料记载,《甘镇志》《甘州府志》上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其二,现场没有任何存留的石窟外部坍塌实物佐证,山崖下没发现坍塌下来的大石块。其三,如果说原先以外部栈道为通道,构建栈道须先搭构施工架,笔者实地勘察发现,石窟崖壁下紧挨陡峭的坡,上面的崖壁中部又向前凸出,没有条件自下而上搭起施工架。其四,如果说窟体外部坍塌了,那么连同窟龛也坍塌了,意味着整个三十三天洞窟都被毁了,明代万历年间又重新开凿了三十三天通道和窟龛,如此耗时耗力耗财的巨大工程要先后进行两次的可能性几乎不可能存在。
其次,题记中有“造主人杨□”。“造主人”,顾名思义,就是营建开凿洞窟或造像的主人。但这位“造主人杨□”是什么身份,因没有旁证资料,一时难以确认。敦煌归义军时期,敦煌当地佛教界设有“都僧统”这一僧官,“都僧统”是地方最高一级僧官,负责管理僧侣、营建寺窟、举办佛事活动等。担任“都僧统”的都出身于敦煌豪门大族。据专家研究,先后担任沙洲都僧统的有洪辩、翟发荣、唐悟真、(康)贤照、氾福高、陈法严、阴海晏、王僧统、(孔)龙辩、氾僧统、法嵩、钢惠等。[14]到了明代,是不是还延续着“都僧统”这样的僧官制?“造主人杨□”是张掖的僧官?还是洞窟开凿造像的出资人(供养人)?这一切都暂存疑待考。
六、金塔寺石窟造像色彩为何那么“新”?
金塔寺位于马蹄寺东南方向大都麻河一源流旁,周围崇山峻岭,面南的一红赭色山崖上开凿有东西两个洞窟(图18)。两窟都开凿中心塔柱,中心塔柱四面分三层开龛造像,每面下层均开一圆拱形大龛,每龛内均塑一结跏趺坐佛,坐佛两侧各塑胁侍菩萨,中上层塑满了各菩萨及泥塑飞天等。菩萨均头戴宝冠,颈饰璎珞,身披宝缯,或坐或立,神情各异,姿态生动。泥塑飞天作凌空飞舞之态,飘带飞扬,栩栩如生。各个造像色彩鲜艳,如新塑妆过一样(图19,图20)。洞窟壁不开龛,均绘有壁画或千佛像。

图18 金塔寺石窟

图19 金塔寺东窟泥塑飞天

图20 金塔寺西窟思惟菩萨
据研究,金塔寺石窟始开凿于北凉或北魏时期,佛教造像即开始于其时。由于过去石窟前面没有封闭,受风雨侵蚀,造像、壁画风化严重,后西夏、元、明各代均有补塑和重绘。而当代凡是亲自到金塔寺瞻仰过的人,包括一些考察者、研究者,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金塔寺的泥塑佛、菩萨、飞天都色彩鲜艳,红、绿、蓝、白、赭各种颜色分明,如新绘过的一样,都会产生一个疑问:金塔寺石窟造像为何那么“新”?甚至有人惊叹: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塑像色彩还是那么新!这显然是错觉。我们可以推测,即使元代或明代曾经给金塔寺的造像补过妆,历经几百年的风化色彩还那么鲜艳,仍然是不可能的。
笔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了金塔寺造像色彩为何那么“新”的原委。笔者于2018 年秋回老家民乐县新天镇王什村,见到了小学时的同学雷祥。雷祥一家是村里的“画师”之家,民间俗称“画匠”。他的祖父、父亲是两代祖传的“画匠”。闲聊中得知,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雷祥的祖父就经常去周边的寺庙、道观给塑像上妆、绘壁画,后来领着儿子雷和春(雷祥之父)继续当“画匠”。这种地方上的“画匠”身份,如同敦煌莫高窟第三窟壁画上所题的“甘州史小玉”、舞剧《丝路花雨》中虚构的“神笔张”是相同职业人。据雷祥回忆,他的祖父、父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经给新天镇北部的灵隐寺佛教塑像添过妆,画过壁画,灵隐寺于七十年代被毁坏。雷祥回忆:他八、九岁时,大约是1963 年至1964年间,有关部门要给金塔寺加装木栅栏和门窗,他父亲去给木栅栏和门窗上油漆,期间雷祥曾跟随父亲去金塔寺玩,吃住都在金塔寺洞窟内,在那里待了好多天。由于木匠活比较慢,导致油漆活时干时停。他父亲看到洞窟内很多佛像上的色彩剥落了,暗淡了,心中不忍。雷和春本身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且画匠行业公认为给寺院的佛教塑像添色、描新是一种善事。所以利用油漆栅栏门窗的闲暇时间,顺便给塑像补妆、添色、描新。这件事没有更多的人知道,更不被后来考察过金塔寺的专家学者们所知。六十年代雷画匠给金塔寺造像补妆、添色、描新,时隔二十多年,八、九十年代去看到的造像色彩自然很新,原因就在雷画匠身上。如今雷和春画师早已作古,他的儿子雷祥的回忆应该解答了金塔寺石窟造像色彩为何那么“新”的疑点(图21)。也由此可以推知,历代都有民间画工给佛教寺窟的造像补妆、描新之事,只是此类事多不为人所知而已。文物部门确认造像塑造年代时,一定要考虑历代民间画工补妆这个要素。笔者谨以此文作记,以备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