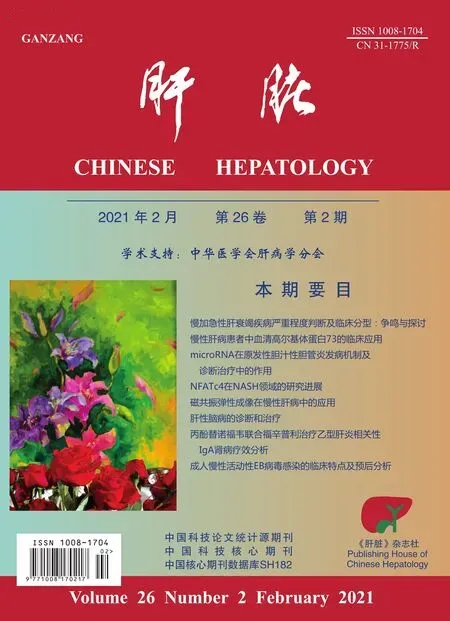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免疫治疗进展
韩瑞瑞 张锦 马立翠 南当当 李士新
据报道[1],2018年全球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新增病例约84.1万例,发病率位居第六位;死亡约78.2万例,死亡率位居第四位。我国数据显示,PLC发病率及死亡率分别位居第四位和第二位[2]。其中,有44.0%~62.2%的PLC合并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在无任何干预措施的情况下,PLC合并PVTT的中位生存期仅为2.7个月[3],这可能是PLC预后不良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关于PLC合并PVTT的治疗,国际上仍未达成统一认识。我国指南推荐[4],以肝功能基础为前提,根据肿瘤情况和程树群教授提出的PVTT程氏分型[5],行手术切除、肝动脉栓塞化疗(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放疗、系统治疗、区域性治疗、对症支持治疗以及通过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联合多种治疗手段.最大程度地使患者获益;在欧洲肝病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EASL)指南中[6],依据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BCLC)分期系统,PLC合并PVTT属于C期(晚期),推荐靶向治疗;2020年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肝胆肿瘤临床实践指南将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共同作为晚期肝癌的一线治疗[7]。PLC作为炎症相关肿瘤,因其独特的免疫微环境,免疫细胞的抗肿瘤活性被抑制,因此,免疫治疗有望成为PLC最有前景的治疗方法之一[8]。PLC的免疫治疗主要包括肿瘤疫苗、过继细胞疗法、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自从2011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上市后,肿瘤的免疫治疗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本文就PLC合并PVTT免疫治疗中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作用机制及治疗进展作一综述。
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作用机制
肿瘤细胞死亡时会释放相关抗原,在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分子的作用下,这些抗原被树突状细胞呈递给T细胞,启动和激活了针对肿瘤特异性抗原的效应T细胞。活化的效应T细胞经过血液运输并穿过血管内皮细胞进入肿瘤组织,通过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TCR)与肿瘤特异性抗原的相互作用,识别并杀死肿瘤细胞[9]。然而,PLC的肿瘤细胞及微环境会产生多种免疫抑制分子,主要有程序性死亡受体1或配体1(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 1 or ligand 1,PD-1/PD-L1)以及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 antigen 4,CTLA-4)2条通路,协助肿瘤逃避免疫损伤。
(一)PD-1/PD-L1 活化的T细胞、B细胞以及NK细胞会诱导表达PD-1。抗原递呈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s,APC)通过MHC识别肿瘤抗原并迁移至淋巴结,通过TCR将抗原呈递给T细胞,T细胞被激活,若APC表达的PD-L1与成熟T细胞上表达的PD-1之间相互作用,T细胞将不会被激活。活化的T细胞迁移至肿瘤部位,识别并攻击肿瘤,而T细胞分泌的干扰素γ(interferon gamma,IFN γ)可刺激肿瘤细胞表达PD-L1,PD-L1阳性的肿瘤细胞与活化的T细胞上的PD-1相互作用会引发复杂的抑制反应,从而获得免疫耐受[10],如图1。

图1 PD-1/PD-L1通路在原发性肝癌免疫中的作用机制
(二)CTLA-4 T细胞激活时诱导表达CTLA-4,它是CD28的一个序列/结构同源物。CTLA-4和CD28竞争性地与APC表面的B7配体结合,且前者具有更高的亲和力。CTLA-4与B7配体结合会产生一个负信号,趋向于使T细胞失活,从而抑制免疫反应;而CD28-B7相互作用对激活和维持T细胞的活性至关重要[11],如图2。在T细胞激活过程中,上述免疫抑制机制被CTLA-4抑制剂所拮抗,进而激活并促进T细胞增殖,增强其对肿瘤细胞的免疫损伤,进一步起到杀灭肿瘤细胞的作用。

图2 CTLA-4抑制剂的作用机制
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进展
在过去的十年中,以前无法治疗的恶性肿瘤如非小细胞肺癌、黑色素瘤以及许多其他恶性肿瘤通过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PD-L1和CTLA-4抑制剂),很大程度上使患者获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迅速成为其新的治疗标准。在PLC免疫介导的发病机制背景下,基于单臂研究的初步结果,在抗肿瘤免疫重建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经显示了治疗PLC合并PVTT(简称晚期肝癌)的潜力[12]。以下将分别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单药及联合治疗进行阐述。
(一)单药治疗
1.CTLA-4抑制剂
CTLA-4抑制剂在增强抗黑色素瘤T细胞免疫后,一部分患者取得了持久的生存获益,虽然抗CTLA-4单药治疗所有患者的3年生存率为22%,但其为长期的免疫重建提供了证据[13]。
Tremelimumab是首次在丙型肝炎病毒相关的晚期肝癌中被检测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21例患者纳入这项研究,部分缓解率为17.6%,疾病控制率为76.4%,中位进展时间为6.48个月,虽然缺乏长期生存数据,但报告中位总生存期为8.2个月,6个月和1年生存率分别为64%和43%,表明Tremelimumab对晚期肝癌可起到一定的抗肿瘤作用[14]。在Duffy等的研究中[15],每4周以两种剂量水平(3.5和10 mg/kg)给予Tremelimumab,总共6剂,维持治疗3个月,在第36天给予消融,以引起协同免疫原性细胞死亡。结果显示,患者6个月和12个月无进展生存的概率分别为57.1%和33.1%,中位进展时间为7.4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12.3个月。最常见的临床不良反应是瘙痒,无剂量限制毒性记录。证明Tremelimumab联合肿瘤消融治疗晚期肝癌安全有效。但令人疑惑的是,目前CTLA-4抑制剂单一疗法还没有大型的Ⅲ期临床试验。
2.PD-1/PD-L1抑制剂
CheckMate-040是一项开放、非对照、Ⅰ/Ⅱ期剂量递增和扩展的试验,用来评估PD-1抑制剂纳武单抗(nivolumab)治疗晚期肝癌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在剂量递增阶段,每2周给予纳武单抗0.1~10 mg/kg(采用3+3设计),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为15个月,客观缓解率为15%,出现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似乎与剂量无关,也没有达到最大耐受剂量,25%的患者(12/48)发生3/4级事件;在剂量扩展阶段,每2周分别给予乙肝病毒感染组、丙肝病毒感染组、未使用或不耐受索拉非尼组(无病毒性肝炎)、索拉非尼进展组(无病毒性肝炎)4组患者纳武单抗3 mg/kg,客观缓解率为20%,中位进展时间为4.1个月,6个月的总体存活率为83%,9个月的总体存活率为74%[12]。基于此项研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纳武单抗用于接受过索拉非尼治疗的肝癌患者。在后续的CheckMate-459随机、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中,纳武单抗与索拉非尼相比,两组的中位总生存期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但作为晚期肝癌一线治疗,其总生存期、客观缓解率以及完全缓解均有临床获益,安全性与之前报告一致[16]。
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是一种抗PD-1的单克隆抗体,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在Keynote-224中得到评估。Keynote-224是一项非随机、多中心、非盲法的Ⅱ期临床试验,共纳入104例因疾病进展或不耐受而停用索拉非尼的晚期肝癌患者,受试者每3周静脉注射200 mg帕博利珠单抗,持续约2年,客观缓解率为17%(18/104),其中77%的患者至少有9个月的应答,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4.9个月(95%CI:3.4~7.2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12.9个月(95%CI:9.7~15.5个月),1年总生存率为54%(95%CI:44%~63%),24%(25/104)的患者出现了与治疗相关的3级事件,最常见的不良事件是7例(7%)患者的天门冬氨酸转氨酶浓度升高,3例(3%)患者发生了免疫介导性肝炎,但没有报告病毒暴发的病例。以上结果表明,帕博利珠单抗对既往索拉非尼治疗后的晚期肝癌患者有效且可耐受[17]。基于Keynote-224的研究结果,FDA批准了帕博利珠单抗用于索拉非尼治疗后肝癌患者的二线治疗。随后的Keynote-240是帕博利珠单抗在晚期肝癌二线治疗的一项随机、双盲、Ⅲ期临床试验,纳入索拉非尼治疗后进展或不耐受的患者413例,按2:1随机分为帕博利珠单抗组(278例)和安慰剂组(135例),每3周静脉注射200 mg的帕博利珠单抗或盐水安慰剂,治疗至少35个周期。帕博利珠单抗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13.9个月(95%CI:11.6~16.0个月),安慰剂组为10.6个月(95%CI:8.3~13.5个月)(HR,0.781;P=0.023 8),两组的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3.0个月(95%CI:2.8~4.1个月)和2.8个月(95%CI:1.6~3.0个月)(HR,0.718;P=0.002 2),两组分别有18.6%(52/278)和7.5%(10/135)的患者发生3级或3级以上与治疗的相关不良事件,没有发现乙型或丙型肝炎的暴发[18]。虽然两个主要终点(总生存期、无进展生存期)均有改善,但仍未达到预先设定的统计学显著性界值。
抗PD-L1单克隆抗体durvalumab的一项多中心、Ⅰ/Ⅱ期临床试验显示[19],40例肝癌患者每两周静脉注射durvalumab 10 mg/kg,客观缓解率为10.3%(95%CI:2.9%~24.2%),中位总生存期为13.2个月(95%CI:6.3~21.1个月),1年生存率为56.4%(95%CI:38.8%~70.7%),3~4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20.0%,初步评估了其安全性及抗肿瘤活性。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单药治疗临床上虽然有一定获益,但疗效欠佳,故进一步探索联合治疗。
(二)联合治疗
1.CTLA-4抑制剂联合PD-1抑制剂
伊匹木单抗(ipilimumab)是CTLA-4的单克隆抗体,Checkmate-040测试了其与纳武单抗联合治疗晚期肝癌的疗效及安全性。将患者随机分为3组,给予不同剂量的伊匹木单抗和纳武单抗。结果显示,3~4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37%,皮肤毒性最常见,患者对于联合治疗有良好的耐受性;客观缓解率为31%,明显优于纳武单抗单药治疗(14%)[20]。
2.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分子靶向药物
目前的研究表明,异常的肿瘤微环境阻碍T细胞的浸润,同时,肿瘤血管内皮细胞也抑制T细胞的聚集、黏附和活性,从而有助于肿瘤细胞的免疫抑制[21]。因此,通过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尤其是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有助于免疫细胞进入肿瘤组织,同时,也可解除VEGF对APC的抑制,激活免疫反应,起到协同抗肿瘤的作用[22]。
阿替利珠单抗(atezolizumab)及贝伐珠单抗(bevacizumab)分别是PD-L1、VEGF的单克隆抗体,IMbrave150Ⅲ期临床研究评估了二者联合与索拉非尼对比治疗不可切除肝癌的疗效及安全性。将501例患者以2:1随机分为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组(336例)与索拉非尼组(165例),给予阿替利珠单抗1 200 mg+贝伐珠单抗15 mg/kg每3周1次,索拉非尼400 mg每日2次,两组总生存期的风险比(HR)为0.58(P=0.0006),无进展生存期的HR为0.59(P<0.000 1),客观缓解率分别为27%和12%(P<0.000 1),3~4级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分别为57%和55%。与索拉非尼相比,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有显著的临床获益,且有良好的安全性[23]。2020年NCCN指南推荐索拉非尼、仑伐替尼及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为晚期肝癌的一线治疗方案[7]。
仑伐替尼(lenvatinib)是一种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研究表明[24],在VEGF过表达的肝癌模型中,仑伐替尼通过抑制VEGF信号通路,从而发挥其抗肿瘤和抗血管生成活性。帕博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的Ⅰb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客观缓解率为44.8%(30/67),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为18.7个月,62.7%(42/67)的患者发生严重不良事件,提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及尚可接受的安全性[25],其Ⅲ期临床试验(LEAP-002)正在进行中。Study 117是纳武单抗联合仑伐替尼治疗不可切除肝癌的Ⅰb期临床研究,纳入30例患者,均发生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手足综合征及发音困难最常见,客观缓解率为76.7%(95%CI:57.7%~90.1%),抗肿瘤活性高,不良事件可控[26]。
3.局部治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局部治疗(如TACE、消融等)所致的肿瘤组织缺血或细胞毒性作用可导致免疫原性细胞死亡,激活APC,从而促进抗肿瘤免疫反应[27]。一项meta分析提示,以TACE为主的微创治疗后辅助细胞免疫治疗肝癌,在短期反应和长期生存等方面均可提高临床疗效[28]。TACE术后给予帕博利珠单抗的Ⅰb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50%的患者发生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皮疹、腹泻等,二者联合无协同毒性[29]。
三、总结与展望
PLC合并PVTT发生率高,预后不佳,免疫治疗虽有一定的抗肿瘤反应,但其改善长期生存的作用还需进一步探索。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治疗对比,联合治疗似乎有更好的临床获益,但可能出现联合毒性作用。为了充分利用医疗资源及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检测生物标志物来预测免疫治疗的反应十分重要,以达到个体化治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