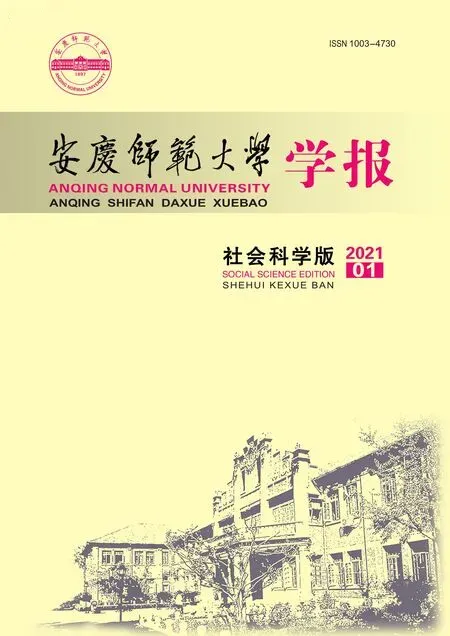创作目的与真实性:宋代碑文撰写者的理论思考与应对策略
杨树坤
(廊坊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廊坊065000)
碑的概念非常宽泛,本文所论及的碑主要指墓碑,也包括神道碑、墓表、墓碣等立于地表之上的志墓碑刻,碑文即刻在志墓碑刻上的文字①各朝代的作者除了撰写碑文,也往往会撰写数量更多的墓志。墓志不同于碑文,是安放于逝者坟墓中为防陵谷变迁作标记用的石刻。碑文和志文的撰写目的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又都属于记述逝者生平的传记文字,有很多共性,所以往往碑志并称。本文在论及碑文的真实性和作者的应对策略时也会涉及部分墓志。。关于碑文的创作目的、碑文的真实性及应对策略的思考从碑文产生不久之后的东汉就已经开始了,到宋代出现了专门论述碑文创作目的及碑文真实性的文章,有了更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创作思考。关于宋代碑文创作目的及碑文真实性的论述,前人已有学术积淀。如台湾学者刘静贞的《北宋前期墓志书写活动初探》,刘成国的《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李强的《漫谈宋人的碑志创作观》,浙江师范大学魏海稳以《宋代碑传理论研究》为题的硕士论文等都曾对此问题有所论述。但此论题仍有诸多未尽之意可供阐发,也缺乏从东汉到宋代对碑文创作目的和真实性思考的脉络梳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爬梳,并详细阐释宋代学者不同于前人的思考与应对策略。
一、宋代之前关于碑文创作目的和真实性的思考
碑文创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东汉刘熙对于碑的解释中看到,“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以引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1]人们最初在用于下棺的碑上,刻写简单的逝者姓名和卒葬年岁,可能只是做标识用,后来“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臣为君、子为父立碑于显见之处,目的是刻写逝者生前的显赫功绩,昭明其美好的德行,使逝者能永垂不朽,也能表达臣子和子孙的悼念、哀伤之情。事实上,东汉很多墓碑文中就清晰地写明了墓碑撰写的目的,如“德之隆者,莫盛不朽,乃共追录厥勋,镌石示后,俾延亿龄,垂不翳坠”[2]916,“名莫隆于不朽,德莫胜于万世,勒铭显于钟鼎,清烈光于来裔。刊石立碑,德载不泯。”[2]717也就是意图借金石这种不易磨灭的有形之物来记载、传扬逝者的不朽令名,这是东汉墓碑文写作的主要目的。写作目的决定了碑文的基调基本上是歌功颂德和悼念、表达哀伤。关于墓碑刻立者,东汉比较特殊的是墓碑多由门生故吏为逝者所建,与后世墓碑、神道碑基本由子孙后代所立不同。
关于墓碑文的文体和写作内容,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得很清楚:“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致也。”[3]认为墓碑记载的内容和史传有相同之处,所以对墓碑撰写者的要求是有史才,即史家的见识和才华,还指出了碑文的基本组成——碑序和碑铭。东汉碑文的体式形成后,直到后世,碑文基本由碑额、碑序和碑铭三部分组成。“碑额,即碑文之首行,标明碑主的身份,或阐述立碑之宗旨;碑序记述碑主姓名、籍贯、世系、仕宦履历,并兼叙德行、政绩,最后记卒年及人们的悼念、颂扬之情;碑铭为结尾的韵语,对碑主进行总结式的颂赞。”[4]由于碑文叙述的逝者籍贯、世系、仕宦履历、生卒年月等都是基于事实的,所以碑文和史传有相似性,但是碑文的目的毕竟是歌功颂德和表达哀悼之情,与史传有着文体上的根本差异。刘师培就明确指出了碑文与史传的不同:“碑前之序虽与传状相近,而实为二体,不可混同。盖碑序所叙生平,以形容为主,不宜据实直书……试观蔡中郎《郭有道碑》,岂能与《后汉书·郭泰传》易位耶?”[5]陆机《文赋》里提到碑的文体特点是“碑披文以相质”。碑要咏功颂德,除了要尊重基本事实外,还要有斐然的文采。东汉的碑文撰写者非常明确碑文和史传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对比东汉碑文和史传,差异明显,写法完全不同,“(东汉)碑文叙亡者生平事迹以形容为主……不注重对具体言行的叙写,而是对亡者行迹进行概括提升,并进行形容夸饰。直接呈现其品性,展现亡者之英烈。行文讲究语气的变化,讲究对偶,讲究文采。”[6]东汉初期的碑文尚质木无文,到桓、灵时期有了基本的行文格式,前序后铭,序长铭短,以序来记述逝者生平,叙咏结合、韵散相间。铭以四言韵文为主,对序的内容进行总结和颂赞。到东汉后期,碑文越来越注重文学性,辞藻趋于华美,语句重视骈偶对仗,多运用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
因为魏晋禁碑的缘故,魏晋和南朝的碑文数量都较少,在碑文的创作目的和文体上和东汉类似,但是字数增多、篇幅变长,受当时文风影响,碑文也更重视文学性,文胜于质。北朝不限制立碑,碑文数量较多,创作目的没有太大变化,仍然是叙颂逝者功德勋业,使之名垂后世。经常但是受到当时士族门阀观念的影响,北朝的墓碑用相当的篇幅来叙述祖先世系和家族后代情况。
到唐代,因为统治者本身对刻石立碑的重视,碑文创作的数量远盛前代,碑文的风格和思想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初盛唐时渐有人主张改变绮丽浮艳的文风,反映在碑文上也是对南北朝碑志程式化、千人一面、词胜事寡、过分铺排事典、浮泛无实的文风开始有所纠正,补充一些历史事实。但是碑志文的写作真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在中唐时期实现的,韩愈、柳宗元等大力倡导儒学复兴、古文运动,反映在碑志上是用史传的手法来写作碑志文。章学诚《墓铭辨例》一文说得极为详细:“六朝骈俪,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文家称为韩碑杜律,良有以也。……墓铭不可与史传例也。铭金勒石,古人多用韵言,取便诵识,义亦近于咏叹,本辞章之流也。韩、柳、欧阳恶其污秽,而以史传叙事之法志于前,简括其辞,以为韵语缀于后,本属变体。两汉碑刻,六朝铭志,本不如是。然其意实胜前人,故近人多师法之,隐然同传记文矣。至于本体实自辞章,不容混也。”[7]韩愈等人不满南北朝碑志的千文一腔、千人一面、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没有实际内容,转而学习《史记》《汉书》的叙事方法,以史传的方式来写作碑志序文,变骈为散,运用细节、语言、心理等多种叙事手法来描写碑主经历,并融入议论、抒情等主观思想、判断。结尾的碑铭仍以四字或其他形式的韵语来总结或抒发情感。这种碑志的创作手法被刘师培、章学诚等人视为变体,但是却为宋以后的碑志撰写所继承,如钱基博所说:“碑传文有两体:其一蔡邕体,语多虚赞而纬以事历,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人碑多宗之。其一韩愈体,事尚实叙而裁如史传,唐以下欧、苏、曾、王诸人碑多宗之。”[8]韩愈以史入碑的写法反而成为后世文章的正宗。碑志的创作目的除了东汉南北朝流传下来的歌功颂德、传逝者令名使之不朽和替丧家表达哀悼之情外,也有了补史之缺的想法,唐代的很多碑志为《新唐书》所采纳就是实证。在唐代之前,碑志因为文体所限,基本不会被史书采纳。
从文体上看,碑文是一种饰终礼文;从创作目的上看,碑文有铭功颂德、显扬先烈并表达亲人哀悼之情的功用。所以碑文不可避免地会有虚饰滥颂、言过其实之处,其真实性会大打折扣。事实上,自东汉以来历朝历代的人们很多都对碑文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就连碑文创作数量众多、成就最高、作品被视为汉碑典范的蔡邕本人也对碑文的真实性信心不足,“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9]作者对碑文不能据实直书有很深的愧疚感。到东汉建安十年(205),因为战乱不断、瘟疫流行、经济凋敝等原因,曹操索性下令禁止立碑。西晋延续了这项政策,晋武帝咸宁四年(278),朝廷下诏:“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2]51禁止立碑的原因,除了经济上“伤财害人”外,还有墓碑会起到私相褒美、助长虚伪风气的坏作用。此项诏令除了有把盖棺论定评价权收归朝廷的意图外,也是对于碑文华辞损实、妄言伤正的官方盖章。东晋碑禁渐松,私下立碑者亦多。义熙年间,裴松之上表请求禁立私碑,他反对的理由是:“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敝无已。”[10]946对碑文寡信不实、虚伪成风、真假相蒙表示不满和担忧。裴松之主张:“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于仰止,道孚于来叶。”[10]946他的建议被东晋朝廷采纳,并一直持续至后来的宋齐梁陈诸朝。南朝碑文衰微与此政策相关。
北朝统治者重视丧葬,厚葬之风又起,文士撰写碑文者众多,北朝碑文继承东汉碑文的写法,又兼融了南朝碑志文的骈俪之风,碑志的真实性也受到质疑,东魏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里借隐士赵逸之口讥刺了碑志不实的现象,“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佞言伤正,华辞损实。”[11]碑文不仅严重与事实不符,而且程式化叙述严重,千人一面。唐代是碑刻的鼎盛期,名碑云起。不同于前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唐代“润笔费”盛行,也即碑文撰书的商品化现象出现,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对这一现象有生动记载:“近代碑稍众,有力之家,多辇金帛以祈作者,虽人子罔及之心,顺情虚饰,遂成风俗。”[12]有钱有势的丧家往往斥巨资付给作者润笔费,以请求其为逝者撰写碑铭,作者收受润笔费后为满足子孙显扬先烈的孝心,往往“顺情虚饰”,这种现象竟成为唐代一时盛行的丧葬风俗。除了碑文本身文体属性的限制,又加上商品化的影响,碑文的真实性更难保障,以至于有“韩碑杜律”之称的碑文撰写大家韩愈都屡遭“谀墓”之讥。也是碑文作者的白居易自己甚至还专门写作一首名为《立碑》的诗歌来讥刺碑志不实的现象:“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13]
从东汉到唐代,不管是官方、旁观者还是碑文作者都对碑文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甚至讥刺。面对“皇帝的新装”,作者一方面有惭德、有愧色,想要据实直书;另一方面又改变不了碑文饰终礼文和应酬文的文体属性,要满足丧家显扬先烈和颂美家族的愿望,就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辗转腾挪,而这种冲突到宋代逐渐发展成了碑文作者的“书写焦虑”。
二、宋代碑志文作者对于碑志创作目的之思考
宋代的碑文作法宗韩愈,“事尚实叙而裁如史传”,宋代碑文的作者多是史官身份或有史官经历。关于碑文的创作目的,宋碑的作者多有自觉的思考,很多在碑文中直接言明。如李至在受诏为钱俶撰写神道碑时就写道:“上乃永怀懿铄,虑或湮灭。诏臣论次其事,楬为丰碑。臣拜命周章,罔知攸措,……然而获在天禄,得游书林,览太史公之传记久矣,阅诸侯王之事迹多矣。夫金石之刻,所以垂劝来代,彰明往懿,故无过实、无虚美,斯令戒之所式,亦微臣之所耻。谨按家牒,详国史,拜手直书,将传信乎刊纪。”[14]明确提到金石之刻的目的是“垂劝来代,彰明往懿”,还提到应该“无过实、无虚美”,这已经突破了碑志的作法而有史传的要求了。范仲淹撰写《宋故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神道碑铭》时也写到了创作此篇碑文的目的:“厥孙以公善状请文于碑。某于公有家世之旧,又与舍人为同年交,爱公治有循良之状,退得廉让之礼,足以佑风化而厚礼俗,敢拳拳以铭云。”[15]范仲淹认为谢涛的循良之治和廉让之体可以裨益于教化礼俗,所以为其撰写碑文。二者都重视碑文的道德教化作用和经世致用功能。
欧阳修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发起者,主张文以载道,也很看重碑文的教化功用,如他撰写的《镇安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师中书令程公神道碑铭》中就写道:“臣修以谓古者功德之臣,进受国宠,退而铭于器物,非独私其后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国有人,而诗人又播其事,声于咏歌,以扬无穷。”[16]238他认为刻写碑文的意义不仅是对逝者本人歌功颂德,也是“不忘君命,示国有人”,认为程琳是作为国家的功勋之臣被记载和颂扬,能起到记载历史和作范后昆的作用。他在写作《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铭并序》时更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至于出入勤劳之节,与其进退绸缪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劝后世,如古诗书所载,皆应法可书。”[16]252他认为碑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褒劝后世”,也就是看重碑文的道德教化作用。
欧阳修的高足曾巩特意写文章与欧阳修讨论碑志的写作目的及碑志与史传的区别,就是《寄欧阳舍人书》,曾巩的本意是感激欧阳修为其祖父曾致尧写作神道碑,但是他在文中提出了碑志创作的理论思考:“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17]253曾巩指出了碑志与史传的不同之处,史传是善恶无所不书,碑志只能书写功德材行之美者,恶行则不书。但是恶人无可记之事,也会愧而惧,善人因为嘉言善行会被记录下来成为后世法则,也会更勉励自己,所以就警示教化后世而言,则碑志的作用和史传非常接近。以上都是宋代碑文作者对于碑志创作目的的理性思考,认为碑志近乎史传,有惩恶劝善、教化后世的功用,他们的创作目的已不局限于为逝者本人歌功颂德,而有了更深层的含义。
除了道德教化的目的外,宋人创作碑文也还有别的考虑。如南宋大将张俊的神道碑文是周麟之奉宋高宗的诏书所作,而高宗敕令其为张俊撰写碑文有现实的考虑,“上曰:‘张某自元帅府提兵从卫,备罄心膂。至为大将,总戎旅于外,独知奉君上、尊朝廷。及释师而归,受命惟谨。其终始恭顺,诚不与他帅比。故报䘏追荣,恩礼特异。汝其志之,朕将有劝焉。’臣仰佩圣训,既退叹息。然后知公之明光盛大,福禄永终,盖一本于恭顺。以是而著之碑,章视来世,用为天下劝,臣不敢辞。”[18]高宗敕令臣下为张俊撰写神道碑的目的是劝诫天下人,特别是武将要效仿张俊“独知奉君上、尊朝廷”“始终恭顺”,神道碑的撰写在这里极具现实意义,宋高宗是把张俊的神道碑作为意识形态的展示板来使用。
苏轼在撰写富弼神道碑文时也有非常现实的考虑,他撰写的富弼神道碑文开篇即用相当长的篇幅来详细叙述澶渊之盟及宋仁宗庆历年间辽国派刘六符来索要关南地之事,富弼受命出使辽,用计谋和雄辩的口才劝说辽放弃割地的要求而增之以岁币,使得宋辽之间又维系了长时间的和平。苏轼对富弼出使之举大加赞赏:“故臣尝窃论之,百余年间,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准与公之功也。”[19]朱熹后来分析苏轼撰写富弼碑文是为了劝谏元丰、绍圣年间用兵之举,“朱子曰:‘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此文,恐未必得,而坡公锐然许之。自今观之,盖坡公欲得此为一题目,以发明己意耳。其首论富公使金事,岂苟然哉!’道夫曰:‘向见文字中有云,富公在青州活饥民,自以为胜作中书令二十四考,而使金之功,盖不道也。坡公之文,非公意矣。’曰:‘须要知富公不喜,而坡公乐道而铺张之意如何。’曰:‘意者,富公嫌夫中国衰弱而夷狄盛强,其为此举,实为下策。而坡公则欲救当时之弊,故首以为言也。’先生良久乃曰:‘富公之策,自知其下。但当时无人承当,故不得已而为之尔,非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谓选择监司等事,一一举行,则内治既强,夷狄自服,有不待于此矣。今乃增币通和,非正甚矣。坡公因绍圣、元丰间用得兵来狼狈,故假此说以发明其议论尔。’”[20]苏轼撰写神道碑文是借碑文发明己意,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主张。
无独有偶,宇文虚中为刘 撰写神道碑文,完全不遵循传统的碑文撰写顺序,碑序全部都用来叙述靖康之难前后刘 的正确建议不能行用与最后的忠义殉国,也描摹了一众相与败国、归过君父、灭弃臣子之礼、归降敌国的士大夫的丑恶嘴脸。关于神道碑的创作目的,宇文虚中说得非常清楚:“公归葬建州之崇安,其子以虚中与公契旧,目见谋议本末,乃以表墓之文见委,因为论著大节,事系天下之所以安危者,揭示道左,且以辨明取燕之失不在上皇。”[21]就是要把神道碑作为宣传的载体,写明北宋灭亡之际刘 等人的忠义表现,也揭露鞭挞其他误国、无耻士大夫的丑恶,同时辨明当年联金灭辽导致亡国的过错不在徽宗。
综上,宋代文人对于碑文创作目的的认识早已超越了碑文歌功颂德的本义,既承继韩愈以史传为碑的作法,看到了碑与史传在惩恶劝善、道德教化方面的共性,并且有专门的文章来讨论二者异同,又特别看重神道碑、墓碑的景观属性与宣传作用,注意到碑文创作的现实目的,用碑文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宋人碑文创作特别重视现实目的,这个特点大概与宋代印刷业发达,碑文能快速地传播被更多人看到相关。
三、宋代作者关于碑志真实性的考虑和应对之策
关于碑志撰写不真实的问题,曾巩在《寄欧阳舍人书》里鞭辟入里地分析了碑志不实的原因:“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17]253子孙请人撰碑志,自然是为褒扬其亲,撰者受人所托当然不能书恶。这是由碑志文本身的文体属性决定的。
除了人情因素外,碑志不能据实以书,还受到政治的影响。刘成国《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一文专门述及此点,他认为党争双方政治立场不同,对同一事件的判断便不同,影响到碑志的叙事,“墓主、孝子、撰者的政治立场,在碑志的叙事中被体现出来,并且决定了对事件的选择、隐没和凸显。”[22]作者认为受到敏感的政治环境影响,一些碑主虽然是某些重要政治事件的参与或主导者,这些事件是其政治生涯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影响了历史进程,但是撰写者不敢或不便清晰地写出来,往往会选择性处理,或模糊或故意遗漏,如欧阳修为蔡襄写墓志铭就故意不提他在范吕党争中的表现,以淡化党争的影响。程颐在元祐年间旧党当权时为其兄程颢撰写行状也有意遗漏程颢政治生涯中重要一笔:曾经支持熙丰新法并积极参与。有的撰写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会故意凸显碑主政治生涯中的某些政治事件,如本文前述苏轼为富弼撰写神道碑文就有意凸显他出使辽通过增加岁币而避免战争用兵之事。更有甚者,受到撰写时政治环境的影响,碑志的撰写有时会出现变体,比如有的碑志用一半以上的篇幅记录逝者之父与元祐时期蜀党诸人的交往,只是为了弥补逝者之父去世时党禁甚严不能实写其交游之事。
既有碑志本身显扬先烈、歌功颂德文体属性的限制,又受到北宋党政激烈、政治环境严重影响碑志书写自由的束缚,再加上宋代延续了唐代碑志书写商品化的风俗,润笔所费不赀。碑志的真实性看上去更难保证,一些负责任的碑文撰写者会对此感到焦虑①参见刘静贞:《北宋前期墓志书写活动初探》,“宋代墓志史料的文本分析与实证运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一方面碑志的撰写者会在碑志中反复申明自己的书写“无过实、无虚美”“直书无愧”,一方面也思考和采用了诸多策略来纾解自己关于真实性的焦虑,尽量取信于当时和后世。
撰写者第一个应对策略是不写或少写碑志文,最典型的是苏轼,他在《祭张文定公文》中说:“轼于天下,未尝志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23]他平生所作碑志行状的确远少于同时代的文人,观其与友人书信,他曾多次拒绝别人让其书写碑志的请求,即使皇帝敕令其为大臣书写神道碑也上奏文拒绝:“臣平生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为光曾为亡母程氏撰埋铭。又为范镇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诏撰司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辞,然终非本意。况臣危病废学,文辞鄙陋,不称人子所以欲显扬其亲之意。伏望圣慈别择能者,特许辞免。谨录奏闻,伏候敕旨。”[24]他的理由除了自谦的“危病废学,文辞鄙陋”外,还有“不称人子所以欲显扬其亲之意”,看到了因为碑志本身文体性质决定的、真实性不能保证的弊端,所以拒绝为人作碑志。苏轼因为曾经遭受过文字狱和党争危害,碑志又涉及到人物的点评和敏感的政治事件,不作碑志也有惕巨怵祸之意。司马光晚年也改弦更张,坚决拒绝为人作碑志。②参见赵冬梅:《试论北宋中后期的碑志书写——以司马光晚年改辙拒作碑志为中心》,收入王晴佳:《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撰写者第二个应对策略是尽可能地为自己熟悉、了解其生平德行功绩的人撰写碑志。这样可以有细节、典型事例可写,也能保证一些碑志撰写的真实性。如周必大为林光朝所写神道碑就交代了写作缘由:“予念昔在两省,公适登第;典贰秘书,公来著庭;佐春官,公为郎;掌史事,公为僚;晩忝宫端,同事寿康皇帝。前后五联官曹,大而道德性命之理无不讲,内而闺门寝食之私无不及。读书未达,赖公析疑;属文未工,资公指瑕。平居相爱,殆同天伦。公之本末皆亲见熟察,非但传闻而已,是宜为铭。”[25]周必大与林光朝一生五次曾经是同僚关系,一起讲谈理学,对于彼此的家庭也很熟悉,一起读书作文讨论,是生平挚交。所以“公之本末皆亲见熟察,非但传闻而已”,碑主的生平德行皆自己亲见亲闻,并非传闻,所以作者认为可以为自己所写碑主平生事迹的真实性背书。宋代神道碑作者交代自己和碑主关系的不在少数,有的是朋友挚交,有的是门生故吏,有的是姻亲,因为熟悉生平,所以言而有文也能保证一些真实性。
撰写者第三个应对策略是尽可能搜集更多关于逝者的材料,多方比对,从而尽量客观地书写逝者生平。宋代碑志撰写者的素材来源众多,有行状、家谱、家牒、家传、墓志铭、国史、实录、缙绅故传、逝者文集、奏疏、制诰文书、他人文本或口头转述等,尤其不同于前朝的是,宋代作者特别注重将丧家提供的材料同国史、实录进行参照比较,这一方面与宋代碑志撰写者多具有史官身份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宋代碑文作者对于碑志的真实性有更自觉的考虑相关。
撰写者第四个应对策略是对待碑文的素材保持一种相当审慎的态度,最典型的是对待行状的取舍,“碑传文之作,大多由他人请托而为,如果碑传作者与墓主素昧平生,行状就成为碑传作者传记材料的主要来源。碑传文之作是否可信,行状的真实属性尤为关键。如果行状中有表述不清或信息不完备的地方,欧阳修会反复要求墓主家属提供更为翔实的材料,不厌其烦。例如梅尧臣受托请欧阳修为唐介(字子方)之父唐拱作墓表,欧阳修看过行状之后,认为行状的内容并不十分具体,无法就事论事,于是写信给梅尧臣:‘忽辱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状,谨当牵课,然少宽数为幸。其如行状中泛言行己,殊不列事迹,或有记得者,幸更得数件,则甚善。常人家送行状来,内有不备处,再三去问,盖不避一时忉忉,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达之。’欧阳修希望家属提供的墓主事迹能具体一些,详细一些,不要空泛的评说。”[26]对于不熟悉之人的行状要反复确认比对,再三询问,以保证素材的真实性。欧阳修为曾巩祖父曾致尧撰写神道碑时,对于曾巩提供的曾家的世系谱牒比照《诸侯年表》反复考论,认为其始封之祖和迁徙世次都不准确,欧阳修本着求真的目的,在神道碑中对于不能确定的世系谱牒都据实直书,并且在书信中责怪曾巩所提供的材料不实。除了欧阳修对待碑文素材态度谨严、审慎外,北宋其他人撰写碑志态度也类似,如苏洵曾经答应为杨美球之父撰写墓志铭,但是苏洵不识其父,只能依据丧家提供的行状来书写,但是行状多有不实之处,苏洵特意写信给杨美球,讨论此事:“洵白:节推足下,往者见托以先丈之埋铭,示之以程生之《行状》。洵于子之先君,耳目未尝相接,未尝辄交谈笑之欢。夫古之人所为志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闵其不幸以死,悲其后世之无闻,此铭之所为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为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铭之实,则亦不得不铭。此则铭亦可以信《行状》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获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铭者,正在其《行状》耳。而《状》又不可信,嗟夫难哉!然余伤夫人子之惜其先君无闻于后,以请于我,我既已许之,而又拒之,则无以恤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铭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兹亦足以不负子矣,谨录以进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状》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后。凡《行状》之所云皆虚浮不实之事,是以不备论,论其可指之迹。《行状》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恸以卒。’夫子夏哭子,止于丧明,而曾子讯之。而况以杀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爱夫吾言,恐其伤子先君之风。《行状》曰:‘公戒诸子,无如乡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乡人,谁非子之兄与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况不至于皆然,则余又何敢言之。此铭之所以不取于《行状》者有以也,子其无以为怪。洵白。”[27]苏洵为杨美球父亲所作之墓志铭最后仅据实书其世系、籍贯、历官,行状虚妄不实之处皆不取。为了尽可能保证碑志的客观、真实,宋人在撰写碑志文时,还经常将未定稿寄给熟悉逝者的朋友共同斟酌,如“范文正尝为人作墓铭,已封将发,忽曰:‘不可不使师鲁见之。’明日以示师鲁,师鲁曰:‘希文(范仲淹)名垂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谓转运使为部刺史,知州为太守,诚为脱俗,然今无其官,后必疑之,正起俗儒争论也。’希文抚几曰:“赖以示子,不然,吾几失之。”[28]从中也可看出宋代作者撰写碑志时态度谨慎的原因是“名垂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即便是写作碑志也提升到写作史传一样的高度来对待。欧阳修在为范仲淹撰写神道碑时也经常与韩琦等人商榷写法,目的也是让对家尽量挑不出可以借题发挥的地方。这种审慎的态度除了追求碑志的真实性外,也与宋代党争背景下比较严苛的书写环境相关。
此外,为了碑文的真实、客观,撰写者往往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不与丧家妥协,如欧阳修为范仲淹撰写神道碑文时写道:“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16]225写了范吕解仇之事,后来引起范家子弟的不满,但欧阳修坚持不肯妥协,甚至在丧家立碑时删去相关碑文的情况下,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仍愤愤不平,希望世人以集本而不是石本为准,不认可删改后的神道碑石本是自己的文章。欧阳修在为尹洙撰写墓志铭时因为注重简而有法,仿效尹洙自己的笔法来撰写墓志铭,所写的墓志不能满足丧家的要求,以至丧家要重新请人撰写墓表来详细叙述尹洙的成就。欧阳修也是绝不妥协,乃至专门写作《论尹师鲁墓志》来阐明自己写作碑志的“春秋笔法”。与之类似的还有王安石,他在为人撰写墓志铭时拒绝写上墓主子孙的通判之署有池台竹林之胜的文字,宁肯收回文稿也不妥协。叶适对待碑文撰写也是一丝不苟,不肯屈从于丧家:“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称水心作汪勃墓志,有云:‘佐佑执政,共持国论。’执政乃秦桧同时者,汪之孙纲不乐,请改。水心答书不从,会水心卒,赵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门下有受汪嘱者,竟为除去‘佐佑执政’四字。今考集中汪勃志文,已改为‘居纪纲地,共持国论’,则子良所纪为足信,而适作文之不苟,亦可以概见矣。”[29]叶适在撰写碑文后坚决不肯修改逝者曾经的事迹,不为丧家所动。
虽然最终还是会受制于碑文本身的文体特性和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撰写者即使很努力也不能完全改变碑志书写不实的问题。但是他们较之前代的撰写者有了更多的自觉思考和更主动、详尽的应对之举,这是碑文撰写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