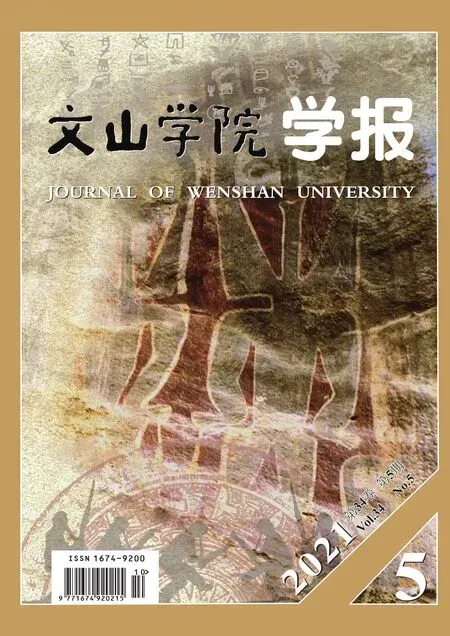对山区缺水环境的文化生态再适应研究
——以岜扒侗寨牛的饲养作为线索
刘月红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岜扒行政村属于从江县高增乡,位于黎平、从江两县交界处,最高海拔约900米,最低点海拔约300米。[1]由于处在山脊分水岭地段,福禄江支流的源头,虽然境内溪流众多,但均不能通航。再加上岜扒村境内山高坡陡,地势崎岖不平,不管是开辟连片的稻田,还是培植杉木林,都难以做到。因而他们与世居在坝区湿地生态系统的其他大多数侗族村寨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民族识别”。当时的研究者根据岜扒侗族乡民保留完好的侗族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和“侗族大歌”等侗族文化要素,[2]与其他地区的侗族相比,虽说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小有差异,但与其他坝区侗族大体相同,因而将他们识别为侗族。
此前大多数学者习惯于以坝区侗寨的田野调查为依据,认定“林粮间作”与“稻鱼鸭共生”是侗族文化的典型标志。但在岜扒村却有所不同,一是在岜扒培育杉木林不仅杉树生长不良,集材量偏低,即使长大成材也难以漂运外售,“林粮间作”也就无从谈起。二是岜扒村因山势陡峭,梯田只能开辟成带状,田块与田块之间落差较大,以至于塘、田、河、渠联网难以实现。虽然岜扒乡民也传承着“稻鱼鸭共生”的生计模式,但是投工大,收益少。但岜扒村每家每户都饲养着大量的黄牛,靠销售黄牛能获取较大的收益,这与坝区侗族饲养水牛不同。三是岜扒村所在的地区属于石灰岩山区,这与坝区的侗族也不相同。岜扒村侗族现有的文化是侗族文化中的一个地方性类型,而建构出这样的地方性类型文化,是文化再适应的结果。通过深入探讨这一文化再适应过程,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侗族文化的理解,而且对生态文明建设有借鉴意义。
一、侗族传统文化的四次转型与再适应
根据前人研究,侗族的传统文化至少经历过四次明显的转型与再适应,即“滨水渔猎文化;低山丛林狩猎-采集文化;湿地游耕文化;山地与坝区林粮兼营农耕文化”[3],但具体的适应内涵却存在着地域性差异。笔者据此将包括岜扒村在内的山区缺水环境下的侗族地方性类型的文化生态历史进程,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其一,滨水生态系统的狩猎采集文化。其时间跨度大致从远古时代一直延伸到秦汉时代,地域空间范围集中分布在珠江下游和沅江下游的宽谷坝区。其核心价值是以获取自然生长的动植物资源为生,但也需要通过社会的合力与其他野生动物展开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就这一意义上说,狩猎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食物,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能够控制的动植物资源不受野生动物的侵夺。当时这样的野生动物就包括野生水牛,在早期的汉文典籍中将野生水牛称为“兕”[4]。但由于受到当时的文化核心价值限制,侗族先民并没有把社会合力运用于驯化野生水牛,而是将精力用于收集水牛的粪便,晒干后做为燃料。如果野生水牛受伤或者有病,他们才会主动猎获。侗族先民在实际的生活中已经认知和利用众多的水生植物,包括莲藕、芡实、菱角都是他们采集的作物,其中最独特的是水稻。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水稻发展成为侗族居民的主食,能够与水稻共生的鱼和鸭也因此而被他们驯化,并作为标志性的文化事项一直传承至今。
其二,滨水“稻鱼鸭共生”的游耕类型文化。其时间跨度起于秦汉时代早期,终于唐宋时代。侗族文化这一时代的核心价值在于尽可能的利用自然力,按照仿生模式将多种可以共生的动物和植物浓缩到有限的可控空间内,让他们自然生长,从而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源。这与固定农耕类型文化不同,他们不需要翻耕土地,中耕除草,也不需要大规模的储备食物。而是随种随收,随收随用。具体到侗族文化生态史而言,标志性的生产模式就是实施“稻鱼鸭共生”种养系统。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耕作系统并不会永远固定在同一个地点实施种养复合生计,而是根据环境和社会的变迁,有规律的更换耕作区段。这一时代对野生动物的认知和利用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驯化了野生水牛并加以喂养。耕田时驱使水牛去踩踏种养区段,将往年的植物残株踩入泥中任其自然腐烂成为肥料,并平整土地以利于插秧。这一时期除了“稻鱼鸭共生”外,驯化野水牛、培育出优质的糯稻品种、从汉族地区引进黄牛等最具代表性的侗族文化延续传承到了今天。
其三,“林粮间作”的固定农耕类型文化。这一时代大致起于南宋时期,终于19世纪。具体到岜扒村侗族文化而言,则是针对山区缺水环境的特殊性发育出通过转型与再适应,最终形成了农牧兼容的山区地方性侗族文化新样式。这一时期坝区侗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凭借社会合力规模性的开辟山区梯田,将糯稻作为主粮加以栽培,将坡面自然生长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人工改造为杉木用材林,从而实现了“林粮间作”,以粮为食,以材为用。而耕地森林也大多由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村寨成员所共有,家族村寨之间则通过“合款”建立习惯法去实现社会力量的整合,消除内部矛盾,以同样的诉求与中央王朝发生直接的社会关系。
其四,当代文化失范和再适应的启动,这一时期起于20世纪中期至今。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外来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传统文化受到重大的冲击。文化对外部市场的适应还处于再适应的启动期,至今尚未完成,还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转型。岜扒村与坝区文化之间的差距也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放大。
二、岜扒地区的历史回顾
侗族传统文化的适应与再适应,转型与再转型,都和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一个独特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侗族不是以一个超然的文化实体而存在,而是与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性。其间不仅要适应于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还得适应于不同的社会环境,特别是跨文化背景下的族际关系。从而使得发展历程充满曲折,其间既有分化也有融合。历史久远的发展历程,由于缺乏史料支撑,当前尚无法作出精准的说明和表述。但具体到岜扒村的定型而言,由于汉文典籍史料记载较为丰富,乡民的传说和记忆尚属完备,因而可以作出相应的精准分析和因果关系探讨。
岜扒村自然生态系统归属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和山脊疏树草地生态系统,没有较大的湿地生态系统。南宋朱辅所编的《溪蛮丛笑》将这样的地区称为“生界”,[5]而将当时侗族密集生息的宽谷坝区称为“沿边溪洞”。这是因为南宋朝廷在这样的地区设置很多“羁縻州县”,委任侗族首领充当州县长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侗族传说中的英雄杨再思。杨再思的十个儿子分管十个不同片区的侗族,也就是所谓“十庄院”,[6]这个名称在《溪蛮丛笑》一书中也有提及。不过岜扒距离“十庄院”还有数百公里之遥,这意味着不仅南宋朝廷不知道有岜扒和当时住在这里的苗族,侗族首领杨再思的后继者们也没有涉足到当时的岜扒地区。
空姐作为客机飞行过程中负责照顾旅客服务人员,尽心尽力的保证旅客在飞机内能度过一个开心且舒适的时光,是航空航天服务业中的重要部分。空姐就如同一个航空航天公司的门面一样,可以直接对旅客的旅途体验产生影响。
《宋史》提到了“三锹”[7]这一名称,其含义是说,从坝区的边缘山麓出发向山上挖掘“三锹”,就是朝廷“羁縻州县”管辖范围的边界,坝区归侗族首领的“羁縻州县”管辖,“三锹”以上的地带则是朝廷和羁縻州长官负责招抚的地带,招扶的对象自然是生活中在山区的苗族或者瑶族。执行这一制度的目的是让当地的山民不下山骚扰“羁縻州县”和汉族集居区。“三锹”显然是当时苗族或者瑶族的分布带,他们尚处于游耕兼渔猎的文化类型之中。因而接受宋朝统治的各”羁縻州县“的侗族乡民都有责任防范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就是侗族传统文化中“合款”制度的由来。
元朝时期,对南宋所辖的“沿边溪洞”各“羁縻州县”实施改组,委任当地的土家族和侗族领袖为土司。通过这些土司对此前所称的“生界”实施招抚代管,其中离岜扒地区最近的土司被称为福禄永从长官司。当时该土司隶属于古州万户府,交由思州田氏土司统辖。不过由于当时的岜扒地区是苗族和瑶族的集居地,因而该侗族土司只有招抚权,而没有管辖权,这一地区依然属于“生界”。
明朝在西南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明初之际,福禄永从长官司由思州田氏土司统辖。明永乐十一年,朝廷罢废思州田氏土司,没收其领地,创设了黎平等四个府,福禄永从长官司交由新设的黎平府代管。到了明代中期,福禄永从长官司没有合法的继承人,根据土司制度的惯例,土司领地由朝廷收归国有,并就此设置了永从县,隶属黎平府统辖。岜扒地区在此前由土司代管,此后则交由永从县统辖,隶属关系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生界”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岜扒地区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改变,只是由土司代表朝廷招抚的“生界”改变为由永从县负责招抚而已。“生界”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末年都是如此。
清雍正年间,朝廷才着手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包括岜扒在内的所有“生界”加以开辟,将这一大片土地设置为六个厅,其中永从县招抚地区中的西部划归为新设的下江厅管辖,东部仍归黎平府管辖。即今天的黎平县黄冈等村,同时将整个“生界”地区统称为“七百生苗地”。[8]现存的碑刻可以为此作证。
岜扒地区的开辟结果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此前的“生界”变成了地方政府可以直接管辖的地区。二是此前以苗族为主的地区通过移民方式,大量的侗族居民在黎平府永从县和下江厅的支持下涌入这片“生界”,民族构成也随之改变,从以苗族为主变成以侗族为主。三是岜扒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往来变得通行无阻。四是朝廷实施优待政策,对新开辟的“生界”一律实施轻徭减赋以促进当地的生产。当地的社会秩序也得到朝廷的监管和保护。侗族和苗族之间的通婚与文化融合都受到了鼓励,这里的社会经济都得到了发展。这一地区的侗族乡民凭借记忆都承认自己是“侗父苗母”的后代,也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侗族文化也因此发生了转型与再适应,最终形成了20世纪初还能直接观察到的岜扒侗族地方文化诸特点。因而岜扒地区的转型与再适应过程,不仅相关的内容可以在汉文典籍中查到可靠记载,对于文化转型与再适应引发的文化生态变迁也有物证资料可以印证。
三、岜扒侗族地方性文化再适应的成效
将野生水牛驯化为家养的水牛是包括侗族在内的“百越”各民族的伟大创举,但是在“百越”各民族中驯化水牛的目的却各有区别。具体到侗族而言,其先民大致是在游耕类型文化时代就实现了这一创举。但驯化的目的与农田耕作无关,而是以获取肉食和获取牛粪作为燃料有直接关联。但这一做法却引起了内地汉族的注意,因为他们可以用很低的代价买到驯化后的水牛,从事稻田耕作。直到侗族经过第三次转型与再适应后,随着稻田规模的扩大,侗族先民从汉族地区学到了翻耕土地和插秧种植水稻的技术体系,实现了对山区梯田的建构,从而确保在山区也能成功的种植水稻。侗族先民的适应手段就是驱赶驯化后的水牛在水稻田中反复踩踏,将上年的稻桩和杂草踩踏入淤泥中,任其腐烂,充作肥料。因此,水牛才具有耕作的价值。
长期生活在坝区的侗族先民,虽说很早就从汉族地区获取黄牛,也学会了黄牛的饲养技术。但问题在于黄牛生性怕水,不习惯食用水生植物和湿生牧草。侗族生息的坝区除了湿地生态系统外,山体坡面都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森林茂密,很难长出草来,更不利于黄牛穿行觅食。正因为生态环境不适应,坝区侗族乡民在很长时期都不饲养黄牛。不过这样的问题对侗族的邻居苗族和瑶族而言,却不成问题。他们通过游耕方式在山脊区段进行砍伐和烧荒,实施“刀耕火种”种植小米等旱地作物。经过日经月累的砍伐和烧荒,山脊地带的乔木和灌木越来越少,牧草长得越来越多。引进黄牛后无需花费过多的劳力投入去放养黄牛,而黄牛也不会闯过茂密的坡面森林,既不会逃脱,也不会被偷盗。改土归流前,岜扒地区的苗族就是如此与内地汉族发生密切的联系。
改土归流后,随着侗族移民不断涌入岜扒地区,坝区侗族的文化被带入到岜扒地区,他们希望按照传统的方式喂养水牛,但新的环境却迫使他们饲养的方式不得不作出再适应。以岜扒村的水牛饲养为例:岜扒的水牛由全村集资购买,并专门聘请村内有名望的老人饲养它。饲养员工作包括喂牛吃草,带牛洗澡,全天守候水牛。就连睡觉也是睡在牛圈旁边,防止他人前来伤害牛或者偷牛。水牛所需的草料由全寨轮流提供,每天两户,每户100斤,还要平摊3斤的米和糠。饲养水牛的成本也比较大,饲养员每天的工资是45元,再加上买牛的成本,寨子每年的支出最少在10万元左右。除此之外,他们还挖水塘给水牛洗澡,养肥的水牛并不用来耕田,只能用于祭祀和斗牛,如此可以说得上是事倍功半。这完全称得上是对新的生态系统的负适应,其原因在于岜扒地区没有适合水牛生存的水域环境。但出于祭祀和延续文化传统的需要,他们却心甘情愿的承担养水牛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从文化适应于环境的目标而言,延续这样的传统,代价高昂。
岜扒侗族乡民对黄牛的饲养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岜扒侗族与当地苗族实现了通婚与文化融合后,苗族已有的黄牛饲养技术体系也被来到这里的侗族引进、吸收和创新利用。岜扒侗族同时还引进了苗族的“刀耕火种”技术,对山地坡面丛林进行砍伐和对乔木和灌木实施矮化处理。一则让砍伐后的树桩长出新芽,可以为黄牛、山羊等动物提供食物,二则又可以腾出空间让更多牧草生长,将森林生态系统改造为草地生态系统。
将岜扒对牛的饲养与坝区侗族加以对比,以下五个方面的差异最能体现文化再适应的取向:一是黄牛多,水牛少;二是黄牛耕田,水牛闲置;三是水牛只供祭祀和斗牛,无法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而黄牛则相反,既能耕田,又能食用,还能提供外销;四是水牛需要集体喂养,黄牛则家庭单独喂养;水牛实行舍饲,黄牛则放牧;五是饲养水牛主要用于村寨之间的斗牛比赛,为本家族村寨获得声誉;喂养黄牛则是为了实行农耕和获得家庭的经济收入,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两者迥然不同。
岜扒侗族乡民为了适应山区的缺水环境,扩大黄牛饲养规模,他们耗费大量的精力饲养黄牛,而黄牛每天需要消耗饲料和劳力,在短期内很难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益,反而造成了沉重的经济包袱。于是,在他们的节日习俗中就宰杀黄牛作为招待宾客的食物,从而缓解这一矛盾。从生态维护的视角看,在节日习俗期间大规模宰杀黄牛也不是一件坏事。其原因在于牛的存栏量过多,对人工草地造成极大压力。更重要的还在于大量消费牧草后,必然导致地表的泥土和石头大面积暴露,留下诱发大规模水土流失的隐患,甚至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大规模宰杀黄牛后,反而有利于草地的恢复和生态的维护。类似的生态维护做法,岜扒村并不是孤证,拉帕波特的著作《献给祖先的猪》也有极其相类似的记载,人类拥有调控环境资源的能力,可以使失衡的生态系统重归于平衡,[9]不同之处在于岜扒侗族乡民杀的是黄牛,而新几内亚地区杀的是猪。
除此之外,此前研究对人工扩大草地规模的评估,同样存在着偏颇,不少研究者认为将森林生态系统改建为草地生态系统,是一种破坏性的做法。类似的结论对平原固定农耕区而言,当然有可取之处,但却不适用于岜扒这样的特殊地区。岜扒属于石灰岩喀斯特快速发育地带,山脊区段包括海拔较高的坡面,土层极薄,保土保水的能力极低,很难抵御季节性的干旱。而且要维护这样的森林,在经济上不划算,在生态维护上也有副作用。正因为这里的地理条件不利于高大乔木生长,即令乔木勉强存活,但生长速度极为缓慢,集材量很低,对地表的覆盖度也很低。将这样的乔木适度修剪后,可以提高地表覆盖度,新长出的枝叶还能为山羊和黄牛提供食物。更重要的还在于腾出空间后,草本植物可以得到旺盛生长,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水平提升。因为草本植物群落的地表覆盖度比单有乔木时更高,更加有利于水土保持,而且草本植物生长周期短,更新快,能够快速有效的提高土壤的有机物含量,形成较厚的腐殖质层。从而提高地表的保土和保水能力,减少地表径流的冲刷,有效控制水土流失。
四、外来文化冲击下的文化生态失范
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岜扒侗族再次出现了最近一次文化生态的转型与再适应,这次适应的对象是外部市场和社会环境。岜扒乡民为了获得经济效益,仿照坝区侗族种植杉树的方式希望获取经济收益。但这一举措不断侵占黄牛放养所需的草场空间,导致饲养的黄牛数量不断锐减,以至于黄牛作为劳力这一实质功能从岜扒侗族农耕社会体系中逐渐消失。
为了获取较高的经济收益,岜扒侗族套用坝区侗族“林粮间作”的农耕模式,但杉树种植的经济收益却没有达到坝区侗族的理想程度。这是因为岜扒侗族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属于石灰岩山区,土壤粘性大,透气性差,导致种植的杉树难以存活。岜扒地区没有河流,无法像坝区侗族那样实施水上运输杉木。即使通过汽车运输的方式销售杉木,但岜扒地区的杉树生长速度根本比不上坝区侗族杉树的生长速度。杉树的技术管理水平也跟不上坝区侗族,所以在岜扒地区种植杉树获取经济效益是一种劳神费力的做法,还破坏生态环境。由此可知,杉树种植并不适合岜扒地区,反而饲养黄牛是岜扒侗族对其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的再适应的成功之处,能够为当地居民获取较大收益。他们为获取经济效益,把疏树草地转变为杉树种植区,这一举措不仅使草地空间缩减,还导致岜扒地区的次生生态系统发生改性,改性后的次生生态系统又诱发岜扒乡民对环境进行再适应。这次转型与再适应是针对外部市场和外部社会环境,外来文化没有与当地的自然与生态系统经过长期磨合,从而导致岜扒地区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在农业种植中使用大量的化肥与农药,物种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加重等等。
黄牛缺失后,岜扒乡民从市场上引进犁田机,从而取代黄牛。引进犁田机后,岜扒乡民为了克服岜扒地区山高坡峭的自然环境,特意修建一条能够通往农田的马路。但由于修建马路对岜扒山体的改动较大,多次引发马路周围的山体滑坡,堵塞新修马路。就算岜扒乡民新修了一条马路,但在农田耕作的时候,仍然需要两个人抬犁田机才能到达目的地。在岜扒侗族村寨进行材料收集时发现,大量乡民外出打工,劳动力缺失严重,就算是市场上最轻的犁田机,当地的留守老年乡民都很难抬得动,因而机械耕作对他们来说很不方便。再加上岜扒侗族乡民的农田分布位置太远,又不集中,因而采取现代机械实施农田种植还需要很长的适应时间。
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黄牛的饲养数量减少,导致岜扒侗族对牛粪等粪便资源的利用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全京秀认为“粪便是珍贵的资源,应该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10]但岜扒侗族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引进大量的化肥替代传统有机肥,导致大量农田的土壤板结化加重,破坏了当地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同时也导致岜扒侗族乡民对农田周围的杂草等植物资源的利用方式也发生改变,以前田埂周围的杂草都是拿去喂牛,现在这些杂草要么是随便丢弃,要么就是直接打除草剂,容易诱发生态问题。当地耕作方式的转变,也是当地人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后导致他们丧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忽视了当地资源的实用性,也是对本民族资源的认识也不到位。
文化的适应能力是当地人在长期适应自然与生态环境后所形成的生存智慧,能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和充分利用。但外来文化没有与当地的文化生态经过长期的磨合,也没有与这里的生态系统结成耦合演替关系,所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最先受损的就是当地原生的文化。原生文化受损后,文化与生态的耦合演替关系也随之失控,导致原有的偏离扩大化,最终引发所处的次生生态系统出现不可自我恢复的损伤。
五、结语
生态民族学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模型必然深受相关理论的影响和节制,以至于不管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会表现为得失参半。此前对侗族文化的研究,大多数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因而其研究对象和结论都聚焦于研究者心中典型的侗族文化村寨,而对于非典型的侗族地方文化样式大多是机械的搬用。用坝区侗族文化的研究结论去加以说明,最终表现为对侗族文化的地方性样式误读和误判,既不利于客观地认识侗族文化的全貌,还会在生态文明建设时对历史资料无法做到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使用,从而影响相关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对地方性再适应的侗族文化展开新一轮的研究,对转型与再适应后的文化进行具体的资料收集和系统的分析。对类似于岜扒这样的侗族村寨作出正确的认识和解读,才能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利的理论支持。也才能发现当前的某些做法有所失误的根源所在,而进行有所改进。
通过这一个案的讨论,我们有理由相信对所处自然与生态环境作出的再适应,都会引发生态变迁。为了确保生态系统能够稳态运行与延续,经济效益只能满足当地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所需,对外的经济收益不大。对社会背景作出的再适应,只要不发生失误,就可以有明显的经济效益,但会在无意中破坏生态环境,甚至酿成生态灾变。因此,只有兼顾两者的利弊得失,找准因地制宜的发展途径,才能做到两全其美,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生态效用,这应该是当下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认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