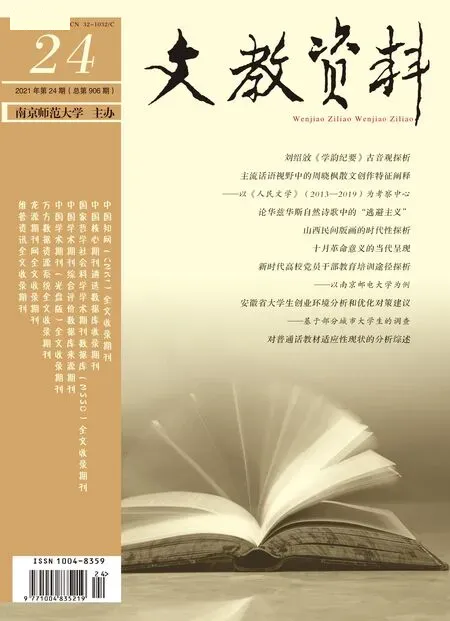东方幻梦的破灭
—— 论严歌苓对《魔旦》中东方主义的解构
张盛捷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魔旦》围绕居住在旧金山唐人街的三代粤剧演员展开,作者严歌苓以叙述者“我”的身份误入“中国移民历史博物院”,讲述三位“关山第一旦”在异国他乡寻找自身价值和定位的坎坷故事,阿三、阿六、阿九虽然不处于同一个时代,但他们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有相似的经历,呈现不同的抵御偏见和霸权的路径。《魔旦》讲述了一位名叫奥古斯特的中年犹太意大利裔男子,被旧金山唐人街的粤剧名旦阿玫深深吸引,然而年轻的阿玫却与一个“大人物”的中国情妇芬芬坠入爱河,导致奥古斯特在绝望中死于秘密暗杀。与涉及性别暧昧演员角色的文学戏剧《蝴蝶君》一样,《魔旦》也用迂回的方式改变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男性的偏见。国内对《魔旦》短篇小说的研究主要从对比的角度,运用互文性理论解构东方主义。如学者葛亮在其“安能辨我是雌雄”中着重对华人男性身份的文学再现,而学者郭海霞则从后殖民的视角分析严歌苓等华裔作家的文化认同态度。有一些学者认为严歌苓的作品擅于描写来自西方对女性性别、等级和种族的文化价值判断,指出对女性、东方和中国这些心理概念的指认,同时从中融入对东方主义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偏见的认同和妥协。本文将从三个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严歌苓在其短篇小说《魔旦》中对东方主义霸权的颠覆和反抗及对东方的真实重现。
一、东方主义幻梦
萨义德(Edward W.Said)书中的东方与其说是被抓住、被借用、被简化、被解码,不如说是充满丰富可能性的审美想象。他将东方主义落脚于人们并未注意到的文本“缝隙”中,试图建立起一个西方对东方的动态宰制机制。在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想象中,尤其是被东方主义影响的中国,经常被描述成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女性”,有时是象征性感的女人及妻妾形象。中国戏剧中不可或缺的乾旦虽为男子身却能在舞台上如鱼得水地将不同的女性角色模仿得出神入化。然而,根据中国几千年来独有的宦官文化,西方社会长期将东方文明女性化、阉割化、附加化,乾旦被视为具有阴性特征的表象。此外,绵延几千年的贵族父权制政治社会,使乾旦的戏剧表演风格包含中国女性的隐忍、美丽、贞节、温柔等多种性格特征。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特有的传统文化表演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地强化了西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女性化”的一种误解,并推动了他们东方主义幻梦的形成。
二、阿玫的人物塑造
阿玫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唐人街上的确是一位显赫人物,当时只有16岁的他,在以深棕色为基调的一张黑白相间的照片上,嘴和眼睛奇大,但是牙齿奇小,下颌从他的脸部一直到两颊都不住地向下尖,就像一张美女漫画。文章的一开头,阿玫的性别便被模糊化。腰缠得两个虎口上,都会用手触摸双手的指头;眉毛也都拔齐了,只有一条线细的阴影;嘴唇比牙还够小,涂了颜色就变成了一粒新鲜而欲滴的红豆。他身上阴柔秀气的女性特质既是他作为一名乾旦的必备条件,又是后来吸引西方男性的致命武器。“难辨雌雄”的阿玫不仅拥有双重身份,还日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与欧洲男性的阳性符号相对的是“东方”作为阴性符号的出现,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渐被贴上“放荡”和“女性”的标签,这种行为唤起并满足欧洲无法得到的性体验。萨义德认为东方是人们可以找到欧洲无法获得的性经历的地方。处于流散背景下,作为戏子的华裔群体渐渐被西方当成标签化、物化的“性对象”。
但是作为乾旦的阿玫,没有混淆现实和舞台上的自己,反而顺应并利用西方男性的“东方幻象”,模仿他们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在“我”的观察下,丰满的阿玫的形象逐渐展现在读者面前,他“与生俱来的气质”和人们心中“理想的雅致”是一致的。对于拥有不少女性特征的阿玫来说,他会朝着别人眼中的那个自己慢慢靠拢,迎合别人心中的美好形象。在与奥古斯特相处的过程中,他顺应着奥古斯特心中的那个自己,扮演一个温顺、美丽、隐忍的女子。为了维持这种美好的形象,他宁愿“吃点苦头,付出牺牲”。阿玫清楚地知道自己身上的女性特征正是武装自己有力的武器,而且只有通过外貌上的“自我阉割”,才能实现自己心理上的完整和独立。严歌苓笔下双性同体的“男旦”阿玫,让我们看到超脱性别之外的人性的无限可能。在西方男权思想的笼罩下,欧洲男性对于东方女性的病态审美未阻挡拥有雄性力量的阿玫。他正是利用这种特殊的雄性力量,打破了“东方幻梦”,实现了对自身移民身份的认同。阿玫努力学习,从会计学校毕业,成为社会主流的金融区人群,与命运抗争,通过不断努力打破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找到自己的人生归宿。中国男性在曲折迂回中最终夺取主动者的地位,为日后破坏基于不同性别、种族歧视的“东方幻梦”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三、芬芬的人物作用
严歌苓擅长从“性”的个性角度切入表现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她曾在《性与文学》中明确谈道,性包含一对对立统一体,性也能够用来解释一个宇宙间的所有的对称或互相对立、和谐或矛盾的社会关系。西方人眼中的华人女性被贴上“危险而性感”的标签,芬芬作为文中唯一一个华人女性,不仅为被压迫、被消音的女人争得一些更有发言权的空间,而且在颠覆东方主义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严歌苓笔下的中国女性经常生存于现代社会的黑暗底层边缘,但是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命运,她们仍然在奋力反抗和呐喊。严歌苓为读者详细地展现属于现代中国女性赖以生存的现代生活的恶劣残酷,甚至将这些现代女性在这种残酷的现代生存环境里的挣扎用一种极具悲剧性精神震撼血淋淋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中国女性通过在受到双重压迫的生活环境中顽强而柔韧地艰苦奋斗求生,凸显真实存在的一种精神道德价值。正是因为在这样恶劣的压迫环境中反抗,完美地衬托出作为一名中国女性身上强大而柔韧的精神生命力。
有史以来,东方女性一直被西方主流社会贴上“蝴蝶夫人”的标签,她们美丽、迷人,对西方男人顺从、忠贞,但又极其脆弱,迫切需要西方男性的保护。她们不仅被当作观赏玩味的主要对象,还被当成没有自由思想的任性玩物。然而,严歌苓对芬芬的塑造,不仅代表了中国女性的反抗之声,还重建了中国女性的身份认同。芬芬是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也是所谓那种“外室”。她有一个暖洋洋的丰满身材,圆圆的脸,含羞或发嗲时下巴向脖颈挤去,便出来并不难看的小小双下巴。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常常在危险的伦理边缘行走,在纯洁的爱情和本能的情欲间迷失,有时她们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芬芬散发着雌性的气息,让同为华人身份的阿玫在相同文化身份认同的作用下对她魂牵梦萦。阿玫也在这种“女性绽放的气息”中不断强化自己的男性身份,并逐渐将自己确立为“欲望主体”。同时,与芬芬调情这个情节的设置使他们共同的母语中文成为强有力权威,夺取了西方男性奥古斯特的发言权,改变了中国在白人统治下作为沉默寡言和弱势族群的被动局面。严歌苓利用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独特的自我性格构建方式,塑造出一位有血有肉、有勇有谋的女性人物。
虽然芬芬不是《魔旦》这部小说的主要角色和人物,但她充分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为了追求生存的权利,当个体上的生存权利和尊严矛盾时,把与其他强势势力的斗争和对抗变成一种阴柔又隐忍的追求生活本领。除此之外,芬芬还展示了她作为中国女性的智慧和勇敢。沈园方将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女性的形象分为三类,芬芬这个人物形象属于第三类“蛇蝎夫人”:她无处不散发着魅力,但是心狠手辣,残酷不留情面。在处理与奥古斯特和阿玫的关系中,芬芬发挥着她作为华人女性的智慧和魅力,利用手段陷害奥古斯特改变阿玫的命运。严歌苓通过塑造中国女性芬芬,打破了东方主义下的传统话语,赋予了那些处于寡言失语、无力反抗状态下的当代华裔女性独立言说的自由机会,并且以此书写着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东方。
四、奥古斯特的人物衬托
“东方主义”下的东西方关系被一分为二,也被冠以先进与落后、优与劣的标签。在西方现代社会,东方人常常被认为是处于由现代生物学上的决定论和现代道德学及政治学的劝诫所需要建立的认识框架之外,是“令人悲哀的异类”,将要被彻底解决、被限定。但是萨义德经过研究总结出来的这些东方的特点,在严歌苓的《魔旦》中,却在奥古斯特身上呈现出来。严歌苓刻意颠覆被标签化的权利关系,倒置西方男性对东方男性的阉割幻象,重构真实的东方。
作为文中唯一一个西方男性,严歌苓笔下的奥古斯特是被边缘化的、被阉割的。奥古斯特那双“自卑”的眼睛将戏内戏外的阿玫混淆,以至于奥古斯特从头到尾都处于被掌控着的境地。他被“舞台上幻化成无数个美丽女子”的阿玫重复不断地控制着,他难以明辨宛如脂粉般的表层和藏在脂粉之下的双重阿玫,同时也为自己心中那个“我”认为“虚构的”阿陆幻象所羁绊。严歌苓将奥古斯特塑造成一个同性恋者,虽然旧金山是同性恋者的“大本营”,但是同性恋群体是被主流社会排斥和避而远之的对象。在父权制意识形态中,同性恋处于男性性别阶层的最底层,他们从霸权男性气质中被驱逐,因为缺乏“男性气概”被边缘化。奥古斯特中等个子,皱纹密布的脸上还挂着“辛酸的笑容”……那双“自卑的眼睛”冥冥中认识到自身致命的弱点—自卑。这个被边缘化的人物从侧面衬托出阿玫的勇敢和强大。
根据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重新构建的性理论基础和框架,奥古斯特之所以无法自拔地迷恋上一个男孩,不是因为身上的男性特质,而是他身上的女性神韵和体态:怯懦、温柔、美丽、贤淑、内向……奥古斯特被心中那个不可能存在的“阿陆”深深地禁锢着,深深地沉迷于一个出自男性的审美视角构建下的“男与女之间游离的美丽小怪物”。奥古斯特在与阿玫秘密交往的两年中,渐渐偏离了自己的家庭,渎职了自己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庄严身份。对奥古斯特来说,芬芬和阿玫突如其来的恋爱是毁灭性的打击。他孤注一掷地控诉阿玫,竟游走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偷情,处在被动一方的奥古斯特被阿玫的一举一动羁绊着,逐渐迷失自我,严歌苓对于这种权利关系的颠覆体现出其对于东方主义的解构。
除此之外,西方的男性对于东方积极主动地探索在被东方主义笼罩的中国也意义非凡,在西方文明、父权制度的双重压迫统治下,由西方男性代言的东方化更具有说服性。萨义德在书中谈到一些东方学家关于东方的基本理解问题时说:“他们完全否认东方是一个有限的发展、转化和新的运动……的概率和可能性。”作为一种一成不变而又无创造性存在的东方,东方慢慢地被赋予一种永恒的负面意义。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来看,虽然奥古斯特没有完全摆脱他所说的“东方幻梦”,但是他已经跳出东方主义的束缚,开始用自己的话语传达和消解他们对东方的错误理解和心愿。奥古斯特对阿玫的迷恋是超越种族鸿沟的,美丽、神秘、温柔且同时带有东方女性隐忍的生命力种种特质,被奥古斯特由舞台上的虚幻表演放大到现实生活中审视东方与东方女性,亦是严歌苓对萨义德构建的一分为二的东西方世界的成功解构。
五、结语
长期以来,萨义德所构建的“东方主义”理论使西方社会对中国乃至东方产生霸权式的偏见。在西方人眼中,东方女人是具有异域风情的,她们扮演着温柔美丽、娇弱顺从、甘愿为爱献身的角色;东方男性则是软弱愚昧、任人摆布的代表。但是,近几十年来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发出了华人反抗的呐喊声,也彻底打破了西方自我陶醉的美梦,使其东方主义幻梦逐渐被摧毁。严歌苓华文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冲突归根结底还是“人性”的问题,作为一名华裔作家,她从人性的视角,打破性别与种族的束缚,试图重塑一个真实的东方形象、重构一个真实的东方人身份。《魔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代表社会上的三类人,严歌苓通过对这三类人物的塑造,打破了“东方主义”的幻梦,重现了原本被西方误读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