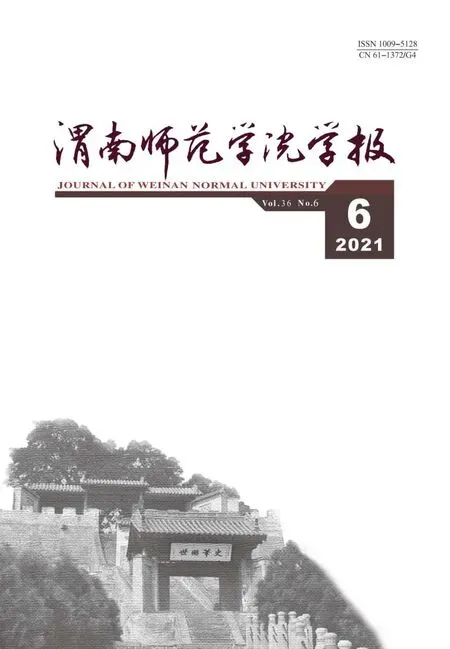《论六家要旨》的学术史意义
霍建波,王 菲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约前169—前110)转益多师,学识渊博。他曾跟随当时许多著名学者请教学习:“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1]3288在担任太史公职位时,他对先秦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广泛的考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撰成《论六家要旨》一文。该文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再见于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在这两部史书中,《论六家要旨》的文字表述基本一致,思想观点亦无不同,只有个别字句略有差异。该文虽篇幅不长,实际字数不足千字,但对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评价却非常精到,所采用的学术方法对后人也很有启示意义,充分展示了作者渊博的学识与深刻的洞见力。下面,以《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载《论六家要旨》文本为例,试对该文在学术史上的价值意义作简要论析。
一、首次对先秦诸子流派进行恰切分类
在我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乃是子学的时代。先秦诸子生活在世界文化史的“轴心时代”[2]69,诸子之学更是处在我国学术思想史的前端、源头,是我国学术思想的大根大本。后代的学术思想,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再到清代朴学以及近现代的思想流派,都多多少少受到了诸子之学的滋养与启发。吕思勉认为:“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3]3作为我国“纯为我所自创”的诸子之学,涌现出了后人艳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流派众多,思想繁杂,如何对其进行较为准确的分类,是一个既重要且非常困难的课题。正如梁启超所说:“分类本属至难之业,而学派之分类,则难之又难。”[4]4697
在《论六家要旨》之前,曾有不少人尝试着对先秦诸子进行流派上的分类。但是今天看来,这些分类均有较大缺陷,都是不成功的。如《庄子·天下》篇把诸子分为墨翟、禽滑釐一派,宋钘、尹文一派,彭蒙、田骈、慎到一派,关尹、老聃一派,庄周一派,惠施一派等六家,并对每派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分析和评价。[5]1077-1112但《庄子·天下》篇既没有提炼出每个流派的名称,且人物的归属也不切当,故其分类也鲜为人知。《荀子·非十二子》篇也把十二子分为六类,每类两人,分别是: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以及子思、孟轲;为了尊崇孔子、推崇儒家思想,荀子也对每类人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6]91-96同样,荀子也没有概括出十二子所属流派的名称,且一些人的著作亡佚,观点亦不为人所知,故其分类也未能得到后人的认可。《韩非子·显学》篇认为先秦显学只有儒、墨二家,并对其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批判。[7]183-187这里在分类时虽然明确了学派的名字,以儒、墨对称,却并没有提及其他各家学派,且其评价立场也不够客观。与司马谈同时而稍早的刘安所主编的《淮南子·要略》篇则大致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分别提及了儒者、墨子以及《管子》之书、晏子之谏、纵横修短、刑名之书、商鞅之法、刘氏之书。[8]534-536这里虽有分类之意,但并非专为先秦学派划分不同派别,其中有后世沿袭的学派名称,如儒、纵横,也有一些人名,如墨子、晏子,还有一些某某书之类,庞杂混乱。总之,这个分类也是不成功的。
而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一文,在继承前代学者对先秦学术思想分类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学派上的划分;同时,其分类又比较允当,得到了后人的一致认可。该文题目就很明确,《论六家要旨》即论析六家思想的要点主旨。而在正文中,更是把先秦诸子明确划分为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1]3288六家学派,后文则又分别称之为“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同时,因为题目中明确有“六家”字样,则“儒者”“墨者”自然也可称为“儒家”“墨家”,“阴阳”可看作是“阴阳家”的略称。如此,司马谈既明确了先秦六家学派的名称,又分别概括了其思想要点,分析了其自成一家的原因。综上可知,《论论六家要旨》完成了我国学术史上第一次对先秦诸子流派的恰切分类,不但拈出了最为重要的六家学派,而且对每派都有较为明晰而准确的评断,为后人探究诸子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谓意义重大。
梁启超对司马谈的分类创举作出了高度的肯定,他评价说:“此六家者实足以代表当时思想界六大势力圈,谈之提挈,洵能知类而举要。”[4]4697“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櫽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4]4697司马谈之后,刘歆《七略》在其基础上对先秦诸子的学派分类做了进一步补充完善,他在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这就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论及的诸子十家。[9]1724-1746至此,由司马谈所开创、刘歆补充完善、班固《汉书》予以明确载录,终于完成了对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流派划分,并得到了后世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先秦诸子流派划分,可谓厥功至伟。
二、首次用辩证法评价先秦诸子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法》一文中曾描述性地对辩证法进行了界定,他说:“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10]1278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辩证法,主要是运用“一分为二”的方式,把一些人物、事件、现象等分为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的两个部分。通过对两个部分的考察、观照,更全面、深刻地认识、把握一些事物或现象的本质、特点。在我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是就是首次采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来探讨学术思想的,并且以此方法为主、以比较法为辅,精辟地指出了先秦诸子不同流派的优缺点。“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与以上这些不同,它最早赋予了各个学派名称,同时并按自己的基准指出了各学派的优缺点。”[11]46
当然,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分为二的辩证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如《周易》中就体现了我国最早的辩证思维。《周易》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就是阴和阳,阴阳二爻按照一定规则排列组合成六十四卦,并且认为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自然现象,都存在着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就是阴和阳,即“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对立着的这些事物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不停地运动变化着的,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系辞上》)。《周易》还认为某一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过渡到“物极必反”的对立面去。《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谓“穷”,就是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变”就是由顶点向反面的变化,“通”就是变为反面之后又开始新的发展,“久”就是说明有这些变化过程之后才能长期存在下去。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1)朴素的对立统一思想;(2)朴素的互补对称思想;(3)朴素的矛盾转化思想”[12]288。
春秋末期的老子,也有相当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成为其哲学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首先,老子认为天地间所有的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性,是辩证存在的。同时对立的事物双方、对立的概念之间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并生的关系。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13]9我们怎样定义美、定义丑?怎样定义善、定义恶?都是没有确定标准的,因为这两组概念本就是相对而言的。一旦我们拿起标尺,对美丑进行判定、对善恶进行区分,从而让大家去追求,那么便带有了某种功利性,反而会使美、善本身失去了独立意义的美,或者说同时就会导致出现与它们相对立的丑、恶。同理,长和短、高和低、难和易也是如此。其次,老子还常常把事物的两面放在一起来立论,如《老子》第十一章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3]43在这里,老子以车轮、陶器和房屋作比喻,证明“无”和“有”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无”和“虚”的存在,“有”和“实”便不能体现出来,事物也就不能发挥其作用和价值。正所谓“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或。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岂虚言哉?故成全而归之。”[13]91矛盾的双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会相互转化。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3]165意思是说:“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向对立的方面发展,这是‘道’的运动变化的规律。而表现出柔弱虚静之性,如谦卑处下、虚静无为,则是‘道’的外在体现。天下之物都是由各种有形之体孳生繁殖而来,而各种具体有形的东西则是由不可视见、不可闻听、不可触及的无形之‘道’孕育化生的。”[14]163老子还说:“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13]235揭示了事物常常是向其对立面转化的,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看似是不幸实则是大幸,看似是大幸实则背后又隐藏着祸根。这种幸与不幸的转化往往是人们难以预料的,而且会一直发展变化下去,没有尽头,所谓“孰知其极”,这正是体现出老子可贵的辩证思想。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的《周易》与《老子》中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辩证法思维,且运用一分为二的方式来探讨自然与社会现象。但囿于时代背景以及人类思维发展的局限,在先秦时期并没有出现用辩证法思维来评价学术思想的哲学散论。而最早运用辩证法思维来评价学术思想,则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开始。司马谈在接受《周易》《老子》等辩证思维的基础上,第一次集中、系统、明确地采用了这种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评价先秦诸子,讨论学术思想,为后人认知、评价哲学思想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学术方法。也许他并不知道“辩证法”这个概念,但并不妨碍他熟练地运用此法评价学术思想。如其《论六家要旨》一文开篇即引用《周易·系辞下》中的话语,从一般意义上概括事物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接着对六家思想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进行了论述,便体现了明显的辩证思想。接着对六家思想中五家的阐述,均是从正反两家角度展开的。如阴阳家“使人拘而多畏”,儒家“其事难尽从”,墨家“其事不可遍循”,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等话语,都是从该流派的缺陷角度来立论的。而阴阳家“不可失”、儒家“不可易”、墨家“不可废”、法家“不可改”以及名家“不可不察”之处,则均是从该流派的长处或优势来讲的。其后,该文对这五家思想的具体分析,就是承接了前文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分别对阴阳家的“使人拘而多畏”、儒家的“其事难尽从”、墨家的“其事不可遍循”、法家的“严而少恩”、名家的“使人俭而善失真”等缺陷,以及阴阳家的“不可失”、儒家的“不可易”、墨家的“不可废”、法家的“不可改”、名家的“不可不察”等长处,逐一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概括,令人信服。仔细揣摩《论六家要旨》的字里行间,都能解读出一分为二的辩证思想。这种看待事物、分析问题的思维方法,今天已经成为人们看待事物、解决问题的常识。但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这种思想的出现以及运用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即使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珠玉在前,也未能引起其后封建时代人们的足够重视,偏重一面、固执一端乃至以偏概全等思想仍然层出不穷,由此反而更能看出司马谈的高明与可贵之处。
三、首次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进行精到概括
众所周知,人们对于任何事物或现象的认识都需要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对学术思想的认知和了解更是如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周天子大权旁落,东周政权名存实亡;各诸侯国尾大不掉,政治混乱,政出多门。在这种局面下,先秦诸子便应运而生,横空出世。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努力宣扬本学派的思想主张,批评和驳斥其他学派。诸子各派的代表人物层出不穷,学术著作亦汗牛充栋。如班固《汉书·艺文志》曾明确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9]1745可谓庞杂纷乱,令人目不暇接。如何对这一百多家按其思想之异同,进行恰当合并、分类,这就要求首先必须要对各家各派的思想主张有较为充分的了解和领悟。
事实证明,司马谈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主张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其《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六家学派的论断,即使放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亦觉得非常深刻、精辟,且持论较为公允。当然,这和其一以贯之的辩证思维也是分不开的。如其批判儒家礼仪烦琐,难以尽从,就抓住了儒家思想的痛脚;赞赏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1]3290,即重视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更触及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对阴阳家禁忌避讳颇多,令人产生畏惧甚为不满,对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1]3290的论述则十分赞同,都是合情合理、富有远见的态度。对墨家的过分节俭等行为,且以此作为所有人都必须要遵循的准则持否定态度;对其“强本节用”的“人给家足之道”,则十分赞赏。这些见解都是相当深刻的、令人信服的。而认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做法,只能“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1]3291的观点,更启示我们认识到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时代,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因为即使在现当代,国家律法的制定和实施也都需要充分考虑人情、道德、习俗等文化因素。对名家过分纠结于名实之辩提出了批判,对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1]3291,即循名责实,要求人或事物等都能名实相副则非常认同。再如其对道家言辞玄妙、难以知晓的缺点有所揭示,更多的是肯定赞扬之词,但是其赞美的言辞也并不是一味阿谀逢迎,而是建立在对道家哲学思想的准确理解之上。同时,也可由此判断司马谈的思想倾向。
笔者认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准确地拈出先秦诸子中的六家学派,且对六家思想所进行的精要概括和恰当论断,是我国学术史上开天辟地的拓荒性工作,对后人认识评价先秦诸子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刘歆在其基础上,又增加了杂家、纵横家、农家与小说家,使得先秦诸子流派更为清楚、完整。但平心而论,前六家思想才是先秦诸子的核心,对后代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后四家虽均也能自成一体,但其重要性与影响力,均无法与前六家相比肩。直到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著名国学家陈柱先生在撰写《诸子概论》探讨先秦诸子时,亦是直承司马谈,弃后四家于不顾。陈柱在《诸子概论·凡例》中开门见山地说:“本书所论述,以司马谈所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为限。以此六家为最要,且限于篇幅故也。”[15]1陈柱不但认为司马谈所拈出的六家最为重要,同时也十分赞同他的论断。故其《诸子概论》在正文中讨论六家思想时,均全文引用了司马谈的原话,或对其予以肯定,或对其分析探微,或指出其对后人如刘歆、班固等人的影响。由此可见,陈柱认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于理解先秦诸子的重要性。
当然,司马谈对于先秦诸子的讨论也是存在着缺陷与不足的。如顾兆禄、孙景坛二人就在肯定司马谈功绩的前提下,指出其至少存有三个缺陷。他们说:“应当说,在他那个时代,他能将百家划分成六家,为后世学术有所本,值得称道。但今天看来,我们不能说他的划分是科学的。司马谈的划分至少有三个缺陷:1.标准不一。儒、法、墨是从政治思想上划分的,道、阴阳是从哲学上划分的,名是从学科性质上划分的;2.百家有百科之嫌。他划分的百家分三个学科:政治、哲学、逻辑;3.对有些家的内涵定义不确。如前引儒家,他认为其核心思想是‘礼’,忽视了‘仁’…… 司马谈的划分远没有涵盖先秦的所有政治思想,以及由这些政治思想引伸出的治国理论。”[16]38-39对于这个评价,笔者虽然并不完全赞同,如认为道家、阴阳家是从哲学上划分的,则便否定了这两家所具有的政治思想因素,但他们毕竟也客观地指出了司马谈的一些局限与不足。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站在经过秦火之后的西汉初期,再结合当今学者对先秦诸子的认识和评价,自然就能够充分感受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难能可贵,体会到其在先秦诸子思想研究史乃至我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