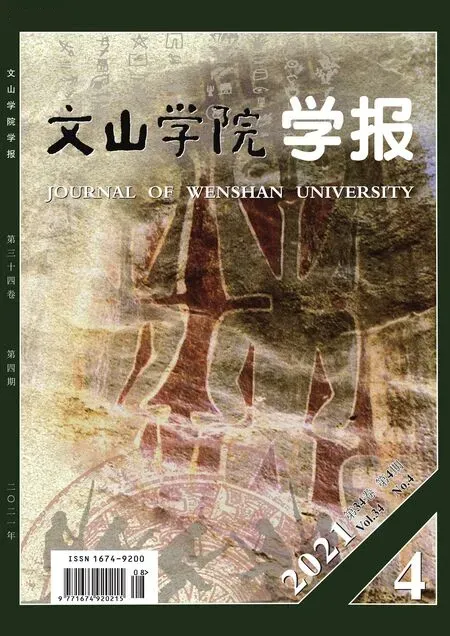文如其人 人如其文
——从《二月兰》谈谈季羡林散文的审美品格
张 勇
(广东理工学院 基础课教学研究部,广东 肇庆 526100)
每每读到文化巨擘季羡林的散文,总会被季老文章字里行间充盈且流动的情思所触动,感动于他对生活透彻的理解以及至善至美的精神品格。《二月兰》是季羡林在耄耋之年写的一篇回忆散文。文章通过对野花二月兰的描写及对自己人生往事的追忆,抒发了对亲人离开的无限怀念和对人世沧桑的无尽感慨,颂扬了生命的顽强与坚韧。《二月兰》以多维的审美意蕴寄寓和彰显了季老乐观通达的精神品格,表现了季老高洁的人格秉性、顺其自然的处世哲学和真善美的生命寄托。
一、多重审美的圆融统一
季先生曾用“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来描述自己散文创作的特点。其文关注的常常是凡人琐事,如小孩、平民、花草、猫狗等,漫谈轻诉而又娓娓动听,“形式似散”却是韵味无穷。“经营惨淡”则在于对文本结构的极其讲究,在写作过程中认真构思和反复锤炼,所以,先生的每一篇散文,几乎都有自己独具匠心的结构[1]。平淡是《二月兰》审美的关键词,平淡之下却有不平淡且多维的审美意蕴。平而实,淡而雅,季羡林将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淡美”思想推升到极致。
(一)言语层之平实中表本真
平淡朴实是季羡林散文叙事的最大特色。平淡朴实表现在对稀疏平常事的叙事和抒发上。二月兰是“十分平凡的野花”,老祖搜挖荠菜,婉如、小保姆、虎子和咪咪在小山上的身影,所有这些“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的物和事,季老却觉得“显得十分不平常”。[2]124而我们读起来也会觉得饶有味道、直抵人心,原因在于季老散文中蕴含的“真”。季老曾说:“我对散文提出来的标准是一个‘真’字。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有真感情,连叙事散文也必须‘真’,不能捏造,也不能胡编。”[3]由此观之,写真事、表真意、抒真情是季老散文的精髓、精妙所在。“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在百花丛中,决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2]123这种极其普通又毫不起眼的野花见证了季羡林的沧桑历程,寄托了情感上的悲与欢,隐喻着对人生的思考和生命的体悟。
《二月兰》中语言简约朴实,不避俚俗,不加修饰,文句自然天成。全文没有一个生僻字,没有一处晦涩语句,生活气息浓烈,好似一位邻家爷爷娓娓道尽家常事,丝毫不会让人觉得有所沉重和颦蹙。梁实秋曾援引胡适的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来化解“初学为文”时“不知如何落笔”的问题。此言竟好像是说季羡林的散文创作,用“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这种顺其自然的方式来还原、表现生活的本真。老话新谈,学者雷达在《我心目中的好散文》一文中也套用这句话来评议散文如何还原“鲜活”,并指出:“这就有可能说出新话、真话、惊世骇俗的话,‘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实话,以及人人皆领受到了,却只有很少的人可以揭穿其底蕴的深刻的话。”[4]127自由、纯正、真诚、无畏、不矫饰、不卖弄、不强求是季羡林的心灵追求和个体精神,他的散文才会尽显“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语体风格和表达方式。
(二)情感层之真情中显品格
对于二月兰这一常见野花之美的发现,季羡林是吃惊的,这不是矫揉造作,而是他发自内心的真性情。从偶然的注意,到模糊的幻觉,再到清晰的意识,二月兰不但闯入了季羡林的视界,还爬满了他的思绪,开遍了他的世界。由此,季老对二月兰的喜爱之情跃然纸上,自然而然地呼出“我的二月兰”。季老是直抒胸臆的“多情人”,有对小山野草的恨,也有对二月兰的爱;有亲人离世的悲,也有老有所为的欢;有世态炎凉中的寂寥与凄凉,也有至亲乖宠不离不弃的温暖与安慰。季老所表达的对事物、人生、生活的感情,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虚情假意,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真诚且自然的深刻情感体验,能引发读者心灵共鸣,与美的陶冶和感受。
季老还是心思敏感细腻的“有心人”,善于发现普通、平凡事物中的美。普通的二月兰遇到大年时,花开之盛、之美震撼到了季老。《二月兰》中三次提到“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了紫色的了”,这种天马行空式的联想看似赘复,实则凸显了花开之盛,以花喻人,赋予了花以人的精神品性,强化了对平凡生命体顽强力的歌颂。这其中蕴含和引发的情感是合乎情理、合乎自然的。因独到的审美视角和审美品格,最为寻常的事、物都有着不寻常的“美”,都有让季羡林悸动的情愫。季羡林朴素的审美追求和审美趣味,是一种更接近生活和人生的审美表达,更是一种大智大德上生发出来的“淡美”思想。“散文的魅力说到底,乃是一种人格魅力的直呈,主体的境界决定着散文的境界。”[4]128季羡林散文中自然流露的真性情源自于他质朴的为人、和气谦让的胸怀、淡泊名利的情操和通达事理的智慧。
(三)意蕴层之多维中见真思
《二月兰》文中平常与不平常、变与不变、悲与欢、世态炎凉与不炎凉等多重矛盾的正反对照,鲜明地揭示了二月兰的外在特征和内在本质,充分表达了季老复杂情感和对心理冲突的深沉思考,从而使文章丰富而深刻的意蕴生动地显现出来。开篇直言二月兰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却有凌驾百花之上的势头,一朵两朵几朵一夜间能变成百朵千朵万朵,小年稀疏几片大年遍地怒放,这无不凸显了二月兰的生长特征。极少注意的小花却在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多情的人问无情的花,人儿思绪万千而花儿却静默无语,二月兰是不会变的,而季老却年年月月在变,季老寂寥凄凉时二月兰却无动于衷、季老义愤委屈时二月兰仍怡然自得,季老囿于悲欢离合中,而二月兰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基于这多重矛盾的对比叠加,季老陷于悲欢难分的心理矛盾之中,不禁对苍松、翠柏、二月兰苦苦追问,最后在二月兰“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的寄寓中给出了回复,即顺应自然,超脱淡然。诚然,对于浩瀚广袤的宇宙天地来说,个人是无比渺小的,如空中沙尘,何来归去;对于永恒发展的大自然而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是微不足道的,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
《二月兰》中季羡林的心理活动变化呈现出“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层次。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论中,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了人的完整人格,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可以从它们之间的联系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本我是人在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面对亲人和爱宠一一离去的残酷现实,季老内心是极不愿意接受的,所以惊讶于二月兰生命力之顽强,借以悲叹人的生命之脆弱,于是在迷离恍惚中产生了幻觉:二月兰疯狂地生长爬升,“爬上了树,有的已经爬上了树顶,有的正在努力攀登,连喘气的声音似乎都能听到”。可是,理性的自我却让人的意识觉醒,与二月兰有关的记忆不断浮现,越来越清晰,仿如昨日,“近在眼前”却“可望而不可即”,物是人非事事休,季老在悲喜交集、悲欢难分的心理矛盾中不断寻找内心平衡。进而,季老希冀达到超我境界,即“纵浪大化中”“悲欢离合总无情”。须知人的生命本是脆弱,现实原本残酷,应如二月兰待世事沧桑如浮云,超脱一点,一切顺其自然,无所谓什么悲与欢;如老猫从容悄然地离开人世,淡然一些,一切循其规律,不较真什么离与合。读者还可以从文末“忘记年龄”“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话语中预见季老即将走出悲伤,放下过往,步入又一个新的人生征途,诚如他在《希望在你们身上》中所说,“像我这样年届耄耋的老朽……虽无棒在手,也绝不会停下不走,‘坐以待毙’;我们仍然要焚膏继晷,献上自己的余力,跟中青年人同心协力,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3]。
《二月兰》文中“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语句的重复反映了“景象—忆象—意象”的寓意层面。第一层为景象,是季老创作此文时看到“整个燕园竟成了二月兰的天下”的现实景观,是恰逢二月兰开花的大年,满园遍地都是紫白相间的小花,似紫云白雾般的壮丽景色。第二层为忆象,是季老涌上心头的回忆,是与二月兰相关联的春日燕园情境,身影晃动在二月兰紫雾中搜挖荠菜的老祖,穿行于二月兰紫雾中的婉如,与二月兰结缘的小保姆,在二月兰丛里玩耍的两只小猫,如画面般一幅幅在季老脑海中闪现,紫雾萦绕了季老整个内心世界。第三层为意象,是季老隐寓于二月兰之中的人生精义和生命哲学,二月兰在季老的沧桑悲难面前,始终怡然自得,“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至此收笔,无须多言,文本境界自成高格,让读者体悟神交良久。
二、情理哲思之深挚旷达
《二月兰》情感浓烈、粘稠、醇厚、深沉,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种情感基调的生发原因有三:其一,亲人的离逝。《二月兰》是在季老失去老祖、婉如两位至亲及两只宠爱小猫境况下完成的。“回忆这些往事,如云如烟,原来是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灵山,可望而不可即了”,“世界虽照样朗朗,阳光虽照样明媚,我却感觉异样的寂寞与凄凉”。[2]126物是人非,亲人的相继离开给季老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对亲人无尽的哀思与深深的怀念如笼罩烟云挥散不去,始终萦绕在季老心间。其二,丰厚的生活体验。从早年弱国子民甚至行将亡国的滋味,到之后留学异国他乡的离愁别绪,到回国后的欣喜奋进,再到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成为“不可接触者”,最后“文革”后的平反,成为了“极可接触者”。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后,这一切对于季老来说,有如“看尽人间繁华,三千浮生若水”。其三,内敛的性格脾气。季羡林不爱出风头,为人处世一向低调,被称为“好好先生”。他的处世原则就是对小事“不解释、不辩解、不争论、不反击”,对大事“有脾气、有观点、有态度、有原则”。可以说他的内敛低调是一种涵养更是智慧。
(一)挚爱生命
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季羡林心中都充满着对世界、对生命、对生活最质朴的挚爱。季羡林对每个生命体都充满着喜爱之情。《二月兰》中老祖、小保姆、女儿婉如、小猫等等每个生命体都鲜活灵动,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寄托了季老的悲与喜、忧与乐。譬如“虎子和咪咪也各自遵循猫的规律……等待死亡的到来”,让季老“忆念难忘”并感到“无边的寂寥和凄凉”;“我的小猫憨态可掬,依偎在我的身旁”给季老“带来了无量的安慰”,并支撑着走过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与动物的心有灵犀、相依相伴,抒发季老的真性情之余却也表现了他对平凡生命的热爱。季羡林似乎格外欣赏二月兰、夹竹桃、野百合、野蔷薇等这般生命力旺盛的寻常花草。他赞赏夹竹桃“看不出什么特别茂盛的时候,也看不出什么特别衰败的时候,无日不迎风弄姿,从春天一直到秋天,从迎春花一直到玉簪花和菊花,无不奉陪”[5]71的韧性;赞叹二月兰“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么悲与喜”[2]124。“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中“我的”二字显得既真切又亲切,这是一种打心底的欣赏、喜欢。二月兰这般“一切顺其自然”和“无所谓悲与喜”的品格与季老的人生哲学是高度契合的。在《八十述怀》(1991)中季羡林引用陶渊明的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来表达自己达观的精神追求,这也正是他性格特征的完美注脚。
(二)深爱故土
季羡林对祖国、对故园也同样饱含深情,“母亲”一词在他的情感体系中分量极重。季羡林曾言:“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在季老的价值观中,亲情远胜过名誉地位。季老在《赋得永久的悔》(1996)中曾言:“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6]这种“悔”意来自于母亲离开带来的深切悲痛及未能尽孝带来的无尽的恨。季老一生中深刻难忘的记忆多是与故土家园有种种渊源,在《夹竹桃》(1962)中有这么一段:“我离开了家,过了许多年,走过许多地方。我曾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过夹竹桃,但是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5]72。见微知著,深沉、深厚、深挚的乡土情结是季羡林情感的重要拼图,也是他博大胸怀的重要根基。
(三)热爱生活
季羡林对生活始终充满着热爱,他知天乐命、笑对人生。“我问三十多年来亲眼目睹我这些悲欢离合的二月兰,她沉默不语,兀自万多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2]126这份从容、镇定、淡然虽说是二月兰,却也是季老自身的人生写照。每当艰难时刻,季老又何尝不是如二月兰这般镇定自若、处变不惊?季老患有老年性白内障,在一次手术中,一面听着两位主刀大夫的交谈,一面听着医疗仪器碰撞的声音,对于这些,他却感觉“一切我都觉得很美妙”[7]264,还不禁默诵起东坡词。季羡林独独推崇李白和苏轼,他认为“太白和东坡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两位最有天才的最伟大的作家。”[7]265推崇太白和东坡不仅仅是因为两人的文采和天才,更是其性情中共有的洒脱、豪放、博大、活力、随性感染到了季羡林,且能从两人的作品中得到人生启示和感召力量。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坚毅乐观精神的一种时空穿越,也是季老对这份精神的一种传承、呼应与和鸣。季羡林纵浪大化般乐观通达的精神品格源于不屈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价值的积极探求,源于面对生活挫折而辩证看待得失的人生观,源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挚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亲人的依恋,源于他是一个心灵旺盛的人,对维持自我主观幸福感有着极强的调适能力。
三、学者型散文的新高度
季羡林先生博古通今、才思敏捷、笔耕不辍,其著作等身。作为东方学大师、国学大师和佛学家,人们所高度关注的是他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罗语研究和翻译文化研究等方面的学术建树,而往往忽略了他的散文创作。季羡林的散文创作看似是学术研究之外的“副业”,却横亘数十年,留下了数百篇的散文作品,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他广泛汲取中国文学史上不同的优秀写作风格,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创作理念和散文品格。
(一)情理兼容、自然天成
季羡林散文有着明显的阶段性。早期的文句较长,辞藻华丽,注重内心苦闷心情抒发。中期文句渐短,语言趋平实,抒情走向直白。后期文句流畅,语言自然质朴,注重情、趣、理。纵观季羡林散文创作生涯,情理兼容、自然天成是最为突出的审美品格。这种品格的形成与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审美经验和人格境界有关,又与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息息相关。中国古典文艺深深地影响季羡林的散文创作,《二月兰》中对苏东坡词、陶渊明诗、欧阳修词、纳兰性德词、蒋捷词等的引用和化用就可见一斑。
季羡林热爱散文,他谈及自己“偏爱散文”时言:“我觉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散文最能得心应手,灵活圆通。”[7]254季羡林对传统散文的理念和格局带来了不小冲击,甚至颠覆性影响,他是20世纪中国散文家的“另类”存在。季羡林打破了传统散文的文体定势和审美图式的束缚,开创了一种闲适、开放、自由、灵动的新范式,继承了古典、传统的诗文语汇并创造性地予以转化、升华,拓展了散文的审美形态和发展空间。季羡林散文体现着对人生存境况的理性分析,渗透着对人生意义的积极思考,充溢着传统散文中不常有的哲学思维。季羡林将散文写作推升到“事、景、物、情、意、理”融合的新高度,可谓是感性和理性圆融统一的典范。
(二)守正创新、大道至简
《二月兰》作于1993年,此时的季羡林心若幽兰、静如止水,无所谓“悲”与“欢”,对人生沉浮的泰然处之。人格上的臻化入境,写作上的长辔远御,平淡的叙事下深藏着季羡林深邃的哲理思想和对生命的无尽思考。在个体精神上,季羡林能传承经典精神又能摆脱现实压力,有着足够的感应能力和辟新能力。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生存环境和文化语境的转变,文学中人文精神日渐滑落。在如此大环境下,季羡林的散文创作仍能坚持“五四”精神传统,充满着理性的智慧,却又饱含人文关怀,与周遭相比较,季老是孤独的。恰恰是对这种理想的坚守,才成就了季羡林散文的醇厚、睿智和理性。
季老散文“随笔”特点明显,什么都说,什么都谈,什么都写,写出来又别有一番趣味。季老是一位学术研究功力深厚的学者,按理来说,其文章应是或艰深晦涩或百思莫解或高深莫测,事实上却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情趣理趣兼容。一个个宏阔的话题说来就来,看似信马由缰、海阔天空,甚至海说神聊,细思量实则是信手拈来、言之有物且细致入微。一个个厚重的话题,季老将写变成“谈”,譬如《谈东方文学》《谈西学东传》《谈中国的“学统”》《谈中国书法》《谈佛论道》《谈文学流变》《谈中国精神》《谈礼貌》《谈孝》《漫谈皇帝》《漫谈散文》《漫谈古书今译》等等。任何话题在季老这里用“论”或“议”或“析”都是一种繁复、负累,所谓大道至简,已无需用华美的字词点缀题目,这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气度和强烈的文化自信。如季羡林认为的一样,“散文精品”要“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娓娓动听、逸趣横生,韵味无穷”[7]257,他正是这样践行的。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季羡林是人品与文品完美合一的榜样,为学者型散文树立了一个标杆。一纪弹指间,季羡林的身影虽愈行愈远,但他的散文读起来却越加醇厚,他的人生智慧、处世哲学和精神气度必将愈久弥深,不断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并启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