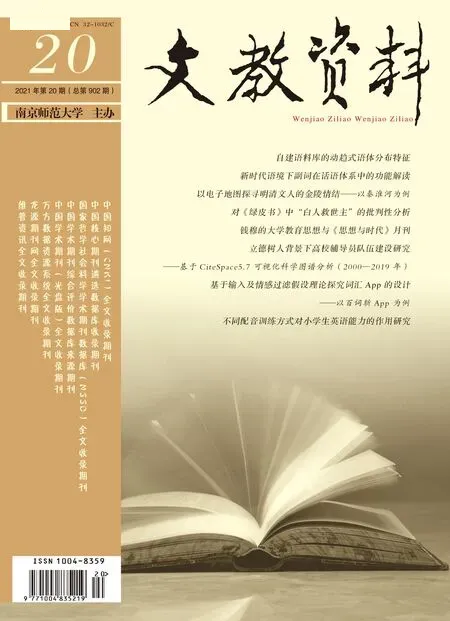《补玉山居》中的双重视角
周延蓉
(天津美术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天津 300000)
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以高质多产的作品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与认可。早年文艺兵和战地记者的经历使她在军旅题材创作上游刃有余;走出国门后,写作题材和风格发生深刻变化,在文化冲突和生存压力之下关注移民话题;同时,置身海外使她能够用旁观者的超然态度凝视故土,创作出一系列与历史、革命相关的作品。出版于2012年的小说《补玉山居》是她重要的转型作品,她从军旅、革命及移民题材中抽离出来,回望故土、聚焦当下,将视线转向北京郊区农家客栈“补玉山居”,借住客的命运流转折射出近二十年的山乡环境巨变。严歌苓说:“我想通过这本书给读者一个放大镜,让大家近距离观赏时代的那个变迁。”(蔡震,2012)“放大镜”下的女性人物包括客栈老板娘补玉、上流人士李欣、散打冠军孙采采、精神病人文婷和吸毒者季枫。她们与男性人物之间的依存、控制和爱恨情仇构成若干相对独立的故事:补玉与周在鹏共谋山居发展大计,李欣和温强燃尽欲火后分道扬镳,孙采采给予冯焕信任与温暖,文婷与张亦武艰难谱奏黄昏恋曲,季枫毅然了断对洪伟的新仇旧恨。“补玉山居”容纳了个体户、作家、军人、商人、富豪、海归、病人和边缘人物,呈现的众生相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缩影。有评论认为作品结构采用了拼贴、杂糅的方式,叙事呈现出一种“花朵式”的形态:补玉的故事是花托,其他几组人物的故事是花瓣(沈昕苒,2015)。另有解读指出,故事以客栈发展为脉络、以时间为横坐标、以历史变迁为纵坐标,呈现出舞台剧式的叙事场景和生活化的叙述结构(马藜,2014)。批评意见强调该作品对现实题材把握无力、人物选择不具备代表性,显示出作者长期旅居国外,对中国现状缺乏深刻、全面的了解。尽管不乏批评声,但小说引领新的创作方向,紧扣时代主题,反映作者的环境忧思,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不容忽视。
本文拟从叙事角度出发,指出作者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和全知视角,通过视角转换较全面地反映特定时代的“众生相”和社会特征,双重视角的运用使叙事更立体和客观,产生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并为读者留下想象、思考的空间。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和全知视角分别指旁观者“补玉”的视角(人物视角)和无所不能的“上帝”视角(作者视角),前者具有主观性,后者具有客观性。人物视角好比放大镜,让读者近距离观察山居当下的零散点;作者视角好比望远镜,带领读者远眺山居之外的时空,弥补“补玉”视角的有限性,消解主观色彩,让人物故事变得完整连贯。两种视角转换使作品交替呈现“场景式”和“全景式”画面,满足读者阅读审美期待,引发共鸣与共情,深化作品主题。视角变化将人物眼中零散的“点”和全知视角里的“线”“面”结合,架构出人物命运的立体图,并反映出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侵入乡间的后果:在历史滚滚向前的洪流中人心摇摆、环境恶化,山村的质朴和宁静慢慢消失,客栈渐渐走向没落,多种不可逆因素齐鸣共振,奏响了“自然乡村”的挽歌。
一、叙事视角和视角转换
叙事视角是指叙事时观察故事的角度。视角转换强调转移、变化或切换。小说创作之初,一般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形式叙事,当“上帝”视角不能满足创作需求时,作者开始转换视角,为作品带来新的活力(陈敏,2019)。“与叙事诗、戏剧、芭蕾舞、电影等其他叙事形式相比,小说具有运用、转换叙述视角的最大自由度和可能性。”(申丹,2001)在全知模式中进行内部视角转换,可产生短暂的悬念,增加作品的戏剧性。当叙述者摆脱了全知的上帝式叙事姿态之后,可以将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感展示给读者,由读者思考和体味作者的创作旨意(吴欢笑,2005)。“现代小说往往先由作者开始自述式讲述,随后渐渐过渡到从人物角度进行论述,只要这样的转换符合逻辑和感情发展的需要,读者就会顺从地跟随作者,不知不觉从作者的角度进入人物的角度,又从人物的角度回到作者的角度。”(安东诺夫,1966)人物的限知性视角无法避免主观色彩,这种角度往往与观察者的态度、观察者与故事的关系(旁观者、叙述者、参与者)和观察的方式有关,全知视角能及时修正人物视角的主观性,使读者形成客观和全面的印象。视角转换对读者产生的效果表现为读者对作品空白的填补,也可以表现为读者对作品的审美期待。托多洛夫指出故事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在读者面前(申丹,2001)。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通俗的“上帝”视角,具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特点。第三人称限知视角是指人物视角,是一种亲身经历的视角(陈敏,2019)。《补玉山居》中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即作者的叙事角度,第三人称限知视角是补玉的观察角度。人物视角因主观和有限存在视线盲区,由此而生的误差不经意间起到“陌生化”效果,使原本普通的印象变得深刻,延长了审美体验。作者的全知视角填补了人物视角的不足,带读者进入更广、更深、更客观的领域,在“全景图”中探寻作品的旨意。人物视角留下较大的空白和假想空间,全知视角揭露真相、呈现全貌,二者的交错使用为作品拓宽维度、增添活力。
二、人物视角的有限性、主观性和陌生化效果
补玉是作品中的灵魂人物,是故事的旁观者、讲述者和参与者。“补玉山居”为三教九流的客人提供表演场域,在“花朵式”叙事形态里,没有补玉这个花托的存在,其余花瓣将无所依附。作家周在鹏的建议和资助使她打造出名冠一方的“补玉山居”;潜在的市场吸引来投资者冯焕和女保镖孙采采;商人温强带着李欣在客栈回味青春、互相补偿;山居对文婷和张亦武而言是享受自由、回归正常的“乌有乡”;季枫和洪伟在那里遮蔽罪恶、隐匿身份。补玉是一名忠实“观众”,多年迎来送往的经验和“猜测身份”的喜好使她注意到一些特殊客人,通过观察、猜测、聊天、偷听了解他们的人生过往。旁观者视角将四组客人的故事雪泥鸿爪般呈现出来,使读者有近距离“放大镜”式的观看体验。补玉虽然明察秋毫,但看到的大多是有限、零散的片段;她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却很难测透虚虚实实的“人性”,曾不止一次看走眼、认错人:认定冯焕和孙采采之间存在不可告人的金钱关系;从未发现文婷和张亦武有精神问题;猜测季枫是受害者,却看不透她内心的愤怒和决绝;发现温强和李欣是“旧相识”,但不知道二人之间存在巨大的隔阂——“猫头鹰事件”。用她的话说:“来我这儿住店的人,个个的我都看不出来:趁不趁钱呀、是不是夫妻呀、有没有偷我一条浴巾要不就一个烟缸啊,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严歌苓,2012)
由于无法知道客人在山居外和私密状态下的情形,深受自身经验和见识的影响,补玉的视角不仅有限、片面,还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20世纪90年代初,“不知北京人是怎么顺着河道找到了这里,把这个夹在笔陡的山缝里的小村庄说成仙境”(严歌苓,2012)。许多“野鸳鸯”陆续来到小村子过周末,补玉靠着干净的利落及高中生的遣词造句水平将全村的客源截到她家,由于男女客人成双成对,她想当然将这种关系推及很多人身上。富豪冯焕每次光顾都带着年轻女子,补玉很快发现女子并非秘书、保姆,而是招之即来的风尘女子。冯焕受到恐吓聘请退役散打冠军孙采采当保镖,采采单纯善良,不仅保证安全,还激活冯焕麻木僵死的心,二人之间形成一种充满信任、超越年龄、类似亲情的关系。当他们为躲避仇家来到山居时,补玉断定瘫子换了口味,“冯焕太长进了,找的这位小姐一点不美艳,就是让你看着舒服,像渴了的人见了水,冻着的人看见棉花一样舒服”(严歌苓,2012)。当她和冯焕发生利益冲突时,看到采采百般向着“老板”,对其产生恶感,认为这个“五大三粗、没心没肺,反而比那些浓妆艳抹、水蛇腰流水肩的妖冶小姐们更算计。是一百六十斤的大诱饵”(严歌苓,2012)。采采被误认身份后受辱出走,冯焕失去精神支柱,进入绝食状态。补玉开始愤恨起来,认定采采用尽方法折磨冯焕,算计对方的钱财。在这个例子中,补玉的看法越离谱,读者越会觉得采采无辜正直;补玉越是同情冯焕,读者越倾向于改变对瘫痪富豪的看法,用补玉的眼光看到他身上被采采激发出来的善良和真心,对他任性失意的状态持体谅的态度。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艺术创作手法和效果,原指诗歌语言对日常语言的变形、扭曲和重组,核心是事物的反常化、形式的复杂化,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延。艺术是为了换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朱立元,2001)。旁观者视角的有限性、主观性与真相之间的差异造成陌生化效果。补玉不了解采采的运动员背景,在她的叙述中后者明显被异化:这个身形高大的女孩是“半截柱子式的女孩”“大块丫头”“憨脸鸡贼”“铁塔似的”“五大三粗”“膀大腰圆”的“彪形女孩”。她相貌单纯,身形不凡,“短短的脸,圆鼻子单眼皮”“一笑嘴巴从东咧到西,肚里的念头都看见了”“海碗粗的腿、茶杯粗的胳膊”。采采锻炼时,“河对岸一个金鸡独立的身影一脚立地、一脚登天,两腿拉成一条线,碗口粗的腿被她轮番玩”;收拾屋子时,“所有物什在她手里都没有了分量和体积,干起活来好像玩活儿”(严歌苓,2012)。以上透过旁观者眼光的描述令采采成为作品中最鲜活真实的人物,在带来陌生化效果的同时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性。
三、全知视角的全景图效应和客观性
全知全能视角,或是“上帝”“隐含作者”视角,及时填补补玉观察猜测的局限性,多方面呈现山居之外的事件和窗帘背后的状态,完善人物性格和经历,使作品成为反映人性幽微和社会变迁的全景图。通过适时地转换叙事视角,作者邀请读者从高于小说人物的角度远观各路房客,关注他们的人生往事,感受他们的内心变化,体会当时的社会环境背景,对他们保持认同、支持和理解的态度,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以冯焕为例,全知视角中他被仇家威胁跟踪,经历了办公楼火灾、剧院暗算和短信威吓之后,曾威震四方的富豪脆弱得像婴儿,随时需要采采的保护、安抚。读者会随着描写进入这位身体残缺、徒有金钱之人的孤独内心,对其产生谅解和同情。在“上帝”视角下的前妻、女儿、兄弟都是为钱而来,读者便不难领会他为何对采采产生如此强烈的依赖和需要。季枫与洪伟的故事亦是如此,在补玉眼里,季枫是幽魂一般、没有形体、行动诡异的人物,她与丈夫的关系难以说清,似乎存在“迫害”“施虐”的情况。当叙事转换为全知视角后,季枫不为人知的身份——打工女孩、幸福妻子、安心母亲、社会边缘人物一一呈现,她从“赵益芹”变成“赵晓益”,最后成为“季枫”,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巨大的人生变故。读者随着视角转换进入她的内心,惋惜她被迫成为“零”的命运,即成为洪伟眼中毫无价值的社会渣滓。补玉看到温强和李欣是“旧相识”,不知道他们由于阶级差别只是互相试探,从未“相好”过。当他们离开客栈后,补玉发现李欣留下一双高跟鞋,温强变了电话号码,但不知道从此二人各走各路,不再联系。唯有在全知视角下,读者才能了解温强从军、提干、转业、下海的经历。他与李欣数度相遇,但后者高高在上、遥不可及,温强只能借着话务员小方偷听电话的机会想象李欣的情感生活。李欣成了外交官夫人,长期生活在国外,温强娶了小方,过起了平凡的日子。多年以后,成为富商的温强和海归李欣偶遇,一起来到补玉山居弥补多年前的遗憾。纵使温强特意购买豪车装派头,假称戒烟提升形象,以便在李欣面前摆脱自惭形秽之感,但他发现差距依旧不可逾越,内心依然受着导致战士横死的“猫头鹰事件”的折磨,他选择表达压抑多年的不满和彻底放手。文婷和张亦武同为精神病人,在山居无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全知视角下有关二人的叙事呈现模糊、凌乱和碎片化的特点,符合精神病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有常人无法理解的疯狂举动,张亦武在双重人格的驱使下自伤;文婷有强烈的“受害者”情节,反复喝肥皂水洗胃对抗肮脏的世界。他们被局限在“福利院”和亲人的监视当中,却有追求自由、享受精神恋爱的执念。一对疯子的感情如此克制纯净,摒除一切杂念和杂质,与山居里众多的红男绿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纵观以上四组故事不难发现,首先,全知视角的应用弥补了人物视角的不足,使人物多角度呈现出最真实的样貌;其次,全知视角修正了人物视角的主观色彩,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真相;再次,全知视角深入人物内心,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人物情感发展和心灵困境,理解他们在特定时刻的选择,产生强烈的共情感受;最后,全知视角展现了社会现实的全景图,将20世纪90年代初到奥运会召开前夕近二十年的时间画卷徐徐展开,较完整和生动地刻画出时代变迁和人物被时代潮流裹挟的命运。
四、结语
严歌苓在《补玉山居》中交错使用人物视角与全知视角,讲述一个农家客栈近二十年内发生的变化,以放大镜模式近距离观看山居内的客人,以望远镜模式眺望广阔时空里的人物命运,透过近景和远景的切换,呈现出场景图和全景图。人物视角的主观叙述和事件真相之间的差异产生了陌生化审美效果。同时,人物视角为读者留下了悬念和想象空间,使读者有机会形成个人化解读。全知视角呈现了宏大的社会背景,并标明了其中的重大节点,当人物置身于历史洪流中时,他们或顺应潮流抓住机会、赢得利益,或在泥沙俱下之时无力抗争、被浊浪拍成碎片。总之,双重视角的应用描绘了时代众生相,折射出了社会变革带来的多重影响,当山乡建起法式“卢浮宫”、孩子们兜售假冒“鸡血石”、补玉用养殖兔子冒充野兔时,读者难免发出“乡野消逝、世风日下”的感慨。几组核心人物因为误解、差异、现实和仇恨在人生中交错,他们将何去何从,小说留下了开放性的结局,任读者想象。但山村的结局是注定的,当资本侵入乡间,带来一时繁华并践踏环境之后,一切都难以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