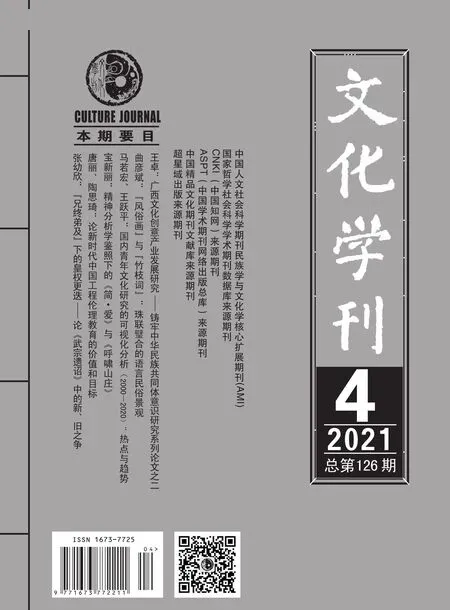以诗歌的针线绣出石家庄历史画卷的经纬
——评田耘的城市史诗《石家庄长歌》
陈玉巧
当代诗人西川曾言:“历史之于中国人相当于神话之于希腊人。”[1]这句话表明了中国人极为重视历史。的确,几千年来朝代不断更迭,但中国的历史记载却不曾中断,历史撰述的翔实度更是其他国家不能企及的,这也是中国文明能源远流长的重要原因。对历史的重视也影响了历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咏史”是自古以来中国诗人着重书写的一种题材,历史上曾产生了大量优秀的咏史诗。杜甫以诗歌为主要书写体裁,对当时的社会动荡、民生疾苦进行了深刻的刻画,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诗史”的美誉。进入现代以后,古代汉语革命性地转换成为现代汉语,古典诗歌体裁也随之转换成为白话文的自由诗体裁,但这并不影响现代诗人以诗歌书写历史的传统延续。因为现代新诗体裁更加自由、灵活,书写历史的方式反而变得更加活泼、多样和丰富。只是进入当代以后,尤其是朦胧诗出现之后,以口语诗歌乃至后来的网络诗歌为潮流,诗坛上呈现出反理性、反崇高、反英雄、反传统的文化倾向,一味偏向于日常化、平凡化,盲目追求文字游戏化,过分强调个性化的表达,逐渐形成诗歌创作的庸俗化潮流。
在当代诗歌创作越来越聚焦于自我内心世界、个人灵魂自白的时候,诗人田耘始终坚定地进行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正如她所言:“我就从来没有盘桓于个人化的抒写,而更多的是对人类命运的整体表达和对宏大的外部现实世界的诗学观察。”其创作于2018年的诗集《石家庄长歌》,试图对河北省会石家庄30万年的历史做出独具匠心的阐释,使其成为一部宏大叙事之作。本诗集由61首咏史诗歌构成,叙述的历史从2018年一直追溯至商王朝,按古代、近代、辛亥革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时间顺序分为四个部分。在文学长河中,以石家庄的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散文与诗歌是存在的,但是,用整整61首咏史诗歌整合成史诗性作品的形式来书写这个城市,将石家庄30万年历史兴衰的磅礴画卷铺开在读者面前,未曾有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石家庄解放七十二周年的献礼之作,这部史诗性作品可谓史与诗互现,匠心独运。
一、诗具史笔
诗具史笔是指诗可为史、以诗证史的创作手法,即富有历史感的诗歌可作为史料使用,可以之证实历史。在反映历史真实方面,诗不如历史文献翔实,不能做到细致入微的描述,但可以用白描的写实来摹状历史的具体情状,甚至可以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之所以称《石家庄长歌》为“诗具史笔”,是因为它的题材、内容不是关于诗人的经历、自我的情感和心理内容,而是石家庄30万年的历史事件的书写,饱含着诗人对石家庄发展史的认知性质。
(一)诗歌中真实的历史再现
有人评价《石家庄长歌》是诗歌中的报告文学,可见作者在写作时把历史真实性放到了首位。
一方面,这部史诗性作品广泛征引经过反复考证的相关史料、掌故乃至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史料、掌故乃至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是历史再现的基本要素以及主要依据,历史的再现取决于诗人的智慧与灵感,更强调史料、掌故乃至当事人、亲历者回忆的精准。诗人在该诗集后记中强调:“书中与石家庄相关的众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所有细节,都经过了反复考证。”《石家庄长歌》中的很多诗歌开篇有对相关史料整段的引用,如《在井陉口》的开篇引用了宋朝诗人苏轼的《紫团参寄王定国》,《吴禄贞,或石家庄1911》的开篇引用了孙中山《悼吴禄贞文》,《在太行山上》的开篇引用了合唱曲《在太行山上》中的歌词……所述之事皆有材料为证,强调事事有出处,这充分说明诗集中的人物、事件及其过程并非作者凭空虚构或想象出来的,而是遵循历史真实原则的再创造。此外,诗作还采用了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父亲的轨迹》在阮英利的讲述中回忆阮平的事迹:“此刻,已经上了年纪的讲述人阮英利/正在用一根又细又长的语言的线/把这些发光的轨迹,用一个名字串联起来/——阮平。”《让时光倒流回1965年的石家庄》通过王志国的记忆,展现1965年的石家庄:“就请跟随2017年/熙熙攘攘的中山路过街天桥上/古稀老人王志国的记忆/穿越回1965年的石家庄。”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是解读历史有力的资料,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再现历史,这种强烈的现场感使作品的真实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另一方面,该诗集试图再现历史上的时空情境,凸显当时事件、人物、场景的现场性。人们不能再回到历史现场,但可以镜像式地再现历史的曾经,即在诗歌中再现真实的人物、情境、话语,营造历史的“现场感”。其一,人物形象的真实。在选择历史人物时,受诗歌篇幅的限制,田耘选择了特定时期事迹丰富和富有性格特点的人物,如刘邦、刘秀、吴禄贞、高克谦、傅崇碧、毛泽东、马胜利等。诗人把他们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选取典型事例,对人物的语言、行动、神态等方面进行刻画,尽力还原人物的真实面目。如在《石家庄汉朝那些事·刘邦篇》中,诗人通过分别列举刘邦一生中重要的事迹,展现了刘邦的疲惫、豪爽、仗义以及负心,让读者认识到了一个凡人刘邦。可以说,石家庄历史本身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缺乏人性的温度,然而史诗性作品《石家庄长歌》能够让死去的历史和人物重新站立起来。其二,历史情境的真实。诗歌在缝合历史碎片时注重历史考据和因果论证的历史叙述,尽可能全面地阐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营造逼真的历史场景;而在具体历史情境的营造中,注重历史事件时间、地点及人物的准确。时间、地点、人物是事件的三要素,客观准确地介绍时间、地点、人物是历史的方法,但也成了诗人对史诗作品的要求。《石家庄长歌》中的每一首咏史诗都明确交代了真实的时间、地点、人物,合理地运用史料素材,重构鲜明的时间氛围和空间环境,极力再现史诗作品叙事的史实性,凸显事件的场景性,强化人物形象的具体性,增强读者的现场感,使读者在阅读它们时被带入一种受到具体限定的、有着强烈现场感的当时情境之中,叙事更加具体、形象、鲜明、生动。其三,语言描述的真实。历史人物的经典话语贴近人物的角色、身份和性格特征,直接引用人物的话语来对有关事件的描述,可以使史诗作品读起来真实、亲切。面对厚重的历史,诗作采用平实、明净凝练的叙述话语,以便吻合历史情境。注重历史人物、情境、话语的真实性,体现了作者对历史本然的追求和尊重。
(二)诗歌中强烈的历史意识
诗歌以概括化的意象凝聚人的思想情感,成为人类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历史意识在诗歌中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意识强调史诗不仅要对历史作出严肃的回应和书写,还要能够体现个体的声音和群体的声音,让个体的声音与群体的声音一起体现集体意识。诗人正是将这种历史意识渗透于史诗性作品《石家庄长歌》中。诗人在史诗作品中引入与石家庄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众多小人物,将他们置于石家庄的历史舞台上进行刻画,在对历史整体的感受和认识上完成构思。即便是以具体人物的遭遇作为表现对象的《父亲的轨迹》,其构思焦点也不仅仅在刻画阮平这一人物的具体可感的形象,还以人物命运作为骨架,去追求有普遍性的时空情绪的获取。诗人以“现在”贯通“过去”,通过历史链条式的对接,拉开审视距离,让“过去”成为“现在”的回顾和反思,让“现在”成为“过去”的接续和拓展,这也正是诗人自觉的历史意识的表现。例如“走在2018年石家庄的丰收路、/大桥街、公里街上,我用我的心/和我的脚,静静阅读着/1947年的英雄诗篇”通过那些象征性的事物,巧妙地完成了把历史和现实之间相互的逻辑融会贯通起来,让两者遥相呼应并展开哲理意义上的对话,以便在历史中探寻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深层特质与内在根源,在现实的对照比较中反观历史的价值。这样就使史诗作品获得一种横跨古今的浩瀚意境与韵味,内涵更为丰富。此外,诗人把握历史的方式、观察历史的视域与“新史学”的某些观念不谋而合。比如,在考察传统的主流的同时关注传统的支流,关注和历史整体相关联的局部性细节与日常生活状况,及其具体的人物、群体、事件,而且还注意考察史事如何被重构、被言说等问题。
史诗是记忆形塑和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和媒介,可以把孤立的个体记忆转化为共同的文化记忆,相较于普通历史文献而言有着独特的价值。诗人创作史诗《石家庄长歌》的主要诉求便是纪史和存史,让人们回顾与铭记石家庄30万年的历史。她在这部史诗性作品的后记中就直接指出:“我写石家庄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不是怪物,我要努力让石家庄人认识、了解并爱上自己城市的光辉历史。”从中可以看出她以诗纪史,怀古咏史的用意颇为明显。石家庄这座城市积淀极为厚重却长期被人误读为是“火车拉来的”城市,《石家庄长歌》填补了冰冷的历史书和简单的数据留下的空白,是一部活起来的历史,是正史著作的补充,是为石家庄量身打造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诗史”。其中包含了诗人的经世情怀,关系石家庄历史文化忧患之体认,也关系历史记忆与生命存在之深切感受。
二、史蕴诗心
诗人撰写史诗性作品时要求以真人真事入诗还原历史,但毕竟是文学,也不排斥适当的艺术加工,因为“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隐藏的本质,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责任,抛弃了它的创作的职能。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2]。可见,史诗性作品具有心史的特征,一方面,要求文学创作必须遵循历史人物的性格及事物发展的逻辑,以达到接近历史;另一方面,在叙事中允许进行适当的想象建构以及表达感情倾向,可以使叙事对象更形象生动地深入人的心灵,从而更好地形塑人们的记忆。诗人在《石家庄长歌》的后记中也表明了这一特点:“我心目中的好诗不一定是美的,但它一定是真诚的,是能够直击人心的。”诗人自始至终都站在独特的角度,从历史中感受不同的情感,以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和思想性来追忆和认识石家庄的发展,重新让历史题材发出文化的光芒。
(一)历史镜像的文学审美呈现
将历史转换成为文学性的叙述,要求诗人在搜集、归纳、分析和综合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地探索历史,把握历史的要义,理解历史的真精神,然后跳出历史,通过艺术手段将历史的画卷再现于读者面前。诗人将读者带进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氛围中,艺术地反映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历史运动的规律。用诗歌的形式叙述历史,便是将复杂多变的历史故事局限在短小精悍的篇幅中。如此囊括这般繁复的素材,能够做到在凸显局部和刻画细节的同时,不被这种繁复所囿限、所裹挟,依旧持有一种贯通和穿越的本领,这是《石家庄长歌》创作的一个不易达到的高度。诗人通过穿插、灵活剪裁历史,安排了众多人物、事件。作为一部史诗性作品,《石家庄长歌》的历史叙述没有像历史著作一样采用编年体或者纪传体,而是以历史事件、人物或是事物为中心点,赋予那些遥远的历史事件、人物、事物以意义,使其变成可以亲近、具体感知的人与事,同时借助抒情,与读者产生最大程度的共鸣。如诗作第二部分,围绕“正太铁路”“石太铁路”“吴禄贞”“大石桥”“高克谦”“太行山”和“美穗子”这些石家庄近代历史上代表性强的典型事物和人物形象来表现。与此同时,不断采用起兴、铺陈与排比等手法延伸拓展诗作的空间。“这座城市还有太多太多的‘忘不了’/忘不了中山路曾经的名字‘解放路’‘长安路’/忘不了博物院曾经的名字‘展览馆’/忘不了新中国第一百货——人民商场……忘不了六十年的工业记忆”,《石家庄记忆(序诗)》的十五个“忘不了”构成的排比增强了诗作语言的节奏感,而且在有限的篇幅里打开了读者记忆的闸门,引导读者领略1947年解放后石家庄的发展速度之快、变化之大。诗人对历史事件选材精当、高度概括,可以使该诗集避免不知所云、抽象及玄奥。
《石家庄长歌》叙述的是石家庄30万年的历史风云,即古代、近代、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到当代的石家庄,这个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度足以具备史诗性作品的品格。整部诗作所选历史题材厚重、叙事结构宏大,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和线索,在巨大的框架中,时间的流逝与事物的发展演变相互发生作用,由时间的推移推动历史事件的进展,从而引出历史人物的活动情况,反过来带动历史的进程,使读者能直观地感知社会形态的演变。阅读《石家庄长歌》也让人觉得作者对日常生活里的人和事有着一般人习焉不察的敏感和细腻。诗人善于捕捉生活细节,将其与宏大历史记忆相融合,由于历史追忆的进入,平淡的诗意中多了一分婉曲的情节性。如在回忆八家庄小学时引入了一张“缺了一角且已泛黄的1953年‘八家庄小学四年级毕业照’”,在与今天的对比中感叹岁月磨不去的“浓浓母校情,依依校友心”。
(二)历史重构的文学思想反映
《石家庄长歌》若要包含史诗性的意义,仅仅停留在镜像式地再现石家庄30万年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表现一些史料性的内容,显然是不够的。一部优秀的史诗性作品还要体现文学叙事背后的史鉴深度。
第一,《石家庄长歌》的历史重构与当代反思中蕴含着丰厚的人文情怀。无论是当代的还是历史的素材创作,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都饱含着诗人田耘的人文立场与诗意情怀。《石家庄长歌》以真实客观的方式再现石家庄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不能阐明自身的思想立场与人文情怀。一方面,《石家庄长歌》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探寻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原因,以史为鉴,反观当下。另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石家庄辉煌的历史文化,高度赞扬了领袖人物、杰出人物、普通人物崇高的民族气节与奉献精神。如对落入敌手宁死不屈、为革命献身的19岁青年高克谦等历史人物,作者赞扬他们是“耀眼的启明星,划破黎明前/看似无尽的黑暗,预示着/东方即将到来的曙光”。
第二,《石家庄长歌》的历史思想深度背后潜藏着特殊的文学内在价值。史诗内涵的高度和深度不是依靠史实素材的简单罗列,而是依靠诗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局部细节的描绘、事件场景情境的重塑来实现的。30万年的时间让石家庄这一方热土经历了历史的纵横捭阖与岁月的沧桑巨变,诗人站在2018年这一个时间坐标上,回顾石家庄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通过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真正拉开审视距离,梳理出清晰的历史发展演变脉络。诗人通过《石家庄长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命运的交织来探究历史深处的思想脉动,以一个当代人的眼光与历史观来重新审视,仔细梳理石家庄30万年的历史线索,深刻反思历史事件的千秋功罪,反思众多人物的历史命运,具有史识的深度和史鉴的价值。史诗中的事件、人物、情节、场景是史诗主线的载体,而中心思想是石家庄变迁的动因、发展与历史辩证规律。阅读《石家庄长歌》给人的深切体会是所读的不仅是纪实的历史,还是一部声情并茂、引人深思的史诗性作品。
三、结语
黑格尔认为:“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3]在文本内涵上,《石家庄长歌》具有记录石家庄重大历史事件和歌颂其中重要历史人物业绩的特点和作用。而且,全书以真挚的情感贯穿始终,饱含作者的爱国情怀,所以在时代现实的大背景下具有抒写襟怀的艺术,体现出“诗具史笔”“史蕴诗心”的特点。
石家庄30万年的历史不仅是石家庄人民的记忆,也是中华民族记忆的一部分。《石家庄长歌》用史诗性作品的形式讲述历史,既尊重历史的真实,又富有艺术创造性,由此呈现“诗具史笔”“史蕴诗心”的特质。每一篇咏史诗仿佛万花筒中变幻的袖珍舞台,诗人则化身一个冷峻的、反思的写史者,以史诗性作品的具象之真摹写历史事实,在历史真实上呈现诗歌的艺术之真。在诗人笔下,历史不再是干枯的历史,不再是简单停留在史料中的历史,而是经过艺术加工和思想情感渗透的诗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