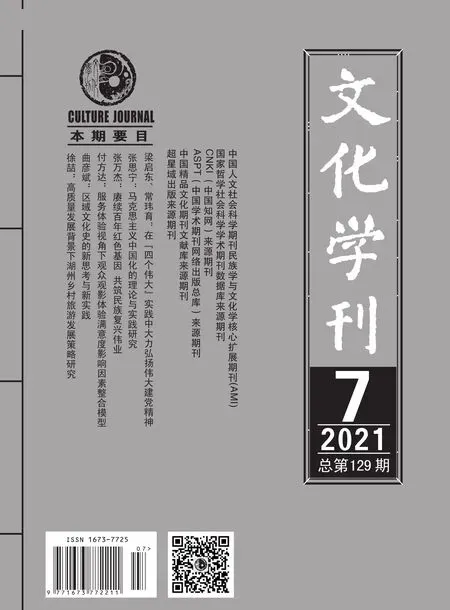比较诗学研究视野下的《文心雕龙》文学史观探析
姜深洁
一、引言
大卫·达姆若什曾说过,21世纪“经济、传媒和文化的全球化正在对学术生活和学术工作的许多方面发生着深刻影响,而最具戏剧性的影响则发生在比较文学领域”[1],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文学都被纳入世界文学多元语境的范畴,重构世界文学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世界文学史新建构也被提上日程。作为世界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诗学新建构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样值得当下学者进行多角度讨论。
中国诗学传统渊源已久,上溯先秦两汉可作为其肇始,至曹丕《典论·论文》,魏晋文人已实现“文学的自觉”,中国诗学开始逐步确立。《文心雕龙》作为中国诗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不仅从文体论的角度讨论了诗歌、辞赋、论说、颂赞、章表的功用与创作特色,还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各种文体在文学史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本文重点探讨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诗学的系统建构和独特文学史观。
二、《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
(一)以“文德”为代表的文学叙事方法论
《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首先体现在其对文学叙事传统与文学创作典范的梳理。刘勰在继承前人“德言说”和“文言说”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文德”作为行文叙事方法的概念,区分了“文”与“言”的含义,厘清了诗、书、辞赋等文学体裁的发生过程。
《文心雕龙·原道》开篇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2]章太炎认为“文德”的说法,“发诸王充《论衡》。杨遵彦依用之,而章学诚窃焉”[3]。其实“德言”之说,早自《诗经》便有记录。据现行《诗经》刊本统计,全书出现“德音”共计十二处,于省吾考证后认为,除了“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乐只君子,德音不已”“乐只君子,德音是茂”这三处应当为“德音”以外,其余的九处都应为“德言”,即应作为“神圣而庄严的言语”之意[4]。刘勰所述的“文之为德”,一方面延续了《诗经》中“神圣而庄严的言语”之意,另一方面将“文德”诠释为“文学的方法”,即文学的本质特征。
正所谓“德者,得也,若物德之德。犹言某物之所以得成为某物”[5],是故“文德”亦即“文道”。刘勰在《原道》篇中将“文道”归为自然之道,将文字作为对天地的反映和对混沌之初的“道”的模仿——“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故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将天地之道加以圣化形成文字,进而通过撰写文章实现自然之道与人文之道的和谐统一。在《宗经》一篇中刘勰指出,“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里的“经”指以《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为代表的具有历史传承性和传统性的作品,儒家“五经”的共同之处,在于“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文心雕龙·宗经》),具有言志教化的功用,是天地人三才的究极之学,不仅是国家正纲纪、肃纪令的典范,也是中国传统文体的渊源和典范,为文人的创作提供了内容、思想的模板。
(二) “文”“言”相异的叙事艺术辨析
除了强调“文德”——即“文道”,也就是文之为文的方法——《文心雕龙》仔细区分了“文”“言”相异的内涵、性质。刘勰认为,言先于文而产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章的作用在于将内心的“志”通过“言说”表现在外,进而记录为“文”,实现“情信而辞巧”。
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是经过修饰的文辞,是由言语到文学的艺术化、抽象化的审美过程。对于如何把握“文”“言”的辩证关系,尤其是“文”对“言”的艺术化程度,曹丕在其著作《典论·论文》中探讨道:“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不同的体裁施用的艺术化手段不同,应加以明确区分,使其在形式与内容上各具特点,以丰富文学的多样性。刘勰发展了曹丕的观点,提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即情深不诡,风清不杂,事信不诞,义贞不回,体约不芜,文丽不淫。刘勰以此“六义”为行文规则,强调文字书写不仅要把握好义理的可信度,更要注意艺术化的程度,文体上应当简约精要、言之有物,反对铺陈华丽、空洞浮华的过度修饰。刘勰将文章视作对经典的延伸、拓展,目的在于立德建言,“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文心雕龙·序志》),这与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主张一脉相承,一方面反映了文学摆脱政教功利性的自觉意识,一方面点明了文学的重心在于传递经典、经世致用,特别是注意将文学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相统一。
三、《文心雕龙》的文学发展观
倘若只从文章经世致用的角度讨论文学的功用、特点,《文心雕龙》只能算作一本“文学评论集”,而未能凸显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还体现在对文学流派、题材的发展脉络的梳理中。以往文学评论大多仅限于一朝一代文学的特点,忽略了它们在整个文学发展中的价值。而刘勰对文本的讨论既具有共时意义,也不乏对文学发展的历时的、宏观的把握;不以史为题,却以独特的视角贯通古今。“德言”“载道”强调的是文学的政治功用,这只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的一部分,时之有序,文亦有脉,文学内部前承后继的关系同样反映着时代的兴衰。刘勰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以《文心雕龙·时序》篇最为突出: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风”者,亦“讽”也,是文学对时代的记录、反映,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风”的有一百多处,如“风采”“风韵”“风雅”,又有“八风”“晋风”“和风”等,其含义历来众说纷纭,各有偏执,但我们大致可以将“风”看作是文学创作者将成熟思理蕴于作品中而形成的较明朗的情思。在《文心雕龙》中,“风”“骨”往往并论,“骨”即文骨,是文章的结构、事义,须以精炼质素而劲健的语言来表达。文章要做到有风骨,不仅要会控制文章的体采、风貌,还要能“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这秉承了刘勰一贯的“宗经”思想。一代有一代之文风,溯其本源,仍在师法“五经”,因为“五经”之风最为雅正。针对当时盛行的“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的玄言诗赋,刘勰批评了其言贵浮诡的文风,提倡作文唯有宗法“五经”,其文风方能正本归末。因此,在众多文学中刘勰尤其重视儒家经典的发展轨迹,甚至将文学的昌盛与否与儒学的兴衰紧密联系:“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
统治阶层对文学的不同态度,影响了各时期文学的迁改。总结历史经验,刘勰认为只有通过崇儒兴礼,帝王方能鸿业,文章方能华彩纷呈;只有在崇文盛世才能广纳贤才、嘉会有识之士。“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关注到了时运变换和社会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必然影响,同时关注到了文人自身有意识地、自觉地创作对文学发展的潜在影响,如建安文章“雅好慷慨”,是因为“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代精神影响了文人心理,他们有意识地记录下这样的情绪,在发展叙事传统的同时,也延续了文学的抒情脉络。
《文心雕龙·通变》篇中指出,要使文章文质交得、富有文采,必须建立在对儒家经典的宗法与借鉴基础上,而不是一味地求新制奇;创作文章必须先规略文统、以正文风,平衡好文与质、雅与俗的辩证关系,使文章情采相符、雅俗各宜。刘勰以魏晋之前九代(楚包含于周)文章为例,论述了同一种体裁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强调前后文章的循环相因;虽然言“变”,实则着重说明在变化中恒定的、不变的因素:名理有常,文章尚实。因此,刘勰在《通变》篇总结后指出,“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在因陈前人定式的基础上,文学创作的重点在于以情动人,以气适变,克服诡巧寡情的文风。
由此可见,刘勰对文学发展的评论基本建立在儒家“教化论”的基础上,反对空空而谈、故弄玄虚。无论是论世论人,都应秉持“宗法儒家经典”的原则进行,提倡凝练、质朴的文风。然而由于时代局限性,刘勰本身也受到当时绮靡文学风格的影响,在论述中不时有华丽空泛的文辞,在细节上也有刻意雕琢的痕迹。但纵观刘勰对文学发展的态度,虽仍遵循传统“载道观”,但已经有意识地将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讨论,将文学从政治附庸中独立出来探究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这既是对前人理论的系统归纳与推进,同时也提高了文学评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影响了以后的文学品谈之风,促进了文学评论史的形成与发展。
四、《文心雕龙》与西方诗学文学史观之比较
以往的文学评论大多倾向于将中国诗学定义为一种“言志”“抒情”的评论体系,而忽略了文学评论中的叙事传统,也忽略了其反映出的文学史价值。结合《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与本文前面所引用的诸篇,可以看到该书对文学的叙事性特征十分看重。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宗经”,即强调规范言行与礼法的文学功用。文体规范是创作的基本要素,之后才是文风变化、辞藻运用;首先注重的是文学的叙事、记录功用,其次才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抒情、言志。
相较之下,西方诗学的发展基本沿袭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建立的——或比亚氏更早的柏拉图就已提出的——“摹仿的”轨迹。厄尔·迈纳将这种“摹仿的”轨迹的内涵进一步扩大,认为“对西方文学史中许多阶段来说,‘摹仿—情感的’这一描述比单纯的‘摹仿的’更准确”[6]。区别于柏拉图仅仅将诗歌作为单纯的、对“理念”的影像再现,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将诗的再现定义为对现实的本质的、具有创造性的摹仿,是带有主观审美的合理构成。亚里士多德系统地构建了审美层面的诗学理论,总结了诗歌、戏剧(尤其是悲剧)等艺术活动的创作经验和发展规律,摆脱了以往哲人在文学讨论上易落入自然哲学或政治哲学的窠臼。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诗人的职责”,并不是像历史学家那样去记录历史上发生过的事,而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7],这才是诗歌作为摹仿的艺术之于现实的意义。
然而,不能简单地将文学史观等同于文学手法撰写的历史观,否则文学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附庸,而不能真正体现其作为文学理论的审美性。比较诗学中的文学史观应该更多地体现关于本学科、关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史观,对西方诗学中文学史观的讨论也应当着眼于文学、文学理论的发展上。
西方的诗学是从“诗”(包括史诗和悲剧)中衍生而来,以“摹仿”为线索,主张现实主义,强调“诗”这种艺术形式的社会功用,这与《文心雕龙》以“宗经”“德言”思想为准则来实现文学的教化意义颇有相通之处。西方诗学擅长于将哲学的理念运用于文学的创作论中,对文学的评论往往交织着哲学的理性的、形而上的思考,如近现代西方文论中以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诗学体系,就是将哲学理论运用于文学是文学创作经验升华的例证。而《文心雕龙》将儒、道观念运用在文学品评中,也是把中国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系融入文学经验中,得出来的一套符合中国传统文学体系与社会价值体系的诗学系统。所以,无论中国诗学还是西方诗学,其基本理论与审美体验都是相通的,都是以实现社会功用和抒发情感为目的搭建的理论框架,然后在不停的理念更替中进行补充、巩固,所以并不能单纯地以“叙事诗学”或“抒情诗学”进行概括。
而且,西方诗学中也不乏对作家之间、作品之间文学关系的探讨,如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写道:“我们必须把文学视作一个包含着作品的完整体系,这个完整体系随着新作品的加入不断改变着它的各种关系,作为一个变化的完整体系它在不断地增长着。”[8]同时韦勒克将作品渊源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作为重点探讨的问题和传统研究的重心,认为编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在于确定作家之间的文学关系,这些观点与刘勰不谋而合。他们二者都强调了艺术作品的延续性,将文学的历史联系作为各自传统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诗学的文学发展观基本上都围绕着作家、作品研究展开,而《文心雕龙》早于《文学理论》一千四百多年便系统论述了中国诗学的研究重心,这是中国诗学的卓越建树,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挖掘《文心雕龙》的比较诗学价值,在更广阔的研究视野中使之与西方经典文论比肩齐晖。
五、结语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传统中国诗学的系统建构,完善了中国诗学的载道、言志理论的叙事抒情观,与西方诗学传统中重视“摹仿”与“再现”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通过对中西方诗学差异性的比较,以对话交流的方法代替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冲突论,为中国诗学融入世界诗学提供了桥梁。比较诗学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比对寻求一种互相激发、增益的关系,以辩证的方法寻求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或文学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求同存异、对话交流的方式代替文化冲突与自我中心主义。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世界诗学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将中国文论放置于全球化的视野中,寻求中国古代文论与相似的文化体系的联系。通过解构经典文本,对中西方诗学差异性加以比较,不仅为中国诗学融入世界诗学提供了桥梁,也有利于中国诗学在中西比较诗学的观照下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