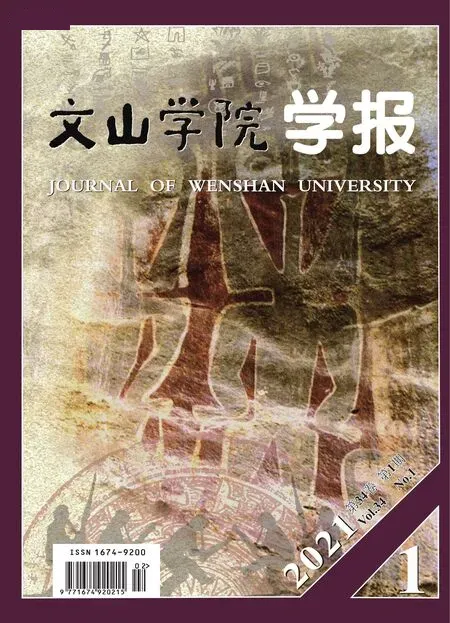贴近现实的别样写作
——谈李司平的小说《猪嗷嗷叫》
孙伟民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2019年4月,云南文山学院在读学生、青年作家李司平凭其中篇小说《猪嗷嗷叫》一举摘得第九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小说类作品一等奖,且是唯一的一等奖,一时名动高校文坛。王蒙、徐坤、程绍武、陈晓明等文坛名家和评论家都对李司平的这篇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王蒙评价李司平为“怪杰”,《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对《猪嗷嗷叫》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称其“是一篇现实主义的好作品,接地气,关注社会,直面生活,有疼痛感。”《猪嗷嗷叫》先是作为头题发表于《中国作家》2019年第5期《青年作家专辑》,这篇小说后又被《小说选刊》2019年第5期《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青年作家专号》及《新华文摘》2019年第13期转载。在李司平读书的云南文山,文山日报社《七都晚刊》编辑部和文山州文艺理论学会于2019年5月22日举行了《猪嗷嗷叫》的作品研讨会,与会人员同样对李司平和他的小说《猪嗷嗷叫》予以了高度评价。①2019年12月6日,第十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李司平凭《猪嗷嗷叫》获得了该奖项的新人奖。
如果从作品的得奖、发表、转载、评价等角度来看,李司平的《猪嗷嗷叫》无疑已是一篇成功的小说,但《猪嗷嗷叫》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其成功显然有着更深刻的原因。《猪嗷嗷叫》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云南“南方高原”的故事,村民李发顺伙同黑顺、老岩、二黑几人一起宰杀上级下拨到农户做扶贫用的建档立卡猪,但这头猪却冲破种种阻碍、死里逃生跑进了莽莽山林,发顺一行人寻而不得。为应对县市领导的视察,驻村扶贫干部李发康和发顺几人另购一头猪代替跑丢了的建档立卡猪,但最终还是被畜牧专家识破,李发康被免职后去了沿海某城市工地上打工。此外,这篇小说还有着另一条故事线,发顺的妻子玉旺不堪发顺的家暴后离家出走,发顺却坚持认为玉旺的离家出走是因为李发康的建议,并以此为事端在乡里、县里游走希望获得补偿,均未得逞后还想到省里上访。但在玉旺失踪数月,大家都认为其可能已丧命山林之时,她却在某一天和跑丢的猪以及一窝野猪崽奇迹般地回到了村寨。在乡政府的支持下,村里的野猪养殖场成立了,全村人全都脱贫了。由上来看,《猪嗷嗷叫》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并不古怪离奇,也谈不上惊心动魄,但却能够在同类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并获得比较广泛的认可,除却因为小说贴近时代、写实深刻之外,其最根本的特质、最大的亮点当可概括为“别样”二字。但《猪嗷嗷叫》作为李司平发表的首篇小说,在艺术上也并非无可挑剔,笔者就创作手法和情节设定这两个问题与小说作者李司平商榷。
一
李司平在《猪嗷嗷叫》中塑造了一系列别样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典型、立体、鲜活、生动,也都有着其独异性。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塑造最成功、最饱满的莫过于发顺这一人物。对发顺这个人物,我们很难用固有的、传统的道德标准对他进行论评,如果坚持这样做,那么只会削减这个人物的丰富性。虽然发顺并非一无是处,传统农民的淳朴品性还尚未完全泯灭,但他的身上存留着太多显而易见并难以更改的劣根性。好吃懒做和小偷小摸的秉性使得他难被村民所容,人人对他惟恐避而不及,他却靠“忽悠”娶了妻子玉旺。但发顺对妻子丝毫不知疼惜,在玉旺面前表现出格外的霸道与强势,醉酒后殴打、辱骂玉旺更是家常便饭,有时候这种打骂甚至还有向他人炫耀和表演的成分。因对国家扶贫政策的不了解(也有可能是直接无视),发顺伙同村民老岩、二黑以及村中的杀猪匠黑顺要把建档立卡的扶贫母猪种当作年猪进行宰杀。面对驻村扶贫干部、也是堂哥的李发康的大骂,他又表现出对基层权力的敬畏而唯唯诺诺。当妻子玉旺因为自己的暴力相向而离家出走,他完全不知反思,反而将一切归结于是李发康建议玉旺敢于反抗。发顺以此为事由将其性格中的无赖成分充分表现了出来,他的小算盘是“以一条人命为筹码,肯定能在这里吃到一些甜头。”②在县里要求补偿被断然拒绝后,他还打算到省里上访。在李司平看来,发顺显然是广大农村中那类“贫穷得善于自欺欺人并苦中作乐”的底层小人物的缩影。从这个角度看来,发顺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但他又有着异于阿Q的别样复杂,且具有着更多种解读的可能。
在《猪嗷嗷叫》这篇小说中,李司平很擅长选定一个特定的场景来表现在场的多个人物的性格特点,这样的创作手法显然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在小说的第一节,老岩、二黑来找发顺喝酒,三人喝醉之后,发顺竟会向老岩、二黑表演家暴妻子玉旺,原文是这样写的:“至少发顺还有一个女人可供他呼来喝去,所以发顺更加神气一些。有理的,无理的,他都要呼来喝去。甚至于,昨夜三人大醉之后,发顺揪醒睡梦中的玉旺,为老岩和二黑表演打婆娘这个节目。”寥寥几句,便将充满戾气、喜怒无常且无视和肆意践踏妻子的尊严以此来确立自己可笑的优越感的发顺的形象呈现了出来。与此同时,玉旺的隐忍与逆来顺受、老岩和二黑的麻木与漠然等性格特点也在这样一个情境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类似这样的描写在《猪嗷嗷叫》中并不是孤例,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当李发康和发顺等人以换猪来应对县市领导检查却被畜牧专家识破后,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的发顺又一次借酒打骂玉旺,并且前所未有的惨烈。当村里人听到玉旺被打的惨叫声和讨饶声后,村民们的反应也不一样,有的为玉旺揪心,担心玉旺会被发顺打死,也有的村民不想掺和发顺的家事,不想和发顺有什么关系。无论出于哪种心理,结果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村民们的“坐等,观望”以及玉旺“持续的惨叫和求饶。”最终,还是驻村扶贫干部李发康的出现制止了这场家暴,并在李发康“以暴制暴”的方式之下,发顺不得已向玉旺道歉。短短几行之间,李司平便将发顺、玉旺、李发康以及村民们的性格特点素描般地勾画了出来。将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安排在同一场景出现的设定很有话剧表演的意味,在有限的空间和篇幅内,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碰撞将人物的性格特点最大化地彰显,这是很考验作者功力的创作方式,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显得杂乱而让人不知所云,但李司平却完成得游刃有余,让人不禁拍案叫绝。
李司平在《猪嗷嗷叫》这篇小说中不仅成功地塑造了像李发顺、李发康这样的核心人物的形象,而小说中“戏份”较少的玉旺,甚至黑顺、老岩或二黑这样相对次要的角色也毫不逊色,他们的形象往往在一两句的对白中就得以勾勒出来,这是因为李司平真正抓住了每个人物形象最为核心的特点。幽微之处方见真章,这样的效果往往是需要苦心经营才能达到,但在《猪嗷嗷叫》一文中却丝毫不见刻意斧凿的痕迹,况且《猪嗷嗷叫》还是李司平初次发表的小说,这只能说明作者李司平在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有着自己敏锐精准的感受力和令人称奇的塑造力。
二
在笔者以往的阅读经验中,很多乡土小说都将农民生活的穷困、沉重、苦难视为表现的重点,可以说对农民苦难生活的表现已成为了一些乡土小说的精魂和标签,甚至对于某些乡土文学创作者而言,似乎他们所写的苦难让读者越难以置信,他们就会越觉得自己的写作是成功的。可如果文学创作只是为呈现苦难而创作苦难,那实则是在消费苦难,这样的苦难描写除了哗众取宠之外,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与艺术审美。仅在云南本土文学的视域下来看,对农民在极端环境下的苦难生活的描摹在夏天敏所创作的同为农村扶贫题材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当代》2001年第5期)中便可以说已写到了一种难以超越的高峰,既然如此,李司平何不另辟蹊径?在小说《猪嗷嗷叫》中,李司平并没有像某些扶贫题材的小说那样也对苦难进行不遗余力地呈现,他也无意再向读者展示他们早已经不感到陌生的苦难,他将探寻的目光转向了苦难的背后。在讲述一个关于猪的闹剧的同时,他向读者抛出了这样的思考,如发顺这些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的农民何以贫困?他们的出路又在何方?
苦难在《猪嗷嗷叫》这篇小说中只是一个叙述的背景,而非李司平所想要凸显的重点。在《猪嗷嗷叫》的开篇,虽然李司平也描述了发顺家的贫困状态,如“年久失修的土坯墙上搭着同样岌岌可危的房梁和破瓦,房檐之下是发顺乱糟糟的家。客台的一侧拢着火塘,火塘中杵着几根尚未干透的柴火棒子,不见明火,冒着浓烟熏着吊在火塘上面无物可装的几个编织袋。每个可视的角落结着蜘蛛网,蜘蛛网一层层堆积起来,挂满了火塘升起的烟尘以及蚊虫的尸体”。但如果结合之后的部分来看的话,我们便可发现李司平对发顺的家的描写其意并不在表现这个家庭如何贫困,而意在指出这个家庭的“乱”和“破败”。在李司平看来,比年久失修的土坯墙和岌岌可危的房梁、破瓦更让人揪心和忧心的是一个家“蜘蛛网一层层堆积起来,挂满了火塘升起的烟尘以及蚊虫的尸体”的“乱糟糟”。对此,李司平流露出了他对农村扶贫工作的深切忧思,即如果贫困者自身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单纯依靠国家政策的帮扶是无法真正脱贫的,要想在经济上脱贫,首先要在思想上脱贫,如果在脱贫过程中不能克服和消除来自贫困者本身的精神阻力——懒惰,贫困者最终只能“在脱贫和返贫二者之间不停的循环”,脱贫之路断然不会顺利,实现全面脱贫则只会愈发任重道远。
此外,李司平在小说中还安排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千余人多日搜寻玉旺仍无结果,大家已认定玉旺失踪,甚至有人认为玉旺已经死了,但就在玉旺失踪数月后,玉旺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了。回来后的玉旺虽然看着依旧痴傻,但却表现出过去从来没有的“强硬”,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当发顺听到玉旺嘴中嘟囔李发康的名字而心生怒火,一如往常想抬手打玉旺的时候,一向逆来顺受的玉旺竟然选择了还击,反而给了发顺一记响亮的耳光。这记耳光不仅让发顺觉得“世界仿佛倒置,然后变了色”,想必连读者都会觉得意外,为何以前那般隐忍、逆来顺受的玉旺在失踪了几个月后就如同觉醒似的生发了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或者“强硬”又是从何而来?李司平让玉旺回击发顺的这记耳光显然是有其深意的。结合上下文,笔者认为玉旺的反抗精神就来源于莽莽山野,来源于在山野中与一群野猪崽生活的数月。在人类群居社会中,玉旺的人格和尊严被忽视和践踏,丈夫发顺自然是最直接的施暴者,而那些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村民何尝不是发顺的帮凶?但当玉旺逃离人群躲至山林,与林海和野猪为伍后反而唤醒了性情中消匿的野性,激发了内心的反抗精神,反而拥有了生而为人的尊严,这又未尝不是李司平对人类群居社会的道德伦理的一种辛辣嘲讽。李司平似乎想通过玉旺的前后变化来告诉读者,人在何时都是应该有一些野性或反抗精神的,但当人的野性或者反抗精神逐渐消散,当中的退化已成不可挽回的定势,我们又该当如何呢?是不是要从被人类所征服的山野中寻求一些慰藉与寄托?
三
《猪嗷嗷叫》的别样还体现于它的情感基调和语言特色。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用以往的悲喜剧的标准来衡定这篇小说的感情色彩,你会发现明明是苦涩的悲剧内核却被李司平套上了喜剧的外衣,又以闹剧的形式来上演,当你笑哈哈地读完了这篇小说,你也许会反问自己,我阅读的到底是个悲剧故事,还是个喜剧故事?当你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明你又入了李司平预设的圈套。《猪嗷嗷叫》这篇小说虽是李司平的小说首秀,但他所想要实践的创作手法、所想要达到的创作意图却一点也不少。在李司平看来,一个苦涩的故事为什么一定要用传统的沉重的方式来讲述,为什么不能写得轻松幽默些,从而达到笑中带泪的阅读效果呢?在多年以前,夏天敏在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中便运用以轻松幽默的语言来写苦难的叙事方式与表达手法了,但李司平讲故事的方式与夏天敏又有着很大不同。比较来看,《好大一对羊》的感情主调仍是悲剧的、沉重的,轻松、幽默更像是一种调节,但《猪嗷嗷叫》则将轻松、幽默定为了文本的底色,但故事的最核心的内容却依然是悲剧的、让人深思的。李司平以一种近乎漫不经心的、甚至是嬉笑似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很沉重的扶贫故事,但故事本身的情感张力、思想厚度却并未消减,反而因作者苦心经营的叙述策略而被强化,这好比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在夕阳下含笑讲述他悲苦的人生,要比声泪俱下的控诉更能打动人心,这也正是李司平的高明之处。
叙述策略已定,《猪嗷嗷叫》这篇小说的语言在整体上便呈现出一种灵性与野性混杂的幽默。这种幽默是未加雕琢的,自然且质朴,所以当读者在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会感觉像在听一位山间的老农声色并茂地给邻居讲述他辗转听来的故事。笔者认为也正是因为这种拙朴,才使得《猪嗷嗷叫》的语言上别具一格。另外,在《猪嗷嗷叫》一文中,李司平多使用短句,这可能与李司平有比较长时间的散文创作经历以及他对汪曾祺的散文甚是倾心有关,汪曾祺晚年所创作的散文的简洁、明快、爽朗等语言特点在李司平的《猪嗷嗷叫》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流露。
值得一提的是,李司平在《猪嗷嗷叫》中还对某些小说技法进行了大胆尝试与巧妙运用。比如失踪数月、千余人搜寻而不见的玉旺,却突然在某一天带着那头建档立卡的母猪以及一窝野猪崽回来了,这几个月里她去哪了?又是怎么生活下来的?李司平没有按照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那样向读者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或许他认为也无需向读者事事交代,在他想要玉旺出现和回来的时候,她就回来了,这样的写法颇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这样的情节设置不禁让人联想到了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中的两匹马和车夫在雪夜中的突然出现,设定上很相近。在现实主义的乡土小说创作中,混杂使用某些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是并不多见的。还有,作者在小说快要结束的短短几行内便给了两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欧·亨利式结尾”,一是作为叙述者的“我”竟然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李发康的儿子,这样的设置则使得“我”以在场者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一方面使得故事有了更为强烈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则在文本之中和文本之外蕴含了“我”对作为基层干部的父亲李发康人生起伏的感叹;二是玉旺管养殖场里的每一头猪都叫李发康,“玉旺养殖场的每一头猪,都是我爸”,如此处理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喜剧效果,还增强了文本的戏谑意味。
从李司平的《猪嗷嗷叫》一文中,笔者明显感觉到他以文字为武器奋力同既定创作模式的对抗。他视所谓规则为无物,一点都不想按照常规路数出牌,似乎在他看来如果读者能预测到故事的下一步走向就是他创作的失败。因此他有意把故事牵引到读者难以预想的方向,有意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讲述他所要讲的故事,当看到你惊愕的表情他没准会一脸坏笑,这就是李司平。
四
《猪嗷嗷叫》发表后,为李司平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读者惊异于语言和思想如此成熟、老到的作品竟然出自一名在读的大学生之手,这一作品还是李司平的小说处女作。在笔者所看到和听到的有关李司平的《猪嗷嗷叫》的各种或长或短的评价中,有很多评论者都更强调李司平“95后”“校园作家”“理工男”等身份,不得不说这些标签或印象已经影响了我们对李司平及他的《猪嗷嗷叫》的理性解读。在笔者看来,《猪嗷嗷叫》虽然经过了李司平的反复打磨,有诸多可圈可点、甚至让人颇觉惊艳的地方,李司平在小说处女作中思想便能达到如此高度、笔力能达到如此深度实属不易,但这篇小说仍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还是有着可调整的路径和精进的可能。我们如果对李司平和他的这篇《猪嗷嗷叫》予以过多的赞美,而将一些可商榷的地方视而不见,很有可能会捧杀一位有创作潜力的青年作者。
在《猪嗷嗷叫》中,李司平赋予第一人称“我”以全知视角而将故事不断向前推进,不时掺杂一些个人的议论,这种夹叙夹议的方式本身倒没有什么问题,但却无法完全规避作者会将自己和叙述者等同,作家会情不自禁地将本属于自己的感慨或议论夹杂于文本之中,从而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界线而导致叙述的有失节制。比如,在小说的第五节中的开始,李司平对物竞天择、人驯养家畜作了一些议论,字数虽不多,但是却与小说的中心主旨并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完全可以删掉,而使情节更紧凑和连贯。可能作者也意识到了这样的议论似乎多余了些,于是他在议论之后又添了一句“再次回到最开始对猪的描述……”。这样看来,某些议论是完全可以删掉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影响和破坏了故事的完整性,如果把这种先放后收的写法看成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则实在没有必要。相反,叙述者过多的叙述反而会弄巧成拙。作品的深刻性是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而非是作者或者叙述者通过议论来附加上去的,而叙述者的某些文白交杂的语言也与这篇小说的人物不够贴合。
此外,这篇小说让笔者最不理解或者最不认同的地方便是李司平给小说安排了个光明的结尾。当玉旺和她精心饲养的猪如凯旋般再次回到村寨后,故事下一步该如何推进?特别是那群猪又该何去何从?这是李司平所面临的又一叙述难题,其难度不亚于当初安排李发康买猪顶替跑掉的那头建档立卡猪。但让笔者感到无比惊讶和难以接受的是,李司平以一句“村里的野猪养殖场弄起来了!村里的人都顺利脱贫了”便草草收场,他对“村里的人都顺利脱贫了”以及“现在国家政策那么好,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的补充表述显然是对当下社会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的一种政策呼应。玉旺野猪养殖场得以兴办、村民“都”顺利脱贫,如此美好的结局在现实中不是断无实现的可能,但作者显然把“村里的人都顺利脱贫了”这一过程的艰难、坎坷与复杂做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实际的困难又何止发顺等人将建档立卡猪当作年猪进行宰杀一事?李司平在小说前面的部分中颇费心力地去写围绕着发顺家的建档立卡猪的种种风波,显然他并非不知道脱贫攻坚过程中的艰难,但他仍为这篇小说安排这样一个轻松、光明、急促也草率的尾巴,不仅让人觉得缺乏足够的合理性,而且有头重脚轻之感。从故事的合理性、深刻性及艺术性出发,“村里的人都顺利脱贫了”的设定可视为作者无视客观现实、有失艺术准则的画蛇添足式的败笔了。
但在整体上看来,李司平的这篇《猪嗷嗷叫》仍是云南文坛新近涌现的少有的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研究者段守新在《“城乡中国”的浮世绘——2019年中篇小说述评》[1]一文的开篇便评价《猪嗷嗷叫》为“本年度并不多见的惊艳之作”,并指出作者李司平“在小说中所体现的对农村问题思考的精警深透,对农村日常景象描摹的细致生动,以及流荡于字里行间的特别的讽刺喜剧风味,都能给予我们深刻的印象,也让我们对这个年轻的作者、对乡土叙事的未来前景,充满着热切然而并非盲目的期待”[1]。通过这篇小说我们可充分感受到了一位年轻作者善于思考、敢于进取的蓬勃锐气以及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无限可能,这也让笔者对李司平以后的写作充满了期待。
注释:
① 详细报道及评论见《文山日报·七都晚刊》2019年5月23日,第2版.
② 本文中所引用的小说内容均来源于李司平发表于《中国作家》2019年第5期的小说《猪嗷嗷叫》,下文皆是如此,不再一一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