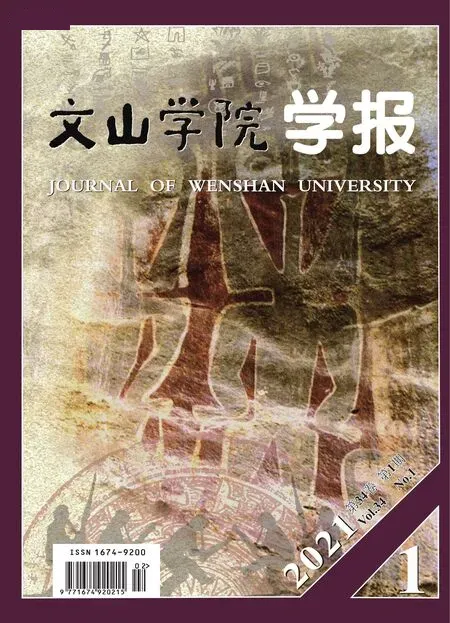西南联大刊物《边疆人文》中的民俗文化研究
刘 薇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抗战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来到云南的学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纷纷加入到边疆的调查研究中,边疆研究的风气日渐深厚,与此同时,国内报刊杂志也如“雨后春笋,相互竞长”。在当时众多的刊物中,《边疆人文》是最为集中刊登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少有的刊物,为民众了解少数民族民俗开启了一扇窗。
一、“边疆人文研究室”与《边疆人文》的创办背景
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恶化,除西北、西南地区外,中国的半壁江山成为了沦陷区。西南地区,特别是西南边陲的云南,以拥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而成为连接国际交通的主要区域。鉴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政府计划再修筑一条由滇南的石屏通往佛海(今云南勐海)的省内铁路,以便连接滇越铁路。与此同时决定提供一笔专款,委托一个学术机构,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风民情、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过程中参考与应用。据研究室成员邢公畹回忆:“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子坚)教授和冯柳猗教授在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先生的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铁路的委托与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一个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室,开辟一个科研阵地。”[1]
1942年6月,在黄钰生和冯文潜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全称为“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任聘陶云逵教授为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成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入的邢公畹,西南联大毕业生黎国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生高华年等人。在《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章程》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中都强调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的调查,计划调查内容包括传统教育、民间口头传统、社会组织、民间信仰、民间手工艺等内容。[2]584-586
在研究室章程和计划的指导下,同仁们很快就进入到田野,开始了有计划的调查工作。从1942年7月至1945年,研究室成员对修路计划经过的沿途地区开展了走访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边疆人文研究室调查工作表》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2]587-588除了陶云逵是对宗教信仰的调查外,其他几位学者关注的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这里有学者自身专业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前提。
调查组成员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车里(景洪)、佛海(勐海)等地,对沿途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民间信仰、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抗战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工作危险艰苦,各种各样的热带病流行,民众对调查工作的不理解,再加上社会治安没有保障,路上还要准备跟土匪交手,甚至有丢失性命的危险。当时的调查困难重重,甚至会威胁到生命,调查工作能按计划顺利进行,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实属不易。
陶云逵调查了新平县彝族的民间信仰和社会组织;邢公畹在新平、元江的傣族、彝族的地区搜集、记录、整理了大量的当地的口头故事和当地习俗;高华年在调查新平彝族的语言和文学的同时,还对民间信仰和人生礼俗进行深入的调查;袁家骅在峨山对窝尼语调查时收集了不少的故事;黎国彬在车里调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贸易、经济情况等人文和地理状况。调查者除了收集到丰富的调查材料外,还注重民俗文物的收集,在民间收集到的有宗教经书、宗教用品、生产生活用具品、少数民族服饰等。这次综合性的大调查,内容包括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石佛铁路沿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水平、语言文化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
研究室为石佛铁路提供的调查资料主要有:石佛沿线少数民族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1942年云南省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以西南边疆人文研究名义出版了一辑油印本。其内容包括:黎国彬《峨、新、元三县的糖业》《漠沙社会经济调查》《青龙厂社会经济调查》、黎宗瓛《杨武社会经济概况》四篇调查报告。[3]研究室成员在调查过程中,除了按石佛铁路委托的要求完成调查任务外,在研究室同仁们的努力下,还取得民俗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张伯芩称赞道:“内容详实,蔚为大观,望继续努力,俾能对于我国文化多有所贡献”。[4]
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不多,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他们都是来自研究所或大学,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治学严谨,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在田野调查中很快就有新的体会和学术成果反馈。但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学术刊物的发行量有限,出版商大多都不愿接手专业性强的学术期刊,这类刊物一般都是不赚钱的买卖,研究室也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发行刊物,看着研究室成员来之不易具有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文稿都一叠叠地搁置起来,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决定带领同仁们自己蜡刻,以油印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边疆人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见图1)。

图 1 蜡刻油印的《边疆人文》第一卷第一期
《边疆人文》刊物分为甲乙两种形式,甲种为语言人类学专刊,共出了三种,分别是邢庆兰(邢公婉)《远羊寨仲歌记音》、高华年《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研究》和《黑夷语法》。乙种为综合性的刊物1943年9月开始面世,除第一卷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月刊外,在昆明蜡刻发行的都为双月刊,1946年7月第三卷五六期在昆明出版后,随着南开大学返回天津,蜡刻版的《边疆人文》也随之终结。1947年12月铅印版第四期《边疆人文》合刊在天津出版,同时也成为《边疆人文》期刊的终结版。《边疆人文》乙种综合性刊物在艰难中走过了四年,共发表文章41篇。从文章的数量来看并不算多,但其历史价值却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成果值得学术界加以探求。
二、《边疆人文》与民俗文化
《边疆人文》发行之初,原来打算只作为内部交流的材料,但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精心组织和号召下,受到学术界不少名家的重视。在第一卷第一期只发表了研究室成员陶云逵和邢公畹的两篇文章。从第一卷第三、四合刊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学术界有声望的学者开始向《边疆人文》投稿,先后发表了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一多的《说鱼》,向达的《瞰青阁识小录》等。除此之外,还有来自青年学者的高质量论文,如马学良对彝族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成果,张清常对边疆民歌的研究等。《边疆人文》成为了传播新文化,发表学人们对云南民俗文化调查成果的重要渠道。发表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比重相当大,其内容涉及民歌、信仰礼俗和民间故事等各方面,为全面了解云南社会文化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一)民歌与《边疆人文》
民歌是少数民族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歌唱传统,又以歌唱日常生活的形式呈现。《边疆人文》发表民歌类的文章见表1。

表1 《边疆人文》民歌类论文汇总
十篇民歌文章中有五篇出自张清常的研究,可见他在民歌研究上的用心。张清常1915年出生在贵州安顺,幼年随家人迁到北京。193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邀请他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30岁的他成为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传唱后世的爱国主义经典名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就是由他谱的曲。来到昆明后的张清常对少数民族民歌非常关注,在《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一文中说到,“有一些人说,我国边疆的许多民族并不属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因而极尽挑拨离间之事,怂恿我国边疆各民族独立。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是在于证明此种谬论不成立。”[5]张清常带着民族主义的情怀论证边疆民歌与内地民歌具有共性,以此从民歌方面反驳民族分裂主义的阴谋。他以云南民家(白族)情歌为调查对象,虽然侧重点在于民歌的曲调方面,对民歌与日常生活方面的关联性调查还不够深入,但其记录的民歌材料却为后人研究民家(白族)歌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参考。
闻一多的《说鱼》一文发表于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从隐语的定义和文化功能进行分析,从《周易》《左传》《诗经》等文献中引出中国以“鱼”代“情侣”“匹偶”,并以西南少数民族民歌为依据,论证其打鱼、钓鱼是求偶的隐语,烹鱼、吃鱼喻义合欢或婚配。民间以鱼象征配偶是因为鱼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而在原始人类的观念中,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闻一多认为,“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婚姻渐渐失去了保存种族的社会意义,因此也就渐渐失去了繁殖种族的生物意义。”但“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着生物的本能,也都摆不脱生物的意识。”[6]闻一多运用数十首西南民歌挑开古典文献中的层层迷雾,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启发了后人去发掘民歌艺术中所隐藏的深层意义。
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叫阿细人,他们的歌唱题材十分广泛,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到人们社会的形成都融入到歌唱内容中,无论在田间地头、山林,还是在“公房”里,男女相遇都会激发他们的灵感相互对唱。1942年流亡缅甸的光未然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谋得教员的职位,他根据彝族青年毕荣亮的演述,记录整理了长期流传在阿细人民间的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7]1953年再版时改名为《阿细人的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语言学家袁家骅也流亡到昆明,1945年受邀到路南修县志时,看到光未然出版的《阿细的先鸡》后,找到了光未然调查时的同一个演述人——毕荣亮,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全部内容,同时在阿细人居住的几个村落进行调查和记录。袁家骅通过调查后,1946年在《边疆人文》第3卷5、6合期上发表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一文,对于没有文字的阿细人,这些缠绵的情歌记录了他们的历史、情感、生活和性格。1953年《阿细民歌及其语言》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发行。
(二)民间信仰与《边疆人文》
对于产生于原始社会,历经岁月的传承、发展与演变延续至今的民间信仰具有自发性,是民族固有精神的持续,对民众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民间信仰调查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边疆人文》有关民间信仰的文章见表2。

表2 《边疆人文》民间信仰类论文汇总
《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一文就是陶云逵在云南新平县的调查成果。大寨黑夷(今纳西族),考察的内容为姓氏与宗教图腾之关系。本文分为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对大寨黑夷宗族考察,以祭祀和族长人选来分析其信仰民俗;另一部分是在宗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宗族社会组织中的图腾现象。通过西方图腾理论与大寨黑夷动植物崇拜的比较分析,发现“第一,鲁魁山一带黑夷,除以动植物为族称之外,服装、发饰、用具、房屋装饰均看见有象征宗族姓物之图案或形状;第二,宗族对于姓物守有若干禁忌,类如禁吃、杀、触、用等,并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表现犯禁的后果;第三,族人是其姓物的后代或姓物是其祖先的保护者。这些表现方式说明图腾的存在以及图腾与人们生活的关系。”[8]
《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是陶云逵非常有名的一篇调查报告,考察了西南地区鸡骨卜的起源与传播状态。材料来自于陶云逵的田野调查和参考他人的田野材料,田野调查地及民族分别是: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部族(黑夷)、同县赵米克寨纳苏族、云南澜沧县酒房寨阿卡部族、四川栗波昭觉两县金□□□支阿庄支恩扎支布兹支之黑夷、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花腰摆夷、云南娥山县化念乡青苗、云南武定禄勒黑夷、云南元江大羊街车库寨查窝、云南耿马县和澜沧县的卡瓦山之卡瓦人。从地理上看鸡骨卜主要分布在川滇两省,从语系来看主要是西南的三大部族。通过陶云逵的田野调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占卜的具体方法和习俗。语言学家罗常培对此文给予高度的评价,“综合堪究胜义殊多”。[9]
当时北京大学大四学生马学良在“湘黔滇旅行团”途中曾在闻一多的带领下采风问俗,既积累了调查经验,也培养了对民俗调查的兴趣。1939年马学良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组汉语历史音韵学专业,师从罗常培和丁声树两位教授,后在罗常培的推荐下跟随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方桂做田野调查,开启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礼俗调查研究。《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和《倮译太上感应篇序》两篇文章都是马学良在云南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他用“以俗解经”和“经俗互证”的研究方法探寻彝族社会文化。
1943年夏天根据“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安排,高华年在峨山莫石村苗寨进行语言调查。当时他除了记载苗人的神话故事、山歌和语汇作为语言上的研究之外,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也进行了深入调查。《青苗婚嫁丧葬之礼俗》一文就是在这一带的调查成果。另外,《鲁魁山倮倮的巫术》是对新平县杨武坝鲁魁山和峨山莫石村的调查,文中对巫术不是以迷信的视角进行批判,而是在文中多次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来对巫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对民间信仰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结合田野调查材料,对巫术在少数民族中存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
(三)民间故事与《边疆人文》
民间故事方面有范宁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和邢庆兰(邢公畹)《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及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两则民间故事。《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一文以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牛郎织女传说为原始母题,运用古典文献,如刘向编撰《孝子传》中的《董永》、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用当时的学者如赵景深、常任侠、钟敬文、陈志良等人的论文资料;查阅了英国学者柯克女士等记录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基础上,把这类故事分为毛衣女郎型、乌鹊填河、山伯英台型三种类型去探寻其故事的源头和七夕的起源。通过分析,范宁认为,“楚怀王初置七夕,牛女故事产生至少是完成在汉代,汉代农业最发达,也就是封建社会最稳定的阶段,婚姻制度是家庭的基石,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社会把对偶婚认为不能改变的。牛郎织女这则传说是维持对偶婚制的精神牧师。”[10]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范宁受到当时历史地理学派的影响,力图广泛搜集故事异文,比较研究故事情节之差异,从地理上来确定故事最初的发源地和传播路线,探寻其原型。从材料的运用可见其知识渊博,运用古籍文献、考古资料、外文资料、民俗调查材料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境界,实现古今材料的互证与结合。
1946年《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发表于《边疆人文》期刊第3卷5、6合期。此文是邢庆兰(邢公畹)以1942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调查花腰摆夷(今傣族)采录的《借钱葬父故事》为材料,与查阅到的敦煌石室所记录下的《董永董仲歌》和刘向记载的《孝子传》进行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通过故事的核心母题、传承原因及从民间故事内容分析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影响。
三、结语
当年“边疆人文研究室”五六个学者,为了实现学术报国的理想,坚守一份学术志业,深入边陲,考察民族文化,记录边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等,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图片、资料和研究成果,更为可贵的是为了让年轻人的调查成果能早日面世,在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带领下创办了具有影响力的《边疆人文》期刊。创刊之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边疆人文》早日问世,陶云逵多方拜访或写信给有关专家学者,并亲自编写稿件,刻写蜡版,甚至参加刊物的油印、装订。后来刊物不仅成为本室同人发表科研成果的阵地,而且通过刊物联络汇集了云南民族民俗文化的爱好者,如闻一多、罗常培、马学良、张清常等纷纷撰文支持刊物的发展,学者们者以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细致的调研精神,呈现了一批批优秀的反映云南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成果。
《边疆人文》在艰难的岁月中仅存四个年头,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价值。一方面,在西南联大支持下的“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为办好杂志付出了诸多努力,体现当时学人自力更生的学术精神。另一方面,抗战时期来到云南的学人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调查热情高潮,《边疆人文》为专注于民俗文化的他们提供了平台,所刊载关于云南民俗文化方面的论文,或是经过田野调查,或是通过现实与历史结合的反思,既有民俗文献保存的价值,也有民族与边疆问题解决的现实理论,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