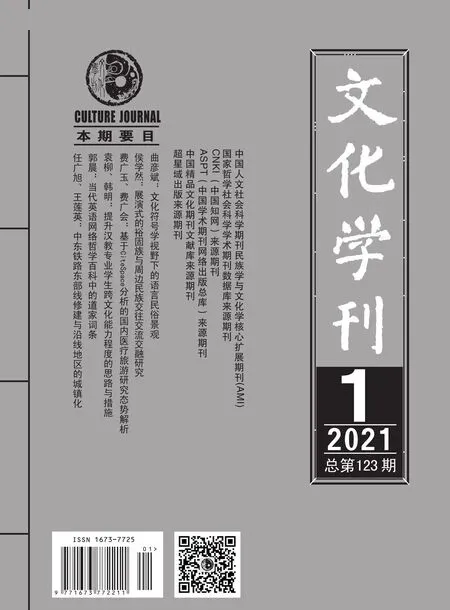赎刑之“赎”如今何“解”
孙佳伟
关于赎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说文解字》有云:“赎,贸也。”“赎,质也,以财拔罪也。”有关赎刑的起源,因为没有相关的史料支撑,所以至今仍无定论,有人认为尧、舜、禹时期便有了赎刑,也有观点认为赎刑起源于夏,但至少可以明确的是,最晚在西周时期赎刑便已经存在。赎刑制度从出现到鼎盛,直至消亡于清朝,其在中国历史上走过了数千个春秋,寻其足迹,觅其因果,与今对照,发掘其中的可借鉴部分,可对当今法律制度的改进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以何赎之
(一)钱之赎
《尚书·吕刑》就赎刑的具体内容作出以下规定:“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1]锾即当时铜的货币单位,一锾系六两。自此,开启了以钱赎刑的序幕。
以钱赎刑在其后的朝代都有所沿用,且各朝代对以钱赎刑的适用对象、赎刑标的、交纳标准均有具体规定。直至清末修律,废除了赎刑制度。
对于以钱赎刑中的“钱”,需作广义的理解,并不单指铜。明代赎刑的财物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清代允许犯人纳谷或米等实物,折算标准是每谷一石,折米五斗,每米一石,折银五钱。康熙年间,捐赎则以米、谷、骆驼等实物为主。
(二)役之赎
秦朝丰富了赎刑标的,规定赎刑除用金钱外,还可以用劳役。《秦律十八种》记载:“有罪以赀赎及有责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赏,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2]即是说,无力交纳赎金,可以用劳役赎罪。
唐代创设了“官役折庸”制度,《通考·一百七十一》中记载了唐玄宗天宝六年(747)时的敕令:“其赎铜,如情愿纳钱,每斤一百二十分。若欠负官物,应征正赃及赎物,无财以备,官役折庸。其物虽多,限三年。”[2]即规定了以官役折换刑罚。
明代赎刑制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赎刑方式上以罚役为主。罚役有屯田、种树、运粮、运灰、运砖、运炭、煎盐炒铁以及其他劳役[3]。同时,对于不同的罪名,明朝在赎刑罚役的时间上还作出了规定:“死罪拘役终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计日月。……满日疏放。”《大明律》还专附“纳赎诸例图”,例图明确周详。
劳役赎刑,在清朝被沿用且适用范围也愈加广泛。
(三)功之赎
康熙十六年(1677)有“出征之处杀人赎例”的规定,其大意为武职杀人既要追银赎罪,还要军前效力赎罪。此后,军前效力赎罪不仅包括武职人员,还包括大量文职官犯。
通过效力赎罪,在当时确实使一些官员以“戴罪”去“赎罪”,也确实赎了罪,如修筑塔兰奇水渠终将“石田”变“乐土”的苏龄阿。
二、因何立之
(一)起之缘
最初定赎刑究竟为何,由于无史料的支撑,已不得而知,张兆凯先生曾言西周《吕刑》规定的赎罪是赎刑萌芽状态[1]。事实上,西周以前的社会活动中就已经出现赎刑适用之实例,如《尚书·虞典》就记载过舜“金作赎刑”的实例。
秦代以役赎刑的出现,使得应受刑者通过无偿劳动而减轻刑罚,这种做法其实不仅减轻了受刑者的劳役负担,而且为国家财政节省了开支。《明史·刑法志》中载:“国家得时籍其入,以佐缓急。而实边、足储、振茺,宫府颁给诸大费,往往取给于赃赎二者。”[2]
清朝官员效力赎罪的出现也有着其独特的历史背景。清初在经兵燹战乱之后,各地城池急需修整,但是官府并没有足够的经费,认工赎罪条例应运而生[4]。
(二)兴之因
有学者评《吕刑》中的五罚之赎时说道:“周律之繁极矣,五刑之属至三千,若一按律尽而刑之,何非投机触罟者?天下无完肤。是穆王哀之,五刑之疑各以赎论。”[1]汉朝首创“女徒顾山”(一种赎刑)对妇女进行了特殊保护。由此可见,赎刑最开始适用的目的在于怜恤、在于恤刑。这种慎刑思想,是赎刑可以在历史上存在许久的原因之一。
清朝的效力赎罪则彰显了对官员的改造作用。清雍正帝指出:“获罪之人赐之以自新之路令其图功赎罪。”[4]清乾隆帝也指出官员效力赎罪意为原谅过去的过失,在其他领域重新录用,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三)灭之故
有学者认为,赎刑自始便展示出极强的封建特性,是为维护封建等级身份、维护特权阶级利益所服务的。如朱熹认为:“古人之所谓赎刑者,赎鞭扑耳。夫既已杀人伤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赎,则有财者皆可以杀人伤人,而无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5]统治者对于赎刑的规定大多看似适用广泛,官民均可适用,但由于赎金高昂,穷苦百姓无力支付,其依旧是富者得赎。
清朝末年,平等、自由的观念逐步兴起,反对特权也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维护特权的赎刑制度势必遭到抵制。赎刑在此背景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三、以何“解”之
赎刑因其落后性停下了脚步,留在了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这是符合发展需要的。但是,对其全盘否定也不合理。在现今社会,反观一些制度的设定,让人们以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赎刑,感受赎刑带来的现代价值,即对赎刑作以“新解”。
(一)取其精华
赎刑最开始适用的目的在于怜恤、在于恤刑。各朝代的刑法几乎都把怜恤观念当作适用赎刑的重要指导思想。现今,轻刑化思想所蕴含的宽和、人道化的精神与赎刑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以钱赎刑贯串赎刑制度的始终,是重要的赎刑方式。现今,刑事和解制度中被告人对受害人予以赔偿,得到受害人谅解,进而作为对被告人量刑考量的依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中第25条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量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6]
现今的刑事和解制度中的部分内容似乎对古代劳役赎刑给予了扩大解释,不再是简单地做工服劳役,而是着眼于解决现今的实际问题,基于所犯之罪,有针对性地完成作业,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实践探索在全国率先提出“绿色司法”,主要内容为:“涉林刑事案件发生以后,积极促成被告人与受害人之间刑事和解,并签订‘补种复绿’协议,且由法院进行司法确认,作出补植管护令,按规定责令被告人对其破坏的森林资源及时进行原地或者异地补种及管护,福建省法院在五年时间里,共审理了适用‘补种复绿’的毁林案件516件;共作出‘管护令’‘补植令’等五百余份;责令涉林刑事被告人及时管护、补种林木面积达四千多万平方米。解决了以前刑事被告人重新回归社会难、被毁山林复绿难、受害人权利得不到救济的难题,实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3]
(二)去其糟粕
赎刑,归根结底所体现的是特权思想,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即“特权阶级享有最终解释权”,似乎与受害者无关,受害者反而被排除在外,犯罪者符合赎刑标准的均可适用,无论受害者赞同与否。古代赎刑解决的是犯罪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以钱作赎,钱的去向即收归国家所有。
现代的刑事和解制度规定了将赔偿直接给予受害者。刑事和解制度的目之所及,即是受害者,因为犯罪行为对受害者的伤害最为直接、最为严重,理应受到合理的对待,让受害者决定是否接受与犯罪者的和解并作为量刑的考量因素,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于受害者而言,身体与精神所受到的伤害不言而喻,刑事和解制度中受害人得到相应的补偿也可解决其迫切的需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让受害人收取赔偿这一规定的首功不在我们,因为清律在有关过失杀伤收赎中便规定了过失杀伤准其收赎,但赎银并非上交政府而是由被害人之家收领,作为营葬医药的费用。可见,古代赎刑确实有其可供借鉴之处。
(三)赎刑现代价值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部分学者对赎刑的现代价值有着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研究,并且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成果也愈见其多。
张兆凯先生对赎刑没有采取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其在《赎刑的废除与理性回归》一文中提出了赎刑的现代价值,认为在契约社会平等观念的指导下,没有了特权阶层,如果赎刑仍行用于当今,赎刑和易科罚金刑应当具有同等的适用理念[1]。
在世界刑法向着轻刑化方向迈步的潮流中,我国也在逐步探索解决之道,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及适用便与之紧密相连。
徐欣欣在《论中国古代赎刑制度及启示》一文中对刑事和解制度与赎刑制度进行了对比研究,其认为赎刑的兴衰对现今刑事和解制度的构造有所启示:必须要认清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目的是弥补受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也是为了解决当事人诉争的法律问题,进而使罪犯真正悔罪,以便促使其更好地重返社会[2]。
四、结语
赎刑制度固然以其落后性、特权性势必被淘汰,但是其根植于我国土地之上,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发展变化,适应当时历史阶段的需要,做出了它的贡献。赎刑制度也许没有被人们完全忘却,但自它灭亡开始可能就被疏远了,对其研究、探索并不多见。法治的发展需要符合国情,刑事和解制度需要完善,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固然可取,但从挖掘类似赎刑这些渐被疏远的本土法律资源入手,进而批判继承、改造完善,相信更易被接受,因为有一脉相承的文化理念作为根基,这也许是一条合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