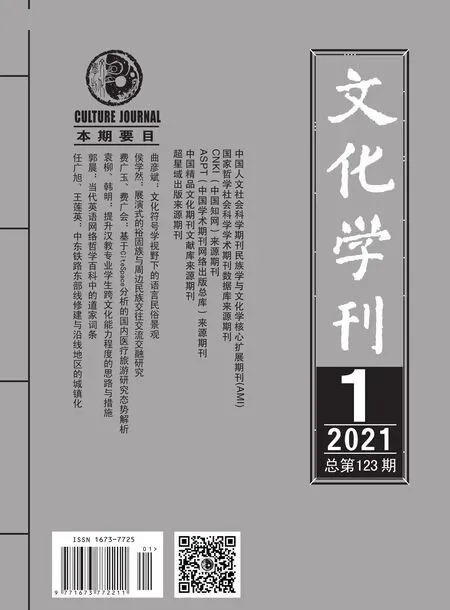简论留待小说《杀人时间》的叙事艺术
张梦琪
鲁西作家留待的中篇小说《杀人时间》发表在《十月》杂志2015年第4期,与许多山东作家惯常于传统的乡土文学创作不同,留待的作品独树一帜,充盈着丰富的奇幻想象力。《杀人时间》讲述了唐城里“我”的哥哥为给死去的母亲复仇而设计并实施的一场“杀人行动”,同留待的其他作品一样,这篇小说在叙事艺术上独具个性,体现出极强的叙事控制感,下文笔者将试从叙事视角、叙事时序、情节安排三方面分析。
一、灵活多变的叙事视角
留待非常注重运用叙事视角,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引用卢伯克的话说:“说到小说的技巧,最关键最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就是视角的问题——也就是叙述者决定跟故事采取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1]在《杀人时间》中,留待使用了三种视角交叉叙事:一是叙事者的全知全能视角,二是第一人称“我”的限知视角,三是第三人称“我哥哥”的限知视角。
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我”是小说的叙述者,小说围绕“我”对往事的追忆徐徐展开;同时,“我”也是被叙述者,是整个杀人过程的感知者。“我”的叙事视点并不固定,可以在故事内外自由出入,兼具切身性和距离感。从“我”的视角来看,即便能知道哥哥的成长经历,却不知道哥哥多年不回家的真正原因和心理活动。这样一个视角为小说留下许多空白,同时制造了悬疑气氛。“我”作为杀人行动的参与者,在叙述时受到了角色身份的限制。例如:哥哥为什么连跑七八回林场,反复催促“我”与谈了没两个月的女友结婚?王大响与母亲的死有什么关联?哥哥的杀人计划和时间到底是怎样的?在引发读者好奇心的同时,使小说变得谜点重重。在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下,小说的结局最后成了一个谜,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又耐人寻味。
留待是个喜欢改变和挑战自我的小说家,因而在《杀人时间》中,他只在必要时使用全知视角,既保留了神秘感又恰到好处地推动情节发展。在全知视角的视野下,读者清晰地体会到妻子林秀云对哥哥至死不渝的爱,看到父亲生活状态由糜烂向安稳的转变,了解到母亲慈爱、心软又通情理的性格。正是这些穿插在其中的全知视角下的描写,将小说的悬疑气氛推向极致。
在小说中,作者留待常常令叙述者融入某个人物之中,只叙述人物视野之内的事件过程,而不对整个事件和人物进行评判,这便是第三人称叙事角度下的限知视角。留待在《杀人时间》中主要将叙述者寄居于“我哥哥”身上,以此来刻画王大响的形象,展现马寡妇找“我”母亲的情景、母亲死亡的整个过程,以及多年未见的父亲形象。跟随“我哥哥”的视角,读者清楚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些心理活动的深入细致描写也使“我哥哥”的形象更加真实立体。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应用,将涉及叙述者个人道德评判和情感倾向的主观因素控制在读者的视线之外,使叙事显得客观、真实,同时制造了悬念。
二、巧妙交错的叙事时序
留待是位擅长调配时间的作家,时空交替、情节跳跃是其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伊利莎白·鲍温曾在《小说家的技巧》中谈道:“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人物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凡是我能想到的真正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地利用的。”[2]在《杀人时间》中,留待运用顺叙、倒叙、插叙以及补叙的叙事方式调整叙事时序,达到了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分离交错,使小说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杀人时间》的基本框架是按照顺叙发展的。开头第一句便是:“杀人的那天,他凌晨四点半就醒了。”[3]1小说的主人公“我哥哥”出场,小说按照杀人计划实施的时间顺序展开。“此时距动手时间还有十三个小时”[3]1、办完离婚手续“离动手的时间还有四个半小时”[3]8、回到老家时“离杀人时间还有三个小时”[3]17……整体上,《杀人时间》采用了顺叙的方式,帮助读者明晰故事的发展。但是,小说又在一开始就设置悬念:哥哥要杀谁?为什么要杀他?杀人计划到底是怎样的?在叙事上,留待不断用清晰的倒计时提醒读者杀戮会在某一刻到来,渲染紧张的气氛。同时,作者又通过补叙或插叙故事的相关信息来对复仇杀人这一核心事件做出了必要的蓄势或是延宕,使情节跌宕起伏,节奏疏密有致,令小说每一环节和细节都充满了张力。
留待在叙述时往往有意打破事件的自然秩序,按照叙事的需要重新排列。在小说顺叙的基础上,倒叙的叙事方式在小说中起着重要作用。小说的第三节,“他骑着摩托车带林秀云去办理离婚手续”[3]5一句话单独成首段,先将哥哥与其妻子林秀云去离婚的事实摆在读者面前,再细细阐述背后的原因。同样倒叙的还有马寡妇的故事。马寡妇在多年后的今天嫁给了一个做炸糕的老光棍,在经过渲染强化后,留待才将“包袱”抖开,徐徐讲述“马寡妇的出现,将我母亲突然推向了死亡”[3]11的真正原因,一方面解除了读者心中的部分悬念,一方面使小说产生更大的艺术冲击力。留待通过对叙事时间的操控,自由地调配着故事线性的时间之流,这样的叙事策略无疑使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大大增强。
留待在《杀人时间》中沉迷于将时间打破重组,使叙述者频繁地跳转于往事与当前事实之间,令过去与现状交织呈现。为了扩大叙述的时间与空间的跨度,不断制造悬念,留待在小说中同样重视对插叙以及补叙的应用。小说插叙了哥哥与王大响的初识、哥哥的参军历程、父亲曾经糜烂的生活、林秀云接二连三电话里的哭诉等,使小说情节更加完整生动;同时,在最后补叙了发生在外省的两个案件,以及哥哥见到王大响时的真实情景,使小说的主旨得到升华,达到意犹未尽的效果。留待独具匠心地安排这样巧妙交错的叙事时序,加上其讲究的叙事人称调配,使小说彰显出独特魅力。
三、精心设计的情节安排
与时间的巧妙交错、相得益彰的是留待精心设计的情节安排。在一场蓄谋已久的杀人行动的背后,隐藏的是“我哥哥”、马寡妇以及王大响三人的复仇行动。复仇作为一大文学母题,在各个时代得到了不同作家的演绎,而留待在《杀人时间》中赋予了三场复仇行动不同的结局,增添新的书写角度的同时展现了作者对复仇的思考。
马寡妇的复仇可以称之为整个杀人行动的源头。马寡妇是父亲年轻时糜烂生活中的“杰出人物”,丈夫死后不能再次获得爱情的她极度失望,她想起了“我”父亲,并把一切症结归结于他。父亲凭借着一句简单的客套话勾起了马寡妇所有的愤怒,顿时她将所有的愤怒化为仇恨,让酒后的父亲乱性。得逞的马寡妇随后继续实施着自己的复仇计划,她找准时机来到“我”家,用暧昧的语言刺激母亲使母亲离家出走。马寡妇以成功拆散“我”的家为结局,完成了自己的复仇,而她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复仇却间接引发了母亲的死亡。
对于王大响来说,复仇是其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我哥哥”复仇意识的萌芽。家境贫穷的王大响终于在四十二岁时“获得了”娶老婆的资格,而女人的儿子和其作为妇女主任的姐姐百般阻挠,一次次的失败使王大响内心积满了对二人的仇恨。当看见“我”母亲骑着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带着哥哥迎面而来时,王大响几乎以为是妇女主任带着那个经常袭击他的小孩而来。哥哥的笑声与一句无心之语彻底让王大响心理底线崩溃,他失去了理智,积蓄已久的仇恨瞬间爆发,用自己的方式残忍地掐死了母亲。王大响将自己的仇恨转移至母亲身上,完成了自己的复仇。
一场复仇的实施给另一场复仇埋下了种子,目睹母亲死亡过程的哥哥从那一刻开始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王大响的种子。二十三年来,哥哥做着同一个梦,每一次做梦都是对仇恨的加深与复仇意识的强化。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复仇计划,他决心要亲手杀死王大响。然而,在杀人计划进行到几乎是最关键的时刻,坐在车里等候的哥哥又从衣兜里掏出母亲的照片。这一次,他再也不能压抑住内心复杂的情感,对“我”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在回忆往事中,哥哥无意识地延宕了复仇行动的时间,使自己的仇恨在等待和内省中逐渐弱化。直至看见死去的王大响,他才解开了二十多年来郁结心中的心结,最终隐匿于世。
在留待的精心设计下,分属三人的三场复仇行动有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复仇后的马寡妇在多年后重新嫁人,生活上她再次得到了宠爱与呵护;复仇后的王大响在监狱中待了二十三年,出狱后的他最终上吊自杀而死;而复仇后的哥哥却是以失踪的方式结尾,乍一看仿佛是整篇小说中的异数,实则灌注了作者对复仇行为的新的理解,寄予了作家对人性乃至对整个社会的精神理想。
四、结语
《杀人时间》是留待有关复仇的故事,小说中人物的视角不断转换,叙述时序巧妙交错,但人物的命运和精心设计的情节安排依然在小说中得到完成,表现出其高超的叙事艺术。留待借小说与时代正面交锋,延续自己独特的整体写作风格,使人类的情感与自身的精神理想在小说中得到完整表达,成功将自己的文学艺术主张乃至生存观念内化于作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