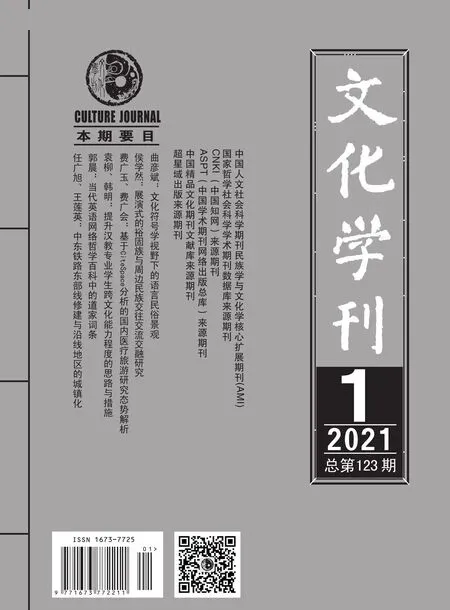微观史的个性与共性
姜成洋
一、微观史一例
20世纪70年代末,微观史兴起于意大利,随后影响延及欧美。多部经典微观著作随即诞生,尤以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为代表。其中,《马丁·盖尔归来》(以下简称“《归来》”)叙事性最强,这里以此书为例,引出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微观史的个性与共性。
《归来》讲了一个冒名顶替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法国乡村。故事发生在16世纪40年代,地点是法国朗格多克,富裕农民马丁·盖尔抛妻离子,舍下家业,不辞而别,一去多年。后来他回家了,或者说人人都以为他回来了。然而,在三四年美满婚姻生活后,妻子却说她被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蒙骗了,于是将他送上审判席。到最后一刻,就在冒名顶替者已经说服了法庭时,真正的马丁·盖尔出现了。
学人阐述该书价值,多认为娜塔莉·戴维斯呈现了历史叙述的另一种可能,在这种可能性中,人们看到了史学与人类学、文学理论的结合[1]。马丁·盖尔的故事之所以被不断讲述,是因为它提醒人们奇怪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离奇故事具有独到价值,戴维斯并不否认这个故事的独特性,她恰恰被这种个性吸引。在《归来》导论中,戴维斯提到一个很有启发的疑问:“我们常常认为,农民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有没有个别的村民,尝试过用不同寻常、出乎意料的方式来塑造自身的生活呢?”[2]11戴维斯的疑问代表了一种声明,她要表现的正是历史中独特的人与事,而不是抽象的阶级标签。
尽管戴维斯不回避历史的个性,但她并不是为个性而个性。个性并非遗世独立的存在,即便讲述的不是典型的人,但其性情仍有明确界限。正如金兹伯格所言,时代的语言、文化和其他结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弹性的、不可见的笼子,每个人都是在这个笼子中有限地施展个性[3]。如何把握个性与共性的关系,这考验的是历史学者的取材视角或者说考验选择故事的能力。至今中国学界没有经典的微观史著作,这或许与史学研究对个性的警惕不无关系。研究者多以为,微观史研究要有典型性、代表性,要以小见大,窥斑见豹。
但寻求典型性、代表性的观念恰恰需要微观史研究者质疑。实际上,那些所谓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故事,几乎不适合作为微观史题材。微观史恰恰适合独特的故事或者说充满离奇个性的故事。离奇的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微观史的写作中,故事个性与对历史背景的阐释互相支撑。故事本身是条主线,没有这条主线,零散的背景信息无法有条理地串联。问题在于,如果故事本身平庸无奇,当它结合背景阐释时,故事本身被历史背景淡化甚至湮没,那么这条不明显的主线将很难支撑足够的背景信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大历史的背景丰富故事本身,又很难解释离奇的故事何以能够存在,同时,离奇的故事何以包含并不离奇的日常生活。
戴维斯对此深有体会。她认为马丁·盖尔故事的好处在于它具备完整的故事线索: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妻子在床上接纳了“冒牌的”马丁·盖尔;在最后一刻,“真”马丁·盖尔出现在图卢兹法庭。同时,当联系到某一特定时空中极其重要或让人困扰的议题时,这些普世主题又能引起共鸣[2]215。戴维斯认为,历史叙述存在普世性与特性的张力,如果这种张力太小,故事就丧失了丰富性,也就无法激起共鸣[2]191。就此而言,微观史适合讲述具有个性、戏剧性、曲折性的故事,也正因如此,微观史的写作更多依赖机缘。
二、个性与共性
“个性”这个概念很少受历史学者关注,甚至可以说学者往往刻意排斥这个概念,因为它与史学客观的原则不吻合。什么是“个性”?对于“现象”与“现实性”而言,个性是一种永不停息地创造其外部存在的内在独特性的努力。拥有“个性”而没有自由是无法想象的,拥有自由而没有持续不断的个性化也是不可想象的[4]。个性是唯一能够显示人们真正是谁、不可替代的地方,那么,如何理解历史中的“个性”与“共性”呢?
福柯关注草根命运,并尝试记录他们的声音。在他看来,一束权力的光线打在这些无名者身上,使他们侥幸留在了历史上。权力的光之所以照在了一些无名者身上,是因为他们冲撞了权力[5]。笔者认为,福柯并没有把问题说透。草根能侥幸留在历史记述中,根本原因不是他们冲撞了权力,而是他们身上留存了独特个性。这些个性要么引起当权者警惕,要么契合文化精英的好奇,于是他们得以留存在某段历史的纸页上。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对中国的乡土社会的研究中就有体会:“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6]历史人类学者作为打捞沉寂的人,在籍籍无名的群体中,他们自然而然被那些有个性、有故事的人吸引过去。这些个性独特者,无论身处哪个社会层面,他们独特个性中蕴含的能量粒子,都使其成为潜在的被记载者。草根的独特个性从不同角度排斥了平庸,因而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精彩。
娜塔莉·戴维斯提示,是否有个别的农民尝试过用不同寻常、出乎意料的方式来塑造自身的生活。这个疑问也在提示我们,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农民时,研究者的第一印象常常淡化了农民的独特性情。不只20世纪,在整个中国史中,农民似乎都给人留下保守、个性萎缩的印象。但事实不能一概而论。“部分富裕的农民自然会产生摆脱宗法网络的控制和对于经济独立性的追求,继而产生对自主意识的要求,并逐渐形成独立的个性。这些都不是贫穷的产物,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7]这样看来,有必要重新思考20世纪的中国农民,起码像戴维斯提醒的那样,去发现那些用不同寻常、出乎意料的方式塑造生活的农民,即便只是个别的存在。
三、何以“碎片化”
再说“碎片化”问题,实际上仍是关于个性与共性的问题。历史研究者常有孤证不立的意识,换句话说,窥斑不能见豹,滴水难见海洋。所以,当微观史在中国学界受到关注时颇有研究者质疑其价值,认为顶多是讲了个曲折、丰富的碎片化故事。目前,中国学界确实没有微观史经典,这种现状尤其加深了学界对微观史“碎片化”的质疑。
实际上,“孤证不立”是对这种研究想法的批评:研究者妄图从个别事件、人物中寻求更广范围的代表性。由此看来,真正受质疑的不是孤证本身,而是用孤证寻求普遍性、代表性的想法。赖特·米尔斯批判枯燥的“人性”概念,认为普遍“人性”的想法违背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性,学者需要谨慎考虑这种特殊性,至少,他们没有权力去做抽象[8]。
因此,当研究者心生追寻典型性、代表性的想法,历史叙述中便出现“人的消失”这个问题[9]23。也就是说,人复杂的意识在追寻典型的过程中被掩盖,或者说人心态的丰富、性情的复杂被“平均化”“集体化”。沈艾娣说:“真实的人总是非典型的。”[10]所谓典型性、代表性,只是历史研究者的一种想象,它与“国家的视角”并没有本质区别,是追求历史研究的规律性解释,或者寻求一种简单化、清晰化的倾向[11]。
孤证并非不可立,前提在于它是一个好故事。那什么才算是好故事呢?贺萧认为,好故事并不一定使我们对过去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但它出人意料且引发思考,根据聆听者的不同需求,会朝不同方向提供线索。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可供再阐释,也可以被编进更大的叙事里[12]。讲述一个好故事,是就故事论故事,也是为了揭示过去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的内部运作[13]。好故事拒绝单一清晰逻辑,它应当留有无法解释的余地,甚至给人留下荒谬感。好故事在表现独特性情的同时,会向读者透露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种共性可以从社会结构和人性深处寻得。正如戴维斯意识到的,《归来》的故事透露了“失落于日常喧嚣之中的动机与价值”,那些离奇冒险活动“与其邻人们更为平凡的经历其实相距不远”[2]16。
当研究者质疑微观史沉迷小叙述而缺乏大关怀时,他们自然指向了对宏大叙事或者整体史学的倡导。诚然,学界研究有“碎片化”问题,但个人以为,产生“碎片化”的原因不在于选取对象的局限(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对的、无可避免的问题),而在于研究者没有把有限的研究对象当作整体的人[14]。学者固然要有整体史学的意识,但这里的整体史学并非布罗代尔的倡议,而是基于个人自成整体的史学。个人自成整体的史学,除了呈现外在政治、经济、文化变动之外,更深入认识人的内在本质,认识个人天然的和历史的条件,包括个人的自愿选择、自我建构、性情风格等。
中国学界对此已有认知,如刘志伟、孙歌号召从“国家历史”转向“人的历史”[9]11-27。微观史不得不收缩横向视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一个史学“碎片”,因为向纵深探索是为了捕捉感觉的相通,捕捉人的境况中的共性。对于历史发生过的各种事件及其复杂性,如果从人的意识或内心世界得不到解释,那它终究只能具有很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