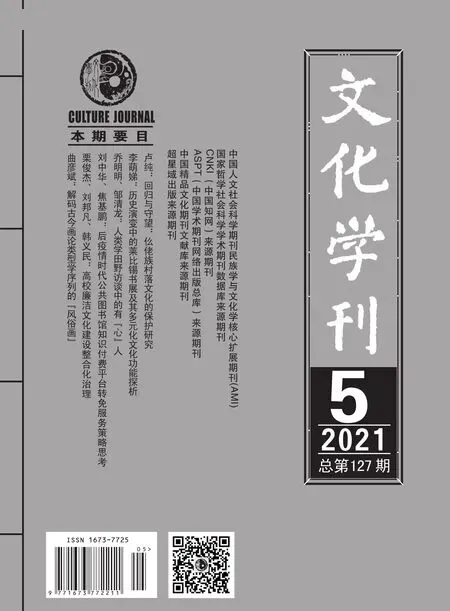论《我的帝王生涯》的叙事策略
胡仟慧
新历史主义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学界。美国学者史蒂芬·格林布拉在20世纪70年代就率先提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概念。新历史主义主张历史不是固定的,是生成的,文学没有“背景”和“前景”之分,需将历史研究带入文学中。新历史主义打破了传统的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是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反驳。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的新的批评方式,因阐释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独特性而被认可和推崇,后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主要趋势。中国的文学思潮受到西方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新历史小说的写作潮流。新历史小说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小说,一改历史写实的特点,以虚构历史的方式重写历史。但新历史小说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历史以全新视角进行重新审视和书写。代表作品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新历史小说的写作者,以转型之后的先锋小说作家和试图拓展题材的新写实小说作家为主,表达了他们关注历史,希望用全新方式演绎历史并借此完成他们写作技巧转变的意图。
苏童最初因为先锋文学的创作而出名。《1934年的逃亡》和《罂粟之家》的发表,引起文坛注意,使他成为先锋小说的领军人之一。除了重视叙述视角的转换、作品的神秘感等现代叙事技巧实验,他也十分看重小说里“古典”的故事性,目的是保证故事的可读性和流畅性。他后来创作的《妻妾成群》和《红粉》关注“意象”的经营,注重对悲剧氛围的营造和对女性细腻心理的刻画,实验性已明显削弱,而被认为有“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色彩。再之后,他创作的《我的帝王生涯》用近乎魔幻和荒诞的笔法叙述了皇子端白的帝王生涯,被看作新历史小说代表作。作为新历史主义观念影响下的产物,《我的帝王生涯》颠覆了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又借鉴了传奇小说的写法以及古典诗境的营造方法,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不可忽视的是,苏童小说在叙事方面的安排不同以往,足以抓住读者眼球。本文通过对《我的帝王生涯》的叙事模式、叙述视角和叙事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探讨苏童在《我的帝王生涯》中所运用的叙事策略。
一、虚构历史的叙事模式
《我的帝王生涯》以历史为背景,用虚构历史的方式来重新解读历史。“叙事文学用话语来虚构艺术世界。……这个话语的世界虽不等于现实本身,但却能在更本质的层次上揭示社会现实的内在意义。”[1]23苏童的小说多从历史中取材,但历史到了他笔下被虚幻化了,只保留了一点残片。他曾坦言:“《我的帝王生涯》是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我按自己喜欢的配方勾兑的历史故事,年代总是处于不祥状态,人物似真似幻,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个做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杂耍艺人,我迷恋于人物峰回路转的命运,只是因为我常常为人生无常历史无情所惊慑。”[2]这样随意搭建的方式,巧妙嘲讽了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
苏童虚构了一个国家——燮国,懵懂的皇子端白在皇甫夫人的阴谋操纵下成了皇帝。本无意为王的端白完全不理朝政,即使是外寇侵犯,也只是平淡地交由皇甫夫人处理。在见过了宫中争斗和血腥场面后,端白变得暴力嗜血、杀戮无常。后来真相大白,这一切不过是皇甫夫人与男人们开的一个玩笑,让端白成为假燮王,只是为了更好控制从而主宰燮国。皇甫夫人死后,端白的昏庸无道还是迎来了燮国的末日。一代帝王沦落民间,成了“走索王”,最终选择了归隐和出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在这样一个虚构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历史细化、缩小化书写的方式,使读者仿佛亲历历史,又猜不透历史的发展方向,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将历史的风云变幻、捉摸不定的特点用虚构的方式呈现,道出了世事无常和人世荒凉。
二、内聚焦叙述视角
“‘内聚焦’的特点是叙述者只叙述某个人知道的情况,即从某个人的单一角度讲述故事。内聚焦叙述的作品往往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通常是故事的一个角色。”[1]31内聚焦叙述方式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方面,这个人物既是事件的参与者又是故事的讲述者,把亲身经历的事件叙述给读者听,可以拉近文本与读者的距离,也利于读者理解故事内容;另一方面,虽然人物的叙述视角受到限制,只能讲述他所知道的局限性部分,不如全知叙述那样全面,但这种限制使叙述更加主观,反而可以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体会其中逼真的故事情节。有些叙事作品以主观心理描写为主,往往会选择这种叙述方式,可以起到透视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的作用。
在这个故事中,以第一人称的内聚焦视角进行叙述。“我”意料之外地继承了皇位。“我”本来作为故事的参与者,甚至是第一人称视角,却有种置身事外的感觉。“我”虽是最高统治者,其实不过是皇甫夫人手中的一枚棋子,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我”的帝王生涯中,我亲身经历了宫中暗斗、权利争夺、外寇入侵、民生艰苦、后宫争宠、民众起义、战争纷乱、国家灭亡等一系列事件,却始终用一种冷静旁观的态度来看待,最后选择了隐逸山林,出家为僧。这些都应验了僧人觉空的那句话:少年为王是你的造化,也是你的不幸。作者通过描绘一代帝王的心灵史,向我们再现了真实的宫廷生活和民间生活。这时,历史不再是遥远而神秘的事,是叙述者所处的环境,一下就拉近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让读者能够亲近历史。他虚构的这段历史能在真实发生的历史中找到类似案例,但那通常都是以史书记载的文字形式呈现,以内聚焦的叙述视角演绎出来,更加逼真而震撼人心。
三、灾难和死亡的书写
苏童和其他的先锋派作家余华、马原一样,热衷于灾难、血腥、死亡等的书写。余华的《现实一种》,用一种近乎冷静的笔调描写亲人间的相互残杀,血腥、暴力与死亡充斥着文本。即使是他后期转型的用温和笔调书写的《活着》,主人公徐福贵仍没能摆脱苦难的厄运,还要悲痛面对身边亲人接连死去,只剩一头老黄牛与他相依为命的命运。在这里面,死亡用以拷问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人为什么活着的永恒精神难题。
苏童也偏爱书写死亡和灾难的叙事策略。苦难和欢乐在故事中交融,苦难的演变折射出人生的动荡和起伏。毒与蜜、水与火的交错统一完美呈现了人生的另一种形态。在小说中,死亡的重复发生,不仅能给人物以强大的心灵冲击,还能给读者造成巨大的震撼。端白作为燮王,却总是重复着老宫役孙信那句不详的咒语:“夜深了,燮国的灾难也要降临了。”文中处处散发着死亡的气息,杨夫人公开揭露遗诏的骗局,却被残忍赐死,成为先王的殉葬品;杨松英勇报国,率领骠骑兵去凤凰关援阵,在战争中受伤,被燮王下旨射杀;郭象兵败红泥河后,在京城城门口引咎自刎;祭天会首领李义芝被擒,被用十一种空前绝后的极刑处罚;弱小可怜的燕郎在彭国军队大肆进攻燮国的动乱中被残忍杀害,以死来完成他对主人端白的忠心追寻。在免不了的灾难中,死亡或许是解脱苦难最好的方式。死亡作为“灾难”一种典型形态,把“人置于极端性的生存境界中进行冷酷的审视”[3],从而“检测人性的畸变和生命的沉沦”[3]。端白多次梦见白色小鬼,表明他在目睹死亡场景之后内心的恐惧。这恐惧背后是无穷无尽的孤独和悲凉。端白目睹死亡、制造死亡,却又害怕死亡,足以显示出人性深处的罪恶和荒凉。
四、换位的叙事结构
换位有两种情况:第一种,两个人在事态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个体身份不变,但在进行着对方原有的生活状态;第二种,故事里的两个人互换身份,在对方的位置上体会在此身份下所能得到的经验和具有的人生体验。换位作为叙事中一条重要的情节链,加以体会,读者便能进而明白作者的构思巧妙之处和所蕴含的深层寓意。
文中,“我”对历代皇帝出巡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既好奇又害怕,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在“我”身上,“我”和燕郎玩儿了个换装游戏。“我”让燕郎穿上“我”的金冠龙袍骑在马上溜圈。然而,穿上龙袍的燕郎仿佛就是皇帝,百姓对他行跪拜之礼,他也享受着做燮王的快乐。“我”对这次的换装游戏非常不满意,因为“我”和燕郎的衣服交换后,好似身份也互换了——“我”成了宦官,燕郎成了皇帝。身份是地位的一种象征,失去能证明身份之物后,人与人之间并无区别。苏童这样安排是想说明,在某种情况下,尊贵的帝王与平凡的百姓之间并无多大差距。这样一下就把帝王拉下了神坛,和普通人无异,现出了真实面目。这只是个暂时的换位,以交换衣服的形式进行。其实文中有一条更深刻的换位线索,也就是端白因为皇甫夫人修改了遗诏代替了本该属于端文的帝王之位。相当于端白代替端文体验了帝王生活,体验了本不属于端白的经历。端文在“池州之战”胜利后攻占皇城,这才结束了端白二十多年的帝王生涯。也就是这时,两人的换位才结束。苏童启示我们,历史不完全是严肃的,它的可能性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它的戏剧性则令人出乎意料。
五、结语
到了苏童笔下,历史透视出存在皆偶然的虚无感,以及人们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无力感。苏童剥掉历史的神圣光环,将历史残酷的一面揭露给我们看。又用审丑的方式,让血腥、灾难、暴力和死亡充斥文本。这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帝王的心灵史,揭示了人性的丑陋和存在的荒诞。苏童非常擅长悲凉意境的营造,那些无可遁形的孤独和悲凉是人对生存的试图逃离以及精神的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