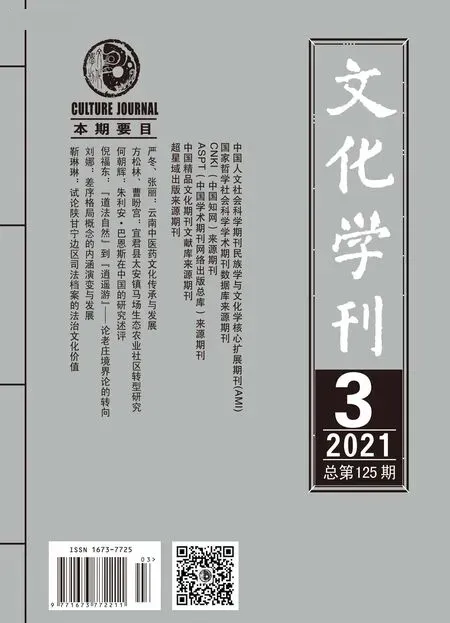郑振铎在近代翻译史上的地位探析
黄茹虹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郭源新等,是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郑振铎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从事外国著作的翻译工作,20世纪20年代前期他主要翻译俄国和印度著作,后来还翻译一些希腊罗马文学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同时,他依托自己主编的杂志与文学社团阐释自己的翻译主张并开展一些关于翻译的讨论,他提出的翻译理论,如翻译的可行性、翻译的目的与作用、翻译的原则等,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郑振铎的翻译成果
郑振铎一生热爱翻译事业,很早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在近代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郑振铎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与茅盾等翻译界前辈相同——也是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开始的。一般而言,他的翻译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俄国文学
郑振铎前期主要翻译的是俄国文学著作,推动了我国新文学思想的发展。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他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图书馆读书,在青年会干事步济时的影响下开始接触俄国文学。郑振铎翻译的作品一般是经过挑选的,侧重于高尔基、契科夫、列夫·托尔斯泰等著名文学家的英语译本。他所翻译的《灰色马》体现了俄国社会革命和人民的思想倾向,具有现实意义。郑振铎编写过一本《俄罗斯戏曲集》,这是我国现代文学最早的俄国戏曲集,其中收录了自己翻译的契科夫的剧本《海鸥》、史拉美克的剧本《六月》,以及瞿秋白、耿济之等人的翻译作品,郑振铎还参与主编了另一部俄国丛书——《俄罗斯文学丛书》,这两部丛书是民国时期最早的俄国文学丛书,意义重大。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有关俄国的政治性翻译作品,如《俄罗斯之政党》《国际歌》等[1]。
(二)印度文学
泰戈尔的诗集和印度古代寓言是郑振铎主要翻译的印度文学作品。泰戈尔是印度著名的作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文学作品对我国产生了重要影响。郑振铎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翻译泰戈尔诗歌,他第一次翻译的泰戈尔的诗歌是《吉檀迦利》[2]。郑振铎分别于1922年和1923年出版了《飞鸟集》(我国最早的一本泰戈尔诗歌译本)、《新月集》的汉译本,随后又将翻译的其他泰戈尔的作品编译成《太戈尔诗》。1925年,郑振铎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太戈尔传》,他希望通过介绍泰戈尔的诗歌来唤醒人们的爱国情怀。
郑振铎在《儿童世界》《文学》《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翻译的印度寓言;之后,他还出版了《印度寓言》,其中共收录五十五篇印度寓言译作。郑振铎的印度文学译作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架起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
(三)希腊和罗马文学
郑振铎是我国较早的比较系统介绍希腊、罗马文学的人之一。郑振铎对希腊、罗马文学十分感兴趣,很早就开始接触和翻译相关文学作品。1927年,郑振铎到西欧避难和游学,经常在不列颠博物馆里看书,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怀着对希腊罗马文学的热情,他又开始译述希腊文学。1928年,郑振铎以“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为题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二十六篇,后整理成册,并以“恋爱的故事”为名出版;1930年,郑振铎继续连载该作品,最后共有七部三十八篇,于1935年以“希腊神话”为名出版,这部著作增进了人们对希腊和罗马文学的了解。
除了翻译以上三大类的文学作品外,郑振铎还翻译了美国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高加索的民间故事、丹麦的民歌、德国莱辛的寓言以及欧洲童话《列那狐的故事》,等等。这些译作填补了一些翻译领域的空白,推动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二、郑振铎的翻译理论
新文化运动十分重视引入外国文学,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郑振铎是当时重要的翻译家,提出了系统的翻译研究理论。同时,他作为一名诗人、散文家和知名学者,能对当时人民的思想文化情况进行观察,进而选择有利于解放人民思想、冲破封建礼教的外国著作。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翻译家,郑振铎论证了翻译外国著作的必要性。
(一)文学是绝对能够翻译的
19世纪20年代,外国文学译作大量涌入国内,很多人开始认识到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但很多人怀疑中国学者是否能准确翻译出外国著作的艺术风格和思想,认为文学是不能翻译的。郑振铎于1921年在《小说月报》第3期上发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中提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这是他基于自身和其他翻译学者从事文学翻译的实践经验所作出的总结。他还主张文艺是不分国界的,我们也可以站在外国人的角度上欣赏外国著作,了解外国风情、思想。他认为“文学不可译”的文学观念在本质上是狭隘的。如果文学无法翻译,那不同国家的文化就很难交流,这实际上否认了国际文学交流的意义[3]。
郑振铎关于文学可译的论述,打消了许多怀有疑问的学者的疑虑,使人们对于文学是否可译及其翻译的限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文学翻译创造了必要的理论条件,推动了我国翻译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翻译的原则
郑振铎注重翻译的质量,为了更好地提高我国学者的翻译水平,学习外国的翻译理念,他曾系统介绍过外国的翻译原则、方法。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一文中,郑振铎首次向国内翻译工作者介绍了英国翻译家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及其中的三原则:“Ⅰ.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原文的意思;Ⅱ.译作的风格和态度必须与原作的性质一样;Ⅲ.译文必须包含原文所有的流利。”[4]郑振铎还根据这三个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条原则即“忠实”,这是翻译的首要条件,反对死板的翻译;翻译应该忠于原文,在译文中要根据原文的风格和态度来翻译;关于最后一条原则,他认为译者应把握一个度,翻译时要保持原文的风格和思想,同时也要使文章通俗易懂。郑振铎的翻译方法较为中庸,但始终强调翻译应紧密联系原文,不能脱离原文。
对于“信、雅、达”的翻译理论,郑振铎认为直译的文章只要意思表达清楚,即使语言缺乏流畅,它仍然是一部成功的译作;反之,如果为了使语言表达优美而失去原意,那它便是失败的。因此,翻译文章应以“信”为先,在此基础上兼顾其他。郑振铎的这些理论立足当时的文学翻译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以后的翻译家的文学翻译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此外,郑振铎还提倡分析与学习外国文学翻译成果。他的这些翻译论述给了当时许多文学翻译工作者以启示。
(三)翻译的作用
郑振铎于1921年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处女与媒婆》,提出了他对新文学翻译事业作用的想法,批评当时文学界忽视翻译作用的错误观点。1922年,郑振铎发表了《介绍与创作》一文,更是将翻译比作“奶娘”,认为在文学急速发展的时期,翻译者往往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使我国的文学创作更加丰富[5]。他认为翻译具有两种功能:一是促进中国文化传统的改变,二是在思想上给人们以启迪。具体来说,郑振铎认为翻译文学作品与创作文学作品同样重要,在世界文化相互渗透的时代,翻译者往往充当着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责任重大[6]。同时,他倡导翻译外国著作应选择有意义的作品,这样才能为我国的文学创作注入生命力;翻译与创作并不是对立的,翻译的作用不仅在于促进不同国家间的文学交流,也可以为国内文学创作者提供素材和经验。郑振铎的这些论述纠正了我国现代翻译的方向,指导着我国当前翻译事业的发展。
郑振铎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贡献不仅局限于以上几点,还涉及重译、译作的选择、语言欧化和文学译名统一等问题,在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三、结语
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作品大量涌现,尤其是文学翻译。有许多学者讨论翻译的重要性,希望通过翻译外国作品、学习西方思想去“拯救”国家。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译者工作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丰富了我国的翻译理论,为后世译者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启迪人们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从文学领域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并且,他的翻译理论与外国翻译观念相结合,从实践层面指导我国翻译活动,引领当时翻译界的发展方向。他还努力提倡翻译活动,论证翻译对我国文学进步的重要意义,消除了当时学者对文学翻译的误解,翻译工作的地位有所提高,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