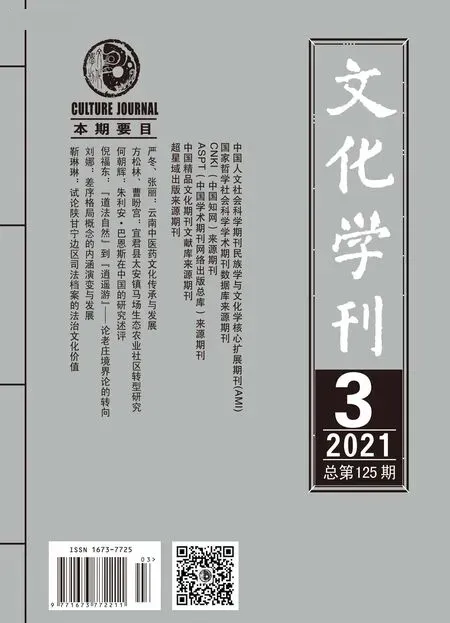试论唐诗中西施形象的重塑
李淑芹
一、唐代以前西施形象的定型
西施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很多,中国早期文献也有相关记载。先秦西汉时提及西施的文献大致有18种[1],其中只能看到西施的原始形象是一个单纯的美的符号。东汉以后,从袁康的《越绝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中可以知道西施是美丽的鬻薪之女,因美人计与吴越兴亡有了联系,但未知西施的结局。魏晋南北朝时,西施从鬻薪之女变成“浣纱之女”,且被神化。不过,西施的结局同样不明朗[2]。可以说,唐代以前的西施从一个美的符号开始,成为施展美人计的越女,又演变成具有神力的仙女,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西施的美女形象基本定型,她用美人计亡吴兴越的故事也开始流传,且愈演愈烈,到了唐代诗人的眼中就是一番新的景象了。纵观《全唐诗》,可以发现吟咏西施的诗歌颇多,几乎贯穿了整个唐代。但不同时期的诗人对西施的吟咏侧重点不尽相同,西施形象因而显得多样化。
二、唐诗中西施形象的演变
(一)初唐定型浣纱女
初唐时期吟咏西施的诗歌不多,大概只有一篇宋之问的《浣纱篇赠陆上人》。从题目来看,这首诗歌是一篇酬赠之作。诗人杂糅历史传闻,勾勒西施从苎萝山走进越国后宫,被献给吴王,以及宠冠后宫的一生事迹。其间不断强调西施的美色,“霸句践”“倾夫差”“夺人目”“鸟惊”“鱼畏”,这些描述明显比前人的历史笔记来得生动形象。诗人还用大量的笔墨铺写西施宠冠后宫时的骄奢,暗示美人计的成功。最后言及西施的醒悟,“知空寂”“永割偏执性”说明,虽未入空门,但西施终于看破红尘,返回故乡。西施不再是宠妃,又变成当年溪边的那位浣纱女了。
结合酬赠主题,宋之问似乎是想借西施“知空寂”来劝慰陆上人。但他对西施并没有做过多的发挥,而是较为完整地叙述西施的故事,点出结局。“越女颜如花,越王闻浣纱”,这是西施第一次以貌美的浣纱女形象出现在唐诗里,此后唐诗中的西施一直定型为浣纱女。
(二)盛唐寄寓才情女
盛唐时吟咏西施的诗歌开始增多,李白笔下的西施尤其生动迷人,她的美貌也更加清晰。《西施》中的西施之美是清新脱俗娇俏可爱的,“浣纱弄碧水”,在不经意间足以撩动人心。西施因美有了机遇,有了这充分展现美的平台。美,可以看作西施自身的一种“才情”。因而,李白大概有意借西施之美来比喻自己的才气。言西施“扬蛾入吴关”“一破夫差国”,尽显豪气之情,掩藏不住李白的自信。
盛唐时期的咏西施诗除李白诗歌外,还有王维的《西施咏》值得注意。诗人一开头就将西施的美拔高到“天下重”的程度。“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西施本是越国民间普通的浣纱女,经过越国的有意培养,最后成为吴国后宫的宠妃。这种身份地位的变化之大在于她拥有“天下重”的艳色。此艳色不仅是自然的美貌,更是令人惊艳的才情。美貌与才情相得益彰,加之明确的政治目的,假戏真做,西施才能令吴王信服迷恋并为之深情付出,从而拥有颠覆一个王朝的资本。王维以西施喻人的寓意很明显,他另辟蹊径,不叙西施与吴越兴亡的故事,而是让她超脱于历史是非,着眼于自然美貌和才情,从而关注她的人生际遇。可以说,王维笔下的西施之美别有一番风味。
盛唐诗人眼中的西施都是一个展现美丽才情的女子,西施因美貌走进历史,走进诗人的眼中。诗人们也有才情,从而借此寄寓自身。他们不甘心一生平庸,希望能够如西施般施展才华。
(三)中唐哀思消亡女
中唐时期的咏西施诗明显有别于前面的诗歌,开始有借西施寄托哀思的迹象。李绅的《姑苏台杂句》开头一笔带过西施的前半生,“越王巧破夫差国”,一个“巧”字颇有嘲讽之味。西施依然很美,“醉舞花艳倾”,但她“妒月娇娥恣妖惑”,这似乎有将西施定位为“红颜祸水”的意味。然无论如何,西施最终还是消亡了:“寂寞千年尽古墟,萧条两地皆明月。”面对吴越兴亡后的萧条,诗人进而想到自己“如今白发星星满,却作闲官不闲散”。李绅一生宦海沉浮,晚年虽拜为宰相,然仕途亦非一帆风顺。又见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不复繁荣,兴衰不由人,不禁悲从中来,已有借史实寄托哀思之迹。
与李绅交往甚密的元稹和白居易也有咏西施诗。元稹的《春词》借西施美色咏怀,同样有兴衰之慨:“西施颜色今何在,但看春风百草头。”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霓裳羽衣歌·和微之》提到西施时说“吴妖小玉飞作烟,越艳西施化为土。娇花巧笑久寂寥,娃馆苎萝空处所”,亦有世事沧桑、盛衰兴亡之叹。然而在元、白二人的笔下,西施与历史上吴越兴亡的是非似乎没什么关系,她只是一个美女,一个美好事物的代言人。
如果说盛唐诗人看重西施美丽的展现,中唐诗人则着眼于西施美丽的消亡,而美丽事物的衰亡总是令人哀叹的。
(四)晚唐借喻普通女
到了晚唐,借西施寄托哀思的迹象愈发明显,西施愈发频繁地出现在晚唐诗人的怀古咏史诗中,但这种哀思又与中唐不同。于濆的《经馆娃宫》通篇都是盛衰兴亡之叹,吴越兴亡已然成为历史。“当时二国君,一种江边墓”,但这与西施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时的西施不再是“红颜祸水”,诗人开始尝试为其洗脱罪名。罗隐的《西施》说得浅显直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吴越兴亡自有定数,越国没有西施,照样亡国。崔道融在《西施滩》中更是为西施鸣不平:“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西施分明是在替人担亡国的历史罪名。崔道融的另一首《西施》则别开生面,颂扬西施的爱国情怀:“苎萝山下如花女,占得姑苏台上春。一笑不能忘敌国,五湖何处有功臣。”
值得一提的是苏拯的《西施》,言辞犀利,矛头直指帝王。西施只是一个代名词,“君王政不修,立地生西子”。西施不仅仅是西施,她还是褒姒,是妲己。可以说,诗人眼中的西施只是一位普通女子,她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左右一个国家的兴亡。国家兴亡系于帝王,所谓“红颜祸水”不过是时人或后人为无能帝王开脱的借口罢了。
晚唐诗人逐渐跳出“红颜祸水”的狭隘观念,开始关注帝王自身,反思帝王的执政问题。西施只是一名普通女子,其背后的历史故事更值得深思。可以说,他们咏西施更多的是为讽喻现实,讽喻君主。
三、唐人褒贬西施的缘由
唐诗中的西施最初只是一名浣纱的美丽女子,进而是倚仗美貌为才情的女子,后又变为美丽消亡的代言词,最后恢复为一名普通的女子。西施形象的多样化体现了唐代诗人对西施或褒或贬的不同态度倾向,这大抵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关系紧密。
唐朝建立后,一切欣欣向荣,文学创作也开始摆脱轻浮之态。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从政权的得失着眼时,坚决反对绮艳文风,重政教之用”[3]3,诗人们也开始走出齐梁绮靡的文风,力求有所寄托。相比之下,诗歌风格显得质朴,逐渐恢复到本真状态,王绩的《野望》便是这样一股清风。宋之问亦是追随潮流,咏西施时虽有所雕琢,但也是努力简化,只关注其人其事,淡化西施神化的色彩,重新定型为凡间的浣纱女。
盛唐时期,诗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理想和浓郁的自我抒情。李白和王维在咏西施诗中寄寓自身感叹,抒发自身情感,正是这一倾向的体现。而盛唐诗人的这种追求“正是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盛唐社会的产物”[3]4。此时社会安定、政治开明,文人们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他们充满自信、充满理想,只为建功立业,实现抱负。所以,因美貌获宠的西施在他们眼里便是一位凭借自身才情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可以说,诗人们在西施身上寄寓了得遇伯乐的理想。
中唐时期,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初现颓败之势。尽管表面依旧繁华,但敏感的诗人们已经洞察到衰亡之势。唐明皇本是精明的统治者,将大唐推向全盛时期,但他又是昏庸的,不理朝政,沉迷女色。盛唐在其治下滑坡厉害,甚至爆发安史之乱,差点被颠覆。究其原因,杨贵妃难辞其咎。因此,杨贵妃算是“红颜祸水”。而西施与杨贵妃何其相似!两人都是美的,都迷惑了君主,都有颠覆一个王朝的资本。诗人们自然会有将西施定位为“红颜祸水”的倾向。然而,西施与杨贵妃还是不同的。杨贵妃颠覆的是一个强盛繁华的王朝,西施颠覆的则是一个可恶的王朝。杨贵妃让诗人们的美梦破碎,是对美的毁灭,而西施是毁灭恶。在正统历史中,吴国是邪恶的一方,西施灭吴可算是善战胜恶、弱者战胜强者的代表,渗透了普通百姓的理想和愿望。所以,西施的消亡是善良的消逝,是美丽的衰亡,是令人同情哀思的。
晚唐时期,王朝的衰亡之势已不可挽回。这时期的诗人没有经历过盛唐的繁华,他们面对国家的盛衰能有更清醒、更理智的认识。盛唐时期的繁荣像是一场遥远的美梦,梦早醒了,只能面对现实。现实中的政治腐败、政党之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众多社会问题暴露出来后,文人们很容易看到这些问题的出现绝非一个后宫宠妃能把控的。所以,他们的视线从杨贵妃转向那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帝王,对最高统治者进行批判,从而为西施脱去“红颜祸水”的恶名。
唐朝诗人对西施会有不同态度当然不仅是社会环境使然,这也跟他们的个人喜恶、个人心理等有关,但社会变化必会极大地影响文人们的心态。这种心态投射到西施身上也就表现出不同的样子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西施故事流传到唐朝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唐朝诗人给西施增添了不少色彩。由于唐朝社会的兴衰变化,诗人们对西施的态度不尽相同,体现在诗歌中便是西施形象的多样化。唐朝的咏西施诗数量不少,“不过唐代诗人也没有足够关心西施的情感心理,他们也只是在尝试开拓,这也为元明戏剧中西施传说的进一步发展开出一条新路来”[4]。总之,唐代诗人对西施的吟咏丰富了西施的传说,但他们忽略了西施的个人情感与个人态度,这也为后世进一步丰富西施形象提供了一个方向。